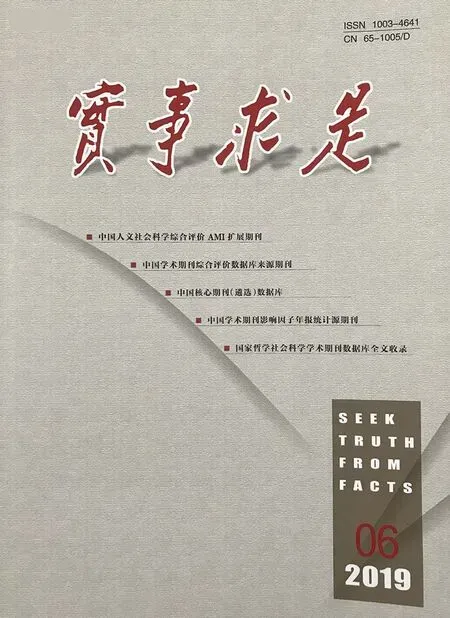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
2019-02-19邵纯
邵纯
(中共新疆区委党校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我国的版图。自此以来,国家统一发展始终是主流方向。新疆的全部历史就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保卫、开发和建设这块热土的历史。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统一安全、边疆和谐繁荣呕心沥血、艰辛开拓、彪炳史册。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左宗棠,垂暮之年抬棺西征,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和组织管理才能,消灭了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匪帮,收复了这片中国固有、且面积广大的领土,为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巩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1983年8月,王震将军邀请左宗棠曾孙左景伊到自己家中交谈时指出:“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①左景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原载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
一、科场坎坷,沙场有为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朴存,祖籍湖南湘阴。他的父亲左观澜是位教书匠,家境贫寒。左宗棠15岁考中秀才,21岁考中举人,此后三次赴京科考,屡试不第。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只有取得“进士”的头衔后,才有可能担任高官,而左宗棠始终只是个“举人”,故自称“湘上农人”,蛰隐柳庄,过起田园生活,长期担任乡村教师。左宗棠虽然科场坎坷,但不乏雄心壮志,自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破书万卷,神交古人”。由于他饱读诗书,秉性刚毅,出类拔萃,因此遐迩闻名,曾受到过陶澍、胡林翼、张亮基等高官的约见、赞许和收纳。
同时代的林则徐,是一位求贤若渴的民族英雄,他于1849年从云贵总督任上请辞后,告老还乡。林公在回福州的路途中,曾在长沙一船上停留过。有人告诉他此地有位左宗棠,虽无官职,但才华过人,于是林公就约见了左宗棠。相差27岁的二人通宵交谈后,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据史学家来新夏先生所编著的《林则徐年谱长编》下卷记载,林公认为左宗棠是“绝世奇才”,当即书写并赠予他一幅对联,其上联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下联是“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左宗棠过人的才能是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显露出来的,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时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大胆地把军权交给了身在他幕府中的左宗棠。他在握有兵权后,充分地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致使气势正盛的太平军攻打长沙三个月未能取胜而退兵。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从此开始。1854年(咸丰四年),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他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在长期沙场征战中,左宗棠逐步成为湘军的重要将领,先后任道台、巡抚、总督、钦差大臣、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职。
晚清时期,面对列强愈益猖狂的侵略,左宗棠努力践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贡献颇多。他于1866年在福建创建了著名的马尾船政局,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厂。此船政局内又设立了“求是堂艺局”,目的是培养与海防有关的人才。此局冠以“求是”二字,说明“实事求是”在左宗棠心中的重要性。实事求事的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今天和未来衡量一切事务的根本尺度。
二、力主塞防、远见卓识
新疆古称西域,自汉代开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的历代中原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清王朝建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政权的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其后又相继平定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的叛乱,确定了清王朝的西北边界。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设立“伊犁将军府”,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进入19世纪,新疆内忧外患不断,地方暴乱频繁发生。如由中亚浩罕国策动的张格尔之乱长达8年之久,于1828年被平息;1830年发生了玉素甫之乱等;1847年发生了七和卓之乱;1852年、1855年、1857年新疆都发生过大小程度不同的暴乱。这些暴乱多与国外的侵略势力有关,与宗教极端势力有关。这些暴乱中发生的血腥杀戮和恐怖活动给各族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晚清时期新疆最严重的暴乱是始于1865至1877年浩罕国阿古柏匪帮的野蛮入侵。阿古柏原系中亚浩罕国的一个弄臣,他曾争夺王位未果,但也掌握了一方的兵权。由于俄军对浩罕国的逼进,他意识到本国的前途处于险境,于是产生了对外侵略,以谋求权势的邪恶之念。1865年(同治四年),阿古柏大举入侵新疆,首先占领了喀什噶尔,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但由于清廷的衰败腐朽,使得阿古柏步步进逼一时得逞。据余太山先生编著的《西域通史》第476~478页中记载:阿古柏攻占了英吉沙尔,次年攻占了叶尔羌与和田;1867年连续攻占了阿克苏、乌什、库车三城,同年底宣布成立“哲德沙尔汗国”这一伪政权。阿古柏自称“巴达乌勒汗”。所谓汗,即“可汗”的简称,是最高统治者的意思。1870年(同治九年),阿古柏匪帮攻占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至此,先南疆,后北疆的多数领地均处在阿古柏的残酷统治之下。阿古柏是一个嗜杀成性的恶魔,据上述《西域通史》记载,仅和田一战,城中就有五万人被屠杀。另据潘志平所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记载的一份维吾尔史料所说,“阿古柏的军队在托克逊,纵马于大街小巷,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砍乱杀,天明之前男女老幼全都让屠杀了。”
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沙俄时时觊觎新疆伊犁丰饶的土地与河流。1871年,沙俄军队越过边境,兵分两路大举入侵伊犁,两个月后绥定、惠宁、宁远等伊犁九城相继沦陷。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沙俄侵略者对清政府谎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实际上却“设官置戊,开路通商,晓示伊犁永归俄辖”,实行殖民统治。而远在大西洋的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中国西北。这就使得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面临着从大清国的版图上消失的危险。
此时的清政府已腐朽不堪,内外交困、风雨飘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引发了清廷高层一场“海防”与“塞防”的激烈辩论。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海防派代表人物。他认为新疆土地瘠薄,人烟稀少,夺回来花费的成本很高,且不能获得多少收益,在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增强海防。他在向清廷上奏时甚至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
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是塞防派领袖人物,虽坐镇西北,对于大清朝的国防形势了如指掌。面对当时朝廷上下大都支持李鸿章观点的局面,他毅然上奏朝廷,勇敢地提出坚决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充分体现出坚定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炽热情怀。他认为,凡是祖国的领土,一寸土地也不能放弃,面对外敌入侵,如果“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所以只有一种选择,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战。
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左宗棠辩证地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反对以牺牲“塞防”来保全“海防”。他认为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不得偏废其一,西北防御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新疆则是重要的战略屏障。他还用清政府早期削平了准噶尔部,使关内一百多年来“无烽燧之警”的历史经验说明:“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深刻揭示了新疆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定位,阐明了收复新疆对于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句富于战略远见和深邃哲理的名言至今还被各界学者广泛引用。
左宗棠还认为,“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他严厉地批驳了那些目光短浅的“败家子”认为新疆无用、得不偿失、出兵必败等奇谈怪论,大声疾呼收复新疆势在必行,充分彰显出在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敢于担当的浩然正气。在这场海塞之争的大辩论中,左宗棠虽然是“少数派”的代表,但他的主张充满着远大的战略眼光和真知灼见,充满着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最终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由此也成就了左宗棠晚年的辉煌。
三、抬棺西征、光复国土
有道是“愤怒出诗人,患难出英雄”,左宗棠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了他一生最辉煌的岁月。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出兵讨伐阿古柏的伪政权,收复新疆。此时的左宗棠已64岁,是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他充满信心,毫无畏难情绪。有资料记载,左宗棠出征时,用一辆车拉了一口棺木同行,以表誓死收复新疆的决心。于是,“抬棺西征”的佳话广为流传,大大鼓舞了西征将士的斗志。
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实为困难重重。他率领的军队有五万多人,在没有开战之前和开战之中的后勤保障工作,就是一个特大的难题。其中包括士兵每日必须吃粮怎么办?买粮的费用从哪里来?这些粮食的运输怎么解决?有了军粮后储存在何处?对这些困难,左宗棠以其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均选择了最佳方案一一予以解决。据台湾的历史学者庄练先生的研究,左宗棠从内地采购粮食,主要靠骆驼,其次靠车辆运输,分别储存到未被阿古柏占领的古城子、巴里坤等地,其军粮总计有二千四百八十余万斤之多。左宗棠特别重视先进武器在作战中的作用,他奏请朝廷,购买了当时德国制造的“义耳炮”。此炮口径大,测距准,命中率高,杀伤力强,其威力远胜过阿古柏所使用的英式大炮。左宗棠所创办的“兰州制造局”,也生产了大量较为先进的武器。
有了军粮,有了先进的武器之后,左宗棠又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他提出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八字方针。所谓先北后南,就是首先收复北疆的失地,在此基础上再收复南疆的失地。所谓缓进,是指攻占一地后,先把军粮运来储存,为下一战做好准备后,再行攻克新的目标,即步步为营;所谓速战,是指为节约军粮等物资,绝不打拖拖拉拉的战争,务求速战速决。1876年(光绪二年)初,左宗棠由兰州西进至肃州(即现在的酒泉),作为进军新疆的总指挥部。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从此开始。
消灭阿古柏、收复新疆,是一项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历史重任。完成这一重任,首要的问题就是要选好将才。左宗棠深知此理,他派张曜、金顺、徐占彪等人领兵分头出关。这些人均有战功,但并非最得力的战将。于是,他看中了年轻有为的湘军将领刘锦棠,并委任他担任统领北疆和南疆讨伐阿古柏侵略军的前敌总指挥。
民间曾有“无湘不成军”之说,刘锦棠也是湖南人,生于1844年,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湘军中的将领。刘锦棠是一位军事天才,他担任消灭阿古柏匪帮的前敌总指挥时只有31岁。刘锦棠按照左宗棠即定的战略战术,进军新疆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1876年九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均被收复,阿古柏匪帮已溃不成军,被迫退守南疆。左宗棠深知收复新疆所必需的军粮,不能长期依靠内地供应,所以他在收复了北疆的大片领土后,立即在巴里坤、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实行兵屯和民屯,自种粮食,以备收复南疆和长治久安之需。
据《西域通史》记述:1877年春,刘锦棠挥师南下,攻破达板城,继而与徐占彪、张曜两部之军收复吐鲁番,天山南路门户洞开。此时的阿古柏集团已分崩离析、众叛亲离,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就在清军开始南下之时,阿古柏突然于1877年5月29日死于喀拉沙尔(新疆焉耆县)。关于他的死因,有着多种说法:《清史稿》说他是饮毒酒自杀,但是有人认为他是被人毒死,甚至有英国人记载其是酒后与小吏扭打而死等。刘锦棠乘势挥师西进、势如破竹,在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连克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地,阿古柏的余党土崩瓦解、如鸟兽散。阿古柏近13年的黑暗统治就此结束。这场战胜外敌入侵的正义之战,总计用了三年的时间。
阿古柏集团覆灭后,左宗棠就积极准备收回被俄军占领的伊犁地区。1880年他将大本营由肃州迁至哈密,分兵三路挺进伊犁,对俄军形成军事威慑态势。虽然当时清廷惧怕与俄国动武,但俄国对左宗棠的军事力量也不敢小觑。在此背景下,清廷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赴俄谈判,于1881年正式签定《伊犁条约》,俄军同意撤出伊犁,中国收回了对伊犁地区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的主权。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频频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清王朝昏聩无能、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此背景下,左宗棠在抗拒外敌入侵的战争中获得完胜,光复大片被占国土的壮举,无疑是当时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在晚清夕照图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左宗棠作为完成这一壮举的倡导者、策划者和指挥者,他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四、建省栽柳、巩固边疆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特别是全境收复后,左宗棠秉承了道光年间龚自珍关于新疆建省的思想,至少四次向朝廷提出了新疆建省的主张。1884年(光绪十年),清廷宣布成立新疆省,省会设在迪化(现乌鲁木齐)汉城,由刘锦棠出任巡抚,这是新疆历史上一个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开创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废军府、改行省的先河。从此,新疆废除了落后的伯克世袭制度,既减轻了农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又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势力与当地伯克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促进了新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中央政令进一步畅通,有利于国防和边疆安全,这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新疆省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左宗棠等人在消灭了阿古柏匪帮之后的又一重大贡献。
左宗棠从小生活在湘江畔,对绿树有着特殊偏爱。1849年,林则徐与这位37岁的后生相见时曾对他说:“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颇以未竟其事为憾。”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埋藏到左宗棠的头脑之中。到了垂暮之年,左宗棠率军西征,来到西北大漠,深感气候干燥,了无生气,遂命将士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柳、杨、沙枣等树,名曰道柳,以便巩固路基,防风固沙,限戎马之足,利行人遮凉。他要求凡大军过处必植树,军士人人随身带着树苗,一路走一路栽,并亲自携镐植柳。在他倡导、示范和督促下,竟然形成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日后人们为了纪念左宗棠,便将这些沿着西征将士的足迹栽种成荫的柳树称为“左公柳”。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还致力于改善当地的运输环境,大规模招收流散人员,开渠凿井屯田,振兴农牧蚕桑,发展当地经济,为巩固边疆和社会稳定打下基础。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的名句,形象地描写了边塞既雄伟壮阔又荒凉寂寞的景象和戍边士兵的怀乡之情,脍炙人口、几成绝唱。一千多年后,清代左宗棠的部下杨昌浚在经甘肃去新疆的途中所见所闻,感慨系之,也吟出了四句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这两首含义不同的诗,反映了历史的巨大变迁。杨昌浚在诗中热情讴歌了左宗棠率军西征的历史壮举,寓意着三千里新栽的杨柳不但是驱除外寇、光复国土、巩固边陲的鲜活见证,同时也是改变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把春风引向玉门关外的一次务实、成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