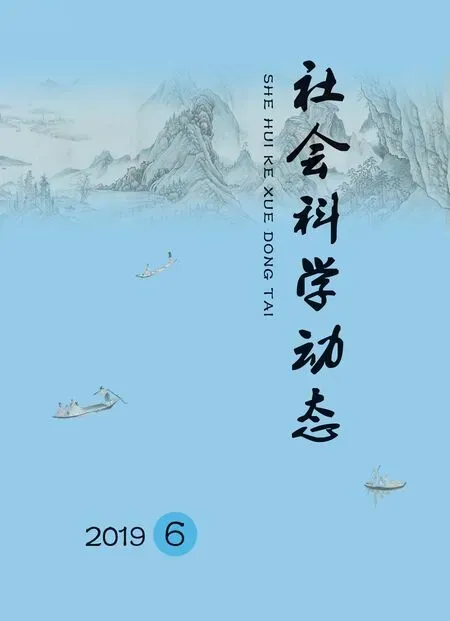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影响初探
2019-02-18胡艺华
胡艺华 黄 琛
1939年5月15日冼星海在《致中共“ 鲁艺”支部的自传》中写到,“ 我希望能接受党的领导,从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创作”①。这表明冼星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和理解已经从感性层面上升到了理性高度,从而实现了由“ 为音乐而音乐”向“ 为人民而音乐”的成功转型,究其根本原因及影响因素,与其广泛而强大的朋友圈是分不开的。正如冼星海在这份自传中所提到的,“ 文艺界、军政界、工农、商界我都有很好的往来……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人我大半认识”②。其中以代表作《大众哲学》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哲学家艾思奇,就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大众哲学家的艾思奇与作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之间的跨界交往,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中的一段历史佳话,同时也构成了冼星海音乐人生转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至今仍闪耀着理论的光芒和时代的风采。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视域下,考察和梳理艾思奇与冼星海之间的友好交往,深刻分析艾思奇对冼星海的重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当代启示,显得十分必要。
一、艾思奇与冼星海交往的历史考察
艾思奇与冼星海自相识到相知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发展过程,两人之间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擦肩而过
艾思奇与冼星海的历史渊源和工作交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在山海工学团的任教经历。山海工学团1932年由陶行知创立,这不仅是一所集学校、工场、社会于一体的乡村教育机构,还是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更是国难教育的实验基地。之所以要起名为山海工学团,按照陶行知先生的解释,既因为地处宝山与上海之间,取山海之名便于对外宣传;又恰逢侵华日军逼近山海关,意在呼唤民众共赴国难、抗击敌寇③。山海工学团主要面向工人阶级以及失学和失业的青年,采用半工半读形式,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海工学团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难题,创造并推行“ 小先生制”,即通过上学的儿童、小学生来教不识字的儿童、成年人甚至老年人,这些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儿童或小学生被称为“小先生”。为了加强对这些“ 小先生”的辅导,提高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水平,山海工学团于1936年专门开办了艺友班,邀请了邹韬奋、钱亦石等一批学有专长的社会名流担任教员。
在上海《读书杂志》担任编辑的艾思奇,以及先后在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担任音乐创作和电影配乐工作的冼星海,出于对山海工学团办学宗旨的认同,再加上左翼联盟的推荐,二人都应邀来此任教。艾思奇负责教哲学与法律,冼星海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以及教学生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在山海工学团期间,他们教学认真负责,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精彩故事。比如,艾思奇以先前在《读书生活》连载的《哲学讲话》作为讲义运用到山海工学团的教学中,用通俗易懂的讲述、灵活生动的比喻,给学生们教授哲学原理,深受学生欢迎。后来该书单独出版,就是闻名遐迩、影响深远的《大众哲学》。冼星海勇于打破生活与教育的围墙,赋予当地农村新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乡村歌者”。“ 上世纪80年代,上海陶行知纪念馆常组织各种晚会,当地老农喜欢唱歌者特别多,经常全场高唱,一首又一首,欲罢不能。原来这些当年的小团员,是冼星海曾教过的学生。”④
一个值得玩味的小插曲是,艾思奇与冼星海都曾在此任教,但彼此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来山海工学团任教的老师流动性大,且大都是临时过来帮忙的社会名流和学者,这使得二人有了一段擦肩而过的奇妙经历。在山海工学团任教的这一段共同的人生经历,好像一颗埋在心底的种子,直到1938年11月二人在延安的相遇才有了破壳而出的新芽。
2.相逢恨晚
生活的哲学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逢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缘分既能让近在咫尺的两个人擦肩而过,也能让远在天涯的两个人千里相逢。尤其是有着共同的人生追求和革命理想的两个人,即便是曾经错过也能够跨越时空再次相逢。这一点,在艾思奇和冼星海身上得到了验证。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人在上海期间虽有工作上的交集,却无相识之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事隔一年之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抗日救国成为了全民族的首要任务,延安也由此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为艾思奇和冼星海彼此相逢、缘分再续提供了可能。
1937年,时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并以《大众哲学》闻名全国的哲学理论专家艾思奇奉党中央命令,奔赴延安出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艾思奇于1937年10月到达延安,他的到来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⑤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过去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艾思奇来了,好了……”⑥1938年9月,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第六处音乐科主任科员的冼星海,因受到国民党的排斥,正处于精神痛苦之中,渴望有一个能够写曲的地方。在收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沙可夫院长的聘书和音乐系师生的集体签名邀请后,冼星海毅然放弃优厚待遇,携新婚妻子钱韵玲不远千里奔赴延安,11月3日抵达延安后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教员。他的到来,同样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
这两位来自“国统区”不同领域的卓越知识分子,于11月6日“在边中赴国难教育会同志的会上”不期而遇,实现了两人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次握手。两人虽是初次相逢,但一见如故。这次相逢,给冼星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此,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深情的记载。从一定意义上讲,两人在错隔两年后第一次相逢,之所以一见如故、相逢恨晚,究其原因,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在于,聂耳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冼星海一直视聂耳为音乐道路上的楷模和导师,而艾思奇与聂耳是相知相依的人生挚友。共同的革命理想、价值追求、道路选择和人生知己,使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3.深度交往
从1938年11月初两人在延安初次相识,到1940年5月中旬冼星海离开延安,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冼星海和艾思奇基于不同的革命分工,进行了深度的交往和互动,结下了真诚而深厚的革命友谊。艾思奇主要从事哲学理论工作,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主任教员,同时在陕北公学任教并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敌协会主任,后又调入马列学院任哲学教研室主任,1939年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在此期间,艾思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他的哲学研究从大众化、通俗化,上升到中国化、现实化。冼星海则主要从事音乐创作与教育,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担任音乐系主任、兼任中国女子大学的音乐教授,讲授“ 自由作曲”等课程。在鲁艺期间,冼星海成功地创作了《黄河大合唱》这一部名垂千史的红色音乐经典之作,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评价。
两人虽然到达延安的时间不一、从事的革命工作不同,但是两人共同的延安岁月,始终贯穿了工作上的交集、思想上的融通、生活上的相交、专业上的互动。两人同为来自“ 国统区”的大知识分子代表,受到了党中央的特殊优待,冼星海的月薪为15元,艾思奇的月薪为12元,远远超过毛泽东和朱德的待遇。他们都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赏识,成为毛泽东联系哲学界和文艺界的得力助手甚至家中的座上宾,多次有机会近距离、面对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受到毛泽东在生活上的关心和思想上的教导,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成为了毛泽东在哲学和音乐上的挚友和知己。同时,两人还经常一同参加各种讨论会、报告会、学习会。冼星海多次聆听艾思奇的报告、研读他主编的《唯物史观》等哲学著作。而艾思奇也多次参与观摩冼星海指挥的演出和歌咏会,他所任教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更是当时抗日歌咏运动的主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人还就音乐创作曾进行了深度的互动和交流。1939年3月25日,冼星海在日记中提到,“ 今天艾思奇寄给我一封信,说及《生产大合唱》的音乐,就这样写:昨晚看了‘ 鲁艺’的预演,许多人都认为音乐很好,都佩服你的创作精力,希望能够再在融化中国民族音乐方面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⑦。1939年5月9日,在鲁迅艺术学院召集的《生产大合唱》座谈会上,艾思奇作了重点发言,充分肯定了《生产大合唱》的成功之处,强调了音乐的大众化、民族化的重要性,也指出了这部作品六个方面的缺点和弱点。艾思奇的发言,对冼星海《生产大合唱》这部作品的修改乃至后期的整个音乐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除此之外,1939年7月,冼星海整理《反攻》歌集,也是在艾思奇的帮助之下,得以在生活书店出版。
4.念念不忘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相聚是短暂而又奢侈的,因为战争总让人分离。1940年,正值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1940年5月中共中央委派冼星海与袁牧之秘密前往苏联。临行前,毛主席亲自设宴为冼星海践行。在辗转前往苏联的路途中,冼星海先后给钱韵玲写下了21封信,在书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人无尽思念之外,对好友艾思奇及其著作也是念念不忘。
冼星海一直非常喜欢读艾思奇写的书,即便离开延安后奔波于路途中,也多次给妻子钱韵玲写信推荐她阅读艾思奇主编的《唯物史观》。例如,1940年5月21日在给钱韵玲的信中写到,“ 有两本书你一定要买(一)《论共产党》、(二)《唯物史观》,您看完之后再看《辩证法唯物论教程》”⑧。又如在1940年6月14日的信中提到,“《 唯物史观》这本书非常好,你可买一本或借一本去读,并且要慢慢地读,同时又要做笔记”⑨。他一再告诫钱韵玲:“ 一切学习都先以政治课为基础,尤其是要热心于马列主义,不要嫌它乏味。假如你不弄通马列主义,你的艺术造就是有限的,请你接受我的忠实话。”⑩还有,在1940年8月2日的信中,冼星海又写到,“ 你如果有多余的钱的时候,你可买《解放》、《唯物史观》及最近出版的 《马恩论文艺》等书来看”⑪。冼星海念念不忘的《唯物史观》是艾思奇与吴黎平合作编写的一本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系统教材,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区以《科学历史观教程》印行。它对于提高当时抗日青年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正确理解党的抗战方针政策起了不小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冼星海在处理个人著作出版的问题上,他把有过编辑经历的艾思奇视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为此,他在1940年6月6日的信中专门嘱咐钱韵玲,“ 同时你可以叫马可整理我的《指挥法》,寄给光未然出版或交生活书店,也可以交周扬,或交读书生活社。由艾思奇转也可以,这样你至少可以拿一百五十元”⑫!除此之外,冼星海在离开延安后,也非常注重从艾思奇力推的 “民族化”、“大众化”理念中吸取思想资源,并以此作为音乐创作的方法启示。他在旅居苏联期间先后创作了《中国舞三首》、《中国生活》、《歼灭》、《中国狂想曲》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从而把音乐的“ 民族化”、“ 大众化”推向了新的高度。可见,冼星海对艾思奇的“念念不忘”,不只是停留在普通的生活层面,更多的是灵魂深处的互通和交融。
二、艾思奇对冼星海的影响
艾思奇作为大众哲学家,在其一生中,尤其是在延安期间,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源源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传递给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他的思想和观点对冼星海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1.为冼星海音乐道路的选择提供价值引领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一个音乐家在音乐道路的选择上往往面临一个难题:是为音乐而音乐?还是为人民而音乐?选择什么样的音乐道路,这不是技巧和方法的问题,而是立场和导向的问题。
冼星海也曾经遭遇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在到达延安之前,他一直在追求一种纯粹的音乐理想。他在1929年发表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院院刊》的《普遍的音乐——随感之四》中提到,“与其缺乏天才,不如多想方法,务使中国有天才产生之可能,才是学音乐的人的责任”。“ 我的主张是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使中国音乐化了,逐渐进步上去,中国不怕没有相当的音乐天才产生”⑬。这说明当时的冼星海,只是一名为音乐而音乐的纯粹音乐人。后来在巴黎留学时,冼星海听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又加上当时生活的艰苦,创作了他平生第一部音乐作品《风》。这部作品虽然运用了三重奏的创新手法,融入了中西方的音乐元素,但是从它的基调上来看,还仅仅只是抒发其个人内心的苦闷。
直到冼星海1938年到达延安之后,他对音乐的追求和理解才有了巨大的改变。1939年4月他在《“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为“鲁艺”一周年纪念而写》这篇文章中写到,“我们创作什么样的新兴音乐呢?我的回答是以‘大众化’为第一要紧。音乐要有力量,节奏要明显,要通过民族的形式和内容来创作民族的新兴音乐”⑭。同时,他也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一系列贴近人民生活、反映人民情感的作品。这样的转变,除了毛泽东对他的引领之外,艾思奇对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从冼星海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多次听艾思奇讲哲学、作报告,艾思奇在这些讲课和报告中反复地强调、科学地阐释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观点。在艾思奇等哲学家的熏陶下,冼星海深刻地认识到“ 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与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懈地奋斗”⑮。他还在艾思奇的推荐下阅读了《唯物史观》、《论共产党》、《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概论》等哲学书籍。以至于在离开延安时给妻子钱韵玲的信中反复提醒她要阅读哲学书籍、“ 热心于马列主义”、“ 弄通马列主义”。由此可见,冼星海之所以能走上为人民而音乐的道路,是因为艾思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他进行了价值引领。
2.为冼星海音乐思想的形成提供理论指导
音乐家之所以为音乐家,不仅是因为他掌握了音乐的技巧、具备了音乐的才能,最根本的是在于他认识了音乐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思想。
冼星海是新文化运动思潮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又加上赴法国巴黎留学的经历,受到了西方音乐的影响,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音乐环境与西方音乐环境的差异。在他十分有限的音乐人生中,一直在苦苦地探索一些宏大的时代命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怎样才能发展这样的音乐”、“ 谁来担当音乐发展的使命”?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冼星海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在1929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院院刊》中的《普遍的音乐——随感之四》中提出,“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⑯。在1938年《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中又提出,“ 我个人是主张以内容决定形式,拿现代进步的音乐眼光来产生新的内容,使音乐的内容能反映现实,反映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生活”⑰。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1940年1月8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他对音乐工作者提出了13条意见,其中写到,“ 我们要不脱离大众以音乐服务抗战,音乐工作者要与大众共同生活,共同患难,没有大众的音乐工作者,是不会工作下去的”⑱。由此可见,冼星海在火热的革命生活中,不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音乐人生的转型,而且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思想。其音乐思想的形成,直接得益于艾思奇给他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1939年3月25日,艾思奇致信冼星海,对 《生产运动大合唱》大加赞赏并希望他能在“ 融化中国民族音乐方面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⑲。
在艾思奇的引导、帮助和关心下,冼星海不但牢固地树立了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革命思想,而且对于政治理论和艺术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把握,从而确立了更强烈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他在繁忙的音乐创作之余,自觉地研读了《什么是马列主义》、《论共产党》、《马恩论文艺》等政治理论书籍。从某种意义上讲,冼星海之所以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下,成功地建构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思想体系,与艾思奇在理论上的传道播火、示范引领是分不开的。
3.为冼星海音乐创作的转型提供方法借鉴
每一部音乐作品的背后,都凝结着创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怎样创作这样的作品,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既是世界观的问题,也是方法论的问题。从人民音乐家成长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来看,一个真正的人民音乐家,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必定会始终坚持扎根人民、深入生活、贴近现实、勇于创新、精益求精,而闭门造车、脱离群众、追求浮华、因循守旧、浮躁虚狂、追名逐利、搜奇猎艳等注定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
翻开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人生履历、审视他各个时期的音乐作品,不难发现,冼星海到达延安以后不仅在价值理念和音乐思想上实现了升华提纯,而且在音乐创作的范式与风格上焕然一新。以冼星海在上海时期的代表作《夜半歌声》与延安时期的代表作《生产运动大合唱》为例,从一定意义上说,《夜半歌声》完全是完成命题之作,展现的是黎明前的黑暗,倾诉的是一己之幽怨,采用的是西洋歌剧的曲风,反映了当时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秉持的纯艺术主义倾向。而从延安时期的代表作《生产运动大合唱》来看,这很显然是“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自由之作。它展现的是延安抗日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场面,表达的是人民大众为争取抗战胜利、追求民族解放而努力生产的愉快情绪,彰显了冼星海为人民而传唱、为时代而放歌的创作之道。
冼星海音乐创作方法的创新,既源自于他对中国民族新音乐的卓越探索,也得益于他身边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大众哲学家艾思奇的引领和带动。艾思奇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 要充分反映现实,从现实中找到艺术创作的题材与主题”,“要用适当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内容”,“ 把握大众所要求的东西,向老百姓中间的艺术学习”,“ 要处理好继承发扬与发展创造的关系”⑳……由此可见,艾思奇从哲学的高度来探寻艺术创作之道,为冼星海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启示。从冼星海到达延安以后的音乐创作来看,他显然是把这些方法论启示很好地运用到了音乐创作的实践中。他走出窑洞的方寸之地,走向广阔的革命场域,在开荒生产的田间地头写下了《生产运动大合唱》。他把视线从人情冷暖的个人世界,转向抗日军民的火热生活,用深沉的家国情怀,创作了《黄河大合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冼星海所创作的《民族解放交响乐》,其创作过程长达6年之久,在创作方法上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这部作品最早写于1935年9月至1936年秋,其创作主要是着眼于反映民族危机和人民的苦难;1938年11月至1941年春,冼星海对原来的草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大幅度的修改,对作品的民族形式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使作品的立意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力图通过这部作品阐释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他在作品前面写道:“ 此作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光荣的领袖——毛泽东同志。”㉑在创作札记中进一步提到:“ 我敬慕着这一代伟大的人民领袖,我把这心血创作出来的微小作品贡献给他,愿他领导着民族解放……给人民以自由平等,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前途定可实现。”㉒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述这些经典作品的成功创作,充分体现了冼星海在艾思奇的引领和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自觉体悟和巧妙运用。
4.为冼星海音乐作品的传播提供重要蓝本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㉓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在本质上是人民心声和情感的表达。冼星海曾深刻地指出:“ 一个大众歌曲如果能反映目前军民抗战情绪,它的感动力量比一篇政治演说来得容易动人而且直接。”㉔音乐要成为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武器、精神生活的慰藉、高雅娱乐的载体,必须最大限度地体现大众性。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在思想立场上要始终坚持为人民、爱人民,而且在主题和内容上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同时在表现形式上,要力求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传得开”、“ 留得下”。
冼星海音乐人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在抗战年代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战第一歌。周恩来听闻此曲后高度赞扬:“ 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㉕79年后的今天,《黄河大合唱》仍然是人们在重要场合和歌咏运动中的首选歌曲,同时在海外演出已有60多年的历史,越来越受到国际音乐界和听众们的赞赏。《黄河大合唱》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广为传唱,并日益显示其国际影响,能历经时代的变迁而不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从内到外展现了大众化、通俗化的艺术特质。认真分析和解读《黄河大合唱》就不难发现,冼星海在到达延安以后,尤其是在经历了理论引导和战火洗礼以后,对于音乐作品的传播之道,已经有了精深的掌握和熟练的运用,这与艾思奇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先驱者,艾思奇以其成名作《大众哲学》为冼星海延安时期以及后来在苏联期间音乐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一部可学可鉴的重要蓝本。《大众哲学》形象而生动地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给青年和群众提供了一部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本。抗战前后,《大众哲学》一连发行32版,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 大众哲学》的出版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㉖以至于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曾哀叹:“ 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并声称,“我不是败给了中共的军队,而是败给了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㉗。他甚至要求他的部下以及孩子好好研读《大众哲学》。《大众哲学》之所以广受欢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 为大众而写”、“为大众所用”。艾思奇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生动浅显的事例、朴实自然的文风,将艰涩的哲学理论大众化、通俗化,拉近了理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解释得生动具体,使大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冼星海在与艾思奇密切交往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大众哲学》的成功经验,把大众化、通俗化的理念贯彻到自己音乐创作的全过程,积极投身于人民当中,倾听人民的呼声,从而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经典作品,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树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三、结语: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影响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不但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为人们确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它不仅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从而体现出强大的真理威力和深沉的实践智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㉘文艺作为人们把握自身与世界的重要方式,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哲学的引领。
进入新时代,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很多新问题、新矛盾,只有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下,才能得到科学的阐释、精准的把握和有效的破解。长期以来,由于学科之间的壁垒,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艺领域里被边缘化、娱乐化甚至妖魔化,出现了“失语”、“ 失踪”、“ 失声”的问题。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最晦涩难懂的学问,对其敬而远之甚至不屑一顾,这种状况既发人深省又令人堪忧。它不仅严重制约了文艺创作的精神高度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格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实效性和影响力。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如何打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艺之间的壁垒,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艺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大众哲学家艾思奇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之间深度融合的跨界交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中的一个历史佳话和成功范例,对于当今的哲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第一,哲学工作者要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传播,积极主动地面向文艺领域,贴近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充分整合运用文艺资源,深入挖掘文艺作品当中的哲学内涵,用文艺生活中的经典案例和丰富素材、文艺工作者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以及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传授给文艺工作者。与此同时要讲好、讲精、讲活文艺名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下成长、成材、成功的精彩故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和力量传递给文艺工作者,从而启发文艺工作者以文载道、以乐明德、崇智尚美、立己达人的“ 红色初心”,由此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魅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时代担当。
第二,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 学哲学”、“ 用哲学”,自觉接受和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精髓,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和体系,切实体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和力量,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要把深奥的哲学原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到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创作出更多精彩纷呈又不失思想高度的文艺作品。要让文艺作品不仅仅作为艺术的表达,而且是集哲学的智慧、精深的思想、丰富的情感于一体的集合,从而让文艺作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重要传播载体。
第三,哲学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应保持深度的互动,二者同属意识形态工作序列,不能因为学科内容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而相互疏远,而应该同向同行、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协同精进。新时代的哲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都应以艾思奇与冼星海为榜样,既要友好往来、深度交流、虚心学习,又要自信张扬、特色鲜明、相互碰撞,这样才能在取长补短的同时产生更多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的火花,共同书写哲学底色与音乐特色交相辉映的现代版 “高山流水”,携手并肩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共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兴盛。
注释:
①②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㉔《冼星海全集》第1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382、262—263、331、 335、335、343、334、 15、 40、293、16、48、94、263、141—142、148、150、65 页。
③ 参见上海市山海工学团:《山海钟声:陶行知与山海工学团》,上海市新闻出版局2001版。
④ 张癸、叶良骏:《天下第一工学团》,《新民晚报》2011年12月4日。
⑤ 沙平:《毛泽东与艾思奇的“ 哲学情”》,《四川党史》2002年第4期。
⑥ 何启君:《想起了延安“ 毛泽东图书馆”》,《人民日报》1995年3月2日。
㉓《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㉕ 转引自陈寂:《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人民日报》2016年7月20日。
㉖ 转引自余炳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纪念艾思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红旗文稿》2010年第19期。
㉗ 许全兴:《一卷书雄百万兵 攻心为上胜攻城——关于艾思奇〈大众哲学〉历史作用的回顾》,《北京日报》2010年3月8日。
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