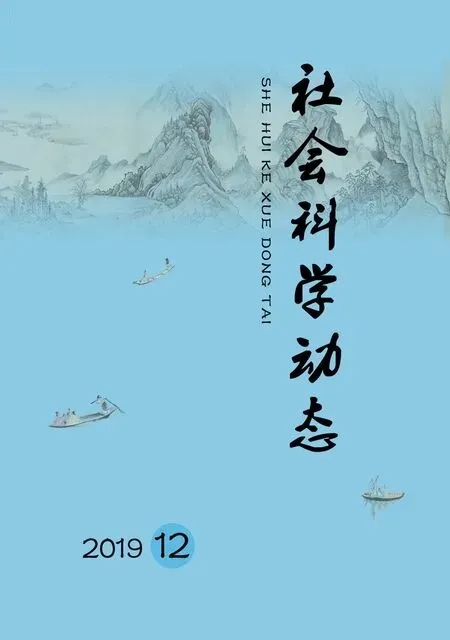制度与族群
——《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评介
2019-02-18陈锋贾石
陈锋 贾石
清代,因战、守之需,八旗军民“星罗棋布,控制险要”,驻防八旗族群遂逐渐形成。在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驻防旗人是“独善其身”,还是“既来之,则安之”?面对窘境、甚至剧变,他们又如何维生,身份如何转变?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清代民族史、社会史等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亟待学界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
可喜的是,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潘洪钢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结项成果《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2018年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起,作者即开始关注“长期生活于异族包围中的少数民族群体”,至今已数十年。本书将上述问题置于清代以降的民族、社会等宏大视域下,以日常生活史视角切入,从田野调查开始,不断深挖。煌煌70余万言,就是作者给出的答案。
一、生活与记忆
回顾相关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八旗驻防族群及旗人社会问题,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定宜庄著《清代八旗驻防研究》,从制度史的角度入手,主要讨论清代八旗驻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兼论驻防地旗民关系等问题。韩国学者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以各地驻防八旗志为主要材料,讨论了驻防旗营建制及其衰败过程。随着史学研究者的“目光下移”,中下层民众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对旗人社会生活的研究,亦逐渐发展。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就是一部以北京旗人社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展变迁的佳作。
以往研究颇具启发性,也留下了讨论空间——从日常生活史视角入手探究驻防八旗社会变迁。本书即是围绕中下层驻防旗人群体的社区生活、土著化问题、妇女生活、婚姻问题、旗人生计、族际交往以及历史转折等方面内容,对驻防旗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进行了长时段、大规模的全面研究。全新的视角,使驻防旗人族群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完成了对驻防八旗从“制度”到“人”的具象化重塑,在驻防八旗的研究领域中,可谓独树一帜。
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下,记忆是历史与现实的媒介之一,田野调查则是获取历史记忆、探索民族心理的重要方法。作者就曾遍访八旗驻防故地,搜寻这一特殊族群的记忆,“代序”中曾写道,“数年来,我们走访了荆州、成都、广州、开封、青州、杭州、南京、镇江、福州、长乐、西安多处清代八旗驻防故地,有些地方反复多次进行田野调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发掘出了大量诸如家谱、祭册、歌谣等承载驻防旗人族群历史记忆的珍贵史料。
历史现场,是复杂史实与丰沛情感的不谋而合,往往会给研究者带来心灵的冲击。在走进历史现场、汲取灵感的同时,本书注重比较文本记载与历史记忆,作者这种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也体现了历史研究者的素养。如,对比文本记载与旗人后裔记忆中的驻防八旗军队,书中写道,“文本记载多将驻防八旗看作一只不能打仗的军队,一个无所依托、无所事事的群体,乃至有人鄙视其为寄生的族群。而八旗驻防族群及其后裔的记忆中,则认为驻防旗人是国家的军队,王朝的基石,为国家和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比较文献与记忆的同时,作者也善于发现并辨别、分析不同族群的记忆。在田野调查中,作者就发现福州旗人记忆最深刻的,往往是他们在辛亥革命后所遭遇的民族歧视;而当地汉人,则大多不能忘却辛亥革命以前他们途径旗营地段曾遭受的欺凌。再如,在汉族人的许多记忆和叙事中,旗人是腐败的压迫者,并将其称为“铁杆庄稼、老米树”。而在满族精英的记忆中,旗人为了和平的环境和安定的秩序,付出过巨大的牺牲,领军饷是理所应当,并认为汉人的这种讽刺是民族偏见的产物。同时,本书也运用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着重分析产生这种“记忆的选择性”的缘由,并进一步探索民族心理及其文化遗传中的“真实”。
以上此类历史人类学式的探索,立足于文献,并结合田野中的历史记忆,使得本书的论据更加多元,论证更加清晰。
二、对话与回应
近些年来,关于“新清史”的讨论,热度不减。作者秉持学术对话的态度,对“新清史”研究的相关论题,进行了回应。这些回应,均以扎实的文献资料与长期的走访、观察为基础。
如关于满汉族群的身份认同问题,涉及对历史记忆本身的认识。“新清史”部分研究,仅通过文本记载,不分地域,笼统分析,不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由于旗人的历史记忆与文本记载存在差异,加之各地驻防旗人的族群认同亦有较大差异,故结合旗人的历史记忆、族群心理,对各地进行具体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本书认为,驻防旗人的流散与其后裔记忆中的文化失落感始于何时,各地情况并不相同。荆州等地旗人的流散始于辛亥革命,开封旗人后裔的生活、心理落差则始于1922年冯玉祥军队进入开封,福建三江口旗人后裔则认为抗日战争才是旗营社区破坏的真正起点。
“新清史”对“满洲的民族性”“汉化”等问题同样颇为关注,本书“驻防族群土著化”一章,也从驻防旗人族群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作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各地驻防旗人后裔的语言、风俗、历史记忆,存在极大差异,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究其基本原因,就是驻防旗人族群的土著化。
虽统治者有防范旗人土著化之心,但制度与实际情况的冲突,使得驻防旗人土著化不可避免。制度上的松动与突破,是势之所趋。如,由“严格的归旗制度”到“驻防旗人可在驻防地建立坟茔,就地安葬”;由“驻防旗人必须附于京师参加考试”到“可就地参加科举考试”;由“户口附于京旗管理”到“逐渐在当地管理”,由“关涉驻防旗人的各类案件须交京师最终处理”到“案件可在当地处理”。以上关于“制度突破”的分析,广泛征引档案、史籍,足见作者的考证功夫。
驻防旗人在200多年间,经历了驻防地文化的洗礼,甚至逐渐成为所在地方的土著居民。其对驻防地的文化认同应是制度突破的原动力,包括对驻防地的故土、语言等的认同。作者搜集到的荆州驻防旗人富察氏魁玉家族的谱书,显示该家族自第一代岱清公起,即葬于荆州城外八里山,二代以降,即以此地为家族墓地。即使于外地致仕的高官魁玉,亦归籍荆州,葬于此地。这就是驻防旗人对驻防地的故土认同。
三、个性与共性
在群体史研究中,史学研究者经常通过研究对象与其他群体的对比、研究对象内部的比较,讨论个中差异,析出研究群体个性,以期得出新的结论。本书的对比,基础扎实、颇具针对性。作者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数据比较,而是广泛结合制度与实例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同时,在对比的过程中,亦有对以往研究的反思、完善与创新,难能可贵。
在“生计维艰”一章“恩养与生计”一节中,作者就通过比较直省驻防旗营与各省绿营的粮饷、红白事赏银、官员养廉银、恩赏救济、借贷及伤亡抚恤等方面的待遇,发现以往学界仅从单一粮饷数字得出的“旗人粮饷水平远高于绿营”之结论并不完全准确。通过进一步分析又认为驻防八旗与绿营在表面待遇上互有高低,但一些制度上的传统变相增加了驻防旗人的负担。其一,八旗官兵有自备马匹兵器的传统,且入关后仍然延续,对兵丁生活影响很大。其二,人口增长,兵饷不增,一份粮饷养活的人口大量增加。驻防旗人全员皆兵或者是预备兵、军属等,原则上不参加资生活动,与绿营兵眷属自谋职业和生计的情况,差异巨大。这种制度上的传统,加深了八旗驻防族群的生存困境,而从绿营与驻防旗营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旗人贫困化的制度性与根本性。
同一个族群的内部亦不免存在差异,旗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禁旅八旗与驻防八旗,满洲旗人、蒙古旗人与汉军旗人,情况不尽相同。本书的研究对象八旗驻防族群亦如是,从各地驻防旗城建置、各地驻防旗人的地方认同与记忆、驻防八旗内部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各地驻防八旗的命运转折时段等方面看,均是差异性与同一性并存。因此,厘清并分析八旗驻防族群中的个性,并于差异中探寻其内在联系、提炼共性,尤为重要。
作者在提到“旗城建立”一部分时,就针对不同驻防地旗城、旗营建置上的个性作了细分。如,江宁、西安、成都、杭州、荆州等地的旗城是典型的城中之城,即在旧城中划一块区域,将其原居民迁出,形成驻防营,此类驻防营规模大,既节省了建城的时间与经费,又便于对驻地居民的管理。各地的驻防旗城、旗营,虽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但无论是城、营,还是界、街,其本质是相同的,即隔离。“从清代旗民隔离的视角看,不论城中城、旗界或是城外城等,其要义在于,将旗兵驻防之地划分为一个独立而封闭的区域,从而构成旗民分治之基础。”另外,本书从明清鼎革的大背景出发,分析其中共性,认为清初留军驻防是征战之需,旗城建立的最初目的也是用旗民分治的方式减少族际矛盾。而后,旗民分治也在“保证驻防旗人的民族性”以及“防止驻防旗人浸染汉俗”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至此,作者既用扎实的史料厘清了各驻防地旗城旗营建立的差异,也从这些个性中分析提炼出旗城建立的共性,即“旗民分治”。
如上两例,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八旗驻防族群的内部差异以及共性的深刻理解。分驻各地,是八旗驻防族群的外在特点。这种地域上的差异,催生了诸如各地驻防旗城建置的个性化、族际通婚的个性化、生活习俗与语言的个性化等等现象。实则,八旗驻防族群的共性暗含于个性之中,如各地旗营的建立有着共同的目的、个性化的族际婚姻内含共同的旗民互动、不同地域的生活记忆暗含相同的驻地认同,应对剧变的不同方式饱含同样的民族情感。
作者综合运用史料,多次比较驻防旗人内部差异,极力还原历史真实,是对实证的“自觉”。而以八旗驻防族群的共性为暗线,亦使研究更加深入,族群变迁的轨迹清晰可见。
四、过往与如今
现实观照是史学研究的升华,探寻历史与现实间的“映射”,更是研究中难度极大的部分。基于丰富的田野调查,作者深知,“武昌一役”不应是驻防旗人族群研究的终点。民初以降驻防旗人社会的变迁、如今旗人后裔的生存状态、民族文化的发展等问题,同样需要被关注。
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的民族政策与久违的民族情感,使满族人口激增至千万,满族文化也开始被重新发掘、解读。满语文的教学与推广,形势喜人。除此之外,新式满族歌曲、新式满族服装、新式满族饮食、新建满族景点甚至新式满族节日等,不断涌现,回归与再造,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但“由于民国时期饱受歧视的痛苦记忆,许多地方精英在回首往事时,直接将满族文化与清代宫廷及清代民俗对接”,本书态度鲜明,“民国已然不再,何况大清,满族文化的复兴,必须是现代化背景下的固有传统的恢复和与时俱进,而非专制王朝的余绪再现。”
史学是“人”的学问,在观照现实问题的同时,本书中亦不乏人文关怀。在访谈中,作者与受访者,共同探寻记忆,建立了情谊。书中多次提到,向作者展示开弓射箭动作的96岁成都驻防旗人后裔刘沔先生、92岁的何氏正骨专科传承人何天祥等受访者。作为史学研究者,感情应是节制的,而情感的共鸣则是合理的。书中就曾写道,“在青州、广州、福州等地,作为一个时常提示自己要保持学者立场的访谈者,我们却时时被满蒙人民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所打动。”这种基于田野调查的现实观照、基于历史记忆的情感共鸣,定会给历史研究者更多启示。
综上所述,本书广泛研读文献,而不止于文献;研究开始于田野,而不迷失于田野。从生活史视角切入,加之游刃有余的“叙事”技巧,也使本书在厚重之余,颇具可读性。短文必无法囊括这部大书的全部特色,未尽之处,尚待方家探索。在此,还望潘洪钢先生,再出佳作,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