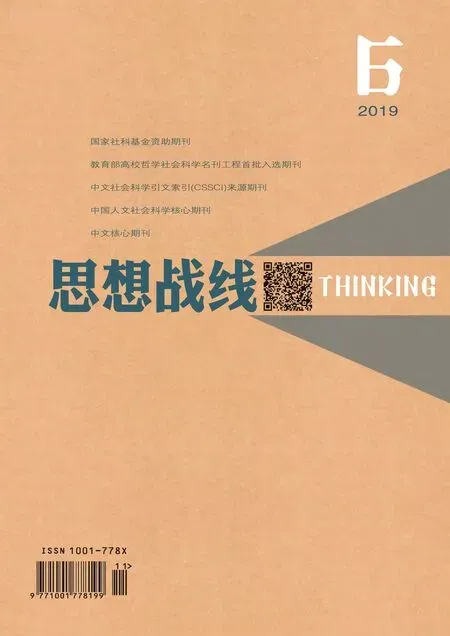虚拟现实本体论地位的现象学反思
2019-02-18张瑞臣
张瑞臣
近年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已经迅速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例如,阿里巴巴公司正在开发用虚拟现实进行网上购物的技术,借助于虚拟现实技术,顾客可以在虚拟商场中逛街、购物等等。虚拟现实技术具有高度的具身性、互动性、参与性等特征,海姆(Michael.Hein)说道:“虚拟现实以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同信息的关系。它是第一种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允许身体的能动使用的智能技术。”①Heim M,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vii.可以预见,虚拟现实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将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密切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乃至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可以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之中,从而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及对自身的理解方式。
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迅猛发展相比,国内对于虚拟现实的哲学反思却非常之少。在我们接受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哲学有责任去进行反思、预见,指出此种新事物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可能的后果。例如,虚拟现实是否会带来新的、程度更深的异化、此种异化是否不可避免、人们是否有一天可能会沉浸在虚拟现实中而无法自拔?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哲学家来进行思考和解答。本文将借助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资源,对虚拟现实进行哲学反思。我们知道,现象学的一个基本的口号就是“回到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它要求我们,回归到生活世界,回归到在当下的生活世界之中直接呈现出来的事情上,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充分无偏见地面对实事自身所要求的东西”。②[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 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49页。因此,从现象学的“回到事情本身”的态度出发,我们也有必要对之进行现象学的反思。胡塞尔的时代并未出现虚拟现实,胡塞尔本人并没有对虚拟现实进行哲学上的探讨,胡塞尔既有的本体论的框架并不完全适应于在存在方式上极为特殊的虚拟现实。因此,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虚拟现实进行现象学的考察,赋予虚拟现实以独特的本体论地位,构建虚拟现实的区域本体论体系,也就成了当今现象学学者不可推卸的任务。
一、从时空的角度看,虚拟现实不是实在的(real)、实项的(reell)或者观念的(ideal)
按照胡塞尔本体论思想,我们可以从宏观上对本体做出如下的划分:实在的(real)、实项的(reell)、观念的(ideal)。在这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用最为言简意赅的话来说,就是:实在的是指处在时空之中的存在物;实项的是指处在内在时间中的存在物;观念的是指超时空的存在物。例如,作为实在的苹果,是处在时空之中的实际的存在,它摆在桌子上(处在空间之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处在时间之中)。这种实在的存在,在胡塞尔那里,也就是所谓的包含着“存在设定”的对象,即从意向性的角度而言,我在意向这个苹果的时候,“默认”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苹果。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则是作为“本质”的苹果观念。作为本质或者观念的苹果,并不处在时间或者空间之中,它并不是一个经验性的存在物。实际上,在实在之物和观念之物之间,胡塞尔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强调二者的本质不同,“本质与事实的关系,不再是型相和事物的关系(柏拉图),也不再是本质(概念)与事物的关系(黑格尔)。具体言之,本质是诸事实的一般性或共同体性,是诸变项中的不变要素”,①杨宝富:《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纯粹性”的危机》,《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胡塞尔自己也说道:“即对本质的设定和首先是对它的直观把握,丝毫不包含对任何个别的事实存在的设定,纯本质真理丝毫不包含有关事实的断定”。②[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3页。作为观念的苹果是先验自我进行主动构造的产物。而且,苹果的本质一旦被构造出来之后,也就脱离了任何的实在的苹果的限制,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是苹果之为苹果的共同的规定性、是“异种之同”。而对于这种“异种之同”的把握,需要通过本质直观的方法。而本质直观的过程,完全可以只借助想象中的苹果,而并不必然地要求现实中的苹果,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说道: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束缚(对世界的设定、存在的束缚)、将它有意识地排除出局,并且从而也使诸变体的最广阔的环境视域摆脱一切束缚,摆脱一切经验的有效性时,我们才能创造出完善的纯粹性。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说是立于一个纯粹想象的世界中,一个纯粹可能的世界中。③[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406页。
如果说观念的存在是全无时空的规定性而实在的存在则必然具有时空规定性的话,那么,实项的存在则仅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而无空间上的规定性。例如在我的意识中所具有的关于苹果的表象。就苹果的表象而言,它并非是一个现实的苹果,它并不像一个现实的苹果那样被摆放在桌子上,它并不处在客观的空间之中,它位于意识之内。说它内在于意识之中,也就意味着它必然地处在时间之中。因为,意识总是时间性的意识,意识总是处在内在时间之中。因而,对于实项的存在之物而言,它必然在内在时间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它意味着对于感性材料的内在的拥有。
如果我们以时间性为线索,回过头来对这三种不同的存在物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实在之物和实项之物,都是可以在时间上定位(即它们都在时间上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只不过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实在之物所占据的是“客观时间”位置,而实项之物所占据的是“内在时间”位置,客观时间和内在时间在胡塞尔那里有着严格的区分,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具体交代);但是,就观念之物而言,则不具有任何的时间位置,它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可定位性。而且,胡塞尔坚持内在性的立场,认为空间性也最终奠定在时间性之上。位于时间之中的意识现象,具有最大程度的明见性。④韩 骁:《胡塞尔“构造”概念的三种图式》,《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内在性的意识之物始终都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超越性的客观的实在之物,则是一种众多主体的共同设定。因为,在胡塞尔看来,我们首先知道的是意识之内的现象,而至于超出意识之外的存在,归根到底也只不过是根据意识现象做出的一个合理认定而已。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虚拟现实是否可以归属到以上的三种本体论存在之中。首先,就现实之物而言,它必然的要求存在于客观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而虚拟现实作为一个虚拟之物,显然并不存在于客观的时空之中。然而,虚拟现实又不是绝然没有时空上的规定性的。例如,在虚拟现实电子游戏之中,其中的游戏角色也可以具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而且,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虚拟的空间和时间也会变得越来越逼真。例如,我在戴上VR眼镜玩虚拟的打棒球的电子游戏的时候,必须要调整我的身体姿势,瞅准时机准确挥出我的球棒,只有这样才能在恰当时间和位置击中棒球。其中的诸多环节,都涉及到了时间和空间。但是,这种时间和空间毕竟又是虚拟的。
正如刚刚提到的,虚拟现实可以具有某种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规定性,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将虚拟现实和观念之物区分开来。观念之物是全无时空上的规定性的,它是无时空的或者“超时空”的。但是,虚拟现实却可以具有某种时空性。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去仔细的考虑一下的话,虚拟现实虽然可以具有“虚拟的”时空上的规定性,这种时空规定性对于虚拟之物来说,是必要的吗?或者说,它可以不具有时空上的规定性吗?在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设想一个孤立的虚拟的棒球,除了这个虚拟的棒球之外再无它物,而且,这个虚拟的棒球是完全静止的,其本身也无任何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我们并没虚构出虚拟的时间或者空间,而且棒球本身也并没有被虚拟的时间或空间规定。
虽然我们可以如此来设想,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从其他方面来把观念之物和虚拟现实之物明确的区分开来:观念之物是抽象的观念构成物,是自我主动的构造出来的,它无法通过我们的感官被知觉到;但是,虚拟现实之物却是具体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感官知觉到的。虚拟现实是借助于计算机程序而被虚拟出来的,而非直接地通过先验自我的主动构造而产生。因此,苹果的抽象概念和虚拟的苹果,毕竟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最后,就实项之物而言,显然,虚拟现实之物并不能够归属到实项之物里面去。实项之物处在内在时间之中,内在时间不是虚拟时间。意识的内在时间就像河流一样,处在不断的流动之中。内在时间是连续的、单向的。并且,每一个时间相位都具有最原初的“滞留—原印象—前摄”的时间意识结构。虚拟现实的时间,作为虚拟的时间,可以循环往复、不断的“再来一遍”(例如,我们可以反复的去玩VR游戏)。在此,为了准确的理解,我们需要明确地区分虚拟现实本身和对虚拟现实的知觉。通过对虚拟现实的知觉而获得的感性素材,存在于意识之中,进而也处在内在时间之中。但是,作为知觉对象的虚拟现实本身并不处在意识的内在时间之中。
二、虚拟现实不是“想象的”也非“现实的”
(一)虚拟现实不可归属到“想象物”里面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按照胡塞尔对于现实之物、实项之物和观念之物的划分与界定,我们似乎很难把虚拟现实归属到其中的任何一类中。虚拟现实在胡塞尔的时代尚未出现,因此,胡塞尔也自然没有将虚拟现实纳入到他的现象学的考察范围之中。因此,如何界定“虚拟现实的本体论地位”,也就成了当代的现象学学者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仅仅依靠胡塞尔自身的思想资源,似乎依旧是不够的。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赋予虚拟现实以某种特殊的本体论地位。
在此,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可以将虚拟现实归属到胡塞尔的想象之中,虚拟现实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想象物。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在此,我们可以回归到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所做的关于经验与想象、现实的世界和假想的世界的相关论述。胡塞尔说道:“从这种关联(现实的关联)中涌现出一切想象物,而这些想象物本身却恰好处于这种关联之外,并且作为世界的假想部分而与经验世界形成了对比,这就是在现实物及其变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别的关联。”①[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48页。在《经验与判断》中,存在着如下的基本的区分:“经验—现实世界”——“想象—假想的世界”。想象不同于经验、由想象而来的假想的世界不同于现实的世界。而且,在胡塞尔看来,现实的世界在本体论上是明显的优先于假想的世界的。胡塞尔说道:“只有当一个人生活在经验中并由此出发插手于想象,同时又把想象与经验活动相对比时,他才能够拥有假想的和现实的概念”①[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48页。“在这里,假想物就是一个从经验及其基底中被建立起来的某个被经验到的想象的对象,就是说它的意向对象处于这对象性正好在其中被想象的模态中。”②[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48页。作为想象对象的假想之物,是建立在现实的经验对象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的经验是假想的可能性的条件。
那么,虚拟现实之物是否可以归属到想象的假想之物的范围中呢?在笔者看来,实际上是不可以的。这是因为,所谓的假想之物,其实是想象活动的产物。其本身的存在与否、如何存在,其实都是取决于主体自身的想象活动的。而且,这种假想之物,也依赖于现实的经验。但是,就虚拟之物而言,其背后所依赖的是一套复杂的程序以及运行程序的物质基础,如电子计算机等。其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存在,实际上取决于程序本身的运作。虽然,程序员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必然的要用到自身的想象力,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却是借助于计算机程序而实现的。而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的想象力是一种直接的构形的能力,而无需任何的计算机程序的中介。而且,虚拟现实之物的存在依赖于计算机程序的运行,而不依赖于某个主体的想象,它并不会随着主体想象的停止而消失。
另一方面,正如在上面所说的,想象出来的假想之物是离不开现实之物的,它建立在现实之物的基础上。但是,虚拟现实似乎更多的是直接的被创造出来的,其同现实之间的关联并不是非常的密切。从原则上,我们可以任意地虚拟出任何的东西,而不必顾虑它们在现实中存在与否。而且,虚拟之物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它远远超出对现实进行“模仿”的程度,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现实”。虚拟之物可以与人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例如,我们可以跟虚拟的人打虚拟的棒球游戏。我会根据虚拟的人所打出的球而做出我的反应,虚拟人也会根据我所打出的球进行反应。更为重要的是,虚拟人如何回应、做出什么样的动作,都是我所完全无法掌控的。我无法通过想象力来改变那个与我玩着游戏的虚拟对象。但是,在想象的世界中,其中的任何一个对象都是自我想象的产物, 因此,它们从原则上都可以随着我的想象的改变而改变,我从原则上可以“掌控”想象的世界。但是,这一切在虚拟的世界中都不适用。虽然虚拟现实可以被编写它的程序员改变,这又存在着如下的区分:程序员总已经是另外的一个主体,而非自我,程序员的想象也不是我的想象;虽然程序员的想象可以改变虚拟现实,但是这种改变需要借助程序的编写和计算机的运行来实现;程序一旦编写完成,虚拟现实的运行就不再依赖于程序的编写者,而是按照自身的规则来运行,具有了“自主性”,乃至可以随着环境态势的改变而不断地学习,甚至变更已有的规则、形成新的规则。所有这些特点,都是想象物所不具备的。
在此,有人可能会说:既然虚拟现实无法归属到想象之物里面,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直接把他看做是某种“现实”。但是,这是正确的吗?
(二)从视域的角度看,虚拟现实不可归属到“现实物”中
在上文中,我们在区分虚拟现实与想象的时候,提到了虚拟现实不单单依赖于想象活动、虚拟现实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自性、虚拟现实甚至可以同人进行能动的互动等等。实际上,以上的这些特点似乎都是现实之物所具备的特点。③实际上,从虚拟现实之“虚拟”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虚拟现实是与想象相似的;而从虚拟现实之“现实”的角度而言,我们又可以说虚拟现实是与现实相似的。我们也可以设想,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现实越来越逼真,以至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真实的现实;虚拟现实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至于我们很难在虚拟现实和现实之间做出区分。
对于上面的问题,我们首先借助于胡塞尔自身的思想资源,从现象学角度对之进行回应。在胡塞尔那里,现实的事物具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即现实对象的呈现总是一种视域之中的呈现,而且,现实对象的视域从原则上讲是无穷无尽的,视域总是可以无限地扩大。这也就意味着,现实事物的完全的自身被给予性,是无法达到的,现实事物总是处在一个尚未清楚的界定的模糊的视域之中,总有什么尚未给予出来。因此,对于现实的事物来讲,事物自身,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达到的“理念”。视域这个词汇在德语中本身就有地平线的意思,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地平线,但是却永远都无法达到它。例如,我在观看一个现实中苹果的时候,虽然我可以看到它朝向着我的这一面,但是,总是还有尚未呈现出来的面。从原则上讲,我总是可以发现苹果自身的新的规定性。我可能会新发现苹果的果皮上的一个小凹痕,进一步发现这个小凹痕的深度、长度等等各种各样的规定性。胡塞尔说道:
目前指出下面几点就已经足够了,即自然事物的空间形态基本上只能够呈现于单面的侧显中;而且,尽管在任何连续的直观过程中这个持续存在的不充分性不断获得改善,每一种自然属性仍把我们引入无限的经验世界;每一类经验复合体不管多么广泛,仍然能够使我们获得更精确的和新的事物规定性,以至于无穷。①[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年,第60页。
这里的环绕着侧显的“无限的经验世界”,实际上也就是无限的视域。关于无限的视域,胡塞尔提到:“但是,我可以确信,没有什么规定是最终的,现实经验到的东西还是无限的拥有对同一物的一个可能经验的视域。”②[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48页。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在胡塞尔那里,现实的经验事物的一个基本的、不可或缺特征就是:它总是被无限的视域所环绕,总有尚未呈现出来的规定性。胡塞尔明确地说道:“这样一来,一个实在的东西的实存就从来没有且永远不会有别的含义,而只意味着实存于其中,意味着存在于宇宙中、存在于时空性的开放视域中,这种视域就是那些已知的、以及并不只是当前现实的被意识到而且也包括那些未知的、可能被经验到且在将来被知悉的实在东西的视域”。③[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0页。
而当我们反观虚拟之物的时候,就会发现,至少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而言,虚拟之物的视域总是一个有限的视域,它的视域并不是无限拓展的,虚拟之物本身的规定性也并不是无穷无尽的。这也是虚拟的苹果和现实的苹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分所在。在现实的苹果那里,它总是被一个无限的可能性的视域所环绕,我们总是可以发现这个现实的苹果的新特征。但是在虚拟的苹果那里,由于在背后支撑它的是有限的程序代码,而这些程序总是可以穷尽的,因此,作为程序表征的虚拟苹果,其规定性也就是可以穷尽的了。这一点,在玩虚拟游戏或者虚拟购物的时候,也是可以体会到的。例如,对于虚拟商城中的一件服装而言,虽然我也可以像在现实中一样拿起它、穿上它,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规定性却是有一定限量的。虚拟世界中每一个对象都是有限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虚拟世界本身,作为一个世界视域,也是有限的。而在我们的现实的世界中,世界视域却总可以无限的拓展下去。现实世界的视域可以不断的向外延伸,而且不会重复。
与之相反,虚拟的世界却总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而且它也总是可以重复的。例如,我们在玩虚拟现实的游戏时,我们固然可以探索那个虚拟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总是有界限的,它不可能无限的延伸下去,而且, 我们始终都可以“再来一遍”。但是,在现实的世界中,完全重复的“再来一遍”是不可能的。它并没有一个最终可到达的尽头。然而,在虚拟现实的世界中,碰到尽头总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谈论的虚拟现实都还是目前阶段所出现的虚拟现实。虚拟现实的技术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我们可以设想,在将来可能会出现由强大的人工智能(AI)所支持的虚拟现实。虚拟现实的程序由强大的人工智能来编写,并且,处在不断的编写进程之中。假如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上面的论述就需要作出修正了。考虑到未来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会显得愈发逼真,这就可能会使得普通人越来越难以区分现实与虚拟现实。原因在于,人们所感知到的都是表象,人们正是基于这些表象来进行真假判断的。而表象本身完全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而被逼真地模拟出来,它可以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就如同“实在”一般,“这暗示着对于虚拟现实被理解成一种交流,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主义依赖于使用者的表象的可信性”。①Magnenat-Thalmann N,D. Thalmann eds,Artificial Life and Virtual Reality,John Wiley& Sons Ltd,1994,p.205.如果未来的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构造出与来源于现实的表象一模一样的虚拟表象,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表象对现实与虚拟现实进行区分将变得不可能,而这也是虚拟现实这个术语所暗示的意思,即虚拟与现实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当虚拟现实这个术语开始被使用的时候,带来了很多的期待,有一种观念认为技术会创造出一个不可与真实的世界相互区分的虚构世界”。②Gutierrez M,Vexo F,Thalmann D,Stepping into Virtual Reality,Springer-Verlag London Limited,2008,p.1.当然,以上是从可能性的角度谈论的,就现实性而言,技术的进步能否最终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也是值得商榷的。
三、虚拟现实的本体论地位的界定
实际上,以上的分析表明,如果仅仅按照胡塞尔的传统的现象学资源去对虚拟现实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虚拟现实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找不到一个既有的恰当的本体论位置。虚拟现实既不是实在的、实项的,也不是观念的;虚拟现实虽然与想象物、现实物有着这样那样的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仍旧无法被划归到想象或者现实的领域之中。换句话说,在胡塞尔的既有的本体论体系中,虚拟现实似乎“无家可归”。当然,这并不能怪胡塞尔,因为当时虚拟现实根本就没有出现。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起某种新的区域本体论,一种属于虚拟现实的区域本体论。在这个新的区域本体之中,处在最低层的是一个个具体的虚拟现实,即虚拟现实的具体项、“此处这个”(tode ti)。它们是虚拟现实之区域本体的基底,是高阶的概念、范畴的基底项。胡塞尔说道:
如果我们现在专注实质对象的类,我们就达到作为一切句法构成核心的最终实质性基底。基底范畴属于这些核心,并位于两个相互排斥的项下:“实质的最终本质”和“此处这个”,或纯粹的、无句法形式的个别单一性状(puresyntaktisch formlose individuelle Einzelheit)。③[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0页。
然后,在一个个的具体的虚拟现实的个体项的基础上,通过本质直观的方法,提取出某一类虚拟现实之为虚拟现实的基本的规定性,从而把握到某一类虚拟现实的本质。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虚拟现实作为一个总的区域,在它的下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划分出不同的较小的区域。较小的区域也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划分,最低的不可进一步划分的对象,也就是基底,即上面所说的具体项。因此,我们并不是一下就把握到虚拟现实的总的本质的,而是一步一步地从虚拟现实的具体项开始,先把握到低层级的虚拟现实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地把握到高层级的虚拟现实的本质。在不同层级的本体上面,存在着一般与特殊之间的种属关系,胡塞尔说道:
每一本质,不论是实质性的还是空的(因此是纯逻辑的)本质,都存在于本质的层级系列中,存在于一个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层级系列中。这个系列必然有两个永不彼此相合的界限。我们向下可达到最低的种差,或者也可说,本质的单个体(Singularitäten);而向上经由逐个种-属本质又可达到最高的属。④[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0页。
顺着胡塞尔的这种思路,我们可能会得出如下的虚拟现实的本体论体系:处于最底层的是一个个具体的虚拟现实,如虚拟的衣服、虚拟的网球等等;我们在多个具体项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得到游戏的虚拟现实、购物的虚拟现实等不同的低阶的区域范畴;在此基础上,经过诸多的中间环节,我们最终可以得到虚拟现实的最高属,即一般意义上的虚拟现实。在把握到虚拟现实的一般本质之后,还有必要将之与现实、想象物等范畴进行比较和区分,阐明虚拟现实与它们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当然,以上仅仅是笔者所给出的一种可能性,原则上,我们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虚拟现实的本体论体系。
这种对虚拟现实所进行的本体论上的本质构建,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在胡塞尔看来,“任何事实科学(经验科学)都在本质本体论中有其本质的理论基础。”①[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0页。关于虚拟现实的任何的一门事实性的科学,都需要虚拟现实的本质本体论的奠基。正是因为有了本质科学的奠基,才使得事实科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并充分发挥其效力。胡塞尔说道:
从认知实践角度上首先可以期待,一种经验科学越接近合理的阶段,即精确的法则科学的阶段,因而它越加以发展了的本质科学作为其基础并利用它们作为其论证的根据,那么其认知实践结果的范围和效力也就越大。②[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1页。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任何的对于虚拟现实进行研究的事实性的科学,都必须要奠基在虚拟现实的本体论的基础上。目前,国内对于虚拟现实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从心理学、认知科学、伦理学等经验性的事实科学的角度所进行的探讨,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虚拟现实所进行的研究,则少之又少,虚拟现实的本体论体系的构建更是远未完成。
除了虚拟现实自身的本体论地位有待厘清与构建之外,虚拟现实对人的自我认同的影响也亟需深入的哲学反思。希利斯(Ken.Hillis)说道:“虚拟现实成为了一个非物质的领域,它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舞台,在这些舞台上,人们可以表演出多重自我认同,进而使得自我认同的持续割裂变得合法。”③Hillis K.Digital Sensations:Space,Identity,and Embodiment in Virtual Reality,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p.180.也就是说,虚拟现实带来了多重的影响:一方面,虚拟现实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式的本体论存在;另一方面,虚拟现实也意味一种新式的感知方式。这种新式的存在与感知对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最终会改变人的自我理解方式。在虚拟现实的时代,虚拟现实提供了众多虚拟的场景,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游戏、娱乐、购物、交往等各种活动,甚至可以“生活”于其中,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对应于这个虚拟世界的虚拟自我认同。虚拟世界显然不同于现实世界,甚至不同的虚拟世界之间也各不相同,这也就意味着与之对应的自我认同也各不相同。总之,人们基于不同的虚拟场景而赋予自身以不同的虚拟身份,身份开始变得复杂且多元化。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的“我”,仅仅是众多自我中的一个。在现实世界之外的众多虚拟世界中,还有与之对应的众多虚拟的自我。
多重自我认同是一种只有在虚拟现实时代才有可能广泛出现的现象。人格分裂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多重自我认同,但是它终究是一种病态的现象。基于虚拟现实的多重自我认同与人格分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是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伴生现象,而并非是因为生理的病症而产生的。也就是说,虚拟现实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虚拟的世界,还有与虚拟的世界相对应的虚拟的自我认同。生活世界的变更总是会带来自我理解的变更,人的自我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塑造的。我们可以设想,在未来的世界中,人们除了具有现实世界中的身份之外,在虚拟的世界中还其他的虚拟身份,虚拟身份的多少取决于虚拟世界的多少。虚拟身份在给人们的心理以极大满足的同时(如人们在虚拟的世界中,可以成为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成为的另外的一个人,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也可能带来诸多的风险。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有朝一日我们可能难以分辨虚拟之物与现实之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也会无法分辨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能够从原则上对它们进行分辨,很多人也可能出于特殊的心理需要而不想去分辨。很多人可能更愿意沉浸在虚拟自我之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虚拟的自我是他们更愿意成为的自我,沉浸在虚拟自我之中是摆脱不完美现实的一种途径。在这种境况下,人生意义也分裂为虚拟的意义与现实的意义。当现实的人生意义无法达成的时候,虚拟的人生意义可以补充乃至替代现实的意义。借助虚拟的人生意义,人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避现实世界中的虚无主义。但是,从根本上讲,虚拟的意义终究无法克服虚无主义。在虚拟现实的时代,虚拟世界、虚拟自我、虚拟意义的出现并没有减轻虚无主义,恰恰说明了虚无主义的加深。当人生意义也可以虚拟的时候,不是恰恰说明了虚无主义发展到极致了吗?在虚拟现实的时代,人们实际上面临着更为深刻的虚无主义危机。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之中的真实的自我,才能够产生出真实的意义。
总之,虚拟现实所产生的效应是全方位的:就存在而言——虚拟现实意味着一种新的本体;就认识而言,虚拟现实意味着一种新的感知;就身份而言,虚拟现实意味着一种新的身份。一言以蔽之,虚拟现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如海姆(Michael.Hein)所说的:“电子世界庆祝电路与人类相联合的那一刻,世界展现出一个新的维度,虚拟现实。电话确实在响起,并且,它们所传递的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①Heim M. 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45.,虚拟现实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世界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同时,也给我们提出全新的形而上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