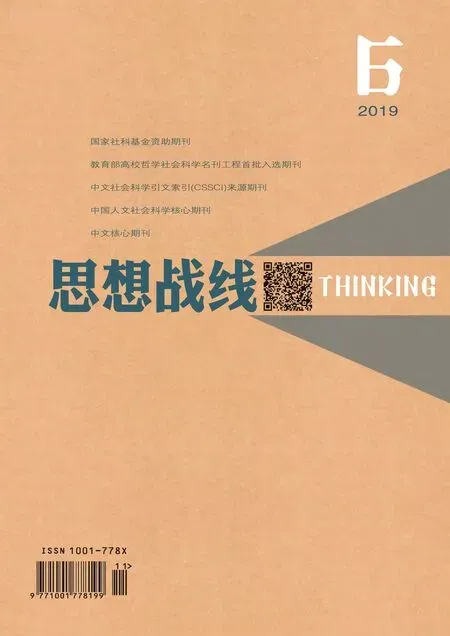空间正义的存在论阐释
——基于马克思的劳动视角
2019-02-18熊小果
熊小果
空间正义,即当前学界讨论的空间正义,是反思空间正义危机①例如,城乡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都市中和区域间的环境压迫、福利差异、空间资源的不公分配、房地产的不健康发展、空间与阶层区隔、社区治理问题、城市权利问题、贫民窟和城中村、种族矛盾等。的理论呐喊,是建制正义具体形态的实践诉求。因此,它在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领域引起了广泛讨论。因为这些讨论偏重于空间正义的具象层面,所以空间正义成为学者们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和一种新方法。②吴红涛:《从问题到方法:空间正义的理论文脉及研究反思》,《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但是,空间正义不仅是一种视角和方法,因为,马克思强调“正义与生产方式相一致”,③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9页。正义与否通常是相对于与之匹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言。④慈继伟:《正义的两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页。作为理论呐喊和实践诉求的空间正义,最终指向人的存在正义。空间正义危机的本质⑤这里,生态正义危机的本质是同人存在危机的道理一样。是人的存在危机。进而,追求空间正义的美好生活、建构空间正义的社会规范是人存在的本质规定。鉴此,必须穿透研究空间正义的视角方法之脉理,以马克思的劳动观审视空间正义的存在论基础,把对空间正义的探析提升和还原到人的存在论场域中,从人的实践存在之本质出发,对空间正义作出存在论阐释。虽然目前学界甚少为之,可这是一项实质性的学理工作。
一、 从正义到空间正义:人对自身存在的“空间立法”
正义和空间似乎互不相关。⑥吴红涛:《从问题到方法:空间正义的理论文脉及研究反思》,《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作为贯穿了整个西方伦理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的正义,⑦龚 群:《正义:在历史中演进的概念》,《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是人在伦理政治领域中努力追求的社会地平线,是人永恒持有的独立概念。空间是摒弃了人主观因素后,绝对化、抽象化、凝固化了的三维形式,①第一,古代西方哲学的原初化经验把空间理解为空虚和处所,他们对空间的感知纯粹是思辨逻辑的。第二,近代西方哲学的科学化经验把空间理解为几何特征。由于受到了英国经验论哲学和欧陆唯理论哲学的影响,科学化经验的空间的几何特征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牛顿为代表,认为空间是绝对的独立的实体;一类以莱布尼茨为代表,认为空间只是事物的关系。而康德的空间观念有意调和二者的分离,认为空间是人认知形式的先验结构。第三,由此可见,空间从单一哲学命题通过科学化过程衍生出数学、物理学等具体的空间形态。他们对空间的感知是形式逻辑的。第四,无论早期的思辨逻辑还是近代的形式逻辑,他们理解的空间都有绝对化、抽象化、凝固化的特征。第五,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身体空间、巴什拉艺术诗学的内心空间、列菲伏尔日常生活的实践空间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个问题。详见李武装《空间对正义的介入和生产——西方哲学的空间发声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批判》,《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不属于主体的存在论范畴。不过,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正义和空间都同人的存在本质深度相关。从正义到空间正义的理论关切和实践拓展,印证了人存在的空间转向。正义对空间的“介入”,不是单纯的方法逻辑之延展或思维观念之建构,而是人存在正义危机的程度加深和范围扩广的产物。空间正义危机是客观事实。越深入考察现代社会的空间正义危机,越明白它不过是人存在必须解决的正义危机的一个新子集。因此,我们从马克思的劳动视角,以正义、空间、人的存在三者间的实质关系为切入点考察这个问题。
(一)正义:人存在的价值追求
16世纪前,哲学家主要在形而上学视域中思考正义。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用神话开启了以人类生活幸福为根本准则的、体现了公正原则的宇宙秩序观即秩序正义。柏拉图把秩序正义伦理化为德性正义。他认为,公民按照自己德性做分内的事就是自己的正义,②[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69页。城邦的公共幸福就是城邦的正义。③[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9页。后来,亚里士多德提出“正义以城邦利益为依归”,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140页。论证了正义得以实现的经济学原则即“比例平等”:“政治权利的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235页。该解释蕴含了正义概念后来的“权利、分配、差异”三项内容。中世纪,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阐释了神学正义观。⑥王柱国:《人权:正义难题的现代解答》,《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及此,“古典”正义还困于形而上学的玄思中,强调其概念的绝对性、独立性、自然性。但正义的道德与政治两个属性已具备。形而上的“古典”正义发展为形而下的“现代”正义是商品交换普遍化的产物,⑦[前苏联]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 昂,张玲玉译,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其内涵的充分展现是17世纪后的事情。⑧因为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人的发现、地理的发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带来了现代市民社会和现代人权(法权)意识。这一点很重要,人对空间的系统化、科学化认知和人对空间变化、空间运动、空间正义危机等问题的自觉反思,也是从17世纪开始成为普遍现象的。正义和空间的内涵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的商品交换时期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自然法正义的基础上,霍布斯、洛克提出以平等权利为核心的契约正义论,生命、平等自由、财产安全是基本人权。在休谟那里,正义发展为分配正义。⑨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 491.罗尔斯将契约正义提升到更为抽象的水平,认为正义包含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平等和分配机会平等,而分配机会平等要以有差别的补偿为操作原则。正义的经济属性和法律属性得到彰显。再后来,正义走向了无力的后现代歧途。艾丽斯·杨、安德森、谢弗勒、舍梅尔等不再强调正义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分配内涵,而是讨论在已严重分化的现实中如何建构人与人之间对称的社会关系。
梳理正义思想史发现,个体与整体如何更好地共存,如何建构普遍的善和分殊的幸福彼此间最大化的价值共同体,是正义关心的根本问题。对正义的探讨始终围绕着人的生活、权利、社会关系,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对人存在的终极关怀,核心关照是“应当”意义上的生存权和财产权。⑩生存权和财产权是空间正义的立论基础。就人的本性而言,生存权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下文会详细论述。正义的困境是人的存在困境,对正义的追求是人存在的价值追求。
(二)空间:人存在的客观形式
严格地讲,整个西方思想均把空间视为人的认知对象。①西方思想史中空间理论的发展概况在前文脚注中已介绍。但空间不仅是认知对象,它与人的存在本身有内在联系。第一,空间是先验式的“物自体”。马克思谈到的“自在自然”即是如此。它的存在同人的存在不发生任何直接联系,但却是人存在的最大环境。第二,空间是“人化自然”。“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8页。人的劳动③这指广义劳动,就是任何形式的实践。始终以一定的空间为前提。这里的前提是指:人的任何劳动都被限制在具体的、既定的、外在的空间中,而非一成不变的绝对实体场域。因此,在历时性过程中,“人化自然”体现为劳动条件的相对性;在共时性结构中,又体现为劳动条件的绝对性。人是历史的剧中人印证了“人化自然”于人存在而言的条件性质。第三,空间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空间及其广延性可以是物质形态的实体,也可以是非物质形态的客观“场域”即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不同于艾丽斯·杨、安德森等论及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印证了人对空间的主体性实践和能动性改造。随着“人化自然”的不断扩大和社会空间的日益复杂,我们应避免机械式、几何式地理解空间概念和空间样态,从而采取辩证式、唯物式的社会化和历史化态度。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劳动。劳动是人存在的本质,空间是人认知和劳动的条件、对象、产物。在人触及的范域中,任何空间都是人存在的客观形式。人的劳动是对自然空间的改造和社会空间的建塑。这是劳动改造自然、社会、人类自身以实现主体价值、从而解放人类的过程。⑤列菲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爱德华·索亚、詹姆逊的空间生产理论不过是突出了劳动实践对象的社会关系层面而已。空间与人的存在以劳动范畴为中介发生内在关联。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既开拓了自然空间,也造就了社会空间,这与人的存在是根本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史也就是开发利用、挖掘创造、生产建构各种空间的历史。⑥庄友刚:《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空间生产、城市发展与人类解放》,《河北学刊》2011年第4期。
(三)空间与正义的交汇:人对自身存在的“空间立法”
正义与空间从平行到交汇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以“主体—身体”为向度的存在论转向。叔本华把主体视为人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立足点。⑦冯 雷:《理解空间》,北京:中央编译局,2008年,第44页。尼采将主体—身体置于权力意志的高度。梅洛·庞蒂顺着现象学存在论路径阐释,空间是连接物体的普遍能力,⑧[法]梅洛·庞蒂:《直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1页。而身体在世界中活动、落脚、并赋予世界以意义。⑨王晓磊:《论西方哲学空间概念的双重演进逻辑》,《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海德格尔把生存场所界定为“此在”,认为它是人本质力量的外显,空间是关联整体状态的、“人诗意地栖居”的、“此在”生存活动中的位置。据此,空间获得了能动的、实践的、社会的解释。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存在论空间观是空间正义危机批判的前身。⑩即现代技术统御下空间生产逻辑的基础。人的存在价值和存在状态在这次转向中实现了发微。但立足于微观身体和感知主体的空间,还属于心理学和美学范畴。寓于身体空间中的正义还只是“隐学”。第二,以“主体—日常生活”为向度的社会批判转向。自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以来,在资本累进式积累逻辑的宰制下,空间压缩和空间加速成为“显学”。⑪⑪详见熊小果《空间生产的资本化与“加速”资本化——基于资本逻辑的历史演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列菲伏尔把日常生活实践、(社会)(城市)空间结合起来,认为人的存在已陷入现代技术和意识形态布控下的空间困境中。基于人日常生活状态提出的空间正义问题正式浮出水面。但列氏的日常生活还是“诗创实践本体论”,①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菲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6年,第358页。与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观并不一样。第三,以“主体—实践”为向度的劳动论转向。此次转向事实上是理论回溯:以大卫·哈维的资本批判和空间哲学为中介,挖掘马克思主体—劳动向度的空间正义思想。②马克思视角下的空间正义,是以劳动正义为基础讨论社会空间中人存在的问题。马克思空间观是实践的和社会的。空间的自由度和全面性为人的自由劳动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切实之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37页。在劳动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平上,社会分工的局限性消失了,由社会分工决定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不正义现象也消失了。因此,空间的正义状态就内在地构成了人个性自由全面之存在发展的实然状态。④阿甘本和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哲学也与空间正义危机和人的存在危机密切关联。
正义与空间的交汇绝非术语拼接,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以来,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主体性反思。正义是人存在的价值追求,空间是人存在的客观形式,空间正义是人对自身存在所努力建构的社会正义的空间形态。它包含了空间的整体状态、空间中的关系结构、正义条件的空间性质。⑤吴红涛:《从问题到方法:空间正义的理论文脉及研究反思》,《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所谓“空间立法”,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基础上的存在形式和主体意识的空间规划,是人对自己存在方式、存在状态的本质关怀,并试图通过社会建制改变空间正义危机现状的活动,是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社会、自身以达到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
当然,把正义和空间、进而把空间正义作为事实提出,这只能是17世纪后资本主义社会肇始的现代现象:资本主义带来了主体意识的觉醒、空间加速且复杂的社会化进程、人异化存在的叠置状态。所以,空间正义的存在论阐释首先要从“反题”方面思考。
二、 空间正义的实存危机:人存在的二歧性状态
以规范为基础的相互性是个人利益与公共规范的交汇点,这是正义秉性的条件性。⑥慈继伟:《正义的两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4~17页。空间正义亦不例外。空间正义的实存危机是异化劳动造成的人存在的二歧性状态:空间的普遍性和分殊性矛盾、集中化和碎片化矛盾。空间正义存在论依据内蕴于此:学界对个人权利的空间诉求和公共权益的空间布局、平等自由和差异公平、⑦所以,罗尔斯正义观的两个原则始终存在争议。空间生产的过程正义和空间分配的结果正义等问题之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争议不休。显然,这与空间正义面临的双重矛盾密不可分。
(一)普遍性、分殊性
人的劳动是以“我的特殊生命和自然界的普遍生命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9页。这句话包含了如下意思:
第一,以唯物主义存在论眼光看,自然空间为整个生命存在和社会发展供给了物质基础。在自然空间那里,所有个体生命活动都带有整体生命的一般性质,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所有生命(整体/个体)都以劳动的方式同自然空间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这也是空间的原初性正义。第二,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是区别于自然空间中其他存在者的类本质,人的普遍性质构成了相对视角下的特殊性质。人的本质就是主体性的劳动。第三,个体生命于整体生命所必然表现出的特殊性质,即阶级、阶层、社群、个体等相互间生存方式的特殊性质。如何开发利用自然空间的普惠价值以实现个体的特殊利益?如何基于个体的特殊利益规划、生产、分配、消费社会空间?这会导致两类冲突。一类是,个体间及个体与整体间的对立。“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的这种两极的关系表现为它们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68页。个体生命的活动方式和利益诉求的彼此对立,造成社会的正义危机,因为这违反了正义的秉性即相互的条件性。另一类是,生态环境、土地资源、山河地理等空间给予人的普惠性价值与人具体的价值诉求、价值实现的具体方式②例如,对不同人的存在意义而言,生态空间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的分殊性对立。这就破坏了空间的原初性正义,也造成了人存在的非正义状态。
同时,空间正义的普遍性和分殊性还有一种颠倒形式的对立。既然“正义包含的首要义务是不损害他人”,③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1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3页。那么空间正义的基本要求亦如此。但事实经常相反,个体和局部基于特殊利益的生产活动造成的空间危机,却要由多数人甚至全人类买单。④例如,空气污染、大气变暖、水污染、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和地理沙漠化、雾霾、生态链和生物圈被破坏、核危机、城市空间危机等。例如,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生态危机的空间转移。⑤例如,输出高污染、高消耗的低端产业和生产生活垃圾到发展中国家(地区),而不是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发达国家(地区)利用先发展的时间、技术、空间、资源优势,假以“正义”之名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实施空间霸权,要求发展中国家(地区)同发达国家(地区)承担一样的空间治理责任。这是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权的剥夺,这是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人的生存权的剥夺。可是,就空间原初正义的普遍性对空间生产具体正义之特殊性的社会历史规定而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量定空间治理责任,才真正符合空间正义普遍性和分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集中化、碎片化
人的生存空间在不断集中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碎片化。这是存在于空间生产和空间分配同一过程的现象,即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内—外”双向重构。一方面,资本的积聚集中从国民体系发展为国际体系,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把非工业化国家(地区)吸纳到世界经济循环的空间中,民族国家(地区)的地理边界、政治栅格空间开始松动和瓦解,去地域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再地域化趋势也很明显。世界一体化既破坏了前现代社会的全球空间格局,又重塑了现代社会不平衡的社会空间,资本的积聚集中空间成为再区域化的地方性经济结构。城市化和郊区化⑥郊区化,亦称市郊化,是指城区范围向郊区扩展,城市人口向郊区迁居的过程和趋势。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城市化的第二个阶段。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大大扩展了人类居住的范围,这是城市空间布局发生这种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其结果造成了城市中心密集的人流和能量开始向城市外围疏散,人口和产业布局向均衡方向发展,并提供了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城市用地。郊区化的第一批受益者往往是城市化的第一批受益者,即富裕阶层。遵循同一逻辑。切记,这个抽象的“内—外”双向空间重构,存在于立体交织的复杂空间结构中的所有层面和节点。
“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中心/边缘’的矛盾来自‘全体/部分’的矛盾,因为所有的全球性构造,都导致集中的中心性的建立。”⑦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5页。人生存空间的有机整体性被分割了,局部空间走向品质对立和景观冲突的碎片化,空间于人存在的公共价值被肢解。空间秩序的等级化,造成了中心对边缘的空间压迫。依照等价交换的形式正义,优质的空间资源,随着资本的积聚集中被配置到局部的空间区域。空间权力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不正义情状时有发生。空间资源“分布不平等是空间差异加剧过程中最明显的结果,这些结果通常产生于众多并常常对立的角色所作的大量个性化决定。在资本主义城市工业化伊始,城市地理就是这样被塑造的,多数都是为了使富裕阶层和权贵阶层获利。……工业资本主义城市更倾向于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发展。”⑧[美]爱德华·W. 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5页。空间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严重不均,空间的碎片化造成了空间利益的冲突,严重损害人生存空间的和谐,局部、个体空间的利益诉求无法实现。显然,这样的空间权益格局违背了正义的内涵,向“最有利者”集中的马太效应是非正义的。
(三)异化劳动:空间正义危机的根源
空间正义危机表明了人空间利益的冲突。任何人的任何空间利益都不可能是抽象空洞的存在,只有在具体现实的关系中,空间权利及其冲突才是真实的。在一切形式的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构成了人存在之所有关系的基本问题,①这里的“基本”不能被替换为其他表述,例如主要关系、核心关系、关键关系。因为,生产关系贯穿了人存在之所有关系并决定着这些关系,生产关系也是人把握自身存在和看待自身存在的根本出发点。在交换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不理解生产关系就不能理解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但是理解了其他关系不见得理解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关系的理解为理解其他任何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是一种经济区别于另一种的本质。这不仅包括决定生产方式的财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也包括如何组织所有权以产生劳动控制形式和产品,以及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②[英]本·法因,[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马克思的〈资本论〉》,王 娟,邱海平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3页。由于,“统治阶级把一切有利于它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东西都宣称为正义,而把一切违反其利益的东西看作是非正义的”,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7页。所以,强调空间分配正义、空间正义的法律形式和道德属性绝非根本,空间正义危机须在人存在的本质中得到解释。因为人的本质关系就是人的劳动关系。
任何公正的观察者都会看到,生产资料越集中,工人也就越集中在同一个空间,工人的居住情况就越悲惨。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7页。这样的集中,一方面造成了英国工业化城市空间布局的极端非正义性,英国工人生存空间的悲惨境遇。脏乱不堪、臭气熏天的工人聚集区挤满了工人,就连猪圈都出租给了劳动者。空间投资、城市规划、工业集中是从资本利润的需求出发,工人生存的人道需要和空间栖居等人权完全被剥夺。另一方面是劳动异化。资本要素及其社会生产的空间集中要求,具体空间中个性化、差异化的具体劳动,从属于总体空间中同质化、抽象化的总体劳动。总体性的生产空间,按照资本逻辑对丰富的现实空间进行具体抽象。⑤吴耀国:《从“价值的空间”到“空间的价值”——〈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与空间意识》,《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劳动空间和劳动主体的同质化,成为全球性空间景观。⑥这就是资本积累所谓“刻板规范”的“福特主义”。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弹性灵活”的“后福特主义”。其实,后福特主义是精致的福特主义,是数字化的现代工业生产。因而从生活到生产,人的一切劳动活动异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人的劳动活动本身均异化了。死劳动压迫着活劳动,发展和解放性质的劳动异化为压迫的、物化的工具性力量。人逃避劳动就像逃避瘟疫。人存在的形式同人存在的本质对立,人的本质与人的实践相矛盾。从物质到精神、从自然到社会,人都为资本生产的空间所奴役。
三、 空间正义的立论基石:人存在的实质性权利
空间正义存在论阐释的“正题”应这样“破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奠定了人权的社会基础和人存在的本质基础,“人权源于人的本性”。⑦李步云:《论人权的本原》,《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人权依据的是存在论意义上(非法律、政治、道德意义上)人本质具有的权利,人的个性自由的劳动构成了人的类存在本质,也就是人权的根本要义。因而,正义是人存在的价值追求,进而人权也就是正义的终极依据。由此,空间正义的立论基石自然是空间人权。
空间人权是人权的空间投射,是空间化和具象化后的人权,即依据人性/人的本质,对空间进行主体性、价值性、对象性活动的权利。空间人权要求“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第166页。所以,空间人权确认了,人与空间的实践关系在人存在的本质维度得到了天赋人权式的规定,指认了一切空间非正义现象是违背人性的实质论断。通过空间人权概念,空间正义与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存在论关系。
笔者认为,空间人权既不是、也不能是空洞抽象的。它包含了很多具体方面,①例如,居住权、管理权、参与权、活动权。这些方面可以归结于城市权和财产权两个基点。前者是空间人权的应然核心,后者是空间人权的实然条件。
(一)城市权:空间人权的应然核心
第一,什么是城市权?城市权是处于首要地位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个性选择权利,居住的权利,进入城市、参与城市管理和支配财富的权利。②Don Mitchell,The Right to the City: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 New York and London:Guilford Press,2003,p. 18.大卫·哈维和爱德华·索亚强调,③[美]哈维:《叛逆的城市》,叶齐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页;Edward W. 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p. 6.个人和集体为城市发展、寻求空间正义进行的改造与斗争的权利,也可以说,这是人的主体性和基本权利在空间向度和对待空间问题上的具体展开。④陈 忠:《主体性的微观走向与空间权利的城市实现》,《哲学动态》2014年第8期。以生产劳动、改造参与为具体内容的实践活动是理解城市权的关键词。在马克思的劳动论看来,实践是建构关系和获得权利的根本途径。当城市权不为人(既是具体的个人,也是普遍的集体)所掌握、而为资本利润所指挥时,人的劳动就异化了,空间正义危机就出现了。出于人的存在需要,城市权必然要求人有生产、分配、交换、使用、选择空间及相应要素之一系列权利。宏观层面,它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生态化阶段,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暗含了人类未来的解放途径。城市权与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权利相统一。微观层面,它根植于人的个体尊严、存在价值,表达了具体生命和家庭对日常生产生活、社交往来、自我发展的基本权利诉求。因此,城市权关系到城市空间中人的主体资格、实践能力、生活状态等人之存在的基本方面。
第二,为何是城市权?城市权之所以是空间人权的核心,是因为空间问题的关键和集中点都是城市,“城市是一种综合性的关系存在,是人的社会性的一种空间化实现,权利关系是城市的基本关系。”⑤陈 忠:《城市权利: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逻辑上,人的空间活动始终同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是一体同时的,但空间正义危机事实始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其理论自觉源于列菲伏尔对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思考。据此,空间人权的核心当然是人的城市权。经验上,一方面,城市空间是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的聚集地,是资本积累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的本质就表现为聚合经济所带来的空间优势。”⑥唐旭昌:《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各种形式的货币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庞大的脑体劳动力、大量的自然资源、大多数的劳动产品集中于城市,农村衰落但城市兴荣。人集中在城市,人的关系和权利当然也集中在城市。另一方面,随着人的关系和权利在城市的集中,人生活于城市中的一系列空间问题和空间权利诉求也在城市中爆发。在农业生产工业化、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分化为剩余利润的食利者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之今天,我们可以说,与人生产生活相关的所有问题即人存在的各种问题都笼统地表现为城市问题。⑦学界讨论的所有的空间正义危机都是城市空间危机,包括一切形式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演变为人的城市权。
(二)财产权:空间人权的实然条件⑧
⑧按需分配的社会,无需“产权”。因为,产权表明的全民所有制度在非私有制社会中,是无所谓产权归属的。
财产权必须为空间人权提供保障。没有财产权,空间人权便是枉然,寻求空间正义的运动就会沦落为资本的镜像。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在城市建设和空间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因而造成了人栖居空间之糟糕的人权状况,一切为资本而规划、一切为资本而生产、一切为资本而消费。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资本化,彻底否定了空间人权指向的空间正义,也彻底否定了人的本真性存在。“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困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赚钱多,花钱少。”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8页。人本质的严重异化,人存在状态的极度恶化,高度资本化的城市空间“几乎必然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9页。土地资源、水、森林资源、空气、阳光等自然空间平等给予人的资源被商品化、资本化,继而造成“地理景观同时也表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③[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页。马克思援引赛·兰格《国家的贫困》一书的典故,解释财产权对空间正义、空间人权的重要性,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8页。表明了财产权是空间人权的实然条件,是实现空间正义的坚实基底。
既然人权是人人享有的平等生存与自由发展的权利,那么把人权引入空间正义就成空间人权的实质内核,即在空间生产、分配、消费等社会活动中,应当为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平等、全面发展而提供空间条件的权利保障。生产决定分配意味着,包括空间人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都很好地说明了,现代私有制是以人与生产资料(土地空间、劳动工具)相分立为事实基础导致的空间正义危机。后果是,人自由劳动权被剥夺、人劳动的异化、人非本质的与非正义的存在。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存在本质不再直接表现为社会化的,而是物化的劳动关系,正义只是市场的交易原则。“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8页。土地空间的过度资本化不仅造成了生态危机,也造成了高额的地租、房租、房价。“巴黎房地产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纯粹的金融资产,一种虚拟的资本形式,它的交换价值被整合到一般的资本流通当中,完全支配了使用价值。”⑦[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其实,现代人努力挣钱买房就是要获取栖居空间的所有权。所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页。才是真正践行空间正义的理念,才是空间人权的实现。
四、空间正义的高阶建构:人存在的超越性实践
一般而言,市场化、全球化的生产和交往就是人劳动的社会化。这是重塑自然空间、开掘社会空间的历史活动。马克思把人类发展阶段同社会空间模型联系起来,划分了三个基本形态:非独立的对人的依赖性社会、人独立的对物的依赖性社会、人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联合体社会。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人的存在经历了从孤立到区域、再到世界的空间化过程。人的存在空间及其样态与人的存在本质是一致的,与人的劳动状态是一致的。“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929页。时间是人发展的空间。只有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非生存手段的自由王国,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科学、艺术、公共事业、社会建构才能获得长足的和正义的发展空间。空间正义的高阶建构在这里才真正开始,人存在的超越性实践本能在这时才彻底释放。
当然,在化解空间正义危机方面,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应当思索,社会主义空间正义事业的可操作路径与带有超越性质的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理念应该有些什么。
(一)空间正义的建构主题:主体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之所以追求正义不仅仅是为了规范和控制主体的行为,而是为了使每个主体都能获得发挥创造性的机会,拥有生活的意义,促进其全面发展。”①何建华:《经济正义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人存在于日益人化的空间中,人只能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来发展自身。建构空间正义必须以主体性和主体的生活意义、存在价值作为重要主题。空间是人主体性存在和社会性纽带的场所,是主体居于其中的、具有生成能力和生成性源泉的母体,正如苏贾所言:“人类空间性的所有形式与表现是由社会产生的。……我们造就了地理,好或者不好,正义或者非正义。……在由过去的社会—空间形成过程和当前由长期的历史、社会构成的地理所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环境中,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②[美]爱德华·W. 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强乃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9页。空间正义不仅要为每个人所享受,还要由每个人来创造,为每个人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开辟道路。
(二)空间正义的建构基础:人的空间生产力发展
相对于空间分配正义而言,空间生产正义是其“第一内涵”,这符合空间人权和社会制度的一般规定。所谓“空间生产力”就是人利用空间、开发空间、改造空间的物质生产能力。③卢嘉瑞:《论空间生产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空间生产力概念由生产力概念衍生而来。生产力概念内涵了人与自然空间的物质信息交换的内容。因此,空间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也就体现为人对利用空间、开发空间、改造空间能力的提高。学界广泛讨论了我国存在的空间问题,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现状,成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障碍。因此,发展空间生产力既是总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也是合理解决一系列空间问题、扎实建构空间正义所必须的物质前提和能力基础。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三)空间正义的建构路径: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
如何进行正义化的空间建设属于操作层面,涉及很多具体政策措施。④例如,城乡规划、乡村振兴、国家中心城市、区域协调发展、交通道路管理、社会治理、市容市貌改造、河流治理、城市新区建设、户籍制度改革、主题公园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建构空间正义须找到一条科学合理的路径。该路径要以制度的形式为空间规划、改造、生产做出原则性规范,即制度的公正和差异相统一的规范。这是人性的体现和人权的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这一原则的根本保证。“无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53页。通过制度规范,空间正义实践才能找到普遍价值与个体价值、局部空间与整体空间、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物质与精神、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点,从而彰显主体性与整体性、多样性与共同性的差异性统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曾批判过,在按需分配实现以前那种不承认事实差别的所谓平等权利的伪善性,因而建构“差异性和多样化为核心的空间”⑥张 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是实事求是的路径。
(四)空间正义的建构目标:空间正义的自我超越
以马克思劳动理论为基石的空间正义,既含有存在论性质的批判和建构,还具备存在论性质的超越。从霍布斯到罗尔斯,正义始终囿于规范性补救措施,而“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超越正义的理想,因为正义是对抗的平衡,而共产主义是对抗(生产关系/阶级对抗——引者注)的消除”。⑦王南湜:《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一种可能的建构》,《哲学研究》2018年第5期。马克思洞察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生产和消费资料在人之间的分配还不得不按照资产阶级权利进行,即实行商品等价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则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写在旗帜上。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306页。即便个体生命的存在是非至上性的,然而整个人类存在的终极使命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消除一切有违自由王国秉性的非正义现象。所以,空间正义的建制目标是,为了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除了空间非正义现象,也就无所谓正义与否了。新的概念范畴会作出更为贴切的表述。这便是超越了空间正义的空间正义,是空间正义的自我超越。
(五)空间正义的建构契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空间正义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契机。这为解决空间正义危机问题供给了思想指导和实践指引,铺垫了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空间正义之远大理想的坚实基础和关键环节。在理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空间正义具有内涵上的科学一致性与价值上的认同互通性。空间正义危机的根源是资本积累逻辑统治下的异化(非正义)劳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对该种空间非正义的反拨和修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尝试探索一条全新的空间正义发展之路,促进人类的平等自由与个性全面之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①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在实践中,一方面,“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社会、地区国家均不可能单独应对各种形式的空间正义危机问题,只有全人类携手共同努力,才能彻底克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全球空间非正义问题、建构人类永久正义空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新思考和新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实现人类自我解放事业的高度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