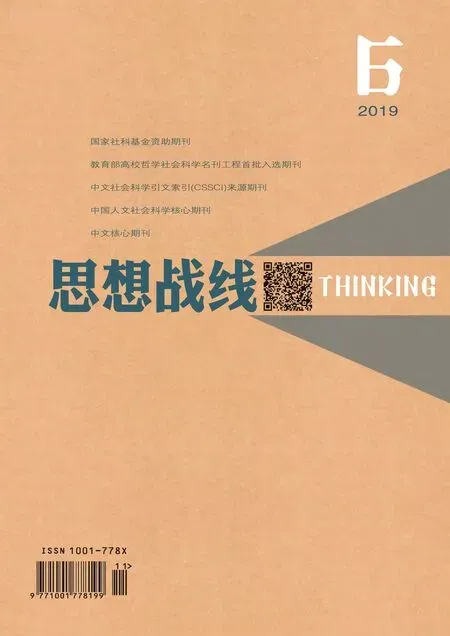第二人称叙述者如何叙述?
——论小说的第二人称叙事
2019-02-18谭君强
谭君强
一
小说类的叙事虚构作品,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故事讲述”,即便扩而广之,将叙事文本的范围扩大到由不同媒介构成的各种文化产品中,其核心依然是其中必须包含“讲述故事”①[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这一基本条件。而讲述故事必定存在着故事的讲述者,即叙述者。在当代叙事学对叙事文本的研究中,不将这样的讲述者或叙述者归为作者本人已成为常识。从讲述行为来说,叙述者在叙事文本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这样的叙述者居于“文本内(文本编码)最高层次的讲述位置上”。②Uri Margolin,“Narrator”1. In: Pater Hühn et al(eds.).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URL=http://www.lhn.uni-hamburg.de/ [view date 18 Jun 2019].在种种叙事作品的讲述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叙述者,因而,对叙述者及其区分是叙事学研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而叙述者的区分又因不同的参照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从上述对故事与故事讲述的基本条件出发,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区分为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同故事叙述者与异故事叙述者、人物叙述者与非人物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可以区分为内隐的叙述者与外显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可以区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等等。③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9页。所谓外显与内隐,是相对于故事讲述时的叙述者而言;而可靠与不可靠,则是就故事讲述中叙述者相对于隐含作者所显露的价值、判断和态度而言,因而,说到底都与故事讲述有关。
还有一类叙述者的区分,与上述区分不同,这就是从人称所进行的区分。这样的区分由来已久。1973年,多勒泽尔在《捷克文学的叙事模式》一书的导言中,对叙事模式进行了分类。叙事模式的核心关涉叙述者,在对叙述者的这一分类中,第一与第三人称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多勒泽尔以三项标准将叙事模式归类:其中,第一项便是故事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讲述。在多勒泽尔确定的6种叙事方式中,其中3种是第三人称的变体,3种是第一人称的变体。①Lubomir Doležel,Narrative Modes in Czech Literature.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3,pp.3~13.这种按人称进行的区分,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与研究中也十分普遍。
然而,按人称进行的故事讲述者来区分,尽管表面看来一目了然,实际上却疑窦丛生。《小说修辞学》的作者——美国修辞叙事学家韦恩·布斯对此便持保留态度。在布斯看来,小说中人称的区分可能是运用得最为过度的区分。他认为:“说一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讲述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更为确切地描绘出叙述者的特性如何与特定的效果相关联。”②Wayne C.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150.布斯的判断自然有其道理。不过,无论对这一区分肯定也好,保留也好,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从人称进行的叙述区分,在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中依然运用得十分广泛,影响甚大。因而,有必要从表面的区分入手,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厘清真实状况,获得更为本质的认识。
在按人称进行的叙述区分中,主要是相对于第一和第三人称叙事,大多未关注第二人称叙事。从创作的实践看,后者在叙事作品中出现甚少,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下面将在对第一和第三人称叙事和叙述者探析的基础上,探讨第二人称叙事及叙述者问题。
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或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在小说叙述从人称进行的区分中广为人知。按照一般的看法,中外传统的叙事作品,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至19、20世纪之交开始的现代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越来越多地被运用。所谓第一人称叙述者,即叙述者“我”的讲述,这一叙述者可以外在于所讲述的故事,成为异故事叙述者;也可作为所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既参与故事中的行动,又进行讲述,成为同故事叙述者,或者说人物叙述者。相对而言,在考量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一概念时,虽不无问题,但引起的歧义相对较少。这类叙述即所谓“我—叙述”,尤以叙说参与故事的人物叙述者“我”的经历为基础的叙事作品中表现为多。
第三人称叙事这一用语使用得十分广泛。按照这一类别所划分的叙事作品在数量上、尤其是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而,第三人称叙事这一概念本身容易产生诸多让人迷惑的问题。就这一概念本身而言,所谓第三人称叙事或“第三人称叙述者”,并不是指叙述者在讲述中以第三人称出现,以“他”或“她”的身份和口吻来讲述。如美国叙事学家阿波特所说,第三人称叙事指的是叙述者并非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是将人物指涉为第三人称:“他做这个”,“她说那个”。在阿波特看来,由于第三人称叙述者在涉及自身时只能以第一人称指涉,因而,第三人称叙述者或第三人称叙事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区分。③H. Porter Abbott,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96.换言之,第三人称叙述者在故事的讲述中,只能将人物指称为第三人称的“他”“她”或“它”,而不能将叙述者指涉为“他”或“她”,叙述者自身必定还是“我”,只能是“(‘我’叙说):‘他’如何如何”。这就显出“第三人称叙述者”这一概念和用语天生的悖论与缺陷。米克·巴尔认为,根据叙述者的“声音”而被称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小说,其“叙述主体总是‘第一人称’”。“一个叙述者并不是一个‘他’或‘她’。充其量叙述者不过可以叙述关于另外某个人,一个‘他’或‘她’”。巴尔最终的结论是:“‘我’和‘他’都是‘我’”。④[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8页。由此可见,第三人称小说叙述,永远不可能出现语法上的第三人称“他”或“她”说故事,而只能是隐含地表现为“我”说……。因而,严格说来,所谓第三人称小说叙述是不存在的。从语法上来说,它不过是隐含的“第一人称”小说叙述。
二
在上述基础上,下面将转入第二人称叙事与第二人称叙述者的探讨。第二人称叙述者讲述的叙事又称为“你—叙述”(you-narratives)或“你—文本”(you-texts)。从文学叙事作品的实践来看,以第二人称“你”作为叙述主体的情况相当有限。在叙事作品中,第二人称叙述者出现得最晚,在作品的数量上也最少。莫妮卡·弗鲁德尼克指出,在欧洲文学中,尽管第二人称“你”叙述远在17世纪、甚至15世纪便可发现个别的例证,但作为后现代叙事技巧的一种新策略,它是在20世纪之交以后才出现在数量日增的叙事作品中。①Monika Fludernik,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9,p.113.这类叙述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各有不同。按弗鲁德尼克所说,在英语和西班牙语文学中,第二人称“你”叙事作品较为常见,而在德语文学中则十分罕见。②Monika Fludernik,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9,p.50.
在中国传统的叙事作品中,第二人称“你”叙述难觅踪迹。从人称叙述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小说绝大多数是所谓第三人称叙事,参与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十分罕见。当然,偶尔的例子仍可寻到。比如,早在7世纪的唐人传奇中便出现了此类第一人称叙述者。张鷟的《游仙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游仙窟》全篇从开头到结尾皆以“余”或“下官”自称,以第一人称之口讲述一个人物叙述者自己参与其中的艳遇故事。不过,这类叙述状况毕竟十分有限,“除了唐人传奇以外,后来的白话长、短篇小说也没有出现过第一人称的小说”。③何满子,李时人:《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页。至于第二人称小说,则绝无仅有。其原因不言自明,与中国传统小说的现成和叙述状况密切相关。如我们所知,中国的传统小说是在说书人即说话人话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唐代已有讲说恋爱故事和三国故事的说话了(说话就是讲故事的意思)”。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23页。宋代的白话小说,就是在这些民间艺人的手里创造、发展、提高而来的。“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人话本,都是当日说话人的底本。说话的借此谋生,……创作的目的,要迎合市民的趣味,要满足市民文娱的需要。”⑤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22~723页。说话人直接面对听众,模拟故事中的叙述者讲述故事。可想而知,这样的叙述者在面对自己的听众时,不可能将作为自己说话对象的听众假设为故事的讲述者,也不可能将听书的对象转为在故事中行动的人物。这样的叙述传统在以后的小说发展中一直延续,影响着此后中国小说的叙述构成机制。
在当代的小说叙述中,第二人称叙事主要是后现代先锋叙述的产物。在以第二人称叙述者讲述的作品中,法国作家米歇尔·布托尔195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变》是出现较早、也是最早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之一。《变》自问世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评论文章铺天盖地,获得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文学奖给它打开了面向读者的大门”。⑥[法]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1900年以来的法国小说》,陆亚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6页。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莱昂·台尔蒙是意大利一家打字机公司巴黎分公司的经理,作品采用第二人称“你”,讲述了作为“你”的台尔蒙在星期五从巴黎乘火车前往罗马,以和他的情人赛西尔共度周末的情景。小说自始至终以“你”作为叙述者,同时以这一叙述者指代故事中的人物台尔蒙。作品的开篇是:“你把左脚踩在门槛的铜凹槽上,用右肩顶开滑动门,试图再推开一些,但无济于事。”“你”这一叙述者的叙述贯穿始终,一直延续到结尾:“你在里昂车站买的那本小说至今还未打开,它一直放在长椅上,在你座位的左方。你把它挪到你的座位上,让它替你占座。”⑦[法]米歇尔·布托尔:《变》,桂裕芳译,载柳鸣九编选《新小说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79页、第444页。
《变》以新颖的形式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注意。但是,采用第二人称叙述者的叙事作品大多都处于一种试验状态中。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出现,却始终处于读者和理论家的质疑中。针对《变》这一作品,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指出,运用第二人称叙事的努力从来都不是很成功的。在谈到《变》开头的叙述时,他认为这一开头确实显得“极不自然,让人一时感到迷惑”。同时,他也注意到:“让人吃惊的是,即便作了(第二人称)这一选择,实际的差异也如此之小。”⑧Wayne C.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150.换句话说,他并不将《变》的第二人称叙事看作是小说叙述的一种根本性变革。
在诸如《变》这类的第二人称叙事作品中,处于阅读状态中的读者除了感觉新奇之外,会发现自己很难在这一叙述状况下进行流畅的阅读;同时也会发现,可以很容易地将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你”改换为第一人称的人物叙述者“我”,或直接以第三人称的“他”“她”来指代人物。在布托尔的《变》中,甚至可以直接改为人物“台尔蒙”,这些改换并不影响故事的展开,也不影响作品的阅读效果。这样的直觉感受出现在布托尔的《变》中,也出现在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依塔洛·卡尔维诺的第二人称叙事作品中。比如卡尔维诺1979年出版、引起一时轰动的小说《寒冬夜行人》。这部作品的开头是这样的:
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请你先放松一下,然后再集中注意力。把一切无关的想法都从你的头脑中驱逐出去,让周围的一切变成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不再干扰你。门最好关起来,那边老开着电视机。立即告诉他们:“不,我不要看电视!”如果他们没听见,你再大点声音:“我在看书!请不要打扰我!”也许那边噪音太大,他们没听见你的话,你再大点声音,怒吼道:“我要开始看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了!”哦,你要是不愿意说,也可以不说;但愿他们不来干扰你。①[意]依塔洛·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萧天佑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页。
这个将要开始阅读的“你”,按卡尔维诺所说,实际上就是作品的主人公,他十次开始读一本书,而这书由于一些与他的意愿不相关的周折而未能结束。一直到小说结尾,他也没有读完,还得“再等会儿”,才能“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②[意]依塔洛·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萧天佑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页。
我们说,任何叙述,都是一种交流行为,这种交流行为的过程,表现为信息的发送者发出信息给信息的接受者。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离不开相互依存的对象“我”和“你”,或“我们”和“你们”,即便这一交流出现在同一个人的独语中,在自我与自我的交流中也同样如此。在自我交流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看作合二为一的同一对象,表现为“我”与“我本人”之间的一种内在交流。在小说中,这一与现实生活对应的、由信息发送者向信息接受者发送信息的交流过程同样存在,它具体表现为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向叙述接受者、或者说受述者(narratee)发送信息的一个交流过程。可以确定的是,在任何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不可或缺,受述者也同样不可少:“至少有一个(或多或少公开地表现出来的)受述者,处于叙述者向他或她讲述的同一叙事层次上。”③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Revised Edition.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57.换句话说,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公开的也好,隐含的也好,分开的也好,合为一体的也好,受述者如叙述者一样,在叙事文本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我们将第二人称叙事中的叙述主体、即叙述者视为“你—叙述者”的话,那么,“你—叙述者”在向谁叙说呢,换句话说,与“你—叙述者”相对应的受述者是谁呢?比如,在像《变》和《寒冬夜行人》这样的叙事文本中,受述者在哪里呢?第二人称叙述者“你”在向谁叙说呢?我们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于找到其中的受述者。哈里·E.肖在谈到受述者时说到,将受述者限定在客观可观察的信息范围内的效果会更富有戏剧性。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受述者应该是某文本的被具体描绘的接受者,可以感觉到叙述者在向其叙述;受述者不可能仅仅是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心目中存在的一个人物。这样就会有两种类型的受述者。一种会出现在框架故事中,其中,一个人物担任叙述者向另外一个人物诉说,后者因此而成为受述者。另外一种则出现在某个人物,突然向另外一个具体的人物诉说的时候”。④[美]哈里·E.肖:《我们的术语为何不会固定不变?叙事交流示意图的细读与历史化》,乔国强译,载[美]James Phelan,Peter J. Rabinowitz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 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6页。这两种类型的受述者在《变》和《寒冬夜行人》中都没有出现。在这两部小说中,作为叙述主体的“你”实际上并不是在从事叙述,它不过是一个被叙述出来的称为“你”的人物。说得更直接一些,第二人称叙述者“你”本身是无法进行叙述的。作为被叙述出来的人物,“你”在乘坐火车,“你”在阅读一本小说。事实上,对第二人称叙事的一个定义便是“故事的主人公由代词你指涉”。⑤David Herman,Jahn Manfred and Marie-Laure Ryan,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552.不言而喻的是,在人物“你”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叙述者,将“你”这一人物叙述出来。这样一来,通常应该是作为接受信息的受述者(受述者可以表现为人物,也可以不现身),在这里变成了人物。
按照普林斯所说,叙事作品中的人称涉及叙述者(与受述者)和所讲述故事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其中的叙述者同时是其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一个人物;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不是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一个人物;而在第二人称叙事中,受述者是“所讲述的情境和事件中的主要人物”,①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Revised Edition.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72.这一受述者甚至可以“成为故事中被他或她讲述的主人公”。②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Revised Edition.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86.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叙事文本中,受述者已经成为被讲述的人物,甚至成为主人公了。这样一来,被讲述的人物或主人公便与受述者在形式上合而为一,我们自然就难于发现单一的受述者究竟在哪里了。与此同时,也就有理由将被讲述出来的人物或主人公背后的叙述者推导出来。
既然受述者已成为人物,甚至是主人公,那么,作为故事讲述人的叙述者何在?叙事文本中的交流过程,源自于叙述者与受述者的交流循环过程,前面提及,这一过程可以发生在人物自我交流的内心独白或独语中。而在第二人称叙事中,只能将这样的交流看作叙述者和受述者/人物合二而一的内心自我交流,也就是说,讲述的“你”成了进行内心交流的主人公。在布托尔的《变》中,“你”本应该是受述者,然而在这里,“你”却成为主要人物,成为主人公台尔蒙的代指。在这里,可以认为在“你”背后存在着一个居于“文本内(文本编码)最高层次的讲述位置上”的叙述者。这种叙述状况与通常所理解的第三人称叙事并无根本区别。另一种情况,如果将“你”视为叙述主体、看作是叙述者的话,那么,叙述者只能是一个第二人称“你”人物叙述者,这个“你”人物叙述者所起的作用与第一人称人物叙述者十分类似,属于所谓同故事叙述。由此可见,在第二人称叙事中,主人公或人物可以与叙述者相分离,也可以与叙述者相同一。这样,“第二人称故事可以是同故事的(主人公与叙述者相认同),或者是异故事的(主人公与叙述者不同)”。③David Herman,Jahn Manfred and Marie-Laure Ryan,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p.552.这种情况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可以参与故事、也可以不参与故事,因而成为同故事叙述者或异故事叙述者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布斯在谈到阅读布托尔《变》的开头时说到,让人吃惊的是,读者很快便被吸引到故事的幻觉“表现”中,“将自己的眼光与那个‘你’的眼光完全等同起来,就像与其他故事中的‘我’或‘他’等同起来一样”。④Wayne C.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150.而在《寒冬夜行人》中,作者卡尔维诺自己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他是一个‘你’,而任何人都能在这个‘你’中认出他自己的‘我’。”⑤[意]依塔洛·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萧天佑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页。也就是说,读者在第二人称叙事这一叙述状况中,很容易会坠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叙述状态中去。无论从理论或阅读实践中,都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情况,即第二人称叙事从叙事的类别来说,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种类,它与其他的叙述状况互相交叉与重叠,充其量可以称为其他类型,尤其是第一人称叙述“我”作为人物叙述者这一类型的一个亚类型。
三
人称代词“我”和“你”,以及与“他”“她”“他们”等相互对照,本身并无意义,并不涉及外在于其说话的情境。只有将它们置于一定的叙述交流状况中,方可显现出各自特定的地位与意义。如尤里·马戈林所说,当叙述者在其语境中运用“我”和“你”这样的标志时,这些标志就在他现时的讲述角色中自动地指涉他,以及他所描摹的叙述接受者,这样的叙述接受者,是正在进行的交流活动中的参与者。⑥See Uri Margolin,“Narrator”22,In: Pater Hühn et al(eds.). 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Hamburg:Hamburg University,URL=http://www.lhn.uni-hamburg.de/ [view date 18 Jun 2019].
任何交流行为,包括出现在叙事文本中的交流行为,都必定存在着交流的主体与客体,而“只有当讲话是指向第二人称时,语言才能够履行其交流使命”。①[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页。因而,每个说话人都由“我”完成,并向一个“你”讲述。正是这一讲述的主体确认了作为说话人的“我”。从根本上说,任何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叙述、抒情或论说行为,都只能由“我”来承担,都只能出自于“我”之口。从作品的文学主体来说,这一“我”是作者自身。就这一意义而言,所有叙事、抒情或论说作品,无论其中出现的叙述者或抒情人以何种人称表现出来,都只能由第一人称“我”、即作者本人来承担。
撇开作品的文学主体不说,从语法的主体来说,任何叙事、抒情都只能由“我”来进行,只能出自于“我”之口。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人称叙述者就显得合理而自然,而第三人称叙事与叙述者不仅显得悖理,而且从语法主体上也说不通。至于第二人称叙述主体就更是如此。我们可以用表现出叙述话语状态的简单陈述句为例,对第二人称叙述主体作探析。就以布托尔《变》和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中的话语作为例子:“你把左脚踩在门槛的铜凹槽上”“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从语法主体的状况来说,上述叙事文本所出现的,无外乎是这样一种表现,即“(我说):你把左脚踩在门槛的铜凹槽上”,或“(我说):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这就是第二人称叙事文本实际的叙述状况。不论是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事,其中的叙述主体总是“第一人称”,“就人称代词而言,叙述者总是‘我’,即便我们涉及的是第三人称小说或你—叙事文本。”②Monika Fludernik,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32.
叙述行为有着自身的运行机制,而“话语施事行为是以一定的方式‘起效’的”。③[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9页。从产生文本话语来源的叙述施动者(narrative agent)的角度看,如果叙述者作为叙述施动者的话,产生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在这里,叙述施动者与叙述者统一在第一人称“我”这一叙述主体中,文本话语的来源是可靠的,其中所展现的人物的活动也很容易接受。马戈林认为:“如果作为叙述施动者的是叙述接受者的话,那么就产生第二人称叙事。而叙述者话语所指涉的实体并非当下交流状况中的一方的话,那么就是第三人称叙事。”④Uri Margolin, “Narrator” 22. In: Pater Hühn et al(eds.). The 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Hamburg:Hamburg University, URL=http://www.lhn.uni-hamburg.de/ [view date 18 Jun 2019].这里,马戈林所进行的是一种逻辑推断。实际上,单一的叙述接受者是不能成为叙述施动者的,因为叙述施动者应该是叙述中的“动原”,一个“履行行动或行为的人或人格化存在;一个行动并影响事件进程的人物”。⑤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Revised Edition.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4.叙述行为本身也同时被包括在行动之内。“发出话语就是实施一个行为”,而一个话语行为的实施,“必定会对听者产生效果”。⑥[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赵京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页、第109页。单一的叙述接受者无法形成“动原”,也无法单独实施话语施事,因为它是接受信息发送的一方,除非这一叙述接受者同时成为一个人物,一个在文本中活动并对事件进程产生影响的人物。
经典叙事理论所界定的叙事通常“围绕着故事世界里已经发生和完成的事情展开”,即所谓回顾叙述,其中,“讲故事行为就是实话道出讲述者所知之事的行为”。⑦[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91页。这样的叙事主要是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展开的,它所显示的故事通常带有确定性与封闭性,指向特定的结局。而在当代叙事作品中,那种将一切已发生之事在叙述者的编织下娓娓道来、并指向确定结局的叙事方式,或多或少受到了冷落,与之相应的是观察方式的某种改变。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观察方式是与被叙述事件同时进行的所谓“同步叙述(‘现在时叙述’)”,以及预示式(未来时叙述)、条件式与祈愿式等。在这样的被叙述世界中,带有更多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因为在这里,“被叙述世界是一个形成过程,在被叙述的过程中逐渐显现,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体”。⑧[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9页。这种叙述方式不仅表现为一种后现代叙述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当代人对未知世界探寻的意愿,对更为直接的交流的渴望,对自身参与叙述世界创造的求索,以及对被动地接受一个确定的叙述世界的抵触。
从《变》和《寒冬夜行人》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的同步叙述与预示式叙述。后者在开篇的第一章出现的是:“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到第二章则以这样的叙述开头:“你看这本小说已看了三十来页,渐渐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可是读到某个地方时你发现:‘唉,这句话一点也不陌生,甚至整个这一段都好像看过。’很明显,这是主题的重复,小说就是由它的主题的反复而构成的。”①[意]依塔洛·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萧天佑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6页。在以后的章节中,也常常提及主人公“你”阅读这本书的进程和他的各种感受。
大多数第二人称叙事都以同步叙述的方式进行,这种情况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叙事作品中,读者通常会将自己置于叙述者的位置,从叙述者的角度去观看和接受被叙述世界,而这种情况,在第二人称叙事中表现得尤甚。对于所有的第二人称叙事来说,读者只有把“你”既看作当前叙述活动的受述者,也看作叙述事件过程的主人公,才能使假扮游戏进行下去。“如果事件和行动与正在展开的叙述和接受过程同步或并列,读者就更容易自然地进入主人公的角色”,并进一步加强情景的直接性和迫近性,“让人仿佛觉得读者就是假扮游戏的参与者,应该由他决定下一步轮到什么事件”。②[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由此可见,带有现代意味的小说同步叙述,恰恰在第二人称叙事中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对第二人称叙事与叙述者的辨析,不仅可以探讨这一类小说叙述的实际状况,以及其产生与发展的某些原因,而且可以由此厘清普遍盛行的所谓第一与第三人称叙事的本质状况,从而有利于我们对小说叙述与叙述者这一重要问题的理解。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就第二人称叙事而言,其中并不存在单纯的“你”或“你们”叙述者,纯粹的第二人称叙述者是不能叙述的,这样的叙述者缺乏作为叙述施动者的“动源”。如果将第二人称叙述者“你”理解为一个人物的话,那么,就存在着一个将其叙述出来的、居于更高位置上的叙述者,一个外在的、异故事叙述者,这与所谓第三人称叙事相似。如果将作为人物的“你”与叙述者相认同的话,那么,可以将这样的叙述状况看作人物叙述者的同故事叙述,这与所谓第一人称叙述相似。因此,作为一种叙述类型,第二人称叙事可以说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