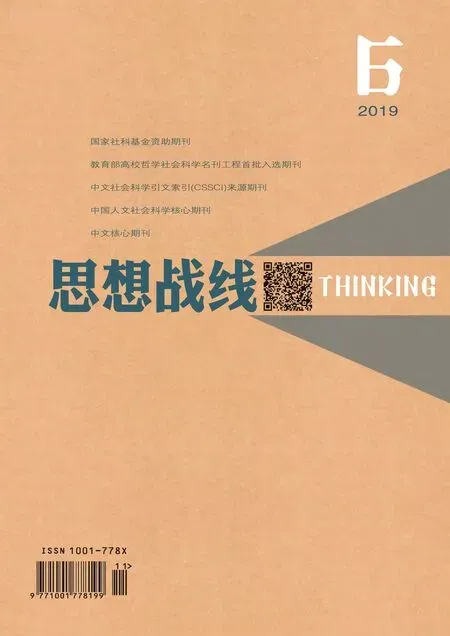使石头具有石头性:“物”与陌生化叙事理论的拓展
2019-02-18唐伟胜
唐伟胜
一、“石头性”与陌生化理论
谈及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引用最多的无疑是下面这段话:
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①[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这段话已经成为了陌生化理论的标签,但凡讨论陌生化理论,几乎都会无一例外地引用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1929年发表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中的这几句话。然而,在翻译这个原文是俄语的著名段落时,尤其是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делать камень каменным)这个关键表述上,不同译者/论者又有或多或少的变异,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他们理解什克洛夫斯基,乃至整个陌生化理论的差别。比如,在一篇批判陌生化理论的文章中,基本接受“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这一译法,只是对个别字词做了改动,成了“为了使石头变成石头”。②孙绍振:《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批判》,《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而在讨论陌生化美学效果如何产生的论文中,引用三联书店出版的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的译法,将“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译为“使石头具有石头性”。③梅子满,黄素华:《论“陌生化”美学效果的产生》,《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再如在讨论陌生化理论的变化时,将“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译成“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④杨建刚:《陌生化理论的旅行与变异》,《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纵观国内所有对陌生化理论的研究,会非常遗憾地发现完全缺失了对“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这一关键表述的讨论,更没有对不同译本及其内涵进行的比较。笔者认为,在以上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中,“使石头变成石头”最值得商榷。这个说法似乎暗示了艺术应该对石头进行忠实的、现实主义式的描写,而这正是陌生化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所极力反对的。“使石头显示出石头的质感”明显更好,它紧承上文的“体验生活”“感觉事物”和下文的“可观可见”,体现了陌生化理论对具体(而不是抽象)和体验(而不是认知)的偏爱。但“质感”似乎过于强调人类体验中的触觉,而忽略了视觉、听觉等,难免过于狭窄。相比而言,“使石头具有石头性”则更具概括力,暗示艺术要让读者感受到作为语词的“石头”之外的神秘属性,从而实现陌生化效果。
事实上,陌生化理论非常强调艺术和“物”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物”构成了陌生化理论的核心所在。首先,陌生化理论(乃至整个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点就是,将艺术从现实主义的反映论和象征主义的神学论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物质实体”。①张 冰:《陌生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2页。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在此不需多论。其次,在陌生化理论的建构过程中,理论家们多次使用“物”来做喻。比如,那句著名的“(艺术)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就使用“旗帜的颜色”来与艺术世界进行比较。在论述陌生化能让我们对生活产生全新的感受时,什克洛夫斯基使用的例子之一是“舞蹈”,并将其定义为“感觉到了的步行”。②[美]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樊锦兴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6~7页。此外,他在讨论托尔斯泰的陌生化手法时,认为其效果来自于“他不说出事物的名称,而是把它当作第一次看见的事物来描写”。③[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2页。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文字显示的那样,陌生化理论把“感受到物的存在”,“使石头具有石头性”上升为艺术的根本宗旨,而实现这个宗旨的办法是“将事物奇异化”。换句话说,艺术的目的是超越日常语言及其引起的自动化联想,让事物陌生起来,让读者得以直接面对事物,从而获得艺术之感受。因此,陌生化理论其实包含了双重任务:首先是要用陌生化的语词或叙事技巧,使“物”从人们对它的无意识反应中突显出来,使之在场于读者的思维;其次是要让读者对“物”产生陌生化的感受,从而加深对“物”的认识。如果说前一个任务主要发生在语言表述层面,后一个任务则势必发生在语言的内容层面。但是,为了急于撇开与现实的联系,陌生化理论高调宣称,陌生化的效果直接来自诗歌语词或叙事形式的陌生化,与其表达内容无关,于是产生了内部逻辑矛盾,引起批评家的不满,有人甚至称陌生化理论是“粗疏”的。④孙绍振:《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批判》,《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我们当然可以回到历史现场,考察陌生化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然后对这一内在矛盾赋予“同情的理解”;⑤杨向荣:《陌生化重读:俄国形式主义的反思与检讨》,《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也可以“从美学和政治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陌生化理论”,⑥杨建刚:《陌生化理论的旅行与变异》,《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对其进行反思和补充。但本文将不纠缠于陌生化理论的内在矛盾,也无意于将陌生化理论的内核从文本内拓展到文本外,相反,本文承认陌生化理论的基本前提,即艺术的宗旨是让读者感受物的存在,“使石头具有石头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考察这个前提对陌生化理论意味着什么,以及在当代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和面向“物”的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等“物理论”(thing theory)的观照下,如何拓展陌生化理论,使“石头”走出与人类的关联,让读者感受其更加陌生的存在,或更深的“石头性”。
二、思辨实在论与面向“物”的哲学
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文学批评领域,对“物”及其本体存在方式的探讨,是过去10年的学术热点之一。就哲学领域而言,2007年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首次使用的“思辨实在论”成为了这一热点的代名词。思辨实在论是欧美近年兴起的一个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昆丁·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雷·布雷希亚(Ray Brassier)、利维·布赖恩特(Levi R. Bryant)等。2011年出版的《思辨转向:大陆唯物论与实在论》(The Speculative Turn: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一书,汇聚了该理论核心人物的主要思想。虽然这些哲学家的理论框架多样,甚至相互矛盾,但思辨实在论最重要的一个靶子就是梅亚苏所谓的后康德“关联论”(correlationism)。关联论要么否认“物”自体的存在,要么认为“物”自体处于人类理性之外,根本无法认识。在通向“物”自体的道路上,关联论总要凸现人类中介的作用,从而搁置本体论,转向认识论。20世纪出现的很多转向,包括语言学转向、符号学转向、叙事转向、认知转向等,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关联论”思维方式的结果,因为这些“转向”共享一个理论预设,即客体不可认知(或者根本不存在),客体不过是语言、文化、叙事或思维的建构。这种“建构”立场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本质主义偏见,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实在的客体的关注。对客体而言,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和操控,其结果是让我们无视客体的存在,而单方面地突显人类作为认识主体的重要性。思辨实在论则意在克服或绕开关联论陷阱:它相信“物”自体的存在,因此是“实在的”;它相信通过想象(而非理性)可以抵达“物”自体,因此是“思辨的”。这样,思辨实在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最大限度摆脱人类理性框架的局限,去探索实在的“物”本体世界。当然,思辨实在论追求的“实在之物”(real object),有别于之前认为人类可以完整把握“物”世界的“幼稚实在论”(naive realism),是更为复杂的“物”本体存在方式。在通向“实在之物”的道路上,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重点,甚至不同的立场。比如,梅亚苏、①Q. Meillassoux,After Finitude,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New York:Continuum,2008.布雷西亚②R. Brassier,Nihil Unbound:Enlightenment and Extinc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7.旨在想象没有人的“广大世界”(the Great Outdoors)的模样,认为“物”的存在前提是偶然性和非理性,哈曼③G. Harman,Tool-Being: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Chicago:Open Court,2002.的重点是指出“物”自体的无穷尽性,认为“物”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都无法穷尽“物”本身。而伯古斯特、④I. Bogost,Alien Phenomenology:or 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2.布赖恩特⑤Levi R. Bryant,Onto-Cartography:An Ontology of Machines and Media,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4.等则将重点放在对“物”的运作、“物”与“物”互动关系的描述上。但无论如何,思辨实在论者基本都会同意如下观点:(1)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去除人类至上的观念,人和“物”处于同一本体地位;(2)“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生命及活性;(3)在抵达“物”的过程中,人类要充分想象,超越理性,忘掉自我。由此可见,思辨实在论总体上很符合“后人文”的精神旨趣,试图从本体上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但又有自己的诉求重心,包括追求人和“物”的平等、追寻“物”的本真、突破人类理性极限等。
哈曼的“面向物的本体论”是思辨实在论最重要的分支之一。面向“物”的哲学试图解决“物的实在性到底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一问题,它首先承认“物”具有实在性,但是,这个实在性隐退于人类或其他“物”的认知。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的理论或实践,还是“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无法穷尽物的现实,因为“物”“拒绝任何形式的因果或认知把握”。⑥G. Harman,“The Well-Wrought Broken Hammer:Object-Oriented Literary Criticism”,NLH,vol. 43,no. 2,2011,pp.183~203.当人们以为已经完全认识或把握某“物”的时候,“物”会通过“坏掉”(broken)这样的方式来彰显其深不可测的现实。哈曼提出了“四面物”(quadruple object)这一概念,认为“物”有四个面向,即“实在的物”(real objects)、“感性的物”(sensual objects,相当于胡塞尔的意向物)、“实在的特征”(real features)和“感性的特征”(sensual features),⑦G. Harman,The Quadruple Object,Winchester,U.K.:Zero Books,2011.这四个面向之间永远存在鸿沟和冲突。其中“实在的物”与“感性的特征”之间的冲突最令人着迷:比如铁锤坏掉之时就正好体现了“感性的特征”与“实在的物”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而这种鸿沟的出现就是一种诱惑(allure),间接地指向“物”的真相。哈曼认为,“诱惑是所有艺术,包括文学的核心现象”,①G. Harman,“The Well-Wrought Broken Hammer:Object-Oriented Literary Criticism”,NLH,vol. 43,no.2,2011, pp.183~203.也就是说,艺术旨在通过揭示或运作“实在的物”和“感性的特征”之间的冲突关系,来诱惑读者瞥见“物”的深不可测的实在性。不难看出,陌生化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一冲突基础上,因为陌生化理论认为,“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②[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1页。换句话说,艺术就是通过恢复或刷新物的感性特征,让读者得以感觉到“实在的物”。为了让读者感觉到“物”的存在,首先必须让“物”进入读者的意识,陌生化理论探讨的重心即在于此:如何通过不同于常规的语言来让“物”陌生化,使之对读者的思维在场。然而让读者意识到“物”的存在,仅仅是陌生化的第一步,揭示出“物”异乎寻常的感性特征——不仅对人类,还包括对其他“物”,才能让读者真正瞥见“物”的那些不同于我们日常认知的、怪异的(weird)实在性。③Harman认为,物的现实是无限隐退于人类认知的,人类对物的任何知识都不是物的终极现实,他用“怪异的”(weird)一词来描写物的实在性。G. Harman,Weird Realism:Lovecraft and Philosophy,Winchester,U.K.:Zero Books,2012.
三、陌生化理论的实质:让“物”对读者在场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写出著名的“让石头具有石头性”那个段落之前,讨论了诗歌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的差异,认为后者遵从节约规律,能够简化就尽量简化,到最后日常语言所表达的事物“会枯萎”,“只以某一特征出现,如同公式一样导出,甚至都不在意识中出现”,随后他引用他最喜欢的作家托尔斯泰的日记来证明,“许多人一辈子的生活都是在无意识中度过”,这种生活“如同没有过一样”,“自动化吞没事物、衣服、家具、妻子和对战争的恐怖”,接下来就是那个著名段落:“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④[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11页。
很明显,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艺术的陌生化,其实质是将事物从自动化反应中解脱出来,使之对读者的意识在场,让读者“看见”它,“感受”它。当然,什克洛夫斯基的下一个结论,即“看见”和“感受”本身就是艺术的最终目的,至于“看见”和“感受”什么则并不重要,引起了学界广泛争议。本文认为,“看见”和“感受”的内容与引发“看见”和“感受”的形式同等重要,因为它们都是陌生化体验的重要成分。但是在这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各种陌生化形式背后的洞见和局限。
陌生化批评家们尤其注重对诗歌形式的系统研究,而本文拟重点讨论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陌生化叙事散文理论。什克洛夫斯基没有对叙事散文的陌生化形式提出系统理论,只是零散地讨论了散文叙事中的陌生化手段。总体来说,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这些手段通过“阻滞和延缓”,⑤[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3页。打破读者对叙事的自动化反应,从而,对情节或所再现的事物产生陌生化感受。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思想与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工具存在论”(tool-being)颇有相似之处。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看待周围事物(比如铁锤)的时候,都倾向于将其看成实现我们意图的工具,眼里只有正在从事的建筑工作,而铁锤本身并不对我们在场。只有当铁锤坏掉(broken)之时,我们才会面对铁锤自身,并惊讶铁锤原来还有很多工具之外的属性。因此,坏掉的铁锤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面对作为“物”(而不是工具)的铁锤,并瞥见它深不可测的、隐藏的现实。⑥G. Harman,Tool-Being:Heidegge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Objects,Chicago:Open Court,2002.同样,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是日常语言的自动性遮蔽了物对读者的在场,为了恢复物的在场,就要打破正常的语言形式,让语言像海德格尔的铁锤一样“坏掉”,这样,读者就可以用一种陌生的方式,直面作为“物”的文学语言及其再现的世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理论,根本目的是让读者面对“坏掉的”语言,从而对世界获得陌生化的感受,其重心并不在于让读者通过“坏掉的”语言来看到世界的本相:我们最多可以说,陌生化理论感兴趣的,是通过一种异常的语言表述,让读者看到或体验到被日常语言遮蔽的世界,但它并不关心这个世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疏漏,因为,最彻底的奇异或陌生感,恰恰发生在我们与世界的真相相遇的瞬间。
例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的奇异化手法在于他不说出事物的名称,而是把它当作第一次看见的事物来描写,描写一件事则好像它是第一次发生”,从而,把“司空见惯的”事物奇异化了。①[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2页。不让叙述者直接说出事物的名称,而是用无知的视角来对事物进行透视,可以有效切断名称蕴含的规约意义,从而让“物”显示出其奇异的原真状态,这种写法在中国文学中也屡见不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小说借用她无知的眼光对挂钟进行的描写:
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似的,却不住的乱晃。
这里的描写,将挂钟与其指代意义之间的规约关系中解脱出来,显示出它的部分“物”性。但陌生化理论显然并不关注这个具有原初意义的“物”性,更没有深入思考它对陌生化感受的巨大潜力,而仅仅是提出这种拒绝使用直接指称的手法可以带来陌生化感受,但这种陌生化感受势必是短暂的,肤浅的,读者并没有因此看见挂钟的更深刻的现实。再比如,什克洛夫斯基论述道,“有一次,(托尔斯泰)由一匹马出面来讲故事,于是事物被不是我们的,而是马的感受所奇异化了”,“这就是马对私有制的感受”。②[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2页。诚然,由非人类来充当叙述者,容易给读者带来奇异化的感受,但非人类叙述者不一定都能带给我们奇异化的感受。实际上,我们孩童时读过的很多童话故事都是由动物来叙述的,但这些被拟人化的动物无论在语言使用还是思维习惯方面,与人类并无两样,因此,它们叙述出来的世界其实很难给我们陌生化的感受。什克洛夫斯基在这里援用的例子也是一样。在他引用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读者仅仅是以一种陌生化的视角了解到私有制的荒谬之处(读者也许早已通过其他方式了解),由马来讲述的私有制依然是人类眼中的私有制:读者既不能通过这里的叙述了解私有制的实在性,也不能了解马的实在性。由此可见,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叙事理论重点关注的是陌生化叙述手段,以及这种手段如何让读者摆脱对物的自动化联想,从而感知到物的存在。也就是说,什克洛夫斯基关注的是通过特殊的叙述手段,让“物”走进读者的意识。很明显,这个陌生化效果的研究项目还远未结束,在当今“思辨实在论”和“面向物的哲学”等理论的观照下,我们可以关注叙述手段如何让读者通过看到物的更多“感性特征”,尤其是超越“人类—物”这一关系中的“感性特征”,体验到奇异的“物”本身,从而获得更大的陌生化感受。
四、拓展陌生化叙事理论:陌生的石头性
如前所述,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叙事理论的核心是让读者感受到“物”的存在,但更大的陌生化不只是看到“物”,而是看到“物”隐藏在我们日常意识之外的“物”性。换句话说,文学不能满足于让我们看到石头,还要让我们看见“石头性”,即石头到底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意味着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叙事理论需要拓展和深化。作为一个尝试,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拓展:(1)消除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中的人类理性痕迹,使“物”超越人类对它进行的镜像式和象征式表征,进入自在自为的真实界;(2)突出“物”的灵性和主体性,使之反作用于人类和叙事进程。这两个方向的拓展都能让读者感受/发现更陌生的“物性”。
(一)“无人的/去人化的”叙述
为了再现无限隐退的“物性”,让读者瞥见陌生的、实在的“物”,叙述声音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人类痕迹,突破拉康意义上的“镜像”和“象征”再现方式,以进入“真实界”。叙述视角也可尽量去人化,让物显示其自身隐秘的特性。如前文所述,用马或其他任何动物(或无生命植物)来讲故事,然后通过拟人化操作,把人类的语言及其携带的理性赋予它,这不过是为人类叙述者找到一个替代者,叙述的依然是人类意识,不能让读者真正看到真实的世界。同理,用刘姥姥的眼光来写挂钟,虽然可以使挂钟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但这段叙述的效果主要是让读者对刘姥姥形成某种反讽的印象,而不是揭示挂钟的真实所在:挂钟还是我们认知中的挂钟,只不过无知的刘姥姥不认识而已。换句话说,这里的叙述并没有显示出陌生的“挂钟性”。与此相对照,美国作家尼克·芒特福特(Nick Muntfort)的《2002:一个回文故事》(2002: A Palindrome Story)仅2 000字左右,没有任何有形的叙事者,也不产生任何连贯的意义,近乎一种文字游戏:小说从前面开始阅读与从结尾开始回读几乎一模一样,完全对称。①Nick Muntfort,2002: A Palindrome Story,spinelessbooks:http://spinelessbooks.com/2002/palindrome/index.html,24-10-2019.这是一种真正摆脱了人类中介的叙事声音,抛弃了语言与其意义之间的镜像式和象征式关联,突显了语言的物质性(materiality)。当然,除了回文这种叙述方式,还有伊恩·伯古斯特提及的“列举”(listing)和“清单式本体书写法”(inventory ontography),也可用来描绘人类意义被抹去后的“物”世界,因为这种“只列举不解释的方式类似哲学,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物”。②I. Bogost,Alien Phenomenology:or 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2, p.45.此外,还包括布赖恩·史蒂芬斯(Brian Stefans)讨论的数字、文字集、句法和结构的递归等。③B.K. Stefans,“Terrible Engines:A Speculative Turn in Recent Poetry and Fic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 51,no.1,2014,pp.159~183.所有这些方法都旨在突破“人类—事物”之间的关联,试图揭示“物—物”之间的“感性特征”,从而让读者获得一种更为深沉的、关于“物”之本性的陌生化感受。克里斯多夫·布鲁(Christopher Breu)在《物的坚持:生命政治时代的文学》(2014)一书中强调“物”对语言和文化赋意的反抗,并将其视为他定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物性文学”的核心特征,他讨论了美国作家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如何在其《裸体午餐》(Naked Lunch, 1959)中使用“真实界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Real),来宣告“物性的”创伤式回归。④C. Breu,Insistence of the Material: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Minneapolis:U of Minnesota P,2014.本书中,Breu定义的“真实界的语言”特征包括打乱正常语法、切断语言连贯性和指称性等。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不可命名》(The Unnameable) 的叙述者更有意思:其叙述者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而是随着时空、位置、话语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多变的形状。⑤E. Effinger,“Beckett’s Post-Human:The Ontopology of The Unnameable”,Samuel Beckett Today,vol. 23,no.2,2011,pp.369~381.这种“物”叙述者在不同的时空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对世界也会产生不同的观察,透过这样的“物”叙述者,读者可以观察到其“物”性、身体性,以及它叙述出来的世界的物质性。
即使不用“物”叙述者或打破正常语法常规的“真实界语言”,文学叙事也有办法将奇异的实在世界呈现给读者。当代美国生态作家瑞克·巴斯(Rick Bass)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巴斯表面上是透过人类眼光来讲故事,但在他的笔下,充当视角的人类几乎没有人类特征,这种“去人化的”(dehumanized)眼光仿佛带领读者走进原初的自然世界。在巴斯发表于2000年的小说《洞穴》(The Cave)中,拉塞尔(Russell)和他女朋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赤身裸体地进入到一个50米深的废弃地下矿井。在这个洞穴里,两个人完成了去人性化过程,⑥E. Hash,“Adventure in Our Bones:A Study of Rick Bass’s Relationship with Landscape”,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Vol. 2,no.1,2015,pp.385~391.然后依然赤身裸体地回到现实世界。当然,此时他们眼中的世界已经与进入洞穴前的世界大为不同了,他们仿佛回到了人类史前时代,能看见的只有草木丛生的大山、湿漉漉的灌木丛、带有绿叶的树枝、枫香树、山毛榉、橡树、山核桃树、母鹿和小鹿,不知道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前的太阳。这里列举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然之物,与他们在地上爬行、摘吃草莓的动作结合在一起,让读者全然忘记他们作为人类的特殊存在:他们完全融入到自然中,与自然中的万生万物没有任何等级差异。饶有兴趣的是,巴斯此时让他们与一头母鹿和小鹿不期而遇,两头鹿“一跃而起,惊恐地看着他们好半天,没有认出他们是人类,最后它们摇着尾巴,慢慢地走进了树林”。①R. Bass,“The Cave”,in Paris Review,vol. 156,no. 4,2000,pp.145~160.在这里,人类和鹿相互对望,互不打扰,然后各自前行,作者没有让动物屈服于人类眼光之下,也没有借用动物的眼光来观照人类,这种人类和动物相遇却不相扰的场景,仿佛将读者带入了理性人类还未出现的、陌生的原真状态。②唐伟胜:《谨慎的拟人化、兽人与瑞克·巴斯的动物叙事》,《英语研究》2019年第10辑。
(二)“灵性/力量物”叙述
讲述陌生的“物”的故事,除了使用“无人的”或“去人化的”叙述手法之外,还可以赋予“物”以灵性,让物在读者(或人物)的意料之外显示出灵性或力量,从而实现陌生化的叙述效果。如果说,“无人的/去人化的”叙述主要是通过让“物”逃离人类表征的控制,从而让读者感受其陌生的原真状态的话,那么,“灵性/力量物”的叙述则具有陌生的反转效果:人类不仅不能影响或操控“物”,反而被有灵性和力量的“物”所影响或操控。比如,劳拉·格鲁伯·戈弗雷(Laura Gruber Godfrey)在其专著《海明威的地理:亲密感、物质性与记忆》(2016)中,考察了海明威叙事中的“地方”如何动态地承载历史文化和记忆,作为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地方”如何影响人物的活动以及海明威的文学想象。③See L.G. Godfrey,Hemingway’s Geographies:Intimacy,Materiality,and Memory,New York:Palgrave,2016.再比如,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1839)中,男主人公罗德里克·厄舍被描绘成既有理性,又相信万物有灵,而厄舍府里的一草一木都仿佛具有某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长期离群索居地生活在神秘的物世界里,罗德里克的理性一点点被蚕食,最后亲眼看到自己妹妹的尸体也显示出活性,终于受惊吓而死。这样,《厄舍府的倒塌》的文学性就体现在它描绘了一个陌生化的场景:在这里,人类理性被神秘邪性的“物”击败,而不是相反。④Tang Weisheng,“Edgar Allan Poe’s Gothic Aesthetics of Things:Rereading‘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Style,vol. 52,no. 3,2018,pp.287~301.再如,美国著名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早期作品《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1937)中,那位名叫鲍曼(Bowman)的旅行推销员开始被描写为一个无法融入世界的流浪汉,后来却与一家农户夫妻产生了情感交流的欲望,而推动人物发生变化的正是“物”:鲍曼的车失控掉进沟里时,他发现车掉进一大团葡萄藤中,葡萄藤“接住它,抱着它,摇着它,就像黑色摇篮中一个奇怪的婴孩”,然后“轻轻地把它放在地上”。⑤E. Welty,“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in Robert DiYanni and Kraft Rompf,eds.,The McGraw-Hill Book of Fiction,New York:McGraw-Hill,Inc.,1995,p.1039.目睹南方无处不在的自然之物的温柔包容,鲍曼似乎感受到了“物”友好的力量,这无疑在某种意义上减少了他与世界的疏离感,因此,才愿意敞开心扉与农家夫妇进行情感交流。这样阅读《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影响人物行动并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力量来自于“物”,⑥唐伟胜:《早期韦尔蒂的地方诗学:重读〈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这无疑会增强读者的陌生化美学感受。
五、结 语
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建立在对“物”的陌生化语言再现,以及读者对“物”的陌生化感受的基础上。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叙事理论提出,可以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比如避免使用直接指称和非人叙述视角等,让虚构世界得以陌生化。然而,陌生化叙事理论的核心,不过是想通过陌生化世界来让世界在场于读者的思维,却没有探讨如何让读者看到世界真相的叙事机制。思辨实在论,尤其是面向“物”的哲学,认为“物”有存在于人类感知之外的真实,艺术的奥秘在于通过描写“人类—物”二元对立之外的“物”的感性特征,让读者瞥见在人类感知之外的“物”的实在性。受这一新近才在西方兴起的哲学思潮的启发,我们可以将陌生化叙事理论往前推进一步,探讨叙事如何讲述“物”的实在性。本文尝试性地探讨了“无人的/去人化的叙述”和“灵性/力量物的叙述”两种陌生化叙述手法:前者旨在呈现存在于人类眼光和语言之外的陌生的实在“物”,后者旨在揭示具有灵性和力量的“物”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类。两种方法均不再局限于仅仅把陌生的“物”呈现给读者,而是努力去探索人类语言和文化表征之外、真实存在、具有主体性的“物”世界。这样呈现出来的“物”世界,无疑会带给读者更具冲击力、更深刻的陌生化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