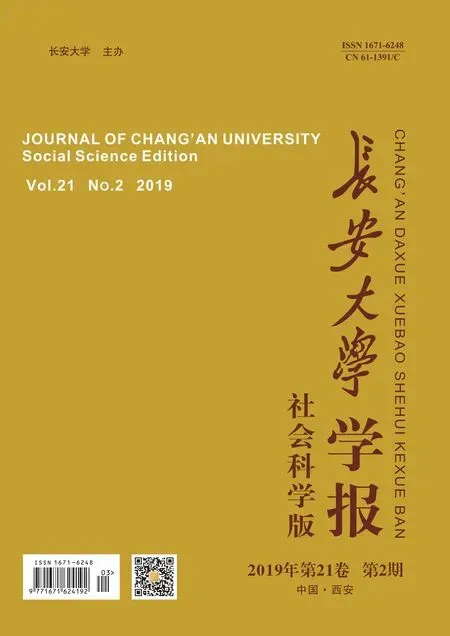国际贸易与劳动失业研究
2019-02-16余淼杰梁庆丰
余淼杰,梁庆丰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在各种贸易谈判和关于贸易开放的争论中,失业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注]Davidson et al. (2004)指出,在2002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被访者被提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导致美国流失工作岗位还是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工作岗位”,45%的受访者选择了前者,相比之下只有24%的受访者选择创造出更多的新岗位。当被问到“美国政府应该限制进口以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还是降低贸易壁垒以使民众有更多的消费选择和更低的价格时”,55%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贸易壁垒可以保护美国的就业岗位,他们宁愿支付更高的价格。。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学家才在国际贸易模型中大量地引入劳动力市场的不完美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同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贸易开放及相关政策是否导致失业上升。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此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理论是一种研究资源配置的微观理论,而失业现象属于宏观经济的研究范畴[注]Krugman (1993)指出,失业是一种宏观问题,在短期取决于总需求,在长期则取决于自然失业率,进口税收这样的微观政策基本不会对失业率造成影响;Mussa (1993)也发表过相似的观点,即经济学家认为贸易保护政策并不会影响经济整体失业率(Employment of domestic resource),而是影响资源在生产性活动间的分配。;第二,1970~1990年,解释失业的微观模型才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1]。大多数理论模型都指出贸易开放会影响均衡的失业率,但是影响的方向莫衷一是,而实证论文的检验结果也各不相同。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作铺垫。
一、理论文献梳理
(一)国际贸易中的最低工资模型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主要有3种方式将失业纳入研究框架。第一种是将最低工资引入国际贸易模型中,其中Brecher是最早将最低工资纳入H-O模型中研究失业的文章之一,论文研究了采取最低工资制度的某国开放国际市场带来的劳动就业水平和经济整体福利的变化。论文证明了如果最低工资制度在封闭经济下是紧约束性的,那么,第一,若本国的专业分工不完全,则开放贸易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和整体福利的下降;如果本国的专业分工完全,则开放贸易可能(并非一定)导致失业率上升和整体福利下降。第二,若本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且专业分工不完全,外国对本国出口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本国就业和福利水平下降。第三,国际上不拥有(拥有)垄断力量的国家,其最优关税并不一定是零关税(加征关税)。在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后,论文对福利和最优关税的考察与经典模型的分析结论出现分歧,这也是该文作者强调应该在国际贸易模型中纳入失业因素的重要原因[2]。
Davis的模型设定为两个国家,其中一个国家采用灵活工资制度,另一个国家具有最低工资限制。该论文的研究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特点: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加大,但是失业率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很多国家虽然工资收入不平等没有加剧,但是失业率一路持续上升到两位数。美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个显著差别就是欧洲大陆很多国家拥有强大的工会及最低工资,而两者共同之处是受到了相似的外部冲击——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进程。在以上的模型设定和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论文得出的结论十分丰富:第一,当世界上只有欧洲和美国两个贸易国时,美国的工资水平会被抬升至欧洲水准,而欧洲的失业率会比封闭经济时有所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市场会进一步提升欧洲失业率;第三,欧洲的最低工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所受到的冲击程度;第四,美国移民(Immigration to America)提升了美国的工资,降低了欧洲工资并提升了欧洲的失业率[3]。
Harris et al.用最低工资的方法研究了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下的失业[4],Krueger在其基础上将此分析框架拓展到开放经济中,深入考察了开放经济背景下的城乡差异,并指出城市最低实际工资的提升将引起城市地区资本密集度上升,甚至会引起城市地区要素密集度逆转,城市地区雇佣劳动力减少[5]。
(二)国际贸易中的效率工资模型
第二种方法是将效率工资引入国际贸易模型中。Shapiro et al.做了效率工资模型的奠基性工作,他们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厂商倾向于提高工资(高于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工资)来诱使工人提高努力程度,这有利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也造成了失业[6]。Matusz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两部门(两个部门工资不同)、两要素的模型来分析贸易政策对就业结构和就业量的影响。研究认为,对高工资部门的出口补贴将导致劳动力由低工资部门向高工资部门转移和总体就业水平的下降;而对低工资部门的贸易保护会提高各部门的实际工资和总体就业水平[7]。Matusz融合了效率工资模型和Dixit-Stigliz的垄断竞争模型,考虑的最终品由多种中间品复合生产,其中生产函数的设定使得中间品种类的增多会带来专业化生产的优势[8]。因此,贸易开放带来中间产品的增多,使得国内工人的实际工资具有上升的趋势,从而放松了效率工资的限制,最终带来就业量的上升。
(三)国际贸易中的搜索模型
第三种方法是将搜索模型引入国际贸易模型中。Davidson et al.假设经济中有两个部门和两种生产要素。这两种生产要素是两种类型的工人,某种类型的工人必须找到另一种类型的工人才能进行生产,否则将处于失业状态。模型的结果表明,均衡时失业总是存在的[9]。进一步地,Davidson et al.将这种方法推广到开放经济以研究国际贸易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个资本密集型大国和资本密集型小国进行贸易会导致总失业的上升[10]。
2000年之后的研究更多沿用的是Pissarides的搜索模型,例如Dutt et al.将这种搜索模型分别引入H-O模型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来解释贸易和失业的关系。论文指出,贸易影响失业机制是由两种不同的比较优势模型所决定:如果贸易由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型所刻画,那么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失业的降低(一个简单的理解是贸易提高了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实际工资,所以人们倾向于投入更多资源去搜索工作岗位,提供了匹配成功的概率)。但是如果贸易模式更接近H-O模型,那么只有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失业率才会下降,而劳动力稀缺的国家失业率反而会上升。虽然这种H-O模型结论支持了发达国家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观点,但是随后的跨国实证检验表明,在样本中,所有国家的贸易开放度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稳健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将Pissarides搜索模型引入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中更为合理[11]。
Felbermayr et al.也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失业率的结论,且都是通过促进效率实现的,但是Felbermayr et al.另辟蹊径,将搜索模型引入Melitz的企业异质性理论中。Melitz模型表明贸易开放会筛选出高生产率的企业,而低生产率企业会自动退出市场,经济整体的生产率会得到提升[12]。因此,Felbermayr et al.认为随着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职位空缺的相对成本就会降低,雇主会在招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社会整体的职位空缺与失业人口的比例就会上升,最终降低失业率[13]。
二、实证文献归纳
因为理论文献众说纷纭,对现实世界中国际贸易和就业市场实证检验的结果就显得更加重要,同时也更加有趣(正如Davidson et al.指出的,贸易是否影响均衡的失业率首先是一个实证问题[1])。下面按照跨国研究和单独国家的研究进行分类归纳。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国际贸易和失业率之间关系时,学者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失业率的数据可信度存疑(notoriously unreliable),且其测量误差和影响失业的经济因素存在系统的相关性;第二,当一个国家遭受失业的冲击时,政治家们通常用高筑贸易壁垒来应对,这会导致开放程度和失业率之间的负向伪相关(a negative spurious correlation)。
(一)跨国研究
跨国研究的代表性研究如下:Krueger 研究了10个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和就业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量的提高,纠正要素市场扭曲、减小贸易保护力度在较长时期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5]。
Schumacher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欧洲6个发达国家(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和比利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彼时,此欧洲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呈现整体均衡的态势,欧洲六国还存在少量贸易盈余。研究结果证明,从总体上看,这6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对就业总量影响不大。以1977年欧洲六国的数据为例,1977年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了2.7%~4.5%的就业量,而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使得就业量减少了0.9%~1.7%,因此净效应甚至为正。除此之外,Schumacher分部门考察了就业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他发现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会导致欧洲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就业量下降,而资本密集型就业部门就业有上升的趋势,就业结构发生了改变[14]。
Scarpetta研究了OECD国家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其失业率的影响,研究背景是作者发现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间,美国和日本的失业率没有明显的趋势,然而欧洲的失业率却上升明显,而且即使在经济复苏期间,失业率也一直维持在高点,且失业人口中长期失业的比例由33%上升到45%。研究发现,遭受外部冲击时(例如国际市场开放时),更高的失业救济保障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且能降低劳动力市场遭受冲击时的调整速度。此外,失业保障倾向于提高均衡时的失业率,同时会提高长期失业的比例[15]。
与大多数短期实证研究结果不同,Felbermayr et al.认为长期内贸易开放会导致更低的结构性失业。考虑到Balassa-Samulson效应,论文度量某国开放程度的变量并非常见的名义进出口占名义GDP的比例,而是用实际进出口(用和美元的汇率折算)和实际GDP(用和美国PPP折算)之比来度量。论文分别研究了OECD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其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不可靠(不同来源的数据相关性很低),论文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稳健性检验。研究认为,从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并没有提高结构性失业,而且在多数模型设定下,贸易自由化反而会降低结构性失业[16]。
(二)单独国家的研究
跨国研究的一个通病是不同国家在基本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往往不能用回归方程中的变量加以控制。近年来,研究单独国家的失业情况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越来越多。
研究发展中国家贸易与失业之间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是:Attanasio et al.采用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贸易自由化前后的劳动力市场调查结果,结合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下的产业数据,发现尽管整体的失业率有提高的可能性,这种提高是由不可贸易部门驱动,而非制造业这种可贸易部门推动的[17]。沿袭Attanasio et al.对产业的分类研究,Hasan et al.对印度的贸易和失业情况进行了研究,考虑到印度各州对经济强大的干预权、区域间受管控的劳动力流动、各州较大的经济体量,该文将失业研究细化到印度各州的层面。根据印度外贸自由化前后各州工业组成的变化以及各产业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来构造衡量各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研究发现,从州的层面看,去除贸易保护后,平均而言各州的失业率和开放前贸易保护程度没有关系;然而具体到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更加灵活的州时,州失业率和城市地区失业率就呈现出和开放前贸易保护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且如果某州有大量净出口产业,那么去除贸易保护将导致该州城市地区就业人数的增加。从产业的角度看,在劳动力灵活流动的州,净出口产业的劳动力失业率会随着贸易保护措施的降低而降低。值得一提的是,论文还提出了一个两部门、单一要素(即劳动力)嵌套搜索理论的国际贸易模型;分别考虑了部门间劳动力完全流动和不能流动这两种极端情况,论文的实证结果正好是这两种极端情况的中和[18]。Menezes-Filho et al.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巴西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巴西受保护产业中正式员工被裁员,与此同时,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出口的产业并不能全部吸收这些裁员。并且他们发现很多失业的正式员工都选择了自谋职业,剩余的一部分则成为了失业人口,还有一部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19]。Porto研究的是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阿根廷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他的估计结果表明阿根廷农业出口品价格的上升会导致:更低的失业率、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和更高的均衡工资[20]。
Revenga是较早发现国际贸易对美国失业产生显著影响的学者之一。1975~1985年间,美国的制造业进口占比提高了一倍,与此同时,工业部门雇佣数和美国工人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之前的许多研究都没有发现国际贸易对失业的显著影响,Revenga认为其原因是在研究方法上有瑕疵。他利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货币的强势升值和紧接着的贬值作为自然实验,货币升值时进口品价格较低,美国遭受的进口竞争程度较大。利用产业关税(产业关税的计算由产业内进口关税和进口品权重得到)和出口国产品成本作为进口价格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制造业的雇佣人数对进口价格的弹性在0.24~0.39之间,而工资对进口价格的弹性在0.06~0.09之间。或者说研究期间美元升值,导致进口竞争的加剧使得美国制造业雇佣人数下降了4.5%~7.5%,而平均工资下降了2.0%,进口竞争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人数上[21]。
Trefler研究了美-加自由贸易(FTA)协定对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以上提到的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不同,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涉及了双方的关税减免,不仅影响进口商还影响出口厂家。Trefler明确指出FTA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干净的经济学实验:第一,FTA签订的同时并没有伴随美、加两国的其他经济改革措施;第二,FTA签订时美、加两国并未遭受大的经济、金融波动。论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FTA造成了最受影响的制造业12%的失业,而从制造业整体部门来看失业率为5%;第二,无论是进口竞争还是出口导向的行业,FTA的签订都导致了最受影响产业中14%的劳动生产率提升[22]。
近年来最著名的一篇研究全球化进程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论文当属Autor et al.,这篇以TheChinaSyndrome为题的论文引起学术圈的极大关注。论文研究了1990~2007年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local labor market)差异性影响,论文用地区产业劳动力占美国该产业劳动力的比例以及美国该产业从中国进口量的变化来度量美国某种产业向中国的开放程度,这样不同地区由于产业组成和劳动力分配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进口竞争。此外,由于进口量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决定的,为了排除美国经济波动造成的需求方的内生变化,论文使用了中国对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增长作为工具变量。如果按照遭受中国进口冲击的程度排名,相比七十五分位点的地区,二十五分位点的地区会损失4.5%的制造业劳动力、人口中受雇佣人数的比例会下降0.8%、周工资收入会下降0.8%(这一工资的下降主要是由非制造业部门的下降造成的),这些地区收到的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也较多[23]。
在Autor et al.的基础上,Acemoglu et al.进一步考察了中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劳动力雇佣人数影响的机制和渠道。论文首先分析了进口冲击对美国劳动市场的直接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如果自1999年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没有发生变化,那么2011年美国制造业岗位会增加56万。这只是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影响还应考虑以下效应:产业间投入-产出的联系所产生的效应,即如果一个产业受到进口竞争冲击,那么该产业对上游产业的中间品需求会降低,同理,对下游产业中间品供给也会降低。但同时,受到冲击的上游产业价格会降低,因此其下游产业的中间品投入成本下降;反之受到冲击的下游产业价格也会降低,因此其上游产业的产出中间品价格受到负面影响。综上所述,当一个产业遭受进口竞争时,其对上游产业的影响方向是负向的,而对其下游产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论文利用1992年的投入-产出关系表衡量产业间的关联度,并用此作为权重衡量了上下游行业受到进口竞争时的相互影响,其结果验证了以上的论述。论文估计出这种间接影响加上直接影响总共造成了98.5万的制造业雇员损失,考虑到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联系,雇员损失高达198万人。除了全国范围的产业间研究,Acemoglu et al.还考察了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两种效应:第一,劳动力的产业间再分配,这种效应源自经典贸易理论。例如H-O模型指出,进口竞争引发的一种产品价格下降会导致劳动力和资本向另一产品的生产上转移,非贸易部门或开放程度较小的部门就会有劳动力的流入;第二,进口竞争导致对国内产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降低,通过凯恩斯乘数效应影响总需求从而导致失业。实证结果表明,非贸易部门并没有表现出雇佣人数的显著增加,这是因为总需求效应超过了再分配效应[24]。
在研究外部冲击(例如贸易开放或者某贸易伙伴国生产力大幅提高)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例如失业)时,因为这种总体的冲击缺乏外生变动,其影响程度往往难以衡量。经济学家有两种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第一,从总体冲击中构造出具有拟实验变动性质的冲击变动来研究冲击对于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例如Autor et al.。但是这种方法的弊端是其结果无法外推到一般均衡框架,因为各地区的分析结果呈现出空间相关性。第二,另一种办法是采用一般均衡下的定量分析,这种方法可以估计出均衡框架下的总效应,却无法将总效应和地区受到的差异化影响联系起来。
Adão et al.提供了一种新的估计方法,将以上两种方法融合起来,从理论上证明了空间联系如何决定外部冲击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影响不仅和本地市场受到的冲击有关(直接效应),还和其他市场受到的冲击有关(间接效应)。Adão et al.证明了地区间的空间联系影响间接效应的规模和在地区间的异质性并提供了MOIV(model-implied optimal IV)的方法构造地区间的拟实验变动,从而估计出地区间的空间联系和本地劳动力市场受到的差异性冲击,同时能够在均衡框架下稳健地将地区差异性冲击导致的失业加总,研究发现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量仅仅下降了0.51%[25]。
三、结语
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并没有把国际贸易和国内劳动市场失业联系起来。事实上,国际贸易理论的两大核心模型之一Heckscher-Ohlin模型认为贸易会使本国丰富要素受益,稀缺要素受损;而Ricardo-Viner模型认为贸易会使得出口部门的特定要素受益,进口竞争部门的特定要素受损,对于可以在两部门之间流动的要素,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些模型都假设劳动力是完全雇佣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解释失业的劳动经济学模型逐步完善后,国际贸易与劳动失业之间的研究才大量出现。
通过梳理国际贸易与劳动失业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第一,3种引入失业的理论框架(最低工资、效率工资和搜索-匹配模型)可以得出贸易对失业的不同方向的影响,关键在于模型设定贸易国的制度环境(最低工资制度和效率工资)、产业分工情况(如充分分工或未充分分工)、禀赋特征(如资本密集或劳动力密集)等,且大部分最低工资模型设定认为,若贸易国存在最低工资制度,开放会带来失业率的提升;第二,实证论文中,考虑到考察的产业部门是否出口、产业间联系(上下游的投入产出)、以及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程度的不同,贸易开放对失业的影响也呈现不同的结果。
当前理论研究成果丰富,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缺少一个较为完备的一般性理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特点在于理论上越来越重视搜索模型在解释失业方面的作用。未来可探索将搜索模型中纳入贸易国的背景因素(如工资制度、失业保障)以得到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解释国际贸易和失业关系的框架,另外还可以考虑产业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长期的结构性失业和短期的部门间劳动力的转移。
在实证方面,由于失业数据的不可得性,国内关于国际贸易和失业的相关研究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而国家层面上的失业数据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失业数据比发展中国家相对要好,但依然要解决失业数据的测量误差。为克服国际贸易这种类型总体的冲击的内生性问题,很多实证研究都构造了区域性的衡量开放程度和贸易冲击的指标来研究地区间的差异。但是这种对失业率变动的影响很难加总到一般均衡的框架中,最近的研究中,Adão et al.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估计方法,可以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中稳健地加总地区差异性的失业。今后的研究可借鉴这种地区到总体的加总方法,并纳入产业间联系,地区差异性、地方政策差异性等因素。这里要再次强调实证论文的重要性,由于理论模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态,国际贸易是否影响失业首先应从实证角度入手。此外,对比以上论文我们发现,考察国际贸易与失业的关系时,不同的考察角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因此,学者在今后研究中应注意国际贸易对劳动失业的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的区别,地区差异化、产业差异化影响和总体影响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