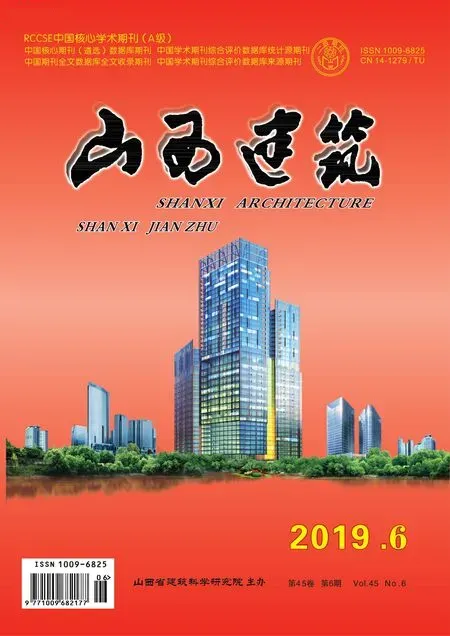浅析杭州西泠印社园林空间造园理景特色
2019-02-15陈青莹
陈青莹 陆 琦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西泠印社位于杭州西湖孤山西侧,是一座初建于清末民国、现今占地约5 760 m2的传统山地园林,是浙江篆刻学术团体“西泠印社”的社址。园林名家陈从周先生曾称其为“(西)湖上园林之冠”[1]。西泠印社自初创至今已近一百一十五年,仍在蓬勃运行,印社园林也在这漫长时光中从最初寥寥数屋,几经添建、整修,曾历战火损伤又在战后逐步恢复,现集有堂、楼、馆、亭、廊等多种传统建筑形式及塔、坊、泉池、石洞、篆刻、墨迹、雕像等于一园。
1 园林布局
西泠印社园林从孤山西南麓一直向北延绵至山顶,总高差约20 m,地形近似多层台地,建筑分布于地势平坦处,在山脚、山腰、山顶形成了三个建筑群。
社门位于孤山路边,为圆月洞门。进门即为一个四面围合的庭院,中有水池莲池;莲池北靠柏堂,是庭院的主体建筑;莲池西侧为竹阁和印廊,东侧为印人书廊,建筑空间都以单面空廊为主。
柏堂后为数条登山石径的起始。跨径立有一古朴小石坊,上刻“西泠印社”。登径而上,可见另一圆月洞门,门左侧为山川雨露图书室,右为仰贤亭,共一屋檐;仰贤亭旁有一折廊蜿蜒连接宝印山房。穿洞门而过,有一眼凿于岩壁前的小泉池曰印泉;印泉右侧的石径沿径覆有棚架,经凉堂蜿折上山,名为鸿雪径。
山顶庭院是“全社艺术处理最精湛的部分”[2]。庭院中央为两泓蜿蜒伸展的石凿泉池,西为文泉,东为闲泉,“是难得的山顶泉池”[2]。庭院南面为四照阁,建于凉堂之上,三面临空,俯览西湖。庭院西部建有二层的观乐楼、藏名碑的汉三老石室以及位于低一层台地上的遁庵、还朴精庐、鉴亭等,另一泉池潜泉淌于遁庵与岩壁间。文泉、闲泉以北有一近曲尺形石埂延伸至庭院东南角;其底部在闲泉边有人工凿穿的洞道,取名小龙泓洞;石埂顶西端耸立着密檐式石塔华严经塔,是全园制高点及全园构图中心;跨过小龙泓洞,在石埂顶的另一边建有曲尺形平面的题襟馆,馆之北为小楼鹤庐,居高临下承接孤山北坡的登山路。
2 空间序列及其分析
对比与引导两种手法的合理运用可以营造特点鲜明、变化丰富的空间序列,悄然编排游人看似随性的游走体验。
西泠印社有一条明晰的空间序列:入口圆洞门→柏堂庭院→夹屋径→石坊小空地→登山石径→夹屋圆洞门→印泉小平地→鸿雪径→山顶庭院。
从中提取出空间形态便是:门→中院→径→小院→径→门→小院→径→大院。
可见,开放性的院空间与约束性的门、径空间一直相互间插。西泠印社占地并不大,空间序列上开放性与约束性的不停对比使园内主要空间获得扩大感。且几个院空间之间也各有形态、环境、大小的差别,如柏堂庭院围合方正,建筑占主体;山顶庭院开敞不规则,林木环绕,山林占主体。空间序列并不因同属性空间的重复出现而单调,反而各显特色。
西泠印社有数条交错石径通往不同建筑物,在主要的游览石径上沿径布有石坊、篆刻、花架等暗示引导,强化空间序列,游人依序游览各空间,获得最佳游览体验。
鸿雪径上的花架则兼具对比衬托与引导的作用。鸿雪径顺山势蜿蜒爬升,花架上藤蔓缠绕,穿行其中拾级而上,阴暗、封闭、曲折、狭长的空间极大压缩了视野,待抵达山顶阔地时,便更觉豁然开朗。
3 理景特色
3.1 依山就势,强化起伏
《园冶》“相地”篇的“山林地”一节认为,山地起伏是不费人力即可得的自然情趣,在山林地建园布局时,顺应天然地势即可,因地取景,不需过多改造地形。
西泠印社即因循了孤山的自然山势而建,建筑随地形高低起落,园路顺岩坡曲折攀升。在局部营建中,适量地挖山堆石,改造地形,使峻悬处有平坦之地可让建筑立基,平坦处有峻悬之势添山林情趣。
“相地”篇还指出,若地势髙而方正,可在高方处建造亭台;若低而深凹,可在低洼处开凿池沼[4]。西泠印社华严经塔至文、闲两泉一片的造园理景处理便与此论契合。经塔自身高20余米,是全园最高的构筑物,又立于石埂之巅,是全园地势最高处,高塔立高台,极其耸峻,气势轩昂;而石埂前地面比四周下沉了几阶,又有下挖的泉池,地形低凹,更强化了一旁石埂壁陡峭之势。低池高塔相对,地形起伏更显鲜明立体。
3.2 疏密有致
书法、金石篆刻等艺术都十分注重构图与位置的经营。位置经营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疏密有致而不可平均分布,最常见手法就是要留出间空。特别是为了加强节奏感,有时也有必要以间空来打破连续性。园林也遵循疏密相间的原则,以建筑布局体现得最明显[3]。如西泠印社山顶庭院,建筑环泉池而布,分散而不平均。四照阁、题襟馆、观乐楼、华严经塔等主要构筑之间均有足够的视距,有利其相互对景;华严经塔与两旁建筑间有一定距离,像是留出了“间空”,在视觉上更加突显经塔的中心位置。
3.3 重视视觉关系
处于园林之中的建筑物或“景”,一般都应同时满足两方面要求:一是被看,一是看。上述两方面要求,往往成为建筑物或“景”的位置选择的依据。乍看起来一切若似任意摆布,纯出偶然,但实际上却又深刻、含蓄地受到这种视觉关系的制约[3]。西泠印社的造园理景在建筑选址上重视“看与被看”的视觉关系,四照阁便是一佳例。陈从周先生曾道:“坐四照阁,全园之胜、西湖之景尽入眼底,全入人怀矣,至此益证建社时主持者学之深[1]。”四照阁从山顶看仅为单层阁,实与崖下凉堂合为二层楼,靠崖临空,居高俯下。从“看”的角度,四照阁四面开窗,四面洞达:南面近可俯柏堂庭院,远可瞰西湖风光;东、西面皆无建筑,可一览山林郁翠;北面可观山顶庭院景致,建筑、植丛连成一幅风景长卷。从“被看”的角度,四照阁自山脚、山腰看皆为仰景;过了山川雨露图书室后,便能较清地看到树丛中四照阁一角;而从宝印山房旁仰望,四照阁的窗扇、屋顶轮廓完整敞露,窗映天光,“翼角起翘如鸟之斯飞”,极有轻巧感。而自山顶庭院看四照阁,则可平视可俯观:从泉边看向四照阁,阁后空广,天空背衬,建筑及林木的轮廓都十分清晰明亮,像裹了一层光晕;从题襟馆前、石埂顶俯看,四照阁掩于叶丛下,屋檐低垂,更显小巧。
3.4 营造空间渗透,丰富视觉层次
两个分隔开的空间之间若有适当的连通,使人的视线能从一个空间穿透至另一个空间,这两个空间便产生相互渗透,显现出层次变化。园林中常借设置门洞或窗口营造空间渗透。若设置的是漏窗,因隔了一重层次去看,视觉上的距离会比直接地看要更深远,也更含蓄。
西泠印社社门两旁是一列深瓦粉墙,上嵌一排方漏窗,以瓦片叠成窗花。园内景致通过漏窗渗透出来,宛转隐约,引园外人欲入园一观。若沿墙而行,因视点的移动不时地通过各个漏窗摄取图像,会构成一幅幅既连续又富有变化的画面,借这种时断时续的许多片段而形成的整体印象,不仅更含蓄,而且还会使人有步移而景异之感。
题襟馆前的园墙上也设有漏窗,将邻园之景引入园内,好似园的范围并不止步于园墙,墙外仍是园内。这是小园常用的扩大空间手法。
传统园林追求境的深邃,特别是范围有限的园林,多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法来增强景的深度感,比如园路尽量蜿蜒曲折,比如将建筑藏于山石花木之后半隐半现,都旨在丰富视觉层次,拉开景的距离。
山川雨露图书室门前的山石比更远处的要高上一层,并在山石顶种了竹丛,形成半张竹屏。透过竹屏看图书室,便有隐约幽深之美。游人随石径上登时,开始只见图书室被山石草木挡住大半,随着拾级而上,图书室自竹屏后愈升愈高而逐渐清晰,待抵达图书室门前时,仍会有庭院深深之感。
3.5 金石文化与园林结合
西泠印社是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的篆刻学术团体,印社园林是其早期的金石保藏之处,金石文化便贯穿于造园理景之中,大大小小的各类摩崖石刻、碑版、雕像等遍布全园。而印社造园之时,在基岩上进行的水池、道路、山石之加工,不也正仿若金石印章之雕刻制作[5]。有题联评价西泠印社为“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笔”“园林与印章共构思,水光偕山光合一色”,正是写照。
园中还多见楹联、匾额等文艺作品,又遍植梅、桂、竹、樟等文人多有吟颂的花木,富有文人园林的高雅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