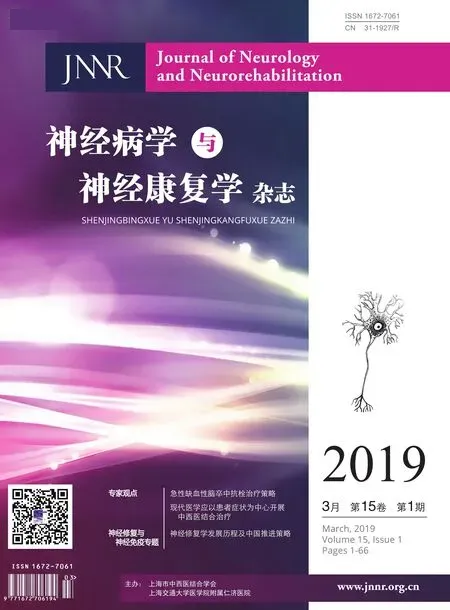免疫炎症与脑卒中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2019-02-12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天津 300052
近年来,脑卒中因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既往被认为是一种局灶性疾病,是脑血栓发生后导致的神经元坏死[1]。随着对脑卒中研究的深入,现在的观点认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实际上是一种系统性疾病,其影响包括导致肾血流减少、肝功能异常和心力衰竭等,尤其是会引起免疫系统的变化。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后,血脑屏障遭到破坏,大量免疫细胞涌入中枢神经系统并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细胞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放大炎症反应,加重缺血性脑损伤。因此,如何通过干预免疫炎症以影响脑卒中患者的预后,是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1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炎症损伤机制
无菌性炎症是缺血性脑卒中后的重要病理生理过程之一。在脑卒中发生后,缺血缺氧的脑组织发生不可逆性的损伤,继而激活机体的固有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系统,并且炎症反应贯穿了缺血性脑卒中的整个病理生理过程[2]。当中枢神经系统稳态发生改变后,脑内的固有免疫细胞,尤其是小胶质细胞受到外界信号的刺激而首先被激活,继而导致其形态和功能发生很大的改变。脑卒中发生后,小胶质细胞转变为活化的阿米巴样细胞,并且具备巨噬细胞功能,可以吞噬病原体和凋亡细胞等物质,同时分泌大量炎症因子和趋化因子以诱导外周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等浸润[3-4];小胶质细胞还能迅速增殖并迁移至病灶区域,位于血管周围的小胶质细胞能够吞噬血管内皮,从而破坏血脑屏障[5-6]。随着血脑屏障被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启动多种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诱导大量的外周免疫细胞向中枢神经系统浸润,这些外周免疫细胞通过释放炎症因子对神经元造成直接损伤[7]。其中,最受关注的外周免疫细胞是淋巴细胞,包括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和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研究表明,脑卒中发生后,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的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水平均在发病后第3天达到高峰,而NK细胞水平在发病后瞬时即达到高峰[8]。既往文献报道,NK细胞通过释放细胞毒性炎症因子,促进缺血性神经元死亡[9];而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浸润的NK细胞是如何被激活进而加重脑损伤的具体机制,目前尚未可知。
本课题组的既往研究采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脑标本和脑卒中小鼠模型,通过蛋白质组学阵列分析,发现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5水平显著上调,且IL-15主要来源于星形胶质细胞[10]。为进一步确定IL-15在脑卒中病理机制中的作用,课题组通过构建胶质细胞原纤维酸性蛋 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IL-15tg转基因小鼠模型,实现了IL-15在星形胶质细胞中的特异性过表达。在正常生理条件下,小鼠未发生增强的神经性炎症;但在实验性缺血性脑卒中造模后,小鼠的星形胶质细胞过表达IL-15,从而加重了脑损伤和神经功能障碍。除此之外,本课题组还发现小胶质细胞中特异性过表达锌指E盒结合同源框 1(zinc finger E-Box binding homeobox 1,ZEB1)的小鼠的缺血性脑损伤有所减轻[11],并通过实验证明其机制可能是ZEB1通过调控小胶质细胞,减少了中枢神经系统内趋化因子的表达和中性粒细胞的浸润,从而减轻了脑内的炎症反应。
2 免疫调节剂干预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试验
大量的动物实验已证实外周免疫细胞向中枢神经系统浸润会促进脑卒中后的神经损伤。目前已开展了数项小规模的临床试验,通过免疫调节剂干预外周免疫细胞,并观察其对脑卒中患者预后的改善作用。
2.1 长春西汀
长春西汀是从长春花中提取出的一种生物碱,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其最初被应用于脑卒中的治疗主要是为了改善缺血脑组织的代谢以及促进大脑血流量等[12]。此后,陆续有学者通过体外实验和动物实验证实长春西汀可以通过抑制核因子 κ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而发挥抗炎作用[13-14],由此为研究长春西汀对脑卒中患者的抗炎效应提供了依据。本课题组既往的一项研究纳入60例发病后48 h内且错过溶栓治疗时间窗的前循环脑卒中患者,将这些患者随机分入长春西汀治疗组和对照组;研究结果显示,长春西汀治疗组患者的临床评分和影像学结果均优于对照组患者,且长春西汀治疗第7天时的磁共振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检测发现长春西汀治疗组患者脑梗死区的炎症水平低于对照组;此外,长春西汀对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无影响,其可能是通过抑制NF-κB的活性而发挥免疫抗炎作用,这是不同于长春西汀发挥磷酸二酯酶 1(phosphodiesterase type 1,PDE1)抑制剂作用的新的免疫干预机制[15]。
2.2 芬戈莫德(fingolimod)
芬戈莫德是一种具有高度亲和力的鞘氨醇-1-磷酸(sphingosine-1-phosphate,S1P)受体调节剂,可将淋巴细胞阻留于淋巴结和脾脏中,减少外周淋巴细胞渗入脑内,减轻脑内炎症反应。基于这一机制,芬戈莫德可以抑制免疫系统对多发性硬化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的攻击[16]。芬戈莫德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首个治疗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的口服药物。2014年和2015年,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施福东教授开展了2项概念性的临床试验,旨在评估芬戈莫德在脑卒中患者免疫调节治疗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第1项临床试验[17]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发病后72 h内且已错过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溶栓治疗时间窗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给予这些患者口服芬戈莫德(0.5 mg/d,连续3d),结果显示芬戈莫德可以明显减少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抑制脑梗死体积的继续扩大,改善血脑屏障的渗漏,改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 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脑卒中发病3个月后,患者的改良 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评分亦有明显改善。第2项研究[18]是给予脑卒中发病后4.5 h内的患者芬戈莫德联合rt-PA溶栓治疗,结果显示与单用rt-PA溶栓相比,联合芬戈莫德治疗可以减少与rt-PA相关的出血转化,抑制病灶继续扩大,改善NIHSS评分。
2.3 那他珠单抗
那他珠单抗是人源化的抗CD49d单克隆抗体,通过阻断白细胞整合素与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抑制白细胞向中枢神经系统浸润[19]。目前,那他珠单抗是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的标准疗法,可以有效抑制疾病复发[20]。那他珠单抗治疗脑卒中的机制主要涉及以下2个方面:(1)减少外周T细胞向脑内浸润;(2)抑制中性粒细胞浸润。此外,一项由3个国家的30个中心参与的Ⅱ期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21]共招募了161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其中79例患者被随机分入那他珠单抗治疗组,另82例患者被分入安慰剂治疗组,并对脑卒中缺血后9 h给予那他珠单抗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研究的主要结局并未达到预期的设想,即那他珠单抗未能抑制自基线期起至第5天的脑梗死体积的扩大,但次要结局的分析结果显示那他珠单抗可能有益于患者功能的恢复和认知的改善,表现为脑卒中影响量表(Stroke Impact Scale,SIS)评分和蒙特利尔认知功能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评分的改善。
3 小结与展望
相较于已有100多年的肿瘤免疫治疗研究史[22],脑卒中的免疫治疗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是否能够借鉴肿瘤或自身免疫疾病的免疫干预策略,是否能够通过精确阐明脑卒中后中枢神经系统内细胞亚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促进靶向免疫调节剂的研发,是否能够明确免疫调节治疗对溶栓时间窗的影响,是否能够明确中枢神经系统自身抗原暴露与脑卒中预后的关联,这些问题均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有理由相信,脑卒中的免疫疗法一定会呈现出更广阔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