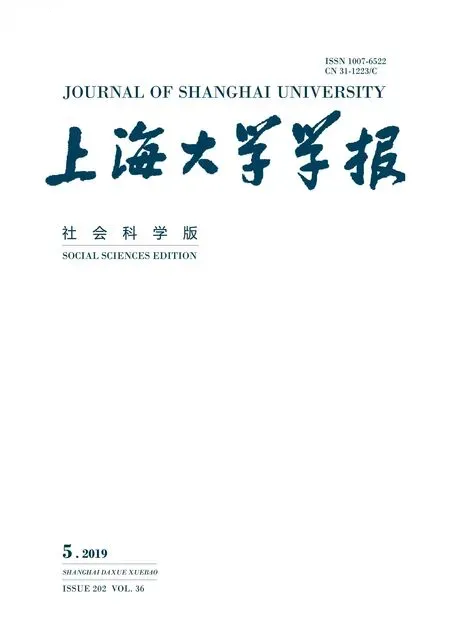《列子》引《诗》的年代及其意义
2019-02-11邵杰
邵 杰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今本《列子》八篇,引用典籍数量不多,其中明确引《诗》仅有一处,见载第四篇《仲尼》之中,其文如下:
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不知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愿戴己欤?顾问左右,左右不知。问外朝,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尧还宫,召舜,因禅以天下。舜不辞而受之。[1]149-150
此处童谣,唐宋以下诸多典籍皆有著录。影响尤大者,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将此谣列入“杂歌谣辞”,题为《尧时康衢童谣》。[2]后世诸多载录皆法此而题名。此谣亦见今本《诗经》,“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见《周颂·思文》;“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见《大雅·皇矣》。已有学者结合先秦典籍引述情况,论证此谣乃《列子》作者组合《诗》句而托名于圣王,实属伪作。[3]以事实层面之误,来论述典籍真伪问题,属于学界流行操作。然古书情况复杂,真伪之外,或可有别种角度与意蕴。故笔者不揣谫陋,草就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材料的产生年代
以目前中国文学史的常识来看,殷商之文字尚嫌简质,早先的尧舜时代应不太可能产生如此整齐的四言诗。若参照保留尧舜事迹最为近古的《尚书·尧典》《舜典》等记载,尧舜时期的文学尚无确切的踪迹可寻,即或有四言之诗,一直传承入《诗经》且分隶两诗的可能性亦极小。故《列子》此处童谣很可能来源于《诗》,具体年代当细致分析。
《大雅·皇矣》中屡言“帝谓文王”,当是设言天帝语文王之辞,其中“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毛《传》并未直接解释,郑《笺》云:“其为人不识古,不知今,顺天之法而行之者。”[4]522本来意思显豁,孔《疏》则以为二者相异,释毛曰:“不待问而自识,不由学而自知。其所动作,常顺天之法则”;释郑曰:“其为人不记识古事,不学知今事,常顺天之法而行之。……此不识古不知今为美者,言其意在笃诚,动顺天法,不待知今识古,比校乃行耳。不谓人不须知古今也。”[4]522《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亦引此诗,孔《疏》释言近似:“‘不识不知’,谓不妄斟酌以为识知,唯顺天之法则。”[5]此种力图调和的解释,显然将“不识不知”植入了逻辑前提:文王自识自知而不待外求。这大约是为了维护文王的圣王形象,也可能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清儒马瑞辰考察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时,曾数引《皇矣》此句来证“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等言辞,认为《诗》句意谓“生而知之,无待于识古知今。”[6]王先谦亦赞同此说,并将早期典籍中引述此句者,悉数归为三家《诗》说。[7]实则典籍引《诗》,并非严格遵照《诗》之原有语境,据以划分《诗》学派别,逻辑上存在缺失。[8]高诱注往往取《诗》句为己用,据以反推《诗》义,于理亦恐有失;但其与道家著述的互参,似乎影响到了《诗》注,孔《疏》所论,或即此类。若《皇矣》中文王果然“生而知之”,何须天帝屡屡告知行动方针,乃至有“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之类的直接指示?比推诗义,可知此处是天帝对文王的嘱托,即不必识知,顺应天帝旨意即可。“不识不知”应是一种角色要求,不是本体状态,孔《疏》而下多牵合文王自身而言,似显迂曲。
《列子》此条言尧不知自身治政效果,出游闻童谣而喜,可知此谣实际上是对其治政的正面评价。《周颂·思文》言“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意在赞颂周之始祖后稷发展农业以养育民众的功德;《列子》此处所言,义应相近,是对尧之治功的颂扬。随后之“不识不知”,若理解为承前之句,应指尧的本体状态,异于《皇矣》中出自天帝的要求,而与道家不求外知的思想较为一致;此下“顺帝之则”自可循《诗》释为遵守天帝的法则。但尧遍问左右朝野,欲知治政效果及百姓是否爱戴自己,则与道家之“不知”理致迥异;其闻谣而喜之情状,与此“不知”亦存在偏差。所以,此处之“不识不知”应区别开前句,理解为朝野诸人对治政效果的“不知”。若此时仍将“帝”释为天帝,则此句似无涉于尧之治政。唯有将“帝”理解为尧,指天下皆遵从尧的规则,才能真正凸显尧治天下的功绩,使尧的疑问终获解答,并触动其心思,产生喜悦之情。文本逻辑,于此方可合理贯通。此种解释,显然已与《诗经》同句所指完全不同。
据研究,《诗经》中出现的“帝”,均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明属性;至于君主,《诗经》中只称“王”“后”“天子”。[9]“帝”用来指称人间的统治者,渊源较早,《逸周书》及《左传》《国语》中均有“黄帝”之称,但其盛行于世,当始于战国中后期时期“五帝”之名的出现,《荀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均有“五帝”,虽然所指并非完全一致。[10]此种观念亦映现在战国后期的政治实践中。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十九年(前288年),秦王称西帝,齐愍王称东帝。[11]212后来两家虽自去帝号而复称王,但其称帝之行,已足以展现出一种超越性的意图,即在当时各国均已称王的背景下,借天帝之名来指称人间君主,以凸显更为尊崇的地位。后来嬴政初并天下,臣属认为其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建议上尊号为“泰皇”,嬴政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11]236不满足于既有成号而自称“皇帝”,无疑是充满霸气的自我设定。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战国以来观念的影响,目前还不易获知,但此种称谓已明确表露出其凌越圣王、直通天帝的野心。如果说司马迁于《史记》立《五帝本纪》,是承战国以来“五帝”话语系统之余绪,那么,书中西汉天子称“帝”,则显然受到了秦始皇的影响。后世之帝,往往成为皇帝的简称。反观《列子》此处引述,以尧为“帝”,可知其思想观念不会早于战国中后期,材料的产生年代亦不可能更早。其中的歌谣,可以确定是源自于《诗》。
《列子》此处出现的“儿童”,有学者论证其为晚汉以降词汇,并以此则材料佐证《列子》之为晋人伪作的说法。[12]实则古籍的定型年代,与其产生年代并不完全一致。古典时期的“伪书”,未必全是有意的伪造,其词语、文字的年代或许较晚,但其主体思想则可能是较早的产物。以《列子》此条材料而论,其最终定型或不早于东汉末期,但其中流露的思想意识,则非汉代的产物。
此处之尧,听到童谣即直接禅让天下,而舜不加辞让即接受之。这种随意的政治交接,虽颇合道家著述中的圣王形象,但与史实显然不合,尤其与《尚书·尧典》中“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等政治考察,[13]存在根本性差异。清儒俞樾据《列子》此处“舜不辞而受之”,论证《尚书·尧典》中“舜让于德弗嗣”(见于今本《舜典》,俞氏以今文家立场言之)为“舜攘于德弗辞”,认为“舜无得天下之心,而天下自来,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赖《列子》此言可以见《尚书》之古义。”[14]其言显未深察《尚书》中尧舜禅让之事迹,而将《列子》与《尚书》轻率通约,忽略了《列子》的道家著述性质。
众所周知,汉代思想史中,尧舜具有特殊意义。汉人在初期的彷徨后,选定尧作为汉家先祖,“汉为尧后”的思想观念在西汉中期以后逐渐盛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认知。[15]王莽后来自称舜帝后裔,以尧舜禅让为成法,逼迫汉室禅让皇位,实际上是对此种思想观念的政治利用。汉代士人文字中,亦常出现“五帝三王”的记载,如刘向曾上疏建议成帝:“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16]1956是希冀汉德可与五帝、三王相辉映。五帝、三王,已成为衡量历代帝王德业的极高标准。又如扬雄在《剧秦美新》的《序》中赞扬王莽“配五帝,冠三王”,[17]678可见其心中对于王莽的定位是超越三代、德配五帝的。东汉在意识形态上,自觉承续了前汉的多种思想资源,包括“汉为尧后”的观念。不过,由于王莽的原因,东汉之初对其追祖的虞舜,似乎有所回避。如班固所作《典引》,屡屡称及唐尧,而不再尧舜并提,显然是忌惮于王莽之事。以此观之,《列子》此处关于“尧舜禅让”的描写,应不可能出现于两汉时期。汉代之后,包含尧舜在内的“五帝”作为圣君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亦不可能产生此种思想倾向。
从另一角度言之,汉代以降士人群体的知识体系中,包括尧舜在内的古圣先王之道主要存留于先代典籍尤其是六经之中,如《汉书·儒林传》所言:“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16]3589足见当时士人的治政理想,基点即是六经为主的典籍。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尴尬与秦代“焚书坑儒”的严酷之后,汉代士人及其奋力投入的经学开始走出困境,并逐步受到重视,成为官方学术的主体。经学的复振,带来的是全社会对于经典的重视,以及对于古圣先王之道的尊重和仰慕。这样的思想文化倾向,不可能催生出经典之外关于圣王的异质性述说。所以,《列子》此条材料的产生,只能在汉代以前。结合前文分析,其所产生的年代,应在思想较为自由的战国,极有可能在战国中后期,与列子生活的时代应相距不远。
二、年代的层级区分
当然,《列子》此条材料未产生于汉代,并不意味着汉代没有此类文献。若在此之前,这些文献即已产生,至汉代才在公共知识领域出现,虽可视为出自汉人之手,却并不能作为汉人思想的产物。如《韩诗外传》《说苑》等典籍中都留存有若干嘲弄古代圣贤的材料,但基本都是杂采先秦故事的结果,并不能代表汉人的观念。《列子》引《诗》的材料,亦应作如是观。
实际上,任何时代的文献都存在两大分野,一类是其时存在的前代文献,一类是时人自身创制的文献。当然,也存在两者兼具的情况。如《汉书》,有些篇章为班氏独创,有些则全取《史记》。至于前代文献的存在形态,也较为复杂,既包括旧有形态的传承与整理,也包括全新形态的诞生与铸造。两者虽有大致界限,亦时常有所交融。如西汉《诗》类文献,既包含零星流传下来的先秦文本,又包含口头传承至汉代而形诸文本的部分。《汉书·艺文志》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6]1708即充分说明了文献新旧形态的交融对于典籍完整度的重要意义。如果充分考虑此种意义,文献的形成年代势必应作更为细致的区分,至少应包括四个层级:一,产生年代;二,记录年代;三,成型年代;四,定型年代。当然,每个层级内部,还可依据具体情况作出更为细致的划分;不少文献也存在年代层级合一的情况。但不同层级间的修整与变异,必须突破单一的年代观念才能更为深入地考察并清晰获知。
产生与记录的年代差异,在早期文献尤其是具体篇章中,较为常见,不难理解。成型与定型的区分,则主要着眼于整部典籍的面貌,需要略作阐述。典籍成型最重要的标志,应是文本的组合及其表现出的一致性。组合决定面貌,一致性则是典籍义例的核心质素。古典时期不少典籍往往有多次成型,有些是同一时间段的各自成型,有些则是初次成型后有所变动的再次成型,其间文本面貌和义例往往会随之产生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定型必然伴随着成型。但定型不同于成型的要素,主要应是文本面貌和义例在公共领域的稳定。成型阶段的典籍,并不一定具备公共性,即或有之,也无法在此基础上形成长期的稳定性;而定型阶段的典籍,必然也必须展现在公共领域,并在其中展现出强烈的稳定性,如此才能充分展现典籍的公共形象,获得公共认可,进而形塑关于典籍的通行性认识。当然,成型与定型,都是后设立场的观察与判断。若置诸当时,每次成型或许都可以是定型,至少含有定型的意味;而站在后设立场,成型只意味着暂时的稳定,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以此而言,定型往往是成型阶段的终结。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终结并不意味着成型阶段的典籍文本就此消亡。
在典籍定型之后,文本面貌和义例可能仍会出现一些改变。典籍的公共形象,在最初定型后,逐步获得了自足的完整性;而新的改变则往往意味着典籍公共形象的整合、增添乃至重塑。与成型阶段不同,定型阶段的改变一般都以最初定型的状态为基准或依归,如典籍亡佚之后被重新辑佚的残本,仍力图按照原本义例来排列。这个过程甚至可能会参考和吸纳典籍成型阶段的某些文本特征,但不会就此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因此,确定典籍的定型年代,需要考虑并注意区分通行性认识的主要依据和现存可见的直接来源。
以《列子》言之,今日通行八卷本的祖本,由晋代张湛完成。张湛《列子序》曾言及所据的三个残本,分别是家藏本三卷、刘陶藏本四卷、赵季子藏本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1]293说明张湛此时虽未有全备之本,但知晓其基本情况。所谓全备之本,应即《列子》之定型状态。《汉书·艺文志》明确著录“《列子》八篇”,[16]1730刘向《列子新书目录》(清代以来颇有怀疑此篇伪者,今人已有辩驳[18])载:“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1]291-292其所校定八篇,正可对应《汉书·艺文志》所载,应即《列子》之定型。而在此之前,《列子》显然已有多种成型的文本,成型年代皆不晚于刘向校书之时。刘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成型之书进一步整理为定型之书。(1)有学者将刘向校书视为早期文献由“开放性”文本向“闭合性”文本过渡的主要转折点,见徐建委《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7-8页。关于此种转折更为精深的论述,可参徐建委《周秦汉文学研究中的〈汉志〉主义及其超越》,《文学遗产》,2017年第2期。
据刘向所述,其参考的成型本《列子》至少有五种,各家的文本表现不甚一致,除了篇数、章节、文字的差异,篇目的不同亦可推知。刘向在书录中已明确提到“《穆王》《汤问》二篇”、“《力命》篇”、“《杨子》之篇”[1]292,而据《列子释文》,《周穆王》“一曰化本”,《仲尼》“一曰极智”,《杨朱》“一曰达生”,[19]说明在《列子》定型之后,亦有篇目相异的本子存世。因刘向代表官方校定《列子》后,相关篇目不太可能发生完全的讹变,故这些篇目相异的本子,应自西汉前中期流传而来,保留着《列子》成型阶段的风貌。其中以《达生》为篇名者,很可能意味着,《列子》在成型阶段曾与《庄子》文本发生纠葛。今本《列子》与《庄子》复见之内容,或可资证。
典籍成型阶段多种文本的相异,显然与先秦古书以单篇流传的方式有关。余嘉锡先生曾有论说:“古人著书,既多单篇别行,不自编次,则其本多寡不同。加以暴秦焚书,图籍散乱,老屋坏壁,久无全书,故有以数篇为一本者,有以数十篇为一本者,此有彼无,纷然不一。分之则残阙,合之则复重。”[20]此种情形下,不同本子中相同篇章内容的相异,实为合理的常见现象。而在各本内部,不同篇章中相关内容的复见,亦可能属于典籍成型阶段的文本特征。《列子》有一段内容分别见于今本《黄帝》与《仲尼》两篇:
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尹生闻之,从列子居……列子曰:“……姬!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庚无是非;从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列子·黄帝》)[1]48-50
子列子学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更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外内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则理无所隐矣。(《列子·仲尼》)[1]132-133
前者为对话体,故有“吾”称;后者为记叙体,却仍用“吾”,令人疑惑。王重民先生即认为:“‘吾’字当衍……此篇既改为作者所述之言,而著‘吾’字,则不可通矣。”[1]132但除“吾”之外,“我”“彼”二者亦存两篇,可知后者在文字上实袭自前者,虽有称谓及字句之改写,如改“夫子”为“老商”,改假借之“庚”为本字“更”,但主干内容并无不同。张湛于后者注曰:“《黄帝》篇已有此章,释之详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极,则乘变化而无穷;后明顺心之理,则无幽而不照。二章双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1]133可见张湛也意识到了二者的重复,但他并未删改,还力辩其别;说明其所据之本中,此条材料即为两出。揆诸常理,此种现象在刘向校定本《列子》中,应不太可能出现;张湛所见,应出自刘向校定之前所谓“章乱布在诸篇中”的本子,含有《列子》成型阶段的特征。
成型阶段各家文本的不同,实际上标示着,《列子》形诸文本不是一次性的,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祖本;《列子》中诸多材料的记录,具有多源性。不同篇章中内容的复见,亦与此种特性密切相关。另外较明显的例证,是人称的相异。如《列子》中既称“子列子”,又称“列子”,还称“列御寇”,应出于不同立场的记录手笔。《天瑞》篇第十节中“子列子”与“列子”并存,[1]29说明此处文本很可能是缀合不同记录而成,故保留有若干痕迹;相似的情况亦见《黄帝》篇第十节,两称“仲尼”而后称“孔子”,[1]67-69似亦合不同记录而成。记录的差异,往往由原始依据的差异导致。这种原生性的差异,是文献年代探究不容回避的问题。《列子》的产生年代,应随具体篇章而有不同,兹事体大,尚需系统而精细的研究,俟来日再做探讨。
目前而言,《列子》中各条材料产生与记录的年代,并不整齐划一;《列子》作为典籍成型与定型的年代,亦非单一时间节点所能笼括。至少在西汉时期,《列子》已经有成型的多种本子,且由刘向校定八篇,此为最初定型;此后诸本亦各自流传而及两晋,由张湛校定并作注,是为再次定型。后世《列子》诸本,皆以张湛定本为依据。
三、政治体制所映现的记录年代
《列子》引《诗》这条材料,产生年代当在战国时期,前文已论。而其记录年代,亦可推见大概。先言此条材料中的政治体制,尧为了解治政效果,先后询问了三个层级:左右、外朝、在野。其中,“外朝”一词,见于《周礼》《礼记》《国语》等典籍。《周礼·秋官·小司寇》云:“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21]873与此相参的记载如《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之职……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21]717可见周之外朝政事,庶民百姓是可以参与的。从居住位置看,这些庶民不会悉数住在城邑之中。以周代金文记载来分析,城邑之中所居多为贵族,而邑外之地,则聚居着较多的农业劳动者。[22]
《尔雅·释地》涉及先秦时期的土地层级:“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23]武王伐纣,有牧野之战;《诗经·野有死麕》次章“林有朴樕,野有死鹿”,[4]293即林野并举,皆可证《尔雅》所载。同时,《尔雅》在此数句后,亦有隰、平、原、陆等多种不同的地名解释,后总题曰“野”。可见,“野”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之“野”,总称邑外之地;狭义之“野”,仅指称郊外之地的一部分。不管从广义还是狭义来理解“野”,《周礼》中“外朝”的参与者必然有居住在野之庶民。《列子》此处将“在野”与“外朝”判然两分,可知其与周之礼制不甚相合。
“野”的地理含义,一直存在;其与“朝”对举,成为政治结构中的两极,当与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变化有关。春秋以降,王官式微,不少礼乐人才散至民间,故孔子有“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引语[16]1746)之说。原本远离城邑的处所,此时成为礼乐文化尚存的载体与象征。《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24]2498内在意涵应深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此时“野人”的构成,在原有的农业劳动者之外,多了一批文化才能出众的人。前者在文献中仍显示出粗鄙的色彩,而后者则逐渐成为贤能人才的指称,代表着当时道德文化的高度。野地多贤,遂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孔子以“仁”作为“道”的核心,来干谒诸侯,其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24]2502),说明在其观念中,“复礼”是“道”行于世的必要条件。而要“复礼”,必先有知礼、守礼、传礼、学礼之人。与礼乐文化传承紧密相关的“野人”,于此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影响现实的政治力量。早期儒家的此种逻辑,后世逐渐发展成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两大模式:以学术文化来影响现实政治,以平民立场来劝导统治阶层。不过,在孔子的自我体认中,“士”作为特殊群体,总体上与庶民颇有区分。到了战国时期,“士”与“民”就呈现出了合流的趋势。如《孟子》中出现的“士庶人”,即说明当时“士”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地位更贴近于民,而非大夫,“士”成为“无官守,无言责”的政治自由者。[25]《孟子·万章下》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取非其招不往也。”……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26]
其中,“市井之臣”与“草莽之臣”的语源,当源自周礼,《仪礼·士相见礼》载:“凡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下臣。宅者在邦则曰市井之臣,在野则曰草茅之臣。庶人则曰刺草之臣。他国之人则曰外臣。”郑玄注:“宅者,谓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国中,或在野。”[27]可知周制中退休官员家宅在野,即可自称草茅之臣,当即孟子所云“草莽之臣”;亦可证“在野”一词在早期应指处所,与其人是否入朝为官并无必然联系。
孟子此处将固有之词进行了意义的改造,“市井之臣”与“草莽之臣”本指致仕的官员,此处则显然被划归为未仕的庶人。而从孟子下文的阐述来看,此处的“庶人”,“不仅是自由民,而且还是未仕的‘多闻者’与‘贤者’,是天子与诸侯都不能召唤而只能就见的独立特行之士,其实指的就是孟子自己。”[28]虽然孟子亦曾出仕[29],也可以“市井之臣”或“草莽之臣”称名,但他刻意强调“庶人”的身份,且解释自己为何不去见诸侯的原因,目的显然是自我砥砺以彰显气节。尤其是他关于孔子“不俟驾而行”是由于“仕有官职”的说辞,充分显示出孟子在思想上已将官与民明确划界;比起“市井之臣”与“草莽之臣”等延时性称谓,孟子对于民众的判断标准,是即时性立场,不再为官者,皆可归入民。此种观念表明,战国时期的政治体制在发生变化,现实中的职位,正在成为政治结构划分的最重要基础。“在野”在词语上演变为与“在朝”相对的未仕状态,后世以朝野之称来指代政治结构中的官民二元分别,皆可推原于此种变化。
以此来观察《列子》“在野”之谓,知其文本记录当不早于孟子晚年与万章之徒讲论著述之时。而其中“外朝”所指,显然已不同于《周礼》所载,应指皇帝“左右”之外的官员。这一点与西汉前中期的情况较为类似。《汉书·严助传》载:“(武帝)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奇等,并在左右。……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16]2775可见在武帝统治前期,严助等人应为“左右”近侍,与外廷大臣的辩论,属于“中外相应”。颜师古注曰:“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16]2776可谓十分精准的理解。司马迁《报任安书》云:“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16]2727-2728所言可与《严助传》互参,说明直至武帝前期,议论朝政主要是外廷的职责,而与外廷大臣相对的,是时常在皇帝左右的近侍。
这种中外之别,至昭宣之世,逐渐演变为“中朝”( 亦称“内朝”)与“外朝”两大类别,成为朝臣中皇权与相权的各自代表。[30]至于“中朝”的涵盖,已远超“左右”之人。《汉书·霍光传》载武帝时,“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16]2931奉车都尉,属内朝臣无疑,而“入侍左右”之辞,说明“左右”当在禁宫之内,与皇帝更为亲近。列于“内朝”者,未必都是“左右”。《列子》引《诗》此条,将“外朝”与“左右”并列,而非“内朝”“中朝”之语,可知其文本记录的年代当不晚于霍光秉政之时。
至于其中出现的“儿童”一词,若果于晚汉以降才产生,则很可能是文献流传过程中文字衍变所致,应不是记录初期的面貌。合而论之,《列子》此条材料的主体内容在战国时期即已形成,其记录年代,应在孟子晚年至汉昭宣世之间。刘向校定《列子》后,此条材料可能由于多种因素而产生了文字的变异,辗转而成今本面貌。
四、《诗》称“古诗”的演进态势及其诗学意义
《列子》此条材料中的“古诗”之称,颇值得注意。将《诗》径称为“古诗”,现存先秦典籍中尚未见及,自汉代以降,却较为普遍。如《汉书·王褒传》引汉宣帝语:“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16]2829《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16]1756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17]21皆以“古诗”之名指称《诗经》。《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的言论,虽然不严格对应于今本之《诗》,但仍属《诗》之系统,与前举情况相类。
不过,此种态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变化,“古诗”除了用来指称《诗经》,还可用以指称汉人之诗。前者的情形,如挚虞《文章流别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31]又如《文选序》:“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17]1其中的“古诗”,都是指《诗经》。后者的情形,如钟嵘《诗品序》:“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32]此处的“古诗”,当是专指汉代的五言诗,而且没有公认的作者。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33]所论汉代五言诗的冠冕之作,即为《文选》所载的《古诗十九首》,其中有九首亦见载《玉台新咏》,题为枚乘所作,故曰“或称枚叔”。陆机有《拟古诗》十二首,亦载《文选》,都是对《古诗十九首》相关诗篇的拟作。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陆机这些拟作的原初名目,但其之前的建安诗人作品中,已经明显可以看到《古诗十九首》的影响。[34]
拟作的风气,在汉代一直存在。辞赋领域较为明显,尤其是《楚辞》中的汉人作品,一定程度上都可视为对于屈原作品的模拟;扬雄的拟经之作,也颇具规模;王莽时期的诏书,多模仿《尚书》为文……至于诗歌领域,西汉四言诗对于《诗经》的模拟,已有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乐府诗中的同题续作,往往是因旧曲而制新词,这些旧曲所对应的旧作,后世常称为“古辞”。据学者考证,“古辞”之名盖创始于南朝沈约《宋书·乐志》。[35]实则以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据汉乐府旧题而改创新词的态势来看,“古辞”名目的产生当不晚于此时,因为要区分同题制作的年代先后,势所必然。
反观“古诗”之名,理亦仿佛。汉人将《诗经》称为“古诗”,一方面是由于《诗》篇的年代之古,另一方面则应是为汉代新的诗歌创作留下“名”的空间。此种称名背后的深意,显然是将汉代的新诗视为自觉承袭《诗经》的体制。这种意识,在汉武帝之时,表露无遗。《汉书·礼乐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16]1045前人多据此以为武帝时始立乐府,后来20世纪70年代秦乐府编钟的出土(2)编钟发现者袁仲一先生明言秦乐府编钟出土时间为1976年,见其《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但此后的多种论著皆言出土时间为1977年,似均本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一文,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使得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武帝“乃立乐府”的真实含义。不少学者都以武帝扩充乐府职能为说,虽不算错,但究嫌质实,赵敏俐先生结合《汉书·礼乐志》“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之语,认为武帝“立乐府”意味着武帝重新制礼作乐。[36]这个看法,更契合文本的逻辑,武帝时的采诗活动,显然是对先秦时期采诗模式的追慕与学习,本质上是意欲制作一部新的“诗三百”,以表征、展现汉朝的鸿业。将《诗》称为“古诗”,是与此相应的时势需要,惟其如此,《诗》外之诗才能有“名”的立足之地,从而名副其实,名实相应。西汉中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中秘,所成之目录《七略》,既有《六艺略》之《诗》,又有《诗赋略》之“诗”,便是此种诗学观念在文献整理中的实践性贯彻。而其根源,则是汉家王朝“制礼作乐”以成就一代基业的雄心。
在此意义上讲,以“古诗”来指称《诗》,至晚在汉武帝时应已产生,并逐渐成为习语。而以“古诗”来指称汉代的《诗》外之诗,与汉乐府的同题创制紧密相关,至早应在东汉。《列子》此处将《诗》称为“古诗”,可知其记录很可能是出自汉人手笔,甚至有可能是刘向在整理过程中的所定;当然,也可能刘向所见版本中即为如此,故采纳而为定本。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古诗”之称是来自先秦的记录。
今存战国文献中,《诗》已逐渐成为一种历史陈迹和遗产,《诗》的规范性、权威性都有相当程度的表露。如《孟子》将《诗》作为一代政典,与“王者之迹”联系起来;《荀子》将《诗》作为体现圣王之志的典籍;《庄子》则将《诗》作为无乎不在的道的体现。[37]《诗》在此时,已失去了春秋时期“赋诗”“引诗”等社会活动所呈现出的鲜活性,其历史属性被刻意强调,如《荀子》中明确提出“《诗》《书》故而不切”,[38]14就是最好的例证。此种《诗》学认知,正是《诗》称“古诗”的思想基础。在观念中将《诗》推尊为“古诗”,应始于战国时期。如此一来,《诗》外之诗,才能真正进入“诗”的行列,沾溉《诗》的荣光与威名,并逐步与《诗》并行,进而繁荣发展,蔚为大国,从而确立继《诗》而起的新的标杆。后来的汉乐府及《古诗十九首》,皆循此理路而进入古典诗歌的标界。也可以反过来理解,《诗》称“古诗”的逻辑前提,是《诗》外之诗的兴起与趋繁。
五、“诗”在战国的演变及其意义
从文献来看,战国时期“诗”的名义确已出现新的变化。如以下材料:
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子舆入,曰:“子之歌诗,何故若是?”(《庄子·大宗师》)[39]228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庄子·外物》)[39]755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天地易位,四时易乡。(《荀子·赋篇》)[38]480
显而易见,此中之“诗”,皆已非《诗》之体系所能笼括,而应视为一种新的创作。尤其是《庄子》讲到儒士发冢掘墓,犹引诗作为理论依据,这固然是对于儒家喜引《诗》《书》为证做派的调侃与嘲讽,但也标示出战国时期“诗”的涵盖不断扩展的态势。除此之外,《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引述的很多“诗”,都不见于今本《诗》,严格来说,都应属自由的文辞创作,说明当时“诗”的指称在逐渐泛化。这种态势,在出土文献中有更为明显的呈现。比如有研究者指出,上博简《子羔》篇有言舜“敏以好诗”之语。[40]以事实年代而论,此处之“诗”绝非《诗》,而“诗”字的产生,已在周代,远后于舜的时代。由于简文没有更多信息,目前尚无法确论此处的所指,但此语无疑彰显出“诗”在战国时期的自由化状态。这种状态,影响了《诗》的固有品格,造就了战国时期诸多文献尤其是故事杂说中《诗》作年代的“错位”及意涵的变化。《列子》引《诗》,即如此类。学者若据战国文献中引《诗》材料,以探究《诗》之本义,不可不先明此理。
先秦各类文献中出现的许多《诗》外之诗,过去常称为“逸诗”,以示《诗经》对于先秦诗学的严密笼罩。曾有学者统计、归纳各类文献中的“逸诗”,“文物和传世文献不完全统计的逸诗篇数为135篇,占《诗经》305篇的44%。如果加上无篇名有歌辞的《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篇》1条,传世文献35条,其数更多。……如果大量的先秦文化典籍不遭秦代文化浩劫,能保存到现在,其逸诗的数量会更多。”[41]近些年来的出土文献,又有大量发现,如清华简中《耆夜》《周公之琴舞》等不少诗篇,大部分都不见于今本《诗》,不少学者以此来论证《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的合理性(3)代表性论述见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刘丽文《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说》,《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似乎《诗经》的来源可据此而定,鄙意恐言之过早。“逸诗”之称,似乎只是在《诗》的权威地位下对于此类诗篇的认定,而未能真正从此类诗篇的自身特性出发来构建认知。其实只要换个角度,从“诗”的名义泛化这一态势来观察战国以降的诗学,便会发现,这些诗篇中有不少只是类《诗》的文本,与《诗》未必属于同一系统,有些作品明显是在《诗》三百定型后依傍《诗》而成的“衍生品”,若悉数视为《诗》成型过程中的“淘汰品”,无疑会改变《诗》的预设,混淆源流。总体看来,战国时期的“诗”,已明显越出《诗》的范围,不宜将此时的《诗》外之诗都概称为“逸诗”。或者说,《诗》在战国时期已不具有西周乃至春秋时的权威性及由此而来的笼括性。至少在文化层面,“诗”的意涵更丰富、更扩展,在体制和风格上也显得更灵活、更自由了。
从商周时期形成的文化区系来看,王朝文化多以中原文化为主干进行建构。但各地方文化显然保存了更多的地域色彩与国别差异。比如今日所见之战国出土文献,以楚地为最多,览察可知,当时楚地的学术文化风气,相较于当时的中原地区,显然要更为自由。楚地传世文献如《楚辞》的许多篇章,比起《诗经》来,在情感、情绪的表达上都更为热烈;《诗》于战国时期虽屡被称述而时有文化意义之突破,但恣肆终难及《楚辞》。《楚辞》中亦有明标《诗》外之“诗”者,共有四端,除去两篇汉人作品(严忌《哀时命》“杼中情而属诗”与王褒《九怀》“抚轼叹兮作诗”),尚有《九歌》“展诗兮会舞”与《大招》“二八接舞,投诗赋只。”[42]75、221旧注亦有解“诗”为《诗》者,但显然与诗篇语境不合,此中之“诗”当属《诗》文本之外的新辞制作,且与乐舞紧密融合,已成为综合性的文艺表演。这在《诗》乐沦亡的背景下,无疑增添了《诗》外之“诗”的鲜活色彩,为“诗”与“歌”的互通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诗”与“歌”的互通,早已有之,但随着春秋以降礼乐体系的变革与更新,《诗》的文辞意蕴逐渐成为《诗》义的主导,《诗》的表演形态则转为遗响。战国之“诗”重新进入表演场域,成为可以表演的歌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诗》教的继承。且综合性的文艺表演,不仅是多种门类艺术的合作使然,亦与当时不同文化的交流有关。如《招魂》:“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42]210-211此段文字应为当时楚地文艺表演的精细描摹:舞蹈方面,是妙龄女子们的郑舞,舞姿动作亦有形容;音乐方面,既有竽、瑟、鼓等多种乐器激昂的音乐演奏,又有庄重的大吕之声;歌曲方面,既有楚国乐曲《激楚》,又有吴、蔡等地之歌。多样化的表演中,先后出现了郑、楚、吴、蔡四个地区的文化要素,且雅俗并存而共赏,最终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热情,不再拘礼,以至“乱而不分”。可见当时楚地文化存在相当的包容性,不同文化元素及文艺形态可以在同一场合进行“乱炖式”表演。此种文艺表演,无疑体现着战国时期的文化融合。然而,这种融合态势,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楚国在政治、军事上的不断失利,文化融合的进程必然受到影响,甚或是阻碍;秦、楚及东方诸国之间日益频繁的战争,并未给文化整合创造出良好的条件和土壤;秦代虽统一天下,但享祚不长,且文化政策残暴。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很多文化问题,只能留给西汉王朝来解决。
汉武帝“立乐府”而“采诗夜诵”,正是将“诗”作为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这种观念无疑是承先秦之余绪。同时,汉之“采诗”也兼顾了不同区域,具有强烈的文化融合意味。《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叙》:“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16]1756其中谈到代、赵、秦、楚,却无中原地区的明确表述,然而在“诗赋略”中却有“《洛阳歌诗》”“《河南周歌诗》”等名目,说明此时中原地区的文化与王朝文化的主体,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故无需从名目上特别说明。以文化地理而言,汉王朝的采诗,主要是为获取更广泛文化区系的歌诗文艺,以地方文化来充实、丰富王朝礼乐的相关建设。若溯源至战国时期的态势,或可如此表述:战国诗学的丰富多元化形态,尤其是根植于地域特色而各具特点的诗歌创作与表演,为西汉王朝的礼乐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基础;而战国时期的文化融合进程,则最终完成于西汉,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