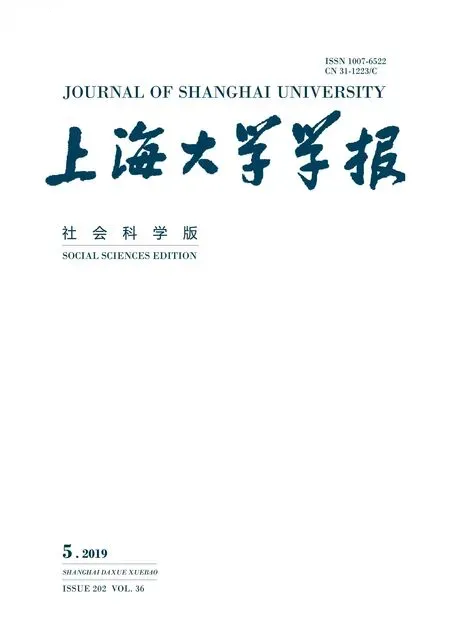基于乡里社会的十六国胡汉民族关系
——以华北与关中地区诸政权为例证
2019-02-11蔡丹君
蔡 丹 君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2)
“五胡乱华”后,胡族政权逐渐林立于北方。考察这一时期的胡汉民族关系,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合作或者对立,而是要看到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的生活联系。毕竟这些胡族政权并非天外来兵,自东汉以来,他们不断内迁,与边疆汉族有着漫长的杂居史;同时,他们也需要在谋求立足的过程中寻求在地乡里宗族的扶助,并颁行与现实相适应的乡里制度以巩固统治。胡主与北方乡里社会之关系,在十六国时期是逐步深化的,而十六国时期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逐步展开的。基于乡里社会的十六国胡汉关系,是当时民族关系、政治关系的重要形式。乡里士人与胡族政权之间在此背景下展开了丰富的政治互动,形成了十六国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为集中论述这些内容,以下主要以活跃在河北与关中诸胡族政权为例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胡、汉同乡关系与胡族政权的建立
自东汉以来,边疆少数民族的内迁之势不可抵挡。仅西晋初年的匈奴,因故内迁者即“至少不下二十余万口”。[1]12早期部分胡族政权的建立,深刻依赖了他们在与汉族杂居过程中所结交的同乡、在地关系。
刘渊从幼年到成为任子之前,生活于并州乡里。刘氏宗族部落“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2]2645并州六郡中胡人人口数量不少,与汉族的融合程度较高。晋阳离上党郡很近,刘渊自幼在此游学,受业于崔游。[2]2645“刘渊父子皆粗知学问,渊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皆是东汉的旧传统。”[3]280在崔游门下,他还与同窗硃纪和范隆有过深层的思想交流。[2]2645虽然刘渊是屠各杂胡,实则与晋阳乡人无异,他获得文化教养的经历,与这个地区的乡里汉族士人没有太大区别。硃纪和范隆等人,后来成为前赵政权的第一批汉族士人。硃纪不仅担任了刘聪的太傅,[2]2657影响了刘聪学养的形成,还与刘氏缔结了姻亲关系——他的女儿入了后宫。范隆“与上党硃纪友善”,博通经籍,无所不览,颇有经学著作,逝于刘聪之世,卒赠太师。[2]2352刘渊所任命的匈奴后部人陈元达,也有类似经历。陈元达“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2]2679在刘渊尚任左贤王时,拒招不至,后又因直谏死于刘聪之手。他以隐士自处,入仕后又好谏诤,文学修养也高,均说明他汉化之深。
刘渊所结交的同乡关系,除了这些早年具有共同生活经历的并州乡党,还有在朝的并州籍权贵。元帝咸熙中(264-265),刘渊为任子在洛阳,[2]2646前后约十年,“晋武帝泰始十年(275)后返回五部接任左部帅”。[4]123刘渊“本人为质子,可见他在匈奴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5]此时其父刘豹势力强大,引起了西晋的戒心。刘豹统一五部是在司马师辅政之初,大致在嘉平三、四年(251、252)间。此后,并州屠各取代了南匈奴,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于是“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2]1534陈勇先生认为,刘渊任子和匈奴分为三率“这两件事并非巧合,应该都是司马氏抑制并州屠各计划的一部分”。[4]119这次任子之后刘渊回到了五部,成为左贤王,并州乡党开始有意与之结交,“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2]2647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其实当时前来依附的,主要是并州乡党,如屯留崔懿之和襄陵公师彧等人。此“二人皆善相人,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2]2646由此看来,刘渊应该也是通过这批乡党,较早结识了王浑。并州太原王浑,乃王昶之子。“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2]2646通过王浑,刘渊在晋廷的地位和声望得到了提高,上党屠各和西晋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进一步壮大力量。王浑甚至曾经救过刘渊的性命。当时刘渊为齐王攸所间,攸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2]2647王浑为之向晋帝进言力保。王浑实际上是刘渊在西晋朝廷中所结交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代表。
刘渊在洛阳所缔结的同乡关系,也惠及了他的儿子刘聪。刘聪同样是“弱冠游于京师”,“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2]2657在洛阳,刘聪“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2]2657,此中应该也少不了王浑的引荐。刘聪颇有才华,能诗善赋。晋帝被俘虏之后,刘聪曾回忆早年造访时为豫章王的晋帝的经历:“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2]2657这里的“王武子”即王浑的次子王济(1)《世说新语》中皆称之为“王武子”,如《言语》篇:“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浑长子早卒,嗣位的是王济。王浑、王济等人盘踞朝廷,势力不可小觑。西晋初年,王濬曾与王浑争平吴之功,所上自理表如此评价:“今浑之支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互,并处世位。”[2]1213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氏在朝中的地位,和匈奴刘氏攀附并州王氏的原因。刘渊长子刘宣,师事乐安孙炎。[2]2653学成而返,也受到太原王氏提携:“并州刺史王广言之于武帝,帝召见,嘉其占对。”[2]2653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渊一族与晋阳王氏一门三代之间的深厚关系。伴随于此,刘氏也与并州乡党中的其他大族建立了一定联系。上党李憙、太原王浑这两位同乡都曾向朝廷表示了他们对于刘渊军事实力和才能的了解。太康中爆发边疆危乱时,他们频繁建议启用刘渊平乱。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树机能攻陷凉州,上党李熹主张“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2]2646刘氏结交朝廷中的并州乡党并且获得他们的支持,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
刘渊建立汉政权后,给汉族士人所留的职位,基本悉属并州乡党:“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族子曜为建武将军;游固辞不就”。[6]2702其中,公师彧在刘聪时期担任过太中大夫,后来见杀于秋阁事件。[2]2671这说明,汉赵胡主和晋末其他汉族领导者一样,十分重视同乡。与前赵同时起兵的山东人王弥,在洛阳歼灭百官,而刘暾因为是王弥东莱掖县之同乡且是“乡里宿望”而独不被杀。其后,刘暾出仕于王弥,为其建言献策。王弥之叛,给晋王朝带来的毁灭之力,不在屠各刘氏之下,《晋书》评之曰:“何丑虏之猖狂而乱之斯瘼者也。”[2]2638但即便如此,曾在西晋身居御史中丞等要职的刘暾,仍然愿意出仕其麾下。其中原因,除了战乱时期受制于人的不得已,同样重要的是他和王弥之间的同乡关系。对乡曲关系的看重,超越了对其他关系的看待。这本是汉族士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但也已经渗透到久居并州、太原、晋阳、上党的匈奴人的意识中了。可以说,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此时人们对待胡汉关系的政治考量,乡曲关系优先于民族关系。然而,虽然并州乡党在刘氏政权中地位突出,但是真正手握权柄的还是匈奴五部贵族,如呼延氏等。汉族士人担任的一般都是文化类职务,并不牵涉要害职务。汉赵国内有“三个相对独立的不同族属的集团”——刘聪“本族”、“汉族人民”及“六夷部落”,其中刘聪本族的军队是核心力量。[7]唐长孺先生也认为:“刘聪在其直接控制区域内建立了胡汉分治的军事化的制度以控制人民。”[8]160所以,并州乡党从属于胡族的地位,主要是这支匈奴政权以单于制为主的军事特性决定的。[9]
除了并州乡党,很少有汉族士人出仕汉赵政权。汉赵政权作为袭破洛阳、长安的第一支胡族政权,被汉族士人视为寇仇,汉人为此拒不出仕。而汉赵政权自起兵之初,便全盘否定西晋政权,这透露出当时胡汉关系的紧张。刘渊《即汉王位下令》中称:“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2]2649他在令中还将声称的“大耻未雪”远溯至董卓、曹氏父子所造成的汉室之辱。晋室之亡,中原士人各怀哀痛,刘渊对晋室的否定态度,事实上进一步加深了胡汉隔阂。因此,汉族人才往往不赴刘氏之征。就连那些与世无争的隐士,如弘农人董景道,博学精究,[2]2355隐居商洛山,“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仍多次征之,“并固辞”。[2]2355即使强征而来,士人也往往二三其心。如刘殷,并州新兴人,每逢征辟,皆以疾辞;[2]2289永嘉乱中,委身于刘聪。刘聪暴虐,刘殷常常告诫子孙不要直谏。作为早期参与到胡族政权中的汉族乡里士人,刘殷感到处理胡汉关系是艰难的:“在聪之朝,与公卿恂恂然,常有后己之色。”[2]2289
刘聪时期的暴政,极大削弱了并州乡党的力量。刘曜《下书追赠崔岳等》[2]2687一文中,有一份追赠名单,其中人士,多为并州乡党之仕刘者。其中“或识朕于童乱之中,或济朕于艰窘之极”之语,正是晋末乱离之后乡党社会中以协作互助为特征的人际关系的写照。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死于刘聪暴政。如中书令曹恂,死于反对刘聪纳后之事。[2]2663-2664又如刘易《谏用宦官王忱等表》,称王忱“知王琰等忠臣,必尽节于陛下,惧其奸萌发露,陷之极刑”。[2]2671但刘聪非但不纳,反而将此表给王忱本人阅看,深辱刘易,使其忿恚而死。刘曜上台后所进行的这一次追赠,算是他对乡党所做的补偿,是一场拨乱反正。这一胡汉的关系变化,体现在刘曜时期对汉族士人多次褒扬和奖赏之中,《下书封乔豫和苞》[2]2688表彰乔豫、乔苞二人对自己纳谏之诚恳,亦是对刘聪暴政的否定。
刘曜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弱冠游洛阳。[2]2683刘聪时,他曾出镇长安。靳准之乱爆发后,自长安奔赴平阳,“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阳奔之,与太傅朱纪、太尉范隆等上尊号。”[2]2684刘曜登位,仍然获得了并州乡党的支持:“以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范隆以下悉复本位。”[2]2684刘曜长期活动于长安,与周边政治势力周旋;随着石勒势力和慕容鲜卑势力的不断扩大,平阳已有受围之危,一旦这些势力联合,刘氏政权将无力抵抗。早在刘聪麟嘉二年(317)二月即有康相上疏《言文》以天象谈及当时紧迫的时势,建议迁都。[2]2674刘曜迁都长安,将匈奴五部与并州乡党也带到了关中。虽然,刘曜表面上仍然尊重这些参与建立政权和扶植自己上位的并州乡党,但是,他已经形成了应对时势的用人主张。当时,前赵政权疲于应付周边地区的多股政治势力:仇池杨难、后赵石勒、流民坞主陈安、前凉张茂等,皆与之交战。[2]2683-2703因此,能够在一系列军事活动中独当一面的人物更受重用。如刘雅,早年即跟随刘曜征战,颇有战功。靳准之乱中,“左光禄刘雅出奔西平”,拒不合作。此后深获信任,奉使迎刘曜母胡氏丧于平阳。攻杨曼于陈仓获胜,使得“(刘)曜振旅归于长安”,遂因其军功被署为大司徒。太宁元年后,刘曜“署其大司马刘雅为太宰,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给千兵百骑,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剑六十人,前后鼓吹各二部。”[2]2684-2693实际地位是非常高的。从前赵政权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并州乡党在刘曜登位后,权力不断式微,但无论是促成刘渊平阳称帝还是扶植刘曜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分析以刘氏为代表的胡族士人在并州乡里私学的教育经历和交游活动,可知他们与汉族人已经有了深度融合。无论是在经学学养还是文学才能的养成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汉族文化的烙印。作为军事色彩浓厚的政权,前赵在建立政权之后,在文学方面疏于经营,但他们不乏文化才华。刘氏诸王皆成长于乡里,并不是刘氏政权自身培养的文化人才,其较高的文学修养,来源于早期在乡里的学习以及在洛阳的游历经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较少。除了我们以上谈到的一些公文文字之外,赋颂和诗歌并没有留下具体篇名和内容。可见,刘氏虽然不乏文学功底,但是在战乱之时也是无暇顾及、经营。同时,刘氏政权之体制,主要仍然是匈奴的大单于制,虽然启用了并州乡党中的寒素汉人,并不依赖他们,更没有拉拢乡里大族。因而在前赵政权治下,文学传统延续性较为微弱,其后都声名消隐。但是,刘氏政权对乡里士人的启用,开启了这一时期胡汉士人合作的源头,而刘氏政权与乡里士人合作的基础是乡党关系。
胡汉之间严格意义上的“同乡关系”,随着胡族政权需要的变化,也将会由更宽泛的同乡关系——“在地关系”来替代,即双方皆为居住于某地的共同利益者,而并不一定是籍贯上的同乡。这一点,在十六国中后期关中地区的氐、羌政权建立过程中尤其明显。前秦和后秦政权的早期经历具有十分相似的一面,他们是在十六国时期经历了长期汉化之后,方才获得北方大部或者局部领土控制权的。石虎征关中时,这两支势力被双双迁徙到了关东地区,分别居住在枋头和滠头。因此,氐、羌在十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一些豪贵,几乎都是在关东出生的,“与苻生兄弟、苻坚兄弟、吕光等同时先后在枋头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氐族豪贵,是后来前秦、后凉的霸业支柱。”[10]而前后秦政权中最为著名的士人王猛、尹纬等人,皆是生活于关陇本地汉族士人,他们共同参与了苻、姚政权的建立。
王猛,原籍北海郡剧县,靠贩卖畚箕为生,晋末大乱之后隐居于华阴山,活跃在关中一带。所谓“隐居”,乃是自高之举,史称其“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2]2930。永和四年(348),东晋桓温入关,王猛为他推荐了河东蜀人薛氏薛强。[11]1323之后,王猛又向苻坚举荐王猛的吕婆楼,即后凉创建者吕光的父亲。苻坚在发动对苻生的政变之前,希望获得吕婆楼的帮助,而吕婆楼自认为不可胜任,并推荐了王猛:“仆里舍有王猛,其人谋略不世出,殿下宜请而咨之。”[6]3163吕氏也是略阳氐人,他与苻氏之间关系深厚。王猛原本地位并不高,类似于吕婆楼的清客。王猛在吕光十岁左右,就已经见过他,并评价曰:“时人莫之识也,惟王猛异之,曰‘此非常人’。”[2]3053这说明他们相识已久,关系密切。王猛得到举荐,主要是依靠他早年在关中地区所缔结的这些关系,亦即他自己所谓的“三秦豪杰”。其他围绕在苻氏家族的硃彤、赵整等人,皆是关陇士人。苻坚之弟苻融“时人拟之王粲”,硃彤、赵整等人“推其妙速”。[2]2934赵整也是略阳人,算是苻坚之同乡。天水人尹纬,在前秦时期因政治原因没有出仕,“及姚苌奔马牧,纬与尹详、庞演等扇动群豪,推苌为盟主,遂为佐命元功”。[2]3005这里的“扇动群豪”所提到的“群豪”,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不断向关中地区回迁的秦雍流民。可见,扶持姚氏政权在关陇地区与苻坚争霸的,仍然是这些本地乡里宗豪。而且,在这之后,尹纬还吸引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关中流民回到长安:“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2]3005在姚氏反对前秦苻登并取得优势之后,甚至于一些早年流亡到南方的关中士人,也开始谋求机会回到长安:“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2]2980这三个流民队伍的首领中,韦华和庞眺其实都是关中人。从以上势力可见,这些关陇本地士人,在共同等待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机会,而苻姚二氏在势力逐渐壮大的过程中,也乐于得到汉族士人的帮助,藉此以扩大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国政权中,并非所有的胡主在起兵时都已注意到依靠同乡关系、在地关系。如石赵统治时期乡里社会的主要形式是坞壁,石勒政权与乡里坞壁之间是一种羁縻关系。石赵政权对“旧族”大加杀伐,不予优待,却对寒素士人倍加信任,石赵政权中出现的名臣续咸、徐光、张宾等人,皆非大族出身。这种社会处理方式,是十六国政权中的特例之一。[12]
二、从流人到宗族:胡主施政与北方乡里社会的恢复
十六国早期胡族政权统治北方,需要考虑整个北方社会的实际情况。永嘉南渡以后,虽然“中州士女”前往南方者十有六七,[2]1746但是仍然有大量宗族留在了北方。然而此时他们大多因为战祸,失去土地、流亡他方。其次,西晋末年以后的基层行政体系完全崩溃,北方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到处林立的坞壁,不再有“乡里”之实。聚拢流人,重新建设乡里社会,是早期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施政方向之一。
当时聚集北方流亡“旧族”最多的,是慕容氏诸燕政权。钱穆先生曾说:“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3]280过去的研究对此讨论颇多。(2)如马长寿:《乌丸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收于《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罗新:《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第4卷,1997年;池培善:《中世东北亚史:慕容王国史》,汉城:一潮阁,1991年再版;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这些研究所达成的共识是,慕容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以及他们的数代子孙,通过出仕诸燕政权,逐渐成为华北名族大姓。北魏入居中原、吞并后燕之后,这批名族又成为北魏政权的中坚力量。正如钱穆先生说,十六国北朝时期和魏晋不同的关键,是“在于基层社会管理的地方性,即由地方大族、地方豪强代表国家来管理和控制地方社会……河北地区的情况也许更加典型”。[3]42
慕容廆政权本来国土狭小,需要不断通过劫掠、攻占周边段氏、宇文氏二部来获得存续。[6]2773至永嘉六年以后方才开始收纳流民。当时,乡里宗族在投靠诸种军事力量以作为乱离时期的庇护时,一般首先考虑的是西晋汉族旧臣,其次才是称臣于晋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最不情愿出仕的,可能是参与破坏西晋政权的胡主。所以北方最初拥有流人最多的本是王浚。“游邃、逄羡、宋奭,皆尝为昌黎太守,与黄泓俱避地于蓟”,但是,“刑政不修,华、戎离叛”。[6]2798乡里宗族名士,对于这项名誉之所以十分看重,是因为在从东汉以来深受“乡论”控制的乡里社会中,家族声誉一向是这些宗族所看重的政治遗产,是“长远之计”。例如范阳李产嘱咐宗族:“当早自为计,无事复陷身于不义也”,[6]2843乃帅子弟十余人间行归乡里。又如邵续一度依附石勒,被王浚评价为“君,晋之忠臣,奈何从贼以自污乎”之后,邵续竟然弃子在石赵而归段匹磾。[6]2838可见晋末的乡里宗族对于自身的政治立场是很敏感的。在晋末诸胡建立政权、无所依托的无奈环境中,频失其主的乡里宗族,最终选择投靠慕容氏政权,存在类似的考虑。慕容氏在晋末之后有着振恤河北的传统,对中原地区也没有发动破坏性的战争,在西晋败亡之后仍以晋臣自居、承认东晋政权的合法性。《资治通鉴》记录了这些流亡士人在不同政治势力间辗转最终归于慕容氏的经历:
初,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抚,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复去之。段氏兄弟专尚武勇,不礼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修明,爱重人物,故士民多归之。廆举其英俊,随才授任,以河东裴嶷、北平阳耽、庐江黄泓、代郡鲁昌为谋主,广平游邃、北海逄羡、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开为股肱,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岌弟真、兰陵缪恺、昌黎刘斌及封弈、封裕典机要。裕,抽之子也。[6]2797
可见,当时前燕慕容氏麾下人物彬彬,堪称十六国聚集乡里宗族士人最盛者,是前后仅有十数位“旧族”入仕的石赵政权所不可比拟的。
慕容氏善于抚接和笼络这些流亡的乡里宗族。慕容廆对高瞻的到来十分重视,而高瞻却一直称病不仕。慕容廆在探疾之时,对他的行为甚为体谅,说他是“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6]2813慕容廆遂宣称要“与诸君匡复帝室”,高举“晋”旗,这与刘氏政权高举“汉”旗,截然不同。蒋福亚先生指出,慕容此举是因为二赵以后民族矛盾激化,所招抚的大量士人皆是原来晋时旧人,需要获得他们的认可。[13]
慕容廆时期汉族士人几乎占据了诸多要职,“任居枢要”,他们往往有着避乱之外的更高政治追求。如河东裴嶷在西晋末曾任荥阳太守,携乡里宗族投靠慕容廆。起初,裴嶷的宗族,应该是不太愿意前往辽东而倾向于南下,而裴嶷向他们表明南下不易,前往辽东则可成进退。[6]2798裴嶷到达慕容氏境内时,“时诸流寓之士见廆草创,并怀去就”,[2]2812正是人心不稳之时,而“嶷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廆甚悦之。以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2]2812之后,裴嶷除了为慕容氏政权提供军事方略之外,还成为改变东晋和慕容氏关系的重要人物。在裴嶷抵达东晋之前,“朝廷以廆僻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2]2812而“嶷既使至,盛言廆之威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朝廷始重之”。[2]2812裴氏曾是西晋大族、“中朝名臣”,正是作为“长史”的他来到南方,方才引起了东晋对于慕容氏前燕政权的重视。晋元帝一度希望留裴氏在江东,但为裴嶷所拒绝。作为流亡士人,裴嶷实现了他最初归附慕容氏政权时的两个目标:“髙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2]2812他显得较为积极和主动,重视慕容氏政权所提供的机遇。而这番出使南朝的经历,也无疑提高了他和他的家族在南方的声誉,这反过来又能促进裴氏在北方政治地位的提高。慕容氏也通过这些乡里宗族的支持,获得了东晋政权对其合法性的相对肯定。如“宋该劝廆献捷江东,廆使该为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玺诣建康献之”。[6]2875早期的慕容氏政权为亲好于江东,故而特别看重旧族,对于东晋的这种要求,恭命顺从。东晋政权于是给予了慕容氏政权多次册封,甚至福及那些留在慕容氏政权中的士人们。[6]2798
由于聚居者日渐增多,前燕立侨郡以统流人。其举措与东晋侨置郡县以居流人大致相似,其中稍有不同的是,前燕十分重视维持这些宗族原本的一些聚居特点。陈寅恪先生说:“流向东北慕容氏治下的人民,在阶级上有士族,有庶民;在籍贯上,有冀、豫、青、并等州人。慕容廆分别为之立郡以统之,并从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辅佐。”[14]这些流民,有一部分本身就是汉族士大夫迁徙时率领的宗族、乡里、部曲和佃客,如渤海高瞻“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2]2812由于短时间内慕容氏政权治下的人口骤然增多,当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2]2823为了扩充土地面积,慕容氏“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并颁布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2]2823的耕地政策,以保证流人骤增之后前燕境内的稳定。至慕容皝时,前燕政权为这些流人重新设置了县郡,“以勃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2]2826这样一来,原来的乡里社会结构得以存留,流亡而来的乡里宗族仍然可以按照之前社会生活的方式聚居。于是,慕容氏政权中集体迁徙而来的乡里宗族,能够形成自己的根据之地。他们在发展的延续性方面,超过了刘氏政权中的那些并州乡党。
前燕政权的这一侨郡政策,使得一部分乡里宗族受到优待,迅速壮大为北方大族。原籍靠近辽西的渤海封氏、乐浪王氏即是其例。慕容氏与渤海封氏之间渊源颇深。永嘉五年(311)之后,东夷校尉封释无力克制众鲜卑之乱,最后依赖慕容氏政权,寝疾时,“属其孙弈于廆”。[6]2733封氏从此成为慕容氏重要盟友。封氏卒,“释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参军抽来奔丧。”[6]2733由于封氏一族势力辐及幽、冀,慕容氏政权亦拉拢二人。旋即幽、冀为石勒所乱,返道不通,二人“皆留仕廆,廆以抽为长史,悛为参军”。[6]2798封氏可谓慕容氏最早合作的乡里宗族。建兴元年(313)是慕容氏在境内建立侨郡之始。“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6]2800为一姓而建“乐浪郡”,且由其本姓人物出仕,基本实现了这一宗族的行政自治。若干年的存续壮大之后,封氏、王氏迅速成为地方土豪,地位几乎不容动摇。之后虽然慕容皝时期曾有渤海人逄约携降人来归,试图取代封氏在渤海的地位,但此事很快平息,渤海太守的位置又回到了“土豪封放”[6]3117的手中。永和八年(352)“燕群僚共上尊号于燕王俊,俊许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国相封弈为太尉”,[6]3121封氏等大族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从此可见,华北大族的形成,与前燕政权的侨郡政策所导致的宗族集聚和养息政策深有关系。在慕容氏政权中较为得志的,主要是原来华北地区即幽、冀的士人,而在石勒时期迁往邺城的秦雍及其周边地区之士人,却无法形成庞大的乡里宗族,无法对慕容氏政权产生真正的影响力。如安定人皇甫真,即石勒时期王擢所说的秦、雍世族之一,在慕容氏政权中并不得志,因谏诤而遭到弃用。[2]2817前燕末年,王猛入邺,皇甫真便见机“望马首拜之”,继而“从坚入关”,迁回离家乡安定更近的关陇地区了。
慕容垂在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叛秦自立,并发起复国运动。这个过程中,留在原籍的河北士人再次成为慕容氏政权争取的对象。宫崎市定先生发现,后燕慕容垂复国之时,虽然有不少的鲜卑和乌桓麇集于大河以北一带,但其主要的郡众,不是鲜卑,而是中原的汉人。[15]33-45但是考虑到邺城战略的长期性,冀州郡县多认为慕容垂不会获得成功,采取观望态度。当时反燕或无所行动的汉族士人有渤海封懿,封孚,封劝,清河崔玄伯、崔逞、崔宏、崔荫,阳平路纂,新兴张卓。复国运动中很少看到汉族士人,倒是慕容氏在幽州、平州地区建立了婚姻关系的可足浑氏,兰氏和段部、宇文部等诸鲜卑、乌丸,屠各、丁零等诸少数民族占主力。[2]3077最后,参加了复国运动的汉族士人有汲郡赵秋,燕郡王腾,燕国平睿、平幼、平规,荥阳郑豁,参军太原赵谦,渤海封衡、封孚等。除了荥阳郑氏和太原赵氏未尝合作前燕,其他皆是在前燕时期就已经在华北地区壮大的乡党。北魏攻占中原时期,河北士人的基本态度是反魏慕燕。很多士人追随慕容氏,有的跟到辽西,有的南渡到了青齐地区。慕容氏政权始终意欲改变乡里宗族势力过分庞大,与朝廷争夺户口的局面,也是造成此番宗族离散的主要原因之一。后燕政权末期,“燕主宝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荫之户,悉属郡县。由是士民嗟怨,始有离心。”[6]3211慕容盛时期,辽西太守李郎在郡长达十年,“威制境内”,“累征不赴”,“以母在龙城,未敢显叛,乃阴引魏军,将为自安之计,因表请发兵以距寇”,[2]3102被慕容盛发现之后灭族。这也是一次乡里宗族对于慕容氏政权的离心之举。但是,仍不排除一些乡里宗族并不愿意出仕北魏。如渤海封懿入魏后,对魏太武帝态度不逊,“对疏慢,废还家”。[11]892广固之战中,昌黎韩范和渤海封融皆被处死,[16]正是北魏打击这些倨傲的乡里宗族的具体行动。但是这些打击,并没有改变整个华北尤其是乡里宗族之后所聚居的关东地区的社会面貌。于是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中才有了一幅这样的宗族聚居的图景:“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高欢)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17]如果要追溯这幅图景的来源,那么最为重要的事情便是慕容氏政权对于这些乡里宗族的扶持,他们的力量是在慕容氏所设置的侨郡中复原、发展和壮大的。北魏建国后,大部分士人来自后燕等地。这种情况以河北最为典型,正是诸燕政权对于河北乡里宗族所采取的政策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胡主在管理北方地区乡里社会过程中,自身身份发生了变化。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胡族政权本身,其实也是较为复杂的乡里宗族。慕容氏政权自身的一些特点,和北方乡里宗族结构内部具有一致性。宫崎市定先生说:“在胡族的国家中,主权者就是其宗族的代表人,国家并不是主权者的私有物,而是宗族全体成员的共有物。因为这种思想浓厚,所以对于国家的政治,宗族的发言权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宗族团结,发挥其异常强大的力量,就会建成广大的国度;但这个团结一旦破裂,宗族中的强有力者各自企图成为主权者,就会招致无穷的分裂。慕容氏的‘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5]81-82由于慕容宗族内部势力错综,慕容氏政权几度四分五裂,最后被北魏所吞灭。
三、乡里选举制度的恢复与胡主的人才管理
从刘氏政权到苻、姚政权,胡族政权与乡党之间的关系,虽然呈现出缓慢发展的特点,但人才的引入逐渐稳定化,而且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北方每逢战乱稍息之时,胡族政权通过逐步恢复选举制度从乡里社会中网罗人才,以保证其发展的延续性。乡里选举制度的逐渐恢复和确立,是北方社会逐渐回到西晋末年以前的行政正轨的重要标志。
先来回顾胡族政权在乡里选举制度方面的情况。直到刘曜迁都长安之后,前赵才开始立学校。在从刘聪所居之平阳,到刘曜定都长安的过程中,并州乡闾流散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刘曜进入关中后,趁着部分战争的胜利,不断向长安迁徙周边乡里大族,例如曾“使乔豫率甲士五千,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2]2691“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2]2694长安的人口获得充实。刘曜在长安兴文教,“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2]2688从史家的叙述来看,“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似乎对学生的遴选标准宽松,因此应该是匆忙之举。但之后刘曜也有“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2]2688唐长孺先生曾推测说:“这些学生虽然泛称‘百姓’,但可以推测必然以他本族豪贵子弟与汉士族为主,而秦、雍大族的被俘正因为他们在刘曜朝身任官职之故。”[8]170事实上,由于史料残缺,很难找到刘氏从太学中发现士人的例子。但公卿之举荐,在当时仍未遁迹。如:“曜时灾异,特甚命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大司空刘均举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问之,(台)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2]2698经学家台产就是由“司空刘均”从乡里直接推举而来的。这样的例子在刘氏政权中存在,但不是很多,可以推知的是此时的制度并不十分稳定,而胡主所期望的人才,往往是咨问灾异的术士而已。这些举动,虽然是为修复被破坏的选举制度,但并不能算成效明显。
相比之下,石勒政权在发展学校、选举等相关体系方面举措更为细密。石勒虽然出身低微,但较为重视文化,立国之后,不但在首都设立了“大小学”,也将学官制度的设计普及到郡国这一层面,教育体系更为完备,吸纳乡里士人更多:“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2]2751同时,对于这些从乡里吸纳而前来襄国就学的年轻士人,石勒颇为关注,“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其后,“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置挈壶署,铸丰货钱”。[2]2729这些行为与刘曜政权设立学校,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时,部分士人的确是从乡里官办的教育选举中获得出仕机会的。“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时大旱,勒亲临廷尉录囚徒,五岁刑已下皆轻决遣之,重者赐酒食,听沐浴,一须秋论。还未及宫,澍雨大降。”[2]2751阎步克先生认为,石赵政权的制度基本上是沿袭魏晋之法:“石赵政权汉化诸制,如清定九品、计吏拜郎、太学试经等等,大抵承自魏晋之法,察举制亦当如此。‘秀异’当即秀才或‘秀才异等’,‘至孝廉清’当即孝廉。其所令岁荐科目与西晋通行之科相同。估计其贤良秀孝之策试,并依上、中、下三等区别等第,分别拜授议郎、中郎、郎中之法,恐怕不是凭空产生,颇有可能是直接沿用了晋朝成规。”[18]可见后赵石勒时所举贤良、秀才、孝廉诸科,以及太学生试经等选官仕途,也应分别具有与之相应的乡品,即与两晋时期相同。
石虎对于石勒时期的选举制度多有继承。石虎也是武将出身,文化水平低,但是对于经学颇为崇慕。《晋书》云:“季龙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2]2774“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除此以外,石勒政权也很重视选举体制的完善。石勒有《下书招贤》:“令公卿百寮,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对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2]2748咸和九年(334),石勒又命王波典秀孝之制度。从石勒末期开始,郡县之中的选举较为混乱,石虎加以了整治:“时豪戚侵恣,贿托公行,季龙患之,擢殿中御史李矩为御史中丞,特亲任之。自此百僚震慑,州郡肃然。”[2]2769另外,石勒时期不太重视与大族之间的合作,而石虎时期则较为注意对乡里宗族的安抚,他在统治期间,扩大了汉族士人的特权。从地域上看,这种特权从原来的河北、中原地区,进而扩大到了关中地区:“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2]2770之前王度对于秦雍士人所负之赋役的上疏,还说明当时秦雍士人尚无特权。唐长孺先生也指出了这种前后的变化:“雍秦大族是平刘曜时的俘虏,此时也和东方大族一样享受免役与选举特权。”这表明“石勒称赵王以后直至灭亡大体上沿用魏晋九品官人之法,对于士族特权予以肯定”。[8]171-172
石虎所颁布的《下书清定选制》进一步明确了选举和考绩的一些细则,并声称沿用西晋九流“旧制”,实行“清定”之制[2]2764。关于“清定”,前人多有研究。张旭华先生认为:“清定工作的主体,应该是中正。石勒在清定九品的同时,也应建立起州郡中正组织。”[19]这就说明,很可能石勒政权在其乡里社会中设置了这样的职位。在石虎统治时期,这种乡里选举制度的最大获益者却并非寒素士人。《晋书·石季龙载记上》称:“季龙以吏部选举斥外耆德,而势门童幼多为美官,免郎中魏奂为庶人。”[2]2769所谓“势门童幼”,即权势高门子弟;“多为美官”,即起家迁转多为清官。这依然是沿袭西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选举陋习。虽然石虎之后免去吏部郎中魏奂之职,仍无法扭转这种风气,但是从客观上看,培养士人,是十六国时期政治与文化走向恢复的重要一步。
前燕时期,慕容氏诸燕政权之胡主,皆慕经学。“(慕容)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2]2842前燕时期重视对乡里大族子弟的铨选和擢用,这些往往是族中有人在朝廷中出任官僚者,他们享有和慕容氏贵族子弟同受教育的机会,其出仕途径也很好:“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2]2840而慕容皝的亲信官僚也是从这样一个体系中产生:“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进入到慕容氏中央统治层面的文人如皇甫真,“攻拔邺都,珍货充溢,真一无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图籍而已”。[2]2860这些情况在过去的研究中多有提及。此外,慕容氏政权虽然大力推行针对地方乡里宗族的选举制度,但制度的真正落实却存在重重问题。
当时的乡里士人对于选举制度的恢复反应强烈,热衷指摘时弊。申绍为尚书左丞时,撰《上疏陈时务》批评朝廷选任地方官定制之失,反对大量委任于拥有部曲宗兵之兵将。[2]2855从文中“今之见户,不过汉之一大郡”来看,当时慕容氏政权实际上所统治的地方组织,是以宗户为单位,舍却了“郡”。其所选之地方守宰,应该大多是拥有宗兵部曲之坞主首领,但是这些人“非但无闻于州闾,亦不经于朝廷,又无考绩,黜陟幽明”,[2]2855因而造成了民生凋敝。而且这些乡闾官员,往往名号繁复,人员众多。因此,慕容氏在中央政权层面所设置的选举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虽然如此,乡里士人对这些制度转化为现实仍然抱有期待,他们应该是有别于那些地方乡里宗族等既得利益者的寒素士人。关于申绍生平,缺乏其他文字记载,他的出身应该并不是华北地区士族。
另有一篇常炜的《上言祖父未葬者权宜铨选》,也值得重视。[2]2838这篇上疏,提到燕之立国,主要的方面皆仿照魏晋旧式,而且在官员铨选方面坚持一条重要的准则:祖父未葬者不可获得官职。但是,战乱造成燕国人口空疏,“孤孙茕孑,十室而九”,且有父子各在异邦者,父死子不能葬,“招魂虚葬”者甚多,故而不容法令如此苛刻,否则无人可选。这篇文章一方面反映了慕容诸燕对魏晋选举制度中的传统规定十分恪守,而另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慕容氏的选举制度实施之难。这说明晋末所发生的大乱以及它所造成的诸多问题,一直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在获得解决。而乡里宗族各拥一方的局面,是诸燕政权始终不能深度展开对于乡里社会的了解和建设之主要原因。直到此时,都不能说慕容氏的选举制度是具有初步恢复的面貌的,他们只是在制度的设置方面又多做了一些工作。
前秦在这几个主要的胡族政权之基础上,实现了对学校和选举制度的完善和恢复。[2]2888其中,“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2]2888一语,反映的正是当时来自郡国的乡里士人,可以前往长安官学中就学的情况,而同时还有一部分学子乃是公卿子弟。将来自乡里的文化士人,以较低标准进行收录,非常有利于长安地区的文化繁荣。但也必须看到,当时的文化水准并不甚高,“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2]2888因此,为了加强对于学校教育的管理,苻坚采取了一月一临的监管方式。这项政策在苻坚统治时期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坚持,成效显著,而且,它是与前秦时期的乡里统治政策相配合而实施的:
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2]2895
可以说,苻坚时期已经实现了对于乡里士籍、学校制度和选举制度的相对修复。而且,苻坚重视从太学之中选拔人才,一次性擢用八十三人之数是较多的。这种全面复兴的局面是苻坚之前的多个政权所未能实现的。长安地区在这种较为清明的政策引导之下,其经济和文化面貌皆开始繁荣,已非晋愍帝据长安时户口仅有百余之时可比。[2]2895苻坚对于学校教育的热情,比年有增,“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署博士以授经。”[2]2897尽量地扩大了接受教育的层面。而这其中最为受益的,仍是那些曾经缺少机会到达中央统治层的普通乡里士人。自苻坚时期开始的对学校、选举制度的大力恢复,对于乡里士人来到长安,重新形成政治文化中心而言,意义极为重大。它使得在乡里士人之中形成一种求学风气,并且提供更为开放的出仕途径。姚苌建立后秦,对于前秦的诸多制度不但未改,而且有深化趋势。姚兴据有长安时,文化兴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姚兴在位时,后秦政权确实达到了全盛局面,当时长安城内,“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2]2979和刘曜时期在长安立学校“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2]2979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四、结论
胡主从依赖同乡关系建立政权,到面向北方流亡乡里宗族施政,再到逐步恢复乡里选举制度,使得十六国时期的胡汉民族关系在具体的乡里社会生活中不断深化。基于此,能够形成对胡汉民族关系的新的认知: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北魏统一北方这段时间内,胡汉民族关系虽然有过一定的对立局面,但更多的是胡汉为了各自的生存而进行诸多方面的合作,而他们的合作是围绕乡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来展开的。胡族的汉化过程、汉族对胡族统治的适应,或曰影响,都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实现的。多民族的融合进程与社会发展的进行始终具有同质的一面,这是在研究民族关系史时需要慎重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