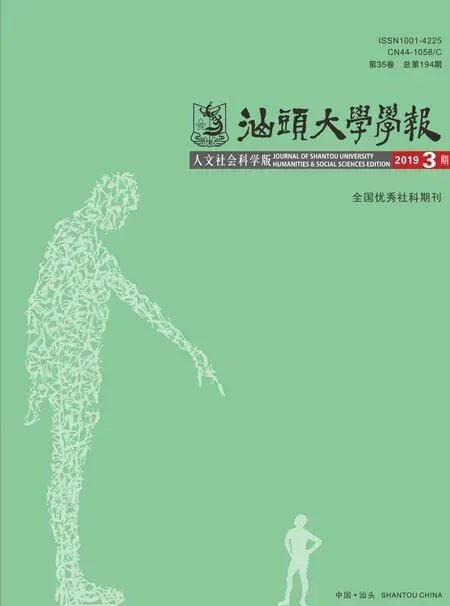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
——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2019-02-11陈文元
陈文元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目前学界对改土归流论述颇多,一般认为改土归流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开发,引起了地方社会的文化变迁与社会整合。这些论述多从国家层面、土司阶层和地方社会的整体视角来探讨改土归流对区域社会的影响,较少从土民的视角来探讨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既包括土司,也包括土民。[1]改土归流所带来的“政治运动”与“移民运动”促使了土民社会转型,对土民社会影响深远。笔者认为,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这一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改土归流在土民社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流官的行政干预与汉文化的影响下,土民利用国家权力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来维护自身的族类边界与社会地位,汉文化的强势进入与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也促使土民选择相应的策略来应对。本文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例,从土民的视角来探讨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的社会转型。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应多关注改土归流过程中土民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一、“容美司”与土民
容美土司地处武陵山地区,是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区。容美土司制度始置于元,至明代趋于完备。容美土司全称“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司”,曾属湖广施州卫管辖,由田氏世袭。“宣慰司”为明代土司中的最高品级,从三品。“(鹤峰)州为容美土司田氏地。元隶四川,明属湖广,其先或称柘溪,或称容美司。”[2]容美土司下领五峰石宝、椒山玛瑙、水浕通塔平、石梁下洞四长官司。明末,容美土司因军功由“宣抚司”升“宣慰司”。清朝定鼎中原,容美土司田既霖向清廷投诚,清廷仍授容美土司为“宣慰司”,统辖如故。容美土司管辖区域较广,拥有众多土民,其鼎盛时期的管辖范围涵盖今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和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大部分区域以及建始、恩施、宣恩的部分区域,是鄂西南诸土司的龙头。
土司是土司地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管辖境内的土民。土民具有亦“兵”亦“农”的“双重身份”特征。在土司境内,土司是“土皇帝”,拥有对土民的绝对控制权。土民是土司的“私有财产”,是他治下的“百姓”,为其驱使差遣。但与此同时,土民除了要接受土司管理、提供赋役外,还要为土司效力,跟随土司外出征战,土民组成的武装力量称作“土兵”。容美土司组建了一支强劲的土兵队伍,并建立了军事组织制度。“容美土司抑勒土民,分风、云、龙、虎等官为旗。旗有长,上有参将、游击、守备、千把总各官,下又有大头目,分管旗长若干千户,皆有执照。至五峰、水浕、石梁各司兵,皆听容美调遣,调以箸则饭至;调以帚,则扫数全出。自高古村菩提寨以西,皆有哨台,有警放狼烟,此起彼应,半日即达於容美司治”。[3]土司统领土民的政治军事结构是土司制度的重要基础。
二、改土归流与土民的选择
经过康熙年间的恢复与经营,清朝国力日盛,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清廷于雍正年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大范围的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起,湖广地区桑植土司、永顺土司、保靖土司等湘西土司相继被改土归流,容美土司等鄂西南诸土司处在被改土归流的边缘,川楚督抚又适时弹压其种种“劣迹”,废除土司只是时间问题。容美末代土司田旻如虽一再申辨,但至雍正十一年(1733)八月,湖广总督迈柱依雍正皇帝谕批,一面派人督促田旻如进京面圣陈述,一面在容美土司周边布置兵力,准备进军容美土司地区。湖广总督迈柱向雍正皇帝奏报称:
至於容美所属土民,众怨亲离,归流念切,土众若得改土之恩旨,皆欣欣向化,得遂云霓之望。即有旻如手下用事数人,孤立无助,料亦无敢狂逞。臣仍钦遵旨,悉心经理,并密扎附近容美之各镇,协密为整备料理妥协,俟临时机调度,不致惊扰。[4]
迈柱作了两手准备,他认为土民是倾向于改土归流的,土民阶层与土司阶层出现了分化,和平改流可行;但与此同时,却又“密扎附近容美之各镇,协密为整备料理妥协”,做好武力改土归流的准备,以保万全。
面对即将被改土归流的事实,容美土司田旻如借处理土司内部事务为由拒不赴京,进驻平山爵府万全洞,并命手下分守平山各隘,试图凭借平山天险、胁迫土民武力对抗朝廷的改土归流。
……奈何一再檄催,及委官守催,犹为赈灾民为词,欺诳奏闻。且於迁延时日之中,与其弟畅如、琰如及中军向日芳,旗鼓田安南等商谋,於拾壹年之霜降日,宰牛歃血,与各土众誓曰:如遇官兵,协力堵御,官不上前,听民杀之;民不上前,官即杀之,等语。[4]423-424
然而,田旻如错误估计了土民的意愿。容美土司“数地人民抗粮结党,携家带眷,将把官亲田文如,头目向玉,黑夜捆缚,尽行逃出,并杀死唐玉虎、覃文荣、金爪等情”,边民逃跑,土民“惊惶朝日,风鹤皆恐”。[4]39-40不久,五峰安抚司下属深溪长官司长官张彤柱率众土民倒戈,投奔夷陵镇控制的渔洋关,缴出长官印及所辖烟户册簿,表示愿入皇朝版籍。是时,中府土民“私相传约”,密谋暴动,容美土司社会出现了分化。土目、土民将田旻如心腹田畅如、向日芳、向虎、田安南、刘冒、仁寿、史东东等拘拿,并使田旻如庶母、正妻下洞,恳请田旻如进京面圣,逼迫他将宣慰司印交与次子田祚南,随后又聚众下山进入万全洞催令田旻如进京。内有土民生变造反,外有朝廷势力紧逼,田旻如最终自缢身亡,结束了容美土司400年的历史。田旻如死后,土民又将田畅如、田琰如、向日芳、向虎、田安南及阉人刘冒、仁寿、史东东、史西西同田旻如之子田祚南、田稚南、田思南等一干人等,及容美土司部印十八颗解赴荆州,公恳改土归流。最终,清廷在“稍用兵”的情况下对容美土司实行了改土归流。清廷在容美土司地区设置了鹤峰州(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和长乐县(今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选用流官充任知州、知县,管理当地的土民。
可以看出,在容美土司被改土归流的前后过程中,土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土民政治转向与改土归流过程中“配合”清廷的行为促使了容美土司被改土归流。“人类集团根据周边集团根据周边环境的变化,在当时条件的制约下,总是去最大限度的争取能量来满足自己的生存。”[5]在整个改土归流过程中,土民作为一个群体,为了博取生存空间,有对自身命运的选择与价值利益的取舍的过程。改土归流后,土民自此脱离了土司时期兵农合一的军政体系,成为“大清”的子民,成为朝廷的“编户”“民人”,这一转换的背后是土民对流官、对清廷的接纳。
三、土民社会的整合与“土俗”的延续
清廷在废除土司后派遣流官对土民社会的治理体现了中央朝廷对土民层面的改土归流。流官的行政干预与随之而来的“移民运动”促使了土民社会的整合,但土民在这一过程中并非被动的“接受者”,在接受流官管理与汉文化的同时选择继续对族类身份的坚守与“土俗”的传承与延续。
(一)土民社会的整合
1.编民入户。土司时期,土民社会主要是由土司设置的旗长、峒长、寨长(称为“土目”)等组成基层政治结构,土民被严格控制在军政一体的社会控制体系当中。改土归流后,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管理,实现对土民的管理与控制,清廷清查人口,编土民入户,实行保甲制度,将其纳入国家直接的政治统治当中,土民由此进入“国民序列”——他们成为了“大清”的子民。“王朝政府登记入籍,目的固然是征税和维持治安,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财政和政治,也是一个文化的议程。”[6]“张家村、观(官)音坡、平山、银硃寨(张家村并入正德坊,观音坡并入茅竹山)、博爱里合为四保”,[7]容美土司平山爵府所在地平山村设为一保。保甲制度“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8]。改土归流后,清廷土民社会改行保甲制度,加强对土民的控制,“保甲之法,一家有犯,连坐十家”,[9]土民被整合进新的政治体制当中。
2.移风易俗。改土归流后,清廷在土司地区纷纷开展“文化革新运动”,容美土司地区亦不例外。鹤峰第一任知州毛峻德上任后,就积极开展相应的文化治理,对容美土司地区的土家族文化多有革除,推行汉文化。(1)禁止土民婚俗,提倡汉族婚俗。毛峻德认为“本州土俗,不知家礼”,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禁止“姑表亲”“同姓为婚”,禁止土民借婚嫁进行勒索、“彻夜恣饮”,“亟宜速改,不得因循,违者必究”。[10](2)禁止土民社会旧俗,提倡汉族伦理理念。当毛峻德获悉“容美旧俗,凡子孙分出另居,即名分火”“旧日土民无子,无论异姓,即立为子”“旧日土民无子,即为婿为子”等“陋俗”时,即以汉俗理念规范之,“祖父母、父母衣食稍有不给,子弟当供奉之。富者勿咅,贫者竭力”,强化土民的供养父母的伦理观念。如果土民“嗣后有无子者,照律先立同胞子侄,次於嫡堂从堂,再从堂依序产侄为嗣……如无子孙,仍按律於同宗应继者……不得以有婿不必另立,绝其宗祀”,向土民灌输严格的宗亲观念与家族化传承“秩序”。[11](3)发展儒学教育,推动文化建设。容美土司地处偏僻,文化教育落后。改土归流后,鹤峰州积极兴办官学、社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得容美僻处楚荒,未渐文教,纲常礼节,素未讲明。不知人秉五常,一举一动,皆有规矩,若不读书法古,举动何所适从。”[12]毛峻德劝诫土民学习汉文汉字,并规定土民子弟七岁以上要入学,如此一来,土民在儒学的教化下,往日“无论亲疏,即外来行客,一至其家,辄入内室,甚而坐近卧榻,男女交谈,毫不避忌”的“陋俗”可尽行更改,“久久习惯,人心正,风俗厚,而礼义可兴矣”。[13]另外,改土归流后的文化建设还包括官方对土民民间巫术活动的禁止。毛峻德曾发布《禁端公邪术》告示,明令土民“切不可妄信罗神怪诞之术,上干法事”[14],违者严惩。
3.推广汉族农耕。改土归流以前,因于地理环境与生产技术,土民多从事游耕,“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是游耕制度”,[15]土民社会处在游耕经济主导下的游耕社会。改土归流后,清廷安抚土民,分田授地,积极推广汉人农耕模式。鹤峰知州毛峻德发布告示鼓励土民耕种无主田地,并称来年如仍空置,将招民开垦:
民间有主荒土,到处尚多未开。原限本年全熟,因何宽缓延挨。来年如有未垦,外地招农进来。不论有主无主,概作官土赏栽。并即发给印照,永远管业不改,敢有执据阻拦,按律计荒究解。此系通详定案,切勿泛视怠懈。[16]
虽然清廷编土民入户,报任升科,但减免了鹤峰州、长乐县头三年的赋税。按理,土民应积极踊跃认领土地耕种才是。但从上述史料记载来看,官方号召土民认领土地垦种,对此政策,土民似乎并不热情,他们或许并不想改变世代以来的游耕的耕作方式,对新的农业耕作方式与制度尚有一段适应的过程。“‘改土归流’前后,土家族土民普遍有一个下山定居的痛苦转变过程。”[17]为此,官府又发布告示劝土民下山认领土地,并命令土民限期开垦:“查得鹤峰、长乐二州县荒芜田地并限三月,令有主者照契坐落细开报认等情……至三月期满,或尚不知有报明指认之事……如逾半年之限无人赴认之土,即照无主官地招民承垦,给管照业。”[18]土民可根据自身劳力多开垦土地,清廷还规定,水田以六年起科,旱地以十年起科,“土民从此长享轻徭薄赋之乐矣”[4]425。在官府的推动下与政策鼓励下,或土民下山开垦土地,或汉族及其它民族进来垦种,鹤峰州大量山川土地得以开发。土民渐从汉人移民中学习到山中沼泽地的开发,提高了农业产量。同时,毛峻德还积极向土民宣传汉人农耕技术与经营理念,如制定“耕凿六则”,发布《劝民蓄粪》《劝民告条》《劝积贮》等告示,引导土民较好地进行农业生产。“改土归流加速了鄂西土家族走向精耕细作农业的进程。”[19]土民社会在改土归流之后经济模式发生转变,由游耕向农耕发展。官方政策的引导与移民的大量进入,还有土民的积极参与与“向化”,是土家族社会在改土归流之后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土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土家族身份的坚守
在改土归流过程,土民并非无条件对汉文化全盘吸收。土民对流官的接纳与迎合是对自我生存一个选择,而对土家族文化的长期坚守与传承则表现出土民社会在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社会转型的多样性,更表现出土家族文化的特质与生命力。
1.土家族文化习俗的传承。与汉族不同的是,土民在除夕前一天过年,俗称“过赶年”。改土归流后,土民提前过年的习俗仍然得以保留,“土司时,于除日前一日祀神过年,今多仍之”[20]。土民以廪君为始祖,立庙以祭之。“向王庙在高尖子下,庙供廪君神像。按廪君世为巴人主者,有功于民,故今施南、归、巴、长阳等地,尸而祝之。世俗相沿,呼为向王天子。”[21]信奉廪君的宗教习俗传沿至今。乾隆《鹤峰州志》载:“旧时土民无子,即以婿为子”[11],流官虽强行禁止,但土民“招赘”习俗并未就此断绝,而是沿袭至今。改土归流以后,鹤峰屏山土民的“招赘”婚姻模式虽然遭到了汉族流官的强烈反对,并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重建了自己的文化系统和礼仪制度,不过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依然排斥汉族的父系血缘制度并保存了招赘婚姻的习俗。[22]毛峻德发布《禁端公邪术》,虽然这一习俗在官方禁令下有所减弱,但依然长期存在。“巫者谓之端公,病者延之于家,悬神像祝祷。又有祈保平安,或一年或二三年,延巫祀神,并其祖先曰完锣鼓醮,一曰解祖钱,此为土户习俗,今渐稀矣。”[21]“乃州属向来土俗,无论亲疏,即外来行客,一至其家,辄入内室,甚而坐近卧榻,男女交谈,毫无避忌。”[13]表明改土归流前土民热情好客,男女交往不受汉俗约束。以笔者之亲历与田野调查感受,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土家族人热情好客的遗风。即便同样的习俗,土民与迁入的汉族移民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灶神信仰)十二月二十四过小年,土著则二十三日夜祀灶神,客户则在二十四日夜送司命上天。”[21]土民日常节日里还有正月十五过元宵,二月初二敬土地菩萨,六月六晒龙袍等,这些土司时期的节日在改土归流后依然长时间流传。可见,改土归流后,流官对“土俗”多有禁止,但并不能禁绝,在土家族地区依然流行,在今鹤峰、五峰等地区仍有存在。“土俗”禁而不绝,表明土民在面对汉文化的强势进入时的选择,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土民对汉文化的“利用”与“抗争”。
不仅如此,土家族游耕、渔猎采集等经济方式的在改土归流后依然长时间延续。游耕、渔猎采集等经济方式在改土归流前是土民社会重要的经济方式。改土归流后的“移民运动”造就了汉人农耕技术在鄂西南山区的大规模发展,但不意味着游耕经济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游耕经济作为土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时间留存。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鄂西南的一些高山地带,仍有较多游耕农业的残余存在,俗称“烧火山”。由于山区的特点与习俗自身的社会属性,土民的渔猎采集经济方式在改土归流之后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咸丰《长乐县志》载:“竹栫,冬月用于取鱼者。渔洋关、水浕、麦庄等保皆有之。其设栫法,于溪流滩口,用石横砌,若闸状,开一口,下用竹编成藩形,合一溪水灌入其中,上复以草,鱼夜出,一入其中,即不能出,曰上栫。栫上有人夜守,遇鱼虾多,一夜可得鱼百余斤。田泰斗竹枝词:‘四围滮滮乱滩声,渔火一星贴浪明,白甲乌鳞都上栫,蓑衣狂卷漏三更。’”[21]这一生动描述体现了改土归流后土民的捕鱼情况。“设县初,山深林密,獐、麂、免、鹿之类甚多,各保皆有猎户。今则山林尽开,禽兽逃匿,间有捕雉、免、狸、獾者,皆农人暇时为之,而饲鹰、畜犬者罕矣。”[21]虽说由于改土归流后,移民增多,导致山林减少,兽类逃匿,但由于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打猎、采集等经济方式仍然成为在汉人农耕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下土民生活的重要补充。
2.土家族身份的坚守。如果从民族识别的角度来谈,土家族是一个较为年轻的民族。但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之所以被识成一个新的民族,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保持与强烈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是重要原因。土家族身份的坚守来自内外因素的推动。
一方面,改土归流后日益增多的汉民引发资源争夺与身份之争,土家族作为“本地人”,自然要捍卫“我类”边界。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废除了“汉不入境,蛮不出洞”的禁令,使得大量移民特别是汉族移民进入鹤峰州、长乐县两地,土、客之分日益明显。我们从改土归流后鹤峰州、长乐县两地食盐用量俱增、土地价格上涨这两个因素可以印证改土归流后容美土司地区迁入了大量的移民。因此,鹤峰州、长乐县“由土司时期世居的土民融合外来民族或二者相互交融的局面,转变为移民(特别是汉族)不断融合土民的局面,造就了不同往日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分布格局”[23],在这一状况下,如何保持自有“领地”不被抢夺,同时又能在新的政治体系下合法拥有,土著身份无疑是最佳选择。土、客之争成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地方争端的一大缘由。“土、客文化、习俗间的差异在交往中亦凸显出来,‘我者’、‘我类’与‘他者’、‘他类’间的区别、界限应运而生。”[24]汉族移民所携带的“汉文化”与“汉人”身份的优势,以及对地方资源与土地的占据,更易引发土民对自身“土著”身份的坚守。
另一方面,虽然在改土归流后流官对土民社会实行“编户齐民,报认升科”制度,并发布《禁乘丧讹诈》《禁肃内外》《禁端公邪术》等,企图革除土民“旧俗”,土民为摆脱土司的束缚而选择与清廷“合作”,一些土民积极学习汉文化,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但我们应该看到,土民这一态度的转变既有对“田土王”的背弃,也有为改变文化形象、踏入主流社会的利益驱使,出于社会资源、身份地位而主动选择学习汉文化,但此举并不意味着土民对汉人身份的完全认同。从土家族传统文化在改土归流后仍然保持,以及对应至现今土家族的民族识别与土家族民族认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与土家族身份的内在文化边界。一言以蔽之,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有时不可同一而语,二者也并非协调一致。
四、结 语
在容美土司改土归流过程中,土民选择背叛土司,对清廷、对流官的接纳以及流官对土民社会的顺利改革,从侧面反映了土民为踏入主流社会、追求王朝政治身份与政治参与的意愿。不可否认,改土归流抑制了土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汉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处于弱势的土家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土民在这一过程中并非被动的群体,无论是一开始废除容美土司制度、革除田氏土司家族势力,针对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接下来对土民社会的“编户齐民”与“移民易俗”,针对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既是“接受者”,也是“掌控者”。正是来自民间的力量,土家族文化在处于弱势形态仍能与汉文化的进行“互动”与“对话”,最终使得土家族文化在改土归流的汉文化冲击浪潮中得以传承与延续。
在对社会转型的理论研讨中,英国人类学家维多克·特纳把社会看作是交融与结构的辩证统一,“阈限理论”为我们描绘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理论模式:“分化”-“阈限”-“整合”,是结构与反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25]以笔者行文的论述与论证,随着改土归流进程日深,改土归流的“政治运动”与“移民运动”逐渐引发了土民对自我身份的坚守与族类边界意识,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从这一层面来说,从土民视角来阐释会发现改土归流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并非单向,社会转型过程中“整合”也并非唯一,土民在经历改土归流的“阈限”过程之后,我们既看到了土民社会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也看到了土民对自身族类身份的坚守与土家族文化习俗的传承,而这也正是土家族文化得以延续并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