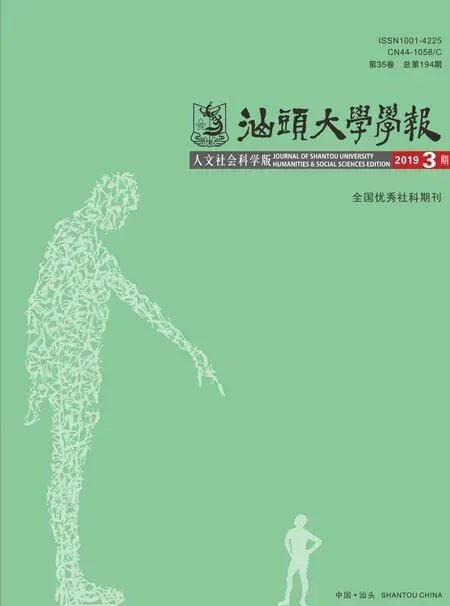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2019-02-11欧阳春勇
欧阳春勇
(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8)
康熙年间方苞论文标举“义法”,经刘大櫆“神气音节”说补充发展,至乾隆时期姚鼐进一步推衍发展形成系统理论,陶铸而为有清一代最大的古文流派——桐城派。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言:“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史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1]310这一看法,是相当公允的,由此可见桐城派之兴盛。
可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有盛极而衰之日,桐城派传至姚门弟子之时,因时移世易,门庭盛大之像中也毋容置疑地隐含转向衰颓危机,到姚门四大高足相继谢世,其衰微之势更是无可阻逆。虽然此时流派人员益众,流布更广,创下“自淮以南,上溯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尽会稽,南逾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2]212的局面,但是,嘉道以后,民族灾难和阶级矛盾日益深重,桐城派那种用规范、雅洁的古文阐释宣扬并践履程朱理学的做法于巨变的时局已不合时宜,因为大清王朝鼎盛气象早已烟消云散,代之而来的是内外交困的阴霾笼罩着整个清朝的天空。何况此时派别内部传衍既久,已入定势因袭而难出新境的困局。盛世要求文学歌功颂德,点缀太平;衰世亦期文学扶危济困,拯时济世。中国文学血脉自来就流淌着文学经世的虔诚,尽管这是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
桐城派一班舞文弄墨的寒微书生,习惯于写些淡素雅洁之作,难以担当振世之时需发雄豪排闼之歌的重任。危困局势呼吁命世豪杰,既挽狂澜,又兴文派,这一双重任务落在了最佳人选曾国藩头上。曾氏不仅政治事功显赫一世,对桐城古文也有别样会解,因时顺势加入“经济”以阔其堂庑,药救桐城空疏之病,宏通卓识,兼收并蓄,倡导济世雄文,弥纶群英,陶铸才杰,振起桐城文脉,因曾氏及其曾门弟子无论思想还是创作对桐城派而言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赢得“湘乡派”名号。
一、问题的提出
那么,从古文流派必备要素论,“湘乡派”能否成立,其究竟又有何特异之处?与之紧密相连的,湘乡派与桐城派之关系当如何厘定?如要研究湘乡派文学,这些既密切与论题相关又非常有助认识清代古文的关键问题均无法回避。尽管自问题产生以来,学界已有一些局部探索成果,但专门做整体剖析的研究努力至今仍然很薄弱。鉴于这一论题的复杂所在,本文先就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做一番详细的学术梳理。
二、湘乡派之得名始末
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详发表于上海《国粹学报》第4卷第12期之《论桐城派》一文:
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侧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3]888
李详敏锐地捕捉到了曾国藩古文与桐城派在师法典范和行文风格两个方面的差异,进而明确提出“湘乡派”称号,并依姚鼐四大弟子之说,指出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和薛福成为曾门四大高足,确定了湘乡派核心成员。其实,与李详几乎同龄的近代同光体诗派巨子陈三立对此亦持同一论调,其作于民国十一年(1922)的《赠袁伯夔》诗中,有言:“武烈翊中兴,楚材冠当代。文派亦俱昌,沿流等起废。湘乡接桐城,雄跨欲无对。羽翼郭与吴,云龙瞻进退。”[4]621诗句中的“湘乡”当指曾国藩无疑。陈氏既肯定曾国藩的武功中兴清廷,又夸赞其文学振起桐城,并以郭(郭嵩焘)和吴(吴敏树)为曾氏之羽翼。诗作虽未明言曾氏开派,但已隐约可见作者对湘乡派轮廓的勾画。
随后曾国藩创湘乡派之说,在一大批民国著名学者那里得到呼应。湘人李肖聃《星庐笔记》强调:“公(曾国藩)于文章具有大志,其始虽启于姚氏,而其后力能独立,自成大家。虽称姚为百年正宗,而惜其才弱少雄直之气,不厌人意。是公于姚氏尚有微词,奚肯低首于梅氏哉?而学者之论桐城,以方、姚、梅、曾并列,而不知湘乡早已别异桐城,自成宗派也。”[5]64李氏抓住曾国藩不满姚鼐、梅曾亮才弱少雄直之气立论,认为一般学者将曾氏与方苞、姚鼐和梅曾亮并列于桐城不妥,因为曾氏不仅“早已别异桐城”,而且“自成宗派”。此处虽然作者并未明确提及“湘乡派”字眼,但我们都不会质疑自有“湘乡派”在作者心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里对之则有更清晰的表述:
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侧其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为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言寒涩枯窘之病。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伟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至欧阳修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势不能复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故能卓然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6]19
显然,钱氏对曾国藩及其湘乡派的评述参照过李详《论桐城派》文中相关论点,但论述的更为细致。概而言之,要点有三:(1)曾国藩古文凭“雄直之气,宏通之识”见长,并对桐城派的“懦缓之失”起到纠偏补弊作用;(2)曾国藩虽“自称私淑于桐城”,但无桐城诸老“徒以一宗欧、归”的偏狭,古文能“以汉赋之气运之”,创桐城派所缺少的“雄奇瑰伟之境”,实已“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3)曾国藩不仅古文创作“能卓然为一大家”,而且论文取经“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又凭据高位,“门弟子著籍甚众”,造就了“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的兴盛局面。陈柱《中国散文史》指出:“国藩尝自谓粗解古文由姚氏启之,列姚氏于圣哲画像三十二人中,可谓备极推崇矣。然曾氏为文,实不专守姚氏法,颇熔铸选学于古文;故为文词藻浓郁,实拔戟自成一军。”[7]292陈柱承认曾氏对姚鼐的尊崇,但认为其文熔铸选学,词藻浓郁,实已越出姚氏藩篱,于桐城派外“自成一军”。显而易见,此处“自成一军”,意实等同于“湘乡派”。
湘乡派自晚清得名以来,至民国以降,在学界一直都有认同的呼声。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指出曾国藩在京师与梅曾亮谈文论艺时,对桐城派已“慨然有振兴之意。其后洪杨事起,乃益罗致当时文人于幕府,用相切磋。于是桐城派遂再振。然此时所谓桐城文派,已非昔日之旧”,认为“胡适以湘乡派目之,盖有故焉。”[8]69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坚称:“至于铺叙‘文治武功’,驰骋震荡,此方、姚、梅之所不能为亦不屑为的,而‘湘乡’独善其胜。变柔为刚,雅而不洁”“把朴实清新的教师文章的‘桐城文派’变为古董式的‘庙堂文学’。”“且在当时位高名重,又颇好士,‘幕府豪彦云集,兼包并罗’,‘陶铸群英’,当时文士,多出其门,因而自成一派。”[9]149甚至觉得“有人说:曾国藩‘中兴’了‘桐城派’,其实非是。”,因为“曾国藩正是在‘桐城派’最主要的一点上,改变了‘桐城派’的精神面貌。”最后吴氏总结说:“‘桐城’自‘桐城’,‘湘乡’自‘湘乡’,‘桐城’与‘湘乡’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若“看不出这种区别,就把握不住‘桐城’的特点。”[9]150熊礼汇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则言:“湘乡派是以其领袖曾国藩籍贯命名的古文流派,派中成员均为其幕僚,并非曾氏同邑之人。当时其幕僚善古文者甚多,成就突出的是张、吴、黎、薛。”[10]520随之,作者将湘乡与桐城两派在“学术思想”“文风取向”“文境之美”和“行文之道”四个方面做了细致比较,得出结论:“湘乡派乃一承袭桐城派基本文学主张而又努力补救其失的古文流派。”[10]535
湘乡派除了在上述有代表性知名学者个人学术研究视野里受到关注,尤其是在现行通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教材里亦见书写。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册),其中第八编第七章第二节论述清后期的散文时指出:“清后期散文,主要为两大流派,一是由曾国藩所领导的承桐城派余绪的‘湘乡派’;一是由梁启超所提倡的‘新文体’。”[11]592编者不仅肯定曾国藩针对桐城派的偏执迂腐所作矫正,而且对负一时文名尤著的“曾门四弟子”亦有评述。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亦曰:“姚门诸弟子之后,桐城派为曾国藩(1811-1872)及其弟子活动的时期。”曾氏“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并肯定曾门四大弟子的文章成就,指出他们“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给桐城文带来了新气象”“尤其是后者,以新奇的事物与略带变化的文风,形成湘乡派文的一大特色。”[12]453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卷)有言:“梅、管、方、姚之后,桐城派的阵脚已不免散乱,尤其经过太平天国在东南一带的活动,对桐城派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也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所以曾国藩在久而不闻桐城诸老声欬感叹之余,又“以努力重振旗鼓自任”,“故以他为中心的文派也称湘乡派。”[13]427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湘乡派在一定程度已为学术研究界所接纳。其得称名,根本而言,主要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群古文家无论是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方面能够“拔戟自成一军”,以至得到世人的认同推重。虽说李详以一位优秀学者特有的敏感,首先揭橥其名,但其不过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如实认识,不是突发奇想,凭空架构。
三、湘乡派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文的别树一帜,因为是相对正统桐城古文而言的,所以大凡论及湘乡派,总是离不开湘乡与桐城两派之关系问题的探讨,又因该派领袖人物曾国藩对桐城派文有相当程度之推崇,甚至口称:“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14]152-153由此一来,则曾国藩、湘乡派与桐城派三者关系扭结在一起,致使问题更显复杂,视个人对问题理解不同,意见亦随之纷纭。
归纳而言,大要可分非此即彼两类意见,两大类之中又可分出彼此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类是否定曾国藩开创湘乡派。在此前提下,一种看法认为曾氏不属于桐城派,如曾国藩身前好友吴敏树对曾氏《欧阳生文集序》将其归入桐城派中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在与友人欧阳兆熊信函《与筱岑论文派书》里声称:“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柳不师韩,而与之并起。宋之后则皆以韩为大宗,而其为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最后坚称:“果欲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引者按:指曾国藩,其时任兵部侍郎职)之心,殊未必然。”[15]394-395从中不难看出,吴氏对宗派之说不以为然,认为韩愈尚不可创派,又遑论后人,并且揭出曾国藩绝非甘心俯首姚鼐隐情,当然亦非桐城派中人物。又刊刻于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张氏在这本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中胪列清代古文家文集时,以“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三种分类加以统摄,其中曾国藩被列入“不立宗派古文家”之类,而与被归入“桐城派古文家”的桐城三祖及刘开、陈用光、吴德旋等姚门诸高足区别开来。可见张之洞认为曾氏既不为桐城派笼罩,也未自立宗派。
一种看法坚持曾氏归属于桐城派,如辑成于光绪八年(1882)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其《例略》有就宗派问题写道:
自惜抱继方(苞)、刘(大櫆)为古文学,天下相与尊尚其文,号桐城派。……姚氏见之真,守之严,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规矩准绳,不可逾越,乃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说,起于乡曲竞名者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浅学者据以自便,有所作弗协于轨,乃谓吾文派别焉耳。近人论文,或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疑误后来,吾为此惧。更有所谓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与![16]2
表面看来,好像王氏非难文学流派之说,其实不然,他是不能接受“以桐城、阳湖离为二派”以及“有所谓不立宗派”的划分,对桐城派则是坚信不疑的,桐城派文在其心中俨然成为最高规范,“如规矩准绳,不可逾越。”王先谦此论是针对时间稍早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划分清代古文派别作出的质疑,因为张之洞未将曾国藩列入桐城派中,而是归入了“不立宗派之古文家”类。曹虹先生对张氏《书目答问》的古文划派持谨慎肯定态度,在其《阳湖文派研究》中指出:
其实,《书目答问》标“不立宗派古文家”,是其史识所在,如其中所列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包世臣《安吴四种》、龚自珍《定庵文集》诸家之文,无疑是很难归于某种宗派之中。这一类古文家的去取当然仍可斟酌。[17]2
而在王先谦看来却是:“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曾亮)郎中、曾(国藩)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姚鼐)遗绪,赖以不坠。”[18]33显然,王氏主张曾国藩不仅应入桐城之列,而且还是桐城功臣。又初刊于光绪十八年(1929)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本着桐城文学蔓延天下的指导思想,将“上至明代归(有光)、唐(顺之),下逮近世马(其昶)、姚(永朴、永概)、贺(涛)、王(树楠)诸老,以致当代之章士钊、于省吾,凡六百四十余人,其中既有桐城派,亦有阳湖、湘乡两派;而三派之外(如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所说之‘不立宗派’古文家)”[19]3,统统纳入桐城派师承传授格局之中,其对别立阳湖派之说有如下看法:
(张)惠言、恽敬、陆继辂、吴育、包世臣、张曜孙皆尝言常州文学传自桐城,并无角立门户之见,自张之洞《书目答问》出,始有桐城、阳湖两派之说,王先谦、孙葆田、马其昶皆不然其说,可谓卓识闳议。不知当日编纂《书目答问》者实为江阴缪荃孙,以乡曲私情分别宗派,引以为重。[19]201
需要澄清的是,江阴(属常州府)缪荃孙虽然在《书目答问》成书过程中有随同助理之功,但书的作者不能因此就不是张之洞,那么全书发凡起例、去取标准的拿捏反映出的学术水准自然也应归属张氏。刘声木“以乡曲私情分别宗派”来指责“有桐城、阳湖两派之说”的划分,是于史实不符的。而刘氏出此失实指责,显然是基于“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顽固观念。其对阳湖派成立持否定态度,也不认同清代桐城之外还有其他古文流派,湘乡派自然概莫能外。关于曾国藩的归属派别问题,刘氏认为其“论文宗旨近祖姚鼐,远祧归有光,为文义法取诸桐城”,虽然“益闳以汉赋之气体,亦颇病宗桐城者之拘拘于绳尺”[19]180,但无改属于桐城属性,所以将其列在卷四姚鼐条下,拟作姚门弟子看待。
另一类是肯定曾国藩创立湘乡派。基于此前提下,一种看法强调两派相承的一面,倾向于视湘乡派为桐城派的旁系别支。如李详《论桐城派》指出曾国藩文先从姚鼐入手,后虽“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3]888陈子展(原名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在肯定湘乡派与桐城派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后,曰:“阳湖派出于桐城派,力矫桐城派气体的纤弱;湘乡派出于桐城派,力矫桐城派规模的狭小。惟以湘乡派后出,中兴了桐城派,更发扬而广大之,替桐城派争得不朽的荣光。而且湘乡派在最近几十年古文界的势力最大。”[20]79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认为:曾国藩“中兴桐城文派,固非其一人之力能办,实由其幕府宾僚及受业弟子共成之也。”“曾国藩之湘乡派——桐城派之别支,影响中国文坛垂数十年”,但“曾氏既殁,古文之命运又衰矣。”因“曾派文人”“皆不能继续曾氏”“盖桐城派全盛时代已过,曾氏之中兴之也,世所谓病人回光返照而已。”[8]75周颂喜在其论文《篡统乎?继统乎?———论湘乡派与桐城派之关系》中强调:“曾国藩和他的湘乡派,与姚鼎与桐城派是一脉相承的,是忠实地以姚氏为宗,以桐城为派的。”所以“曾国藩的湘乡派是继桐城派古文之统,不是篡桐城派古文之统。”[21]116熊礼汇在《明清散文流派论》中亦曰:“湘乡派乃一承袭桐城派基本文学主张而又努力补救其失的古文流派。承袭,缘于彼此学术宗尚相同;补救,则与曾氏等人特殊的政治地位、‘经世’体验、古文修养、审美观念以及所受时兴文学思潮的影响有关。”[10]535
一种看法强调两派相竞的一面,倾向于视湘乡派为摆脱桐城派影响而发展的独立文派。如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指出:“有人说:曾国藩‘中兴’了‘桐城派’,其实非是。曾国藩正是在‘桐城派‘最主要的一点上,改变了‘桐城派’的精神面貌。”强调:“‘桐城’自‘桐城’,‘湘乡’自‘湘乡’,‘桐城’与‘湘乡’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9]150。舒芜在《曾国藩与桐城派》一文亦言:“与其依桐城派某些人之说引曾国藩为‘中兴元功’,倒宁可说曾国藩实以湘乡派取代了桐城派之统,干的是‘田氏篡齐’的勾当。”[22]154作者还进一步理论提升总结道:
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即“正宗”的文学流派,本来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某一个王朝服务得很好,但后来历史条件大变,王朝统治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个文学流派原来的一套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新需要,它的“正宗”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这时,如果这个流派中的人们不肯或是不能改弦更张,便会有大力者从外面来改造。这个改造的程度之大,有时竟会使这个流派表面上似乎得到了“中兴”,实际上倒不如说已经改成了另一流派。[22]156
万陆在其论文《曾国藩与湘乡派》中说:“湘乡派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历史面临根本性转折时期,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它标举桐城‘义法’,但实际上却摈弃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基本观点,而力主‘文章与世变相因’,以‘经济致用’相号召”,认为曾氏“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的做法,“说穿了就是打着桐城派的旗号,贩湘乡派私货”[23]69,认定曾国藩在文学上别有“雄图”。
综上之言,可见曾国藩、湘乡派与桐城派三者关系之纠结。围绕派别成立与否及其湘乡与桐城两派关系,随之意见众说纷纭,甚至观点完全相左,反映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此种情形,似乎为其他流派研究所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