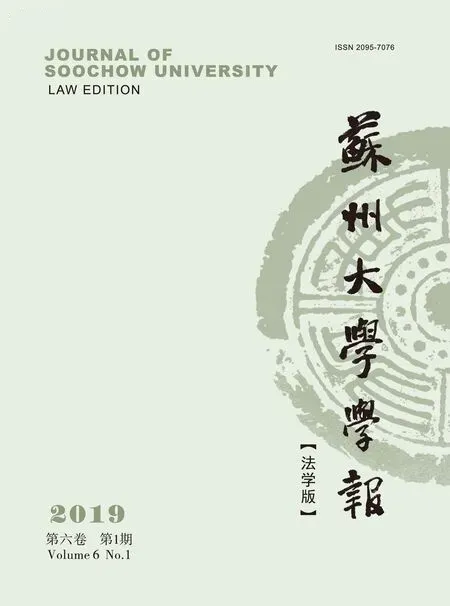侵占罪保护法益的反思与修正
2019-02-11马寅翔
马寅翔
一般认为,法益之于构成要件具有解释论的功能,“对某个刑法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理解不同,就必然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解不同,进而导致处罚范围的宽窄不同”[注]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217页。。就侵占罪的保护法益与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解释而言,这种见解同样适用。鉴于此,努力澄清刑法学界关于侵占罪保护法益所作的种种误读,并进而提出更为妥当的见解,就成为一项极富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工作。
关于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德国当今刑法学界毫无争议地认为是物品的所有权,因而只有所有权人才能成为侵占罪的被害人,即便是在物品交由第三人保管或者是由第三人交由他人保管的情况下,也概莫能外。[注]Vgl. Albin Eser/Nikolaus Bosch, in: S/S-StGB, 29. Aufl., Verlag C. H. Beck 2014, § 246 Rn. 1; Olaf Hohmann, in: MK-StGB, 3.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7, § 246 Rn. 1.与德国这种意见较为统一的情形不同的是,关于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在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相关刑法理论中,却至少存在所有权说、所有权+信任关系说、原占有人之占有利益说与财产所有权行使可能性说等四种主张。[注]参见高金桂:《侵占罪之构成要件分析》,载《月旦法学杂志》2008年第12期。其中,所有权说是我国大陆地区刑法理论的通说。[注]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8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11页。尽管这些见解在各自看来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结合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却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不足,由此导致在我国刑法语境下,这些观点所提及的对象均无法担当侵占罪保护法益的重任。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主张,以求为侵占罪的准确适用提供足够的理论智识。
一、现有各种理论主张的检视
(一)委托关系并非侵占罪的保护法益
对于我国刑法理论通说的主张,即侵占罪的保护法益为公私财产所有权,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除所有权外,财产性利益的所有以及委托关系亦属于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其中,财物的所有权是首要的保护法益。[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66页。另有学者则将委托关系称之为诚信关系,并同样认为其属于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注]参见于世忠:《侵占罪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93页。这种见解与日本刑法理论对侵占罪法益所作的理解相似。如有日本学者认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是所有权以及委托关系。所有权属于第一性的保护法益,委托关系是第二性的保护法益。其中,委托关系属于“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以区别于不存在委托关系、仅侵犯所有权的侵占遗失物等罪。[注]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337、341页。就日本刑法的规定而言,将委托关系视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并不成为问题,但在我国刑法规定背景下,将其视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却会产生以下不合理的现象:
1.导致侵占对象范围的不当缩小。将委托关系视为侵占罪的法益,是日本刑法学者根据日本刑法所作的理解。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将我国《刑法》第270条第2款规定的侵占遗忘物、埋藏物等同于日本《刑法》第254条规定的侵占脱离物,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其会导致无法将遗失物[注]就遗失物与遗忘物的关系而言,笔者赞同通说的观点,认为两者并非一物二名,而是存在显著的区别。但是,笔者并不支持以原占有人的主观心态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而是认为应当以财物的遗留领域属于个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作为判断标准。遗留在个人领域的,如个人的住宅、储藏室、私家车等地方,属于遗忘物,此时财物归相应领域的支配者占有;遗留在公共领域的,如商场、银行、机场等地方,属于遗失物,此时财物处于丧失占有的状态。具体论述,参见马寅翔:《侵占罪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届博士学位论文,第67页以下。以及基于无因管理而占有的他人财物等情形涵括在内,因为这些情形中都不存在所谓的委托关系。如果将委托关系视为保护法益,则这些情形就会因未侵害法益而不能被作为犯罪来处理,这显然不当地缩小了侵占罪的处罚范围。
2.无法与侵占行为的本质保持一致。关于侵占行为的本质,存在着取得行为说与越权行为说之争。从我国刑法要求“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交出)”来看,取得行为说更为合理。既然侵占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取得行为而非越权行为,破坏委托信任关系的僭越权限的行为就根本不属于侵占行为。由此可见,将委托关系视为侵占罪的法益会与侵占行为的本质相龃龉。
3.无法合理解释为何侵占罪的法定刑轻于盗窃罪的法定刑。如果认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和委托关系,而盗窃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和占有,由于占有与所有权存在着紧密关系,而委托关系与所有权则性质迥异,那么侵占罪的法定刑就至少不应当轻于甚至要重于盗窃罪的法定刑。然而,我国刑法规定的侵占罪的法定刑却明显低于盗窃罪的法定刑。由此可见,将委托关系视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会导致无法合理解释为何侵占罪的法定刑会轻于盗窃罪的法定刑。
(二)原占有人之占有利益说的缺陷
原占有人之占有利益说认为,行为人占有他人之物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原占有人移转占有;另一种是非基于原占有人移转占有,如脱离物占有。无论哪种原因,行为人均负有将所持之物返还给原占有人的义务,从而使原占有人恢复其本来的占有状态。因此,行为人将所持之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实际上就侵害了“原占有人恢复占有该物之财产利益”。为便于理解,论者进一步举例加以说明:甲借用乙的机车至电影院观赏电影,将机车寄存于电影院旁的寄存处,如果该寄存处的管理人擅自将该机车据为己有,则该管理人所侵害的是甲对该机车所享有的占有利益,而非乙的所有权;而且犯罪被害人是甲,而非乙。至于甲应当如何赔偿乙的损失,则为民事上的损害赔偿问题。[注]参见甘添贵:《刑法各论》(上)(第2版),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90页。需要说明的是,甘添贵教授在其著作中使用的是“原持有人之持有利益说”这一表述。考虑到大陆地区学者的使用习惯,笔者在引用时将“持有”改为“占有”。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根据台湾地区“民法”第468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借用人依照约定方法或者依照物的性质而定之方法使用借用物,致使物品发生变更或者毁损的,不负责任。在上文所举案例中,甲已经尽到了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根据“民法”规定对其所发生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这就意味着甲并不会因为机车被他人侵占而遭受任何法律上、经济上的损失,将其认定为被害人的做法值得商榷。再者,民法中存在着所谓的占有改定,表明所有权之行使也不以占有物品为必要。例如,甲将一幅名画卖给乙,但并不交付该画,双方签订合同将该画租给甲继续使用,乙计划待该画升值后将其转卖他人,到时甲不必返还该物,而是根据有关指示交付之规定,将返还请求权让与给买主以代交付而转移所有权。后来甲将该画占为己有。在该案中,所有权人乙从未占有该物,仅因为这一原因就不保护其所有权,从而与原已取得占有因而予以保护的情况差别对待,也欠缺合理依据。[注]参见王效文:《论侵占罪之持有与侵占行为》,载《月旦法学杂志》2012年第7期。
上述分析足以揭示原占有人的占有利益说的不足。就侵占罪而言,看不出单独保护原占有人的占有利益有何超越所有权的特别之处。并且,从论者所举案例来看,这种主张实际上人为地增加了处理案件的难度,使权利恢复程序变得过于繁琐。本来,丙作为犯罪行为人,直接向乙承担相关民事责任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先向甲承担责任,再由甲向乙承担责任。此外,将侵占罪的保护法益仅限于占有利益,只是对占有的机械把握,这种做法割断了占有与所有权之间的联系,无法还原所有权内容的全貌,过于限缩刑法的保护范围。鉴于此,原占有人的占有利益说亦不值得提倡。
(三)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可能性说的不足
该说认为,虽然一般认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的所有权,但是所有权并不会因为刑事不法行为而遭受破坏,即使所有人不能行使其所有权,其所有权的主张仍旧存在,并不会因为所有之财物遭受侵占,其所有权即行损坏。如欲解除所有权人对于财产的所有权,仅能通过法律行为方可实现,非法方式并不能动摇所有权的法律效力。因此,侵占罪所侵害的,并非财产所有权本身,而应当是对财产所有权的行使或主张的可能性,亦即所有权人对于所有财物的使用、收益、处分,因侵占行为而致其行使或主张可能性受到障碍。鉴于此,刑法对于侵占罪所侵害法益,不应以所有权定之,而应以所有权之行使或其主张可能性作为保护法益,亦即权利保障者,并非权利之本身,而是权利之实现。[注]参见柯耀程:《刑法问题评释》,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45-146页。对此,在承认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是所有权的前提下,德国曾有学者也认为所有人对于其物品的处分权是更为精确的说法。[注]Vgl. Karl Binding, BT 1, 2. Aufl.,V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 1902,S.255.
这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法理论的主张相吻合。根据近代以来的民法理论,作为民事权利之一的所有权具有观念性。所谓所有权的观念性,是指所有权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并不以对所有物的现实支配为必要。这就意味所有人即使不现实直接占有、支配、管理标的物,其对标的物仍享有所有权。[注]参见陈华彬:《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既然所有权属于一种观念性的民事权利,即便行为人剥夺了权利人的财物,使权利人无法对财物加以现实的支配,权利人也并不会因此丧失所有权。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尽管德国刑法学界的通行观点主张侵占罪所侵害的法益是所有权,但是也同样认为所有权本身是不可能受到损害的,其原因在于,通过盗窃、侵占等行为不可能实现所有权的转变。因此有德国学者认为,应当将所谓的所有权受损害理解为:所有权人根据民法规定所享有的权利无法再行使。[注]Vgl. Fritjof Haft/Eric Hilgendorf, BT I, 9. Aufl., Verlag C. H. Beck Müchen 2009,S.1.按照这种理解,就侵占罪而言,所谓的财物所有权这一保护法益,实际上是指权利人基于所有权而对财物所享有的支配可能性,即事实上的使用、收益和处分。这种支配可能性并不等同于所有权本身,而是“所有权在正常状态下的内容和表现”[注]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实际上,对于所有权本身与所有权的行使可能性所存在的差别,我国刑法学者并非没有注意到。例如,有学者即认为,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并不必然意味着被害人财产所有权的丧失,而是对所有权所包括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侵犯。对任何一种权能的侵犯,都是对所有权不同程度的侵犯,而对作为核心权能的处分权的侵犯,则是对所有权整体的最严重的侵犯,也是绝大部分侵犯财产罪的核心特质。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而言,行为人攫取公私财物,使被害人事实上将永久不可能再对失去的财物行使所有权,但并非使所有人永久丧失所有权。[注]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第3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0页。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引最后半句的原文表述为“但并非使所有人永久丧失行使所有权的可能”,这明显与前面一句的表述存在逻辑上的冲突。笔者猜测这可能是由于论者表达不严密所致,因此不揣冒昧加以订正。由此可见,即便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所有权,实际上也是将其进一步解释为所有权的行使可能性,或者说是基于所有权所享有的对于财物的支配可能性。也就是说,我国通说所说的财产所有权,实际上是针对属于所有权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而言的。[注]当然,对于侵占罪而言,由于在实施侵占之前,行为人已经合法持有了财物,因此不存在对民法中所说的占有权能的侵害。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国《刑法》第270条第1款所规定的“非法占为己有”,仅需满足以下要求即可:通过侵占行为,行为人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转由自己或第三人支配,从而在事实上妨害了所有人对于财物的支配可能性。其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通过非法手段使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了财物的所有权。由此可见,在本质上,财产所有权说与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可能性说所指的内容并无不同,两者实际上是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只不过财产所有权说更为详尽地说明了所有权作为刑法保护法益的内容。[注]参见王效文:《论侵占罪之持有与侵占行为》,载《月旦法学杂志》2012年第7期。在这一点上,本文认同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可能性说这一主张。
但是,“所有权系对物为一般概括支配的权利,所有人对标的物得为占有、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并排除他人之干涉”[注]王泽鉴:《民法物权》(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考虑到这一点,侵占行为毕竟是对这种概括支配权利的侵害,是对所有人对物为全面支配的妨害。而所谓的事实上的行使可能性受到侵害,实际上是所有权受到侵害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认为侵占罪侵害的只是事实上的对于财物的支配可能性,而非所有权本身,则会导向权利不可侵害论,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权利非经正当法律程序是不可被剥夺的。[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型支付方式的出现,通过犯罪行为剥夺他人合法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已并非完全不可能之事。对此所作的具体论述,参见马寅翔:《限缩与扩张:财产性利益盗窃与诈骗的界分之道》,载《法学》2018年第3期。以侵占行为不可能实现所有权的转变为由,认为所有权本身不可能受到损害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所有权的丧失与所有权受到侵害相提并论,认为只要所有权人没有丧失所有权就意味着侵占行为没有侵害所有权,从而导致将所有权受到侵害与所有权丧失这两种意义不同的情形混为一谈。此外,如果考虑到民法中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在极端情况下,侵占行为也同样可以引起所有权发生法律上的变动,即行为人通过侵占行为,使财物的所有权从原所有人那里合法转移至善意第三人的手中。例如,对为第三人侵占中的善意第三人而言,其可以合法获得原本属于被害人所有之财物的所有权。因此,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财产使用可能性说的主张也难言妥当。在这一点上,我国通说在具体的理解上也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
二、修正的所有权说之提倡
由于上述各种少数说或多或少地存在缺陷,经过比较后,在侵占罪的保护法益问题上,本文在整体上仍坚持传统的所有权说。至于具体理由,在上文分析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可能性说时已经提及。概言之,所有权说以民法中的所有权理论为根基。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理解上,应避免上文所指出的存在于通说中的舛误之处,即将所有权的行使等同于所有权本身,并因此认为侵占行为导致行为人事实上丧失了财物所有权。正是由于作为取得型犯罪,侵占罪并不能为行为人创设民法意义上的所有人的法律地位,[注]当然,在第三人属于善意取得的情况下,仍可能为第三人创设该地位。因此,对于侵占罪中侵占的含义,就需要从纯粹的事实意义上来把握:行为人所追求的是获得表面上的“伪法律的支配地位(die pseudorechtliche Herrenstellung)”,以用来补偿为法律所承认的所有人名义这一正式头衔的缺失。[注]Vgl. Reinhart Maurach/Friedrich-Christian Schroeder/Manfred Maiwald, BT I, 10. Aufl., C. F. Müller Verlag 2009, § 32 Rn. 2.也就是说,通过侵占,行为人获得了一种与权利人平等的事实地位,只是该地位并不为法律所承认而已。此外,在侵占罪中,对作为保护法益的所有权的侵害,与盗窃罪中的一样,涉及的是取得的不法,它既不像毁坏物品那样,仅涉及剥夺所有(Enteignung)的不法,也不像使用盗窃那样,仅涉及占为所有(Aneignung)的不法,而是将占为所有的不法与剥夺所有的不法均包括在内。但是,与盗窃罪仅要求存在行为不法不同,侵占罪中还必须存在结果不法。换言之,违法取得对所有权所造成的侵害,在侵占罪中必须在客观上已经发生,而不像在盗窃罪中那样,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意图实现即可。[注]Vgl. Andreas Hoyer, in: SK-StGB, Luchterhand 2009, § 246 Rn. 1.因此,侵占罪中的法益侵害,是在实然上已经发生的,对权利人对于财物所享有的全面支配的妨害。
如上所述,所有权说以民法中的所有权理论为根基。但是,所有权说只适用于一般情况,当涉及特殊财物时,所有权说则难以贯彻。例如,在碰到侵占的对象是属于种类物的金钱时,所有权说的立场就会遭受冲击。这是因为,对处于流通环节的金钱的所有权,我国民法理论通说采行的是占有即所有的主张。根据这种主张,当行为人合法地占有他人金钱之后,在民法意义上就已经获得了该笔金钱的所有权,并同时对原权利人负有相应的债务。即便行为人拒不返还该笔金钱,也不存在对原权利人的所有权的侵害,而是对原权利人所享有的债权的侵害。由此可见,所有权说无法解决以债权等财产性利益为犯罪对象的刑法保护问题。为了解决由金钱问题所带来的处理上的困难,刑法理论中出现了以下两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认为,在所有权的理解上,刑法应独立于民法。根据在金钱问题上是否承认民法理论中占有即所有的理论,这种主张又可以再分为两类:
1.不承认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认为即便是在金钱的场合,权利人也并不会因为占有主体的变更而发生变化。例如,日本有学者认为,刑法上的所有权应当与民法上的所有权相分离,刑法上的概念只需要从刑法独立性的观点加以确定即可,没有必要完全遵循民法上关于所有权的理解。[注]参见[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2.承认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但与此同时,扩张刑法中所有权的涵盖范围,将民法中的债权包含在内。例如,我国有学者认为,刑法意义的所有权并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也包括对一定物质利益的请求权(债权),其在范畴上更接近于民法中财产权的概念,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已经单独予以保护,因此应当排除知识产权的内容。总之,刑法意义的所有权应指具有财产利益的,以通过物理方式可测量的物为对象的支配和请求权利。[注]参见时延安:《论民法意义的所有权与刑法意义的所有权之间的关系》,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1期。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认为,之所以在所有权概念的理解上,刑法与民法会存在这种差异,其原因在于刑法与民法的功能、目的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民法与刑法都旨在对财产权利加以保护,但民法看重实害结果,强调通过对受害人的补偿、赔偿等方式实现权利人的财产权利。民法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活动提供行为规范,其通过个人权利的实现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与此不同,刑法更注重对犯罪行为的法律评价,强调对现存财产秩序的保障以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目标。此外,刑法还是维护、保障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因此,在财产犯罪方面,刑法对所有权的保护范围要大于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注]参见王玉珏:《刑法中的财产性质及财产控制关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页。
第二种主张认为,在所有权的理解上,刑法应与民法保持一致。根据在金钱问题上是否承认民法理论中占有即所有的理论,这种主张同样也可以再分为两类:
1.不承认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德国刑法理论及实务大多持此态度。例如,在德国曾发生过一起“服务员侵占案”,在该案中,作为行为人的服务员没有将顾客支付的餐费交给酒馆老板,而是私自截留。对此,德国司法实务部门认为,该行为构成侵占罪。其判决理由为:虽然顾客是通过服务员订的餐,但是顾客的订餐行为通常只会在他与酒馆老板之间建立权利义务关系,服务员对于订餐行为并不享有什么权利。在顾客付款时,金钱的所有权立即直接转给了酒馆老板。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顾客只可能是为了满足债权人而转移金钱的所有权,而服务员则有义务将顾客所付的餐费交到老板手中。[注]Vgl. OLG Düsseldorf, NJW 92, S.60.有德国学者结合该判例指出,对于现金而言,也并不存在什么特殊之处,起决定作用的依旧是民法关于转让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涉及一方意图转让现金的所有权,而另一方意图收取的问题。[注]Vgl. Albin Eser/Nikolaus Bosch, in: S/S-StGB, 29. Aufl., Verlag C. H. Beck 2014, § 246 Rn. 6.由此可见,在侵占金钱这一问题上,德国的做法实际上是通过民法关于转让的规定,与民法保持了一致,但这种处理方式并没有承认民法中的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的理论。
2.承认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但并不将侵占金钱的行为作为侵占罪处理。例如,有日本学者认为,虽然在所有权的理解上与民法学说保持一致,不采取刑法独立性的主张,对于侵占金钱的行为而言,会导致无法以侵占罪论处,但是就日本的刑法规定而言,也还是可以通过背信罪加以处罚。[注]参见[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页。
在所有权的理解上刑法是否应当独立于民法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违法一元论、违法多元论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之争。虽然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的主张更值得提倡,但即便采取该主张,在解释方向上也应当尽可能地与民法主张保持一致,在涉及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刑法上能否获得承认的问题时,尤其应当如此。按照这一思路,还是应当承认民法通说所主张的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的理论。上述主张中不承认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的观点,因而也就丧失了借鉴意义。德国通行的做法维持了与民法规定的一致性,但实际上是按照寄托人或者委托人通常的意思而赋予相应的金钱以物权的保护,从而认可了所有权的存在,因而金钱当然可以成为侵占罪的客体。对于这种处理方式,日本有学者认为,肯定寄托人或委托人拥有金钱所有权的根据,在于遵循契约的精神而认可综合性利益的物权归属。在此意义上,刑法上所有权的概念更加接近其本来的样子,而在民法上为了交易的安全很可能修正了所有权的概念。关于这些内容,在民法理论中出现了对“占有=所有权”的缓和化的理解,主张按照委托的意思认可所有权的归属。如此一来,刑法和民法之间就不会产生分歧。[注][日]井田良:《刑法与民法的关系》,牛佳靖、周振杰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总第20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但是,对于缓和“占有=所有权”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承认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因此不能说与民法理论完全保持了一致。至于第二种主张的第2类见解,即在承认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的同时,将侵占金钱的行为作为背信罪处理,这种做法在日本有其可行性,但是由于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背信罪,该见解因而也并不具有借鉴意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侵占金钱的行为应当作无罪处理?
笔者认为,从严格解释的角度来说,既然在规定侵占罪时,我国刑法明确将行为对象限定为他人的财物,如果采用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的主张,则在行为人实施侵占行为之前,金钱已经并非他人财物,而是行为人所有之物,此时的金钱因而丧失了他人性,这显然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然而,这种处理结果在合理性上必然会受到质疑。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所有权中的他人性属于实体性的概念,从实体上确定所有权的归属,虽然在一般场合下意味着刑法上的“物的他人性”应以民法上的所有权的他人性为依据,但并不意味着在一切场合下都要以民法上的所有权归属为依据,金钱寄托的场合即为其例。寄托金钱的人尽管不占有金钱,但刑法上仍认为其属于所有人,对于受托者而言,寄托的金钱属于“他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并未采取民法中的“占有即所有”的处理原则,这是基于刑法保护实体利益的需要。如果在刑法上不承认寄托金钱的所有权归委托人,即便受托者将其侵占也没有侵犯委托人的所有权,从而没有成立侵占罪的余地,这显然有悖于刑法规定侵占罪的趣旨。[注]参见童伟华:《所有权与占有的刑、民关系》,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但是,为何在一般场合刑法要以民法为依据,到了涉及金钱的场合就不需要遵守?基于保护实体利益的需要这种理由,实在难以证立置民法主张于不顾的做法具有妥当性。如果将侵占罪的保护法益限定为所有权,就不能认为,为了维护处罚的必要性,侵占了在民法上明明不具有他人性的物品,仍然可以以侵占罪定性。为此,可以考虑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是,在承认所有权说的基础上,例外地承认关于金钱等特殊财物的债权可以成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但是这些关于金钱等特殊财物的债权并不包括由于借贷关系而形成的,本文将这种主张称之为修正的所有权说。
修正的所有权说不同于上述我国学者所提倡的扩张刑法中的所有权概念,从而将债权等包含在所有权之内的观点,而是认为在所有权之外,例外地承认针对金钱等特殊财物而形成的债权。之所以将由于借贷关系而形成的债权(包括金钱)排除在外,是因为借贷合同的特点之一,就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会发生转移。通常情况下,侵占罪中的财物仅限于行为人虽然占有但却没有所有权的财物,而通过借贷获得的财物,借贷人即已取得了对借贷物的所有权,只不过因此负有向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这同将自己占有但却无处分权的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相比,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对于借贷义务人而言,当并不存在抗辩事由时,如果其拒不履行到期债务,则此种行为仅具有民事不法,并不构成侵占罪。因此,应当把侵占借用他人的、自己不享有所有权之物的行为,与通过借贷关系取得的具有处分权的种类物,如货币、水泥、大米等,而事后不履行偿还义务的行为,严格区分开来。[注]参见李洁主编:《刑法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8页。由于金钱的特殊性质,占有一旦发生转移,所有权也随之转移,因此在法律效果上难以与通过借贷而获得的金钱相区分,此时的判断标准则在于获得金钱的原因是借贷还是原所有权人委托保管、行为人拾得等。如果不加限制地将所有债权均视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势必会不当扩大侵占罪的规制范围,混淆民事不法与刑事不法的界限。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当所有人将金钱放入密码箱等装置中交由他人保管时,这些金钱暂时脱离了流通环节,成为特定物,因此并不适用占有即所有的法理,受托人将其据为己有的,存在成立财产犯罪的可能性。至于是成立侵占罪还是盗窃罪,则涉及封缄物的占有归属问题。囿于主题及篇幅,本文对此不作展开。
当然,采用债权也可以成为侵占罪保护法益的做法,会面临着如何理解财物的含义,即财物是否也可以包含债权这种财产性利益在内?所谓财产性利益,指的是财产的积极增加与消极增加,它们均属于财产总量增加的情形。“财产的积极增加即积极受有利益,是指财产权利的增强或者财产义务的消灭。这既包括所有权、他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利的取得,也包括占有的取得,还包括财产权利的扩张及其效力的增强、财产权利限制的消除等。财产的消极增加即消极受有利益,是指财产本应减少而没有减少。其既包括本应支出的费用而没有支出,也包括本应承担的债务而未承担以及所有权上应设定负担的而未设定等。”[注]魏振瀛主编:《民法》(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86页。在我国刑法语境中,之所以对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在内存在疑问,是因为虽然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的标题为“侵犯财产罪”,但在具体罪名的表述中却使用的是“财物”一词,侵占罪也不例外,由此形成了能否将“财产”与“财物”等而视之的疑问。
对此,我国学者在讨论诈骗罪的对象时认为,将财产性利益包括在内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这样做并不属于类推解释,因而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值得关注的是其第五点理由,即“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财物与财产两个概念并没有明显区分,甚至可以认为,二者基本上是在相同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注]参见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以下。结合我国《刑法》第64、224条的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来看,将财产性利益视为财物的做法是恰当的。此外,为了避免解释论上的分歧,以维护司法适用的统一性,我国还有学者对财产性利益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在界定财产性利益的外延时,一般应以无体性、客观财产价值、确定且具体的利益作为判定标准。其中,债权属于财产性利益的主要类别之一。[注]参见李强:《财产犯中财产性利益的界定》,载《法学》2017年第12期。由此可见,将一定的债权作为侵占罪的法益加以保护,能够与整体的财产犯罪法益的理解保持一致,也没有突破立法用语的边界,且符合司法实务的理解,因而具有可取性。
三、修正所有权说的司法贯彻——以“何鹏盗窃案”为例的展开
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受委托人拒不返还代为保管的金钱以外,经常发生的还有错误汇款的问题。所谓错误汇款,是指由于人为错误或者机器故障,导致原本应当汇入甲账户的款项错误地汇到了乙的账户。在出现错误汇款的情况下,如果实际收款人明知错误汇款的事实,却仍然取出存款,对于如何处理这种行为,也同样涉及侵占罪的保护法益问题。为便于讨论,此处以“何鹏盗窃案”为例展开分析,该案的基本案情较为特殊,存在官方版与民间版两个版本。其中,官方版本为:
2001年3月2日,被告人何鹏持账面余额仅有人民币10元的农行金穗储蓄卡,到建行的一台ATM自动柜员机上查询存款余额,未显示卡上有钱。被告人何鹏即按键输入取款100元的指令,时逢农行云南省分行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造成部分ATM机失控,ATM机当即按何鹏指令付出现金100元,被告人何鹏见状,即继续按键取款,先后6次取出现金4400元。3月3日上午,被告人何鹏持卡到中国银行翠湖储蓄所、胜利广场储蓄所、云南省分行、北市区支行、东风支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武成分理处等7台ATM机上,连续取款215次,共取出现金425300元。两日共取款429700元。[注]参见《(2002)云高刑终字第1397号裁定书》,载“北大法宝”,引证码:CLI.C.45862,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displaycontent.asp?gid=117486374,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10月15日。
民间版本为:
2001年3月2日,被告人何鹏持账面余额仅有人民币10元的农行金穗储蓄卡,到建行的一台ATM自动柜员机上查询家里的生活费是否到账,但是发现自己的储蓄卡上的10后面冒出了许多“0”,足足有百万元之巨!于是,被告人何鹏先尝试取款100元,成功后,两天内分别从9台ATM机上取款221次计429700元。[注]参见张寒:《云南“许霆”:为何偏偏我是无期》,载《新京报》2008年4月14日第A15版。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两个版本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何鹏的账户中是否显示有百万元巨款。对此,判决书中认定何鹏的账面只显示了10元存款,但是在新闻报道中,何鹏却自述当时账面显示有百万元之多。这一区别对于认定案件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有学者指出,判决书与何鹏自述所说的两种情况涉及存款占有主体的认定。如果根据判决书的认定,存款并没有进入何鹏的账户之内,此时存款的占有者是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为人采用合法手段侵入自动柜员机,在银行方面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将该机器中所存放的财物据为己有的,构成盗窃罪。如果根据何鹏自述,则存款已经进入何鹏的账户之内,此时存款的占有者是何鹏。对于这些存款,何鹏处于“想取的话,随时都可以取走”的实际支配状态,因此,属于其占有的财物。从此意义上讲,何鹏将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据有己有,应当构成侵占罪,而不可能构成盗窃罪。主张构成盗窃罪的观点,忽视了何鹏对于其银行账户当中的财物具有实际支配的事实。[注]参见黎宏:《论存款的占有》,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5期。有学者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何鹏是从本人的卡中取款,尽管该款是银行过错造成的。此时,如果把储蓄卡中的款项视为持卡人占有的财物,则银行的过错使何鹏不当得利,何鹏将不当得利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符合侵占罪的特征。”[注]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下卷)(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6页。
在两位学者的分析中,都将何鹏的自述作为分析对象,应当说,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即使在判决书中,也明确承认何鹏是在不同银行的不同取款机上分次、分批、分天取得现金,从出错概率上来看,因农行计算机系统故障而将巨款错误汇入何鹏账户内的可能性明显更高。虽然在分析该案例时,上述学者均是从谁是真正的占有者这一角度展开的论述,但是已经明确提及不当得利的概念。不当得利之债的基本内容为受损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注]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2、589页。认为何鹏的行为构成侵占罪的观点,核心在于将储蓄卡中的款项视为持卡人占有的财物,如果以承认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为前提条件,则该主张实际上就等于已经承认了债权可以成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
当然,在错误汇款的情况下,还存在着讨论是否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可能性。这涉及存款名义人占有说与银行占有说之间的分歧。对此,主张银行占有说的学者认为,“存款”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存款人对银行享有的债权;二是指存款债权所指向的现金。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存款人都享有了债权。至于存款债权所指向的现金,则由银行管理者占有,而不是存款人占有。[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47页。这种主张实际上否认了账户占有人对其账户内的金钱拥有所有权,因而与上述两位学者的理解不同。基于这种理解,在错误汇款的场合,有日本判例认为,收款人对于银行的债权并不成立。刑法理论上也以此为前提,认为由于收款人的存款债权并不成立,所以不能对该账号中的金钱行使正当的返还请求权。如果收款人通过柜台取走金钱,就构成诈骗罪;从自动柜员机中取走的则构成盗窃罪;通过自动柜员机转入他人账户的,构成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罪。[注]参见[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对于在柜台取款的行为,有日本学者认为,判例是希望通过因收款人的欺骗致使银行未获得调查、确认错误汇款的机会等,来肯定诈骗罪的成立。应当说,在银行错误的场合,银行拒绝收款人的取款请求具有正当的利益,但是意图通过对取款权限附加这样的限制来肯定诈骗罪的成立,虽然在形式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实质上这一见解却不能不说是脆弱的,因为它与民事规则相抵触。[注]参见[日]山口厚:《从新判例看刑法》(第2版),付立庆、刘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应当说,这种见解也可以用来评价德国在处理错误汇款问题上的做法。在德国,在处理错误汇款问题时,理论与实务依旧采取了与处理现金问题相同的做法,即根据民法关于转让的规定来判断是否对于汇款享有所有权。根据这一判断标准,收款人对于通过汇款收到的钱,并不一定享有所有权,因为银行一般是根据汇款人的意愿汇款,如果实际收款人并非指定收款人,则实际收款人对汇款并不享有所有权。[注]Vgl. Albin Eser/Nikolaus Bosch, in: S/S-StGB, 29. Aufl., Verlag C. H. Beck 2014, § 246 Rn. 6.这种处理方式没有承认民法中对金钱的占有即所有的主张,正如上述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存在着与民法处理规则相抵触的缺陷。
对此,我国有学者指出,首先,作为存款的名义人,收款人对于错误汇入的款项能够向银行主张支付请求,而且银行不得拒付。这就意味着收款人取得了对存款债权的占有。收款人取走错误汇款的行为,属于实现债权的行为,并没有侵犯银行对现金的占有。银行也不因为向收款人支付了现金而遭受财产损失。因为错误汇款人不能主张银行的支付行为无效,并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再次,收款人取走错误汇款的行为,表明其彻底消灭了就该错误汇款形成的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了汇款人对错误汇款的存款债权,从而侵犯了其对于存款债权的占有。总之,收款人取走错误汇款的行为属于将合法占有的他人的存款债权变为非法所有,系对他人存款债权的侵犯,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注]参见黑静洁:《取走错误汇款行为的刑法认定》,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当然,在银行是否可以拒付的问题上,还需要结合具体规定加以判断。此外,汇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否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就结论而言,以侵占罪论处的主张却值得肯定。同时,这种主张实际上也与本文所提倡的观点一样,承认特定的债权也能够成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可以确定的是,即便因为错误汇款而使得账户占有人的存款增加,银行也无权将多出的款项直接划走,而是需要事先征得账户占有人同意。这表明,对这笔款项的实际处分权在账户占有人手中。即使在银行已经查明的情况下,账户占有人无法将该笔款项取走,也只是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所采取的一种类似保全措施的做法。因此,在账户占有人是不当得利的受益人这一点上,并没有因为标的物是存款而有什么不同。由于这一原因,认为构成诈骗罪或盗窃罪的主张,[注]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71页。就会与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制度相矛盾。应当说,在承认债权可以成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的情况下,将账户占有人拒不返还错误汇款的行为以侵占罪论处,是更为妥当的处理方式。
除了金钱这一较为特殊的财物以外,应当注意的是,在刑法中并非所有的不当得利之债均可以作为债权受到保护。对此应当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不当得利并未导致财物的所有权发生变化。例如一方基于无效行为给付给受益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因此处于受益人占有之下的财物仍属于他人所有之物,将其侵占的话,实际上侵害的是他人的所有权。第二种情形是,由于不当得利的发生而导致财物的所有权发生变化,受益人为善意时即为此例。根据民法理论,在受益人为善意时,如果受损人的损失大于受益人取得的利益,则受益人返还的利益仅以现存利益为限。如果受益人受有的利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受益人返还的利益范围以受损人受到的损失为准。利益已不存在时,受益人不负有返还义务。[注]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0页。在这种情形中,受益人已经取得了财物的所有权,如果受益人拒不返还应当返还的那部分利益,则侵犯的是受损人的债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将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权作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无因管理的情况。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无因管理也可以成为占有他人财物的合法原因。如果无因管理他人财物之后,产生了非法转为己有的意图,拒不归还本人,则应以侵占他人财物论处。[注]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第5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994页。虽然无因管理属于债权产生的原因之一,管理人与本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管理人侵占与无因管理有关的财物的,在性质上却并不属于侵犯本人的债权。这是因为,在无因管理之债中,债权债务关系的标的物是因管理而产生的必要费用或损失,因无因管理而取得的本人的财物,所有权仍归本人所有。例如,甲外出时家中发生火灾,邻居乙从火灾中抢出了一些财物。对于这些财物的所有权而言,并不因为乙的无因管理行为而转归到乙的身上。如果乙拒不返还,则侵害的是甲对这些财物的所有权,而非债权。
应当说,这种对于债权在侵占罪中的限制性承认是一种相对保守的主张。在德国,在债权是否属于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债权天然地可以成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非法地将自己从债务中解放出来的事情并不罕见。虽然行为人的直接目的是针对债务总额而言的,但这并不会改变的事实是,它同时也侵犯了债权人的权利。[注]Vgl. Karl Binding, BT 1, 2. Aufl.,V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 1902, S.239.因此,在这种主张看来,可以成为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债权范围要更为广泛,可以将所有涉及财产的债的类型均包括在内。这与本文的理解有出入,至于哪种见解更为妥当,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为了解决将代为保管的金钱占为己有以及因不当得利而发生的财物所有权归受益人所有的情况,本文采取了承认这些情况下的债权属于侵占罪保护法益的处理方法。这种主张并不是所有权说的否定,而是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这种补充存在于极为特别的情况中。即除了为传统主张所承认的所有权以外,将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有限地扩张至债权,这就意味着一定的财产性利益也可以成为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此即本文所说的修正的所有权说,由于相对于全部财产权而言,这种主张只包括一部分财产权,因此也可谓部分财产权说。
四、尾论:对作为理论根基的民法依存模式的初步考量
在确定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时,本文采取了以民法为根据的立场,这涉及财产犯罪法益的解释模式。在解释财产犯罪的法益时,日本刑法学界在解释模式上存在着民法依存模式、秩序维持模式和民事法志向模式三种主张。其中,民法依存模式认为,财产犯罪的成立与否从属于民事实体法上的权利关系,只有当行为侵害了民事实体法所预定的权利关系时,才有可能成立财产犯罪。秩序维持模式则否认财产犯罪的成立从属于民事实体法上的权利关系,认为应该在刑法中确立支配民事关系的规则,为了确立、维护财产秩序而肯定财产犯罪的成立。在这两种主张的对立中,产生了属于折中观点的民事法志向模式,其是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者在解释财产犯罪法益时的立场。该模式认为,在解释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时,应当在坚持民法依存模式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刑法本身的目的和机能。例如,日本《刑法》第242条规定,虽然是自己的财物,但由他人占有或基于公务机关的命令由他人看守时,视为他人的财物。对此,民事法志向模式认为,事实上的占有作为一种法益也被扩张进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但这并非是遵循了秩序维持模式,因为占有本身是一种民法上的利益。在经过民事程序法确认之前,占有者拥有正当的利益。[注]参见[日]井田良:《刑法与民法的关系》,牛佳靖、周振杰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总第20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294页;童伟华:《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财产罪的法益及其展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205页。民事法志向模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其他两种解释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就民法依存模式而言,虽然完全依照民法规定加以判断既简便又合理,但是完全运用民法的解释,未必符合刑法对有关概念的理解,在解释论体系上也未必需要一致。并且,与民法相比,刑法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更为明显,完全以民法规定为导向,会忽视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持功能,一定程度上将背离社会秩序所期待的普遍规则。正是因为这两个缺陷,坚持刑法独立个性的违法多元论者才提出了秩序维持模式的解释模式,但是这种解释模式在强调刑法独立性的同时,却忽视了法秩序的统一性,并且可能导致处罚的边界过宽。例如,以欺骗、胁迫等方式逃避嫖资的行为,在秩序维持模式看来,也应当以犯罪论处。与上述两种解释模式相比,民事法志向模式更为灵活,在维持处罚的实体性这一前提下,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处罚漏洞,但是,其也存在明确性方面的问题,且认为以非法手段行使财产权利的场合也成立财产犯罪,从而与秩序维持模式在实质上不存在差别。[注]参见童伟华:《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财产罪的法益及其展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209页。在解释模式的取向上,有学者认为,尽管上述解释模式各自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相较而言民事法志向模式更为可取,同时,为了减少民事法志向模式的缺陷,应当将民事法解释模式所理解的财产法益解释为民事实体权利,以及民法虽然没有明确保护,但根据刑法的特性和机能,至少在刑法上值得保护的具有民事性质的利益。[注]参见童伟华:《财产罪基础理论研究:财产罪的法益及其展开》,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虽然经过利弊分析,民事法志向模式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但是,既然民事法志向模式在结论上有倒向秩序维持模式的可能性,因而对其必须持谨慎的态度。民事法志向模式的诞生是以日本《刑法》第242条的规定为契机的。根据该规定,在他人保管之下的自己财物也视为他人财物,这实际上是对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单独保护。与此相类似,我国《刑法》第91条第2款也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在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中,明确提及公共财产(公共财物)的,主要有:第304条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第382条贪污罪;第397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第403条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规定这些罪名的目的在于解决贪污、渎职行为中涉及特殊财物时应当如何定性的问题,因此,虽然该规定将特定条件下的私人财产视为公共财产,却不是为了强调对刑法意义上的占有的保护。[注]对此所作的详尽论述,可参见马寅翔:《侵吞不法原因给付物的处理观念之辨正》,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4期。
由此可见,如果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民事法志向模式的立法根据是不充分的,而刑法意义上的占有,正是民事法志向模式主张者们经常拿来证立自己主张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在财产犯罪的法益解释模式上,有德国学者认为:“财产权何时受到侵害,不应由作为保护法的刑法来决定,而应当由财产法来决定。离开了民法、公法对财产权、债权的规定,刑法对财产权、债权便一无所知。因此,认定是否对这种权利产生了侵害时,刑法完全从属于财产法。”[注]Vgl. Karl Binding, Handbuch des strafrecht, Erster Band, 1885, S.9f.这种见解与民法依存模式的主张相一致。民法依存模式认为,只有侵犯民法上的财产权利的行为,才有可能成立财产犯罪,因此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民法上的权利。在对占有的理解上,上引德国学者认为,占有属于财产的经济性的一面,而不是权利性的一面。[注]Vgl. Karl Binding, BT 1, 2. Aufl., V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 1902,S.240.如果结合我国物权法没有将占有作为权利加以规定来看,这种理解在我国也是可以成立的。由此可以认为,即便在占有的问题上,刑法与民法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这与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民法上的权利这种认识并不必然存在冲突。这是因为,这种认识只是说在认定是否侵害权利时,应当以民法关于财产权利的规定为准据,但并没有说,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只有民法上的权利,对此是需要加以注意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占有的问题上,本文虽然认为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与民法意义上的占有存在一定区别,并且认为缓和的违法多元论,或者说刑法的相对从属性说更具有合理性,[注]对此所作的深入分析,参见于改之:《法域冲突的排除:立场、规则与适用》,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但是在财产犯罪保护法益的解释模式上,却坚定地选择民法依存模式。这种选择与缓和的违法多元论的主张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因为缓和的违法多元论的主张本来就是以保持法秩序统一性的违法一元论为导向的。
至于民法依存模式的弊端,笔者认为,在相关概念的理解上,刑法与民法的确存在不同之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我国目前的法秩序体系中,各部门法学者都强调部门法研究的独立性,甚至在民事法内部,也存在着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本文并不否认强调部门法研究的独立性有助于研究的系统化、深入化、专业化,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对独立性的强调却导致以下后果:至少就目前情况而言,作为统一法秩序之下的各部门法学者只讲究分工,却缺少合作。部门法学者看到差异后的本能反应是强调各自部门法的独特性,而不曾设想如何改变差异,以求得法秩序的统一。当然,这种对于法秩序统一性的强调,有着追求将应然变为实然的理想主义成分。然而,既然承认法秩序的统一性是更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在面对实现该目标的障碍时,却又认为这些障碍的存在理所当然,而不试图改变,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可取的态度。而且,对法的应然性的研究,即主要研究法的价值,揭示法的价值取向、价值目标,评判法的价值标准,能够为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提供原则和理想模式。[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从应然性角度来说,同一主体在同一时点上,应尽可能地做到在刑法上和民法上的解释不发生矛盾。[注]参见[日]井田良:《刑法与民法的关系》,牛佳靖、周振杰译,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总第20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在财产犯罪中,当刑法与民法关于权利的认定存在冲突时,应当以民法的规定为根据,这既是对民法所体现的市民平等自治理念的尊重,也是刑法作为保障法所应有的克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片面强调刑法所具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否则将会严重破坏法秩序的统一性,这种代价显然是法治社会所不能承受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