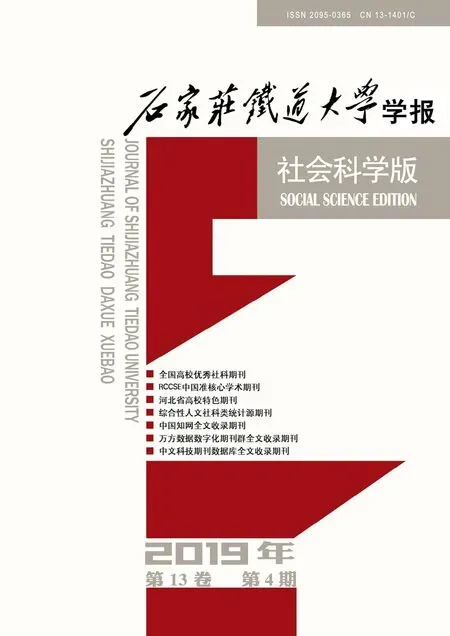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特征分析及启示
2019-02-10张在钊张云岗刘立勇
张在钊, 张云岗, 刘立勇
(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河北 石家庄 050043)
一、引言
在美国独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文学一直深受英国乃至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直到华盛顿·欧文以本土风情为背景、以美国革命为主题的短篇故事集和费尼莫尔·库柏以美国边疆生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的出现,美国文学本土化进程才初见端倪。时至美国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30年代至南北战争结束),美国逐渐形成区别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独特文化心理和民族思想特质:脱胎于清教思想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第二次反英战争的胜利带来的民族主义意识、西进运动中迸发的开拓进取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背景下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个性。美国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独立的呼声随之高涨,美国的文学的本土化历程也就此拉开了序幕。在美国独立诞生地的新英格兰地区,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从美国本土汲取营养,彰显民族特质和民族精神,并不断创新文学表现形式和技巧,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熠熠生辉的文学名作,其文学本土化经验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各国民族文学发展的可贵精神财富。
本文拟选取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成就最突出的作家,如爱默生、惠特曼、霍桑、麦尔维尔和爱伦·坡,从思想特质、作品主题和艺术形式三个方面,对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特征作一分析和阐述,并结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探讨美国文学本土化路径和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启示价值。
二、文学作品思想特质的本土化:浸润超验主义,反思清教文化
超验主义思想和清教文化传统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大重要思想源流和思想特质,驱动着本阶段文学的发展,并决定着本阶段美国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基调。
作为美国的文艺复兴领袖和美国民族文化独立的倡导者,爱默生在19世纪30年代在新英格兰发起了超验主义运动,吹响了美国民族文化和文学独立的号角。他在被誉为“超验主义宣言”的《论自然》中,阐述了超验主义思想的基本观念:自然和上帝是一个统一体,自然是上帝或超灵的象征,而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则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这一论断在社会、哲学和美学层面产生了多维度的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自然的崭新观念。自然被赋予精神性和象征性。人可以与富有灵性的自然进行精神交流,并从中获得深刻启示。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加尔文神学传统对人性的禁锢,切实提升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重要性,热情鼓励与赞扬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由此改变了之前人类面对自然考验时消极被动的地位。这有助于人的自我意识、个体意识、个人价值的形成,为美国个人主义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爱默生又表露了摆脱英国和欧洲文化传统束缚的心声,主张一个新国家和新民族必须拥有自己的新文学和新文化,不能继续步英国作家的后尘。这激励了美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完善,对于美国精神和文化摆脱欧洲大陆的母体,形成崭新而独特的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1837年爱默生发表了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独立宣言”的著名演讲辞《美国学者》,宣告美国文学已经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告诫美国学者不要盲目追随传统,不要进行纯粹的模仿。“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四周,有成百上千万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1]73-74“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1]99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在美国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开始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民族,开始把自己的创作转向书写美国的主题,树立美国的风格,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也开始走向其鼎盛期。
惠特曼是受超验主义思想影响最为突出的作家,超验主义思想在他的《草叶集》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自我之歌》中,作者一开始就抒发了他对于人类个体自我能量的热情肯定和强大的自信心。他在诗中写道:“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2]1诗人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完全融合在一起,表明了精神不只属于人类自己,世间万物皆有灵魂,都可以在超灵的引领下实现内在的交流。自然与人融为一体,这正是超验主义的核心所在。
在这一前提下,诗中的无处不在的“我”似乎化身为爱默生在《论自然》的那个透明的“眼球”,并游走于整个美国乃至宇宙,成为一个具有神性、无处不在、完全脱离了狭隘的个体自我局限的完美的精神实体。诗人写道:“灵感通过我汹涌澎湃,潮流和指标也通过我”;[2]50“我里外都是神圣的,不论接触到什么或被人接触,我都使它成为圣洁”;[2]51“不论我从善从恶,我允许随意发表意见,顺乎自然,保持原始的活力。”[2]2他内心对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怀有无限的信心,那种渴求心灵自由,宣扬个体独立精神的无所畏惧的气质溢于言表。诗中不可言传的“原始的活力”明显带有超验主义当中崇尚“超灵”无限能量的神秘色彩。
清教思想是美国文艺复兴时期另一重要的文化传统和文学思想渊源。自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抵达北美新大陆并立志建立“山颠之城”开始,清教主义在北美扎根生长,对北美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清教主义的宗教狂热到18世纪初逐渐冷却下来,清教传统中的原罪观和宿命论以及愤怒的上帝的形象也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淡化,但是作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文化基因和传统,清教思想被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传承下来,最终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美国精神、文化和国民性。”[3]38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虔诚的理想主义是清教传统留给文艺复兴时期美国作家的精神遗产,成为美国民族文学产生和成长的重要滋养,而清教传统中过滤沉淀下来的宗教沉思、对人性及灵魂的探索和象征主义倾向成为美国文艺复兴时期小说的重要传统和文学特点,清教思想也成为这一时期的小说清晰的美国本土化特征。正如埃利奥特所说,“清教徒对新大陆的展望作为遗产被我们的主要作家继承下来,并以种种方式演变成他们作品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背景。”[4]35朱振武对清教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进程中,清教思想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没有清教思想的影响,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走的必将是另外一条道路,而今天引领着世界文学潮流的美国小说又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3]6
纳撒尼尔·霍桑便是受清教传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家。因受到严格的清教家庭教育,同时深受祖先贵格会教徒迫害案、萨勒姆驱巫案精神遗产的影响,霍桑的作品被深深打下了清教思想的烙印。与超验主义文学作品的乐观、自信、自立形成极大的反差,霍桑受到加尔文教的人性观影响,大部分小说呈现阴郁的心理叙事风格,从不同维度探寻了人类的心理阴暗面,揭示了清教思想中罪恶给人们带来的不同维度的影响。在《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作者描述了祖先的罪恶给后代带来的诅咒和恶果;《年轻小伙布朗》寓言式地揭示了人类在高贵的表象下隐藏着的种种罪恶,并因此受到魔鬼召唤;在《拉帕奇尼的女儿》中,医生拉帕奇尼不惜以自己女儿做试验品为代价,以实现疯狂荒谬的罪恶,而《教长的黑面纱》中,作者又进一步告诫世人,试图将不可告人的罪恶掩藏起来也无法逃脱惩罚,只能使自己在心灵的炼狱里煎熬。引用纽约大学教授弗朗西斯·H·斯托达德在他的学术论著《英语小说的演变》的话说:霍桑的小说“倾向展示个体内部的自我斗争与灵魂的折磨。”[5]
与他的其它小说不同的是,霍桑在在其代表作《红字》中,对清教文化传统进行了理性审视、反思和批判。作品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嫁给了医生奇灵渥斯,他们之间却没有爱情。在孤独中海丝特与牧师亚瑟·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丁梅斯代尔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与海斯特的爱情,只能在孤独中痛苦地挣扎,并默默忍受着奇灵渥斯的报复。而海丝特被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她不仅独自忍受着通奸罪带来的惩罚,还把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秘密埋藏心底。同时又通过勤勉、节制和自我牺牲等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认可甚至尊重,而最终亚瑟也在临终前鼓起勇气对海斯特道出了心声。作品一方面揭示了加尔文教对人们精神、心灵和道德的摧残,揭露了清教统治者的伪善和残酷。另一方面,清晰地表露了对清教统治伦理观念的质疑和“温和的讽刺”[3]67,使作品在清教传统的阴霾下放射出人性和道德的光芒,创造了一种弥漫着清教文化色彩的美国式罗曼司,最典型地展示了美国本土文化与精神风貌。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 “它讲述的故事是绝对美国式的,它属于这片土地,这片天空,它来自新英格兰的正中心”。[6]它与麦尔维尔的《白鲸》被称作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的两座高峰,是美国散文体叙事文学独立于欧洲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文学作品主题的本土化:扎根美国本土,彰显民族精神
作为美国民族文化倡导者,同时作为一名作家,爱默生在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他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应注重美国本土文化精神和当代生活的反映和呈现。他在《美国学者》中指出,“衡量诗人才能的高低不在于他所读过的书,而在于他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感受能力,不在于他对司各特或莎士比亚的迷信和崇拜达到何等程度,而在于他把时代的、民族的事物转换成他诗中具有普遍意义形象的创造力。”[7]受到他的鼓舞,一大批诗人为诗歌的本土化做出了努力。威廉·布莱恩特和菲利普·弗雷诺均以美国本土风物为对象进行了大量诗歌创作,朗费罗则以印第安人风土人情和文化风貌为题材,创作了第一部印第安人史诗《海华沙之歌》,而惠特曼则是贯彻爱默生文学主张的经典民族诗人。哈罗德·布鲁姆曾用“美国经典的核心”[8]213这一评语来评价惠特曼,代表了评论界对惠特曼文学地位的肯定。
惠特曼以关注美国宏大历史主题为中心,揭示本土人物精神风貌,弘扬美国民族性格,在诗歌创作中为美国民族文学的本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草叶集》的序言和后续的诗歌中,诗人表达了他的核心思想:美国诗人应当理直气壮地描写美国人的生活、性格和理想,宣扬美国人张扬自我、勇于开拓和追求幸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人格。他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乐观向上、开拓创新和独立进取的劳动人民——铁匠、木匠、屠夫、伙计、纤夫、排字工人、筑路工和诗人等包罗众生的美国“新人”形象。诗人还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盖房、炼铁、造船、采煤、炼油、制糖、凿石、收棉、酿酒、制鞋、宰牲、磨粉等各行各业的具体劳动,表现出对劳动和劳动群众的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感情,对蒸蒸日上的美国的赞美溢于言表。诗人以第一人称“我”为缩影,最为集中而个性张扬地抒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必须前进,亲爱的哟,我们必须首先冒险,/我们是年轻的强壮有力的种族,别的人全靠我们”;[9]383“我看见我自己的种族,这是最新最伟大的种族的力量之强大与友爱的象征。”[9]325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传达了惠特曼对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利坚民族把握自己命运和国家前途的豪情和信心,热情讴歌着美利坚民族张扬自我、勇于开拓和蓬勃向上的民族性格,凸显了强烈的美国本土特性,描摹了有关整个民族发展前景的想象。正如布鲁姆所言:“惠特曼的经典性在于他成功地永久改变了美国的声音形象。”[8]214-215“惠特曼奠定了我们想象性文学中为美国所独有的东西,即使反对阵营也承认他的先辈地位。”[9]224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的小说家们以小说这种更宏大的文学体裁,从更宽广和深厚的维度展现着这个时期美国人更加深刻的一面。区别于英国和欧洲复杂而盘根错节的传统社会,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固定国界、疆土不断变化的国家。同时,美国又有别于欧洲,缺少一个稳定的、复杂的、使人们心理安全的社会结构,这样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以及清教文化的人文氛围,逐渐浸润和培养出这一阶段美国知识阶层特有的精神气质:孤独、焦虑、不安,又充满理想主义、敢于挑战。霍桑和麦尔维尔便是这些小说家的杰出代表,他们通常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和传统之外的孤独的探索者”。[10]他们笔下的人物性格各异、异彩纷呈,既有萌芽状态的美国式的英雄,如麦尔维尔笔下的船长亚哈,敢于迎接挑战,面对危险和毁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又有孤独、焦虑、寻求灵魂解脱的黑夜旅者,如霍桑《红字》中饱受心灵折磨的亚瑟·丁梅斯代尔和海丝特·白兰,以及《年轻小伙布朗》中孤独地在森林中遭遇行走的魔鬼的布朗。这些孤独的主人公在富于象征意义的情节中,与未知的、黑暗的命运作斗争。作者试图对人物进行深入的心灵探索,以某种神秘或寓言方式,揭示着隐秘的、极度痛苦的灵魂。
以麦尔维尔的《白鲸》为例,整部作品就是一部刻画美国人形象,书写美国民族身份、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作品,是一部美国史诗和民族神话,正如美国学者哈利·斯洛乔厄在《莫比·狄克:民主期待的神话》一文中说:“麦尔维尔的《白鲸》是第一部主要的美国文学神话作品。”[11]麦尔维尔以极其敏锐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社会变迁,赋予作品强烈的美国民族特性。小说透过捕鲸业折射了全面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欣欣向荣的美国社会,而小说中的“裴廓德号”捕鲸船被视作美国的凝缩和象征,森严的船员管理结构、精细的船员职责分工、捕鲸过程和航海技术的专业化和精密化,无不折射着美国工业文明的强大,也流露出作家对美国蒸蒸日上的国家自豪感。以船长亚哈为代表的船员和水手在神秘、未知的大海上的冒险之旅,充分反映了美国人重建自己伊甸园的美国梦。船长亚哈的航海生涯和他与白鲸三天三夜的搏斗,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时的美国人一心征服自然,挑战自然,敢于冲破围困自己的桎梏,成为命运主人的决心和勇气。
同时,麦尔维尔也以极高的政治和社会敏感性,关注着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并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和隐忧。他在作品中赋予了船长亚哈和捕鲸之旅多重深厚的象征寓意。捕鲸之旅暗指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白人开拓者对野牛的大屠杀,借以揭示美国政府的扩张行径给土著居民和大自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以及对狂傲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担忧。而作品最后偏执疯狂的亚哈和他的船员及裴阔德号与白鲸同归于尽,清晰表明了作者对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可能带来的灾难感到忧心忡忡,这些足见作者的思想前瞻性,也给作品打上了强烈的美国时代烙印。
四、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本土化:锐意艺术创新,凸现民族气质
惟有不断地艺术创新和突破,才能使民族文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是美国文学本土化过程的重要特征和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通过个人奋斗而获得拯救的新教价值观,以及求新逐变、不断进取的民族心理特性,促使着美国作家们不断寻求艺术创新和突破。正如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所说:“无论一个人的天赋有多高,只要他不创造,他就不会拥有上帝智慧的清纯泉涌——或许已经有了煤块与烟雾,但却点不着火焰。”[1]98
在小说的创作领域,如果说美国浪漫主义早期的作家还更多地受到英国乃至欧洲文学传统的羁绊的话,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则对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色进行了大胆突破和创新,创作出一系列艺术特色各异、具有强烈思想启迪性、且具有独特文学审美的文学作品,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欧洲的带有美国身份标签和民族气质的文学,霍桑和爱伦·坡则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霍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开创了“心理罗曼司”的写作方法。他将罗曼司定义为想象与现实、梦幻与清醒之间的“中间地带”,[12]而他的罗曼司关注的正是这个“中间地带”,即现实与想象的交接处,以发现人的心理世界的真相。在作品中,霍桑探索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梦幻般的浪漫气氛、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色彩和瑰丽的象征手法,来发现人的心理世界的真相,探索美国清教徒的心理意识。霍桑的罗曼司开创了美国小说的新文体和新传统,他关于罗曼司的阐述“几乎成为所有后来对美国罗曼司结构和功能描述或定义的基准”。[13]当代美国作家盖伊·塔利斯和保罗·奥斯特分别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撰文,均将《红字》列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五本著作之首,甚而认为“它是美国文学的开端”,[14]英国的评论家亨利·F·乔利在伦敦《雅典娜神殿》杂志上把霍桑列入 “最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美国小说作家”。[15]
这一时期另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学开拓者是爱伦·坡。他一生饱受挫折和争议,生前一度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学之外。但是在生活窘迫、疾病缠身的境况下,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执著,不断探索创新、独辟蹊径,在小说和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学体裁和文学创作理论等众多领域有开拓之举,为小说和诗歌在新大陆实现本土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罗伯特·斯皮勒对坡的评价是“艺术天才为自觉艺术在美国本土的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16]
在小说创作方面,坡在继承和发扬恐怖、怪诞与晦暗等元素的欧洲哥特小说传统的基础上,探索书写了属于美国的经典哥特小说,并将哥特小说元素应用到了他所开创的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中。首先,他立足于美国本土的特异性,将作品背景由阴森的欧洲古堡和教堂移植到了广阔的美国疆土,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思想与保守的宗教理念相左时造成的早期居民的精神异化,表达了作者对旧世界的迷茫和对新世界的困惑,对物欲驱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非理性情感予以关怀。其次,坡创新了哥特小说的表现形式。他对作品进行了精雕细琢,成功地进行了心理恐惧的描写以及潜意识思绪的探索,使哥特小说在美国呈现内在化和心理化,并前瞻性地赋予了作品现代性内涵,从而开拓了哥特小说创作空间和表现形式,表达了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
坡在文学创作上展现的非凡的创新力和想象力,凸现了美国人求新图变、追求卓越的精神气质。美国现代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对坡“创造了完全不同于欧洲传统的美国风格”[17]的评价,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坡对美国文学本土化的重要贡献。
总之,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是美国文学本土化进程的重要成长期,文学家们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大旗,摒弃欧洲文化传统的桎梏,以具有美国本土思想特质的超验主义和清教思想为引领,深入美国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多维度地关注美国社会和民众,并锐意进行艺术创新,彰显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思想特质,为之后美国文学真正独立并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文学本土化道路。
五、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启示
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中国文学面临着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受西方文化大潮裹挟,文学作品的民族文化特性日益淡化和疏离,脱离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忽视对社会重大主题、现实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关注。文学失去了应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学思想空洞和贫乏。文学创作呈现出泛化、娱乐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在此语境下,我们回顾和反思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进程的经验,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繁荣中华民族文化,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意义:
第一,以爱默生和惠特曼为代表的美国作家,为摆脱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和确立独立的民族文化而大声疾呼,满怀历史责任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投入到文学创作中。这种对于本民族和国家朴素而热忱的情感,具有跨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在各国人民心中产生了心理共鸣,更成为当下中国作家值得汲取的精神财富。为此,广大作家应增强危机意识和使命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文学作品的创作,应善于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反映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特质、精神和价值,形成中国本土的审视和叙述世界的视角及方式,以消弭西方性的过度泛滥,提高中国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国际话语权。第二,以惠特曼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以饱满的热情歌颂美国的劳动人民,并以细腻的笔触描写美国现实生活,这都来源于作家本人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刻认识,反映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理。这一点值得当下广大作家反思。我们更应超越惠特曼,真正确立为民族大众创作的原则。文学创作不仅要深入现实生活,立足于深邃而广袤的本土生活,还要真心关注普通民众的希冀、痛苦、关切和诉求。惟于此,文学作品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正如学者贺仲明指出“能否深入到生活之中,表达出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处境,是对文学本土化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18]第三,以麦尔维尔、霍桑、爱伦·坡等为代表的作家,以求新图变的创新精神、高度的政治和社会敏感性,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表达着对美国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关切及隐忧。同时,他们深入人性内部,探索人类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危机,体现出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关注和审美观照。这也给中国文学创作以极大启示。在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必须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把握时代主旋律,关注和反映新时期的重大现实社会问题和矛盾,展现改革开放下的当代中国精神风貌,强化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深度揭示和厚重感,增强文学作品对个体命运的人文关怀。同时,作家要不断艺术创新,力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以削弱文学创作的低俗化和浅薄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