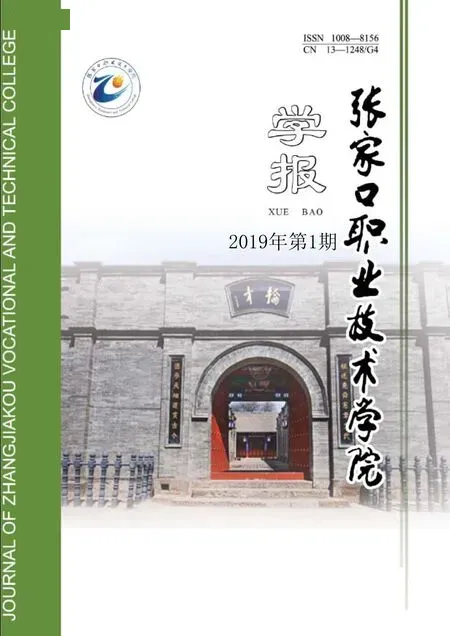尊重和保障人权视角下的“钓鱼执法”措施研究
2019-01-31葛文龙
葛文龙
(浙江工商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2018年12月我国政府颁发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正文第一节即是“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治国理政原则”。[1]可见对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视,行政执法领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尤为重要的一环,行政机关是贯彻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治国理政”指导理念的重要主体,事关基本人权保障,尤其是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在执法中出于执法效果与执法效率往往被忽视,既未做好温情执法、人性执法,又违背宪法核心价值理念,使执法案件存有指摘之处,尤其是“钓鱼执法”问题。“保障人权”即要求行政权力要受合理的限制,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人权的侵犯,是贯彻国家根本法约束公权对人权侵害的要求。[2]
宪法上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价值理念,贯彻于行政执法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其一是行政机关依靠国家强制力制裁违法行为,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不受非法侵害;其二是保障在行政违法行为中受害人的权利,弥补其法益所受侵害的损失;其三是最为核心,也是当今世界人权发展和我国人权保护最为重视之所在,就是在行政执法中保障违法行为人的基本人格尊严、隐私权、人身自由权等基本人权。
一、“钓鱼执法”概念释义
“钓鱼执法”的文义表达生动明了,是为诱惑行为,如同以鱼饵引诱鱼如愿上钩,此处的“鱼饵”即执法人员设置的“陷阱”与“圈套”,“鱼”即潜在的违法行为人,执法人员在“鱼饵”与“鱼”之间供给特定的条件,从而“收网”,以期获得所欲的执法效果。其渊源于英美法系,又称“执法圈套”、“警察圈套”。[3]通常认为其是一种不正当的执法措施,具体表现为执法人员为破获一些潜在的违法行为,但该行为人的踪迹、违法线索、违法地点等隐藏较深,是故执法人员故意设置特定的引诱行为人以及其它线索的违法情境,或为其提供实施违法的时机与条件,待其实施违法行为时将其人赃并获。
二、“钓鱼执法”与诱惑侦查的渊源
“钓鱼执法”源流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措施。其释义如同一辙,只不过是其适用主体、适用对象上存有不同,“钓鱼执法”是行政主体所适用的,针对的是潜在的违法行为人,若滥用针对的对象则是普通公民;诱惑侦查适用的主体是侦查机关,适用的对象是潜在的特别重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二者在本质上存有显著区别,在适用形式上是相同的。
诱惑侦查又可分为犯意诱发型、机会提供型。[4]犯意诱发型表现为侦查人员或其操控的特定人员去诱惑原本没有犯意的人,促使其萌生犯意,并随之去犯罪。机会提供型表现为行为人原本就带有进行犯罪的意思,侦查人员只是为其进行犯罪“提供”一次实施的机会,创造了“天时、地利、人和”。其中犯意诱发型明显违背刑事侦查基本精神以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已然被认定为非法侦查措施,被禁止适用,而机会提供型则具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法依据,其可以在合理规制的特定条件下准予适用。
既然“钓鱼执法”源流于诱惑侦查,如此可推知“钓鱼执法”也有类型化区分,遵照逻辑体例可分为犯意诱发型“钓鱼执法”和机会提供型“钓鱼执法”。置于生活情境下的“犯意诱发型”钓鱼执法,诸如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为整治“黑车”运营,伪装成为“乘客”向过往的非商业营运车辆请求搭乘,待乘车之后行驶一段路程,支付司机一定报酬,此时便出示执法证件,即对司机采用行政强制措施,将其作为“黑车”营运予以行政处罚。此举不乏频繁上演,显然可见司机并无“非法营运”之故意,只是出于“路人”的搭载请求予以好意施惠,却被认定为非法营运,当下的“钓鱼执法”多是此等,行政执法行为显然不合法,自不待言。关于机会提供型“钓鱼执法”置于生活情境,例如公安机关得知某处所时常或曾经有卖淫嫖娼行为,为捕获现行予以打击,伪装成“嫖客”进入场所,待其提供有偿性服务时,采取捕获措施;再如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得知某经营商家经常存有“短斤少两”的欺诈消费者行为,为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消费者权益,执法人员伪装成“消费者”前往该处“消费”,当商家暴露行迹时,将其固定证据予以处罚制裁。此等机会提供型“钓鱼”执法针对已经进行违法的行为人或者曾经有过不法行为的行为人,为捕获现行与固定证据等,为其提供了一次“表演”的机会,被行政机关当作是有效的执法行为,看似从执法过程中获得了行为人违法的事实与证据,处罚结果也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违法行为人也坦认不讳,果真如此符合宪法人权保障之精神?此举需要细密分析。
三、“钓鱼执法”的合法性宏观衡量:是否遵循人权保障之精神
一项执法措施能否在执法中得以正确实施,需要结合衡量原则和评价条件去具体分析,最终在法理上衡判是否符合宪法上的人权保障精神,如若不然,则必然缺少核心价值理念的支撑。针对上文所述“钓鱼执法”中的犯意诱发型与机会提供型的类型化区分,关于犯意诱发型显然不具有行政行为合法性,在此探讨已无意义,本处详细探讨机会提供型的“钓鱼执法”的合法性问题。
即使机会提供型“钓鱼执法”,显然可见其在正当程序的形式上也必然不正当,故需要进一步在实体性正当程序上予以分析正当与否,即分析行为人的违法构成要件与执法的目的价值。需要从行为人违法性的主观层面和客观层面以及结合执法机关的执法标准予以分析。
学界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观点,主观层面是指要以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前是否有主观违法性为参照,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受到诱惑或诱惑程度是否超出法之允忍的限度,并且还需要结合行为人先前的品格、前科等考量其违法性心态。此举是用曾经的“不光辉历史”来佐证今下的“不法心理”,有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犹如曾经有过卖淫行为,难道就能推断出现在依然以此为业吗?曾经有过“短斤少两”的欺诈行为就能推断如今依旧吗?诚然,行为人曾经的不法行为,对于公权力关于出于惩治违法行为的需要,可以调查使用,但是此等类似“品格证据”捕风捉影的有罪推定,实然对行为人的基本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不予尊重。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将被执法者的人权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衡量其希望实现的行为效果,禁止过度的行为与手段。[5]此等授予执法人员较大的主观自由裁量推定的权限,难以达到强有力的法律论证与证据论证,对行为人追究违法责任有自由滥用之嫌,难以客观定性。客观标准,即要以诱惑行为的实质条件作为衡量标准,审视和分析诱惑行为在具体运用之中是否约束在正常人所能接受的限度之内,易言之,过度诱惑导致行为人萌生违法故意则是不正当,如若诱惑程度在合理限度内则是正当的。一方面,人性有罪恶是必然,对于基本人权的尊重,不能予以试探性诱惑其进行不法行为,尽管曾经行为人如此。另一方面,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审查则转换成对执法人员实施的“诱惑行为”的必要性、幅度合理性考量等“执法技巧”的技术性判断标准,就忽视了行为人的主观违法心态的认定,具有客观归责之嫌。
综上,“钓鱼执法”不仅违背程序性正当程序,在实体性正当程序当中亦难以给与法理支撑,在实际运用中显然违背人权保障之精神,被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所摈弃。执法机关片面追求执法效率,置公民的基本人权于不顾,属于本末倒置的公权力滥用行为。[6]在惩治“黑车”中利用人性之良善,而予以犯意诱发的“钓鱼执法”,置人性温情于不顾,人权保障的应然要求除需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之外,还有内心的真挚善良,人性在合法范围内的自由发挥不受干涉。在惩治卖淫等案件中予以机会提供的“钓鱼执法”,无形之中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与隐私权,并且带有罪推定之意。行政违法行为对于刑事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显著偏小,同种形式的诱惑侦查可以适用于针对重大危害的犯罪行为中去,然而“钓鱼执法”措施不能武断地运用到行政执法活动中,简言之,不能擅自把用于侦查重大危害犯罪行为的手段施用于行政执法案件中,实施重大犯罪的犯罪行为人与普通违法行为人不能同等对待。[7]
四、结语
“钓鱼执法”一定程度上体现执法人员的权力异化,是不合法的执法手段,要坚决予以抵制,如若理念上还承认“合法性”的认识,会给执法人员的执法理念造成混乱,澄清不力其势必会蔓延到整个行政执法当中,使“钓鱼执法”等执法圈套愈演愈多并难以规制,公权力追求执法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的所有的“诱惑”行为人的措施,也是公法自身所要强烈抵制的对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贯穿于公权力所运行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