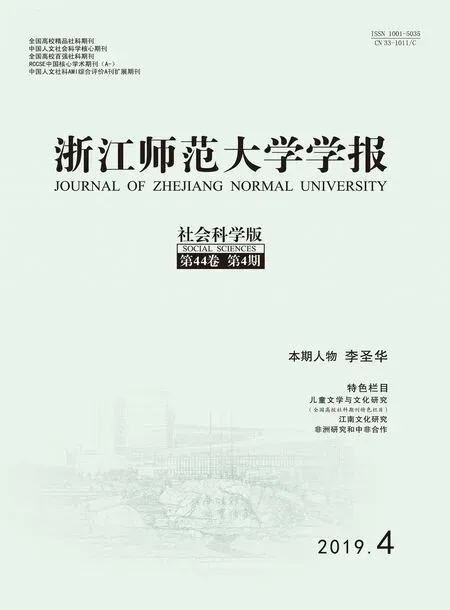古罗马艺术中的黑人形象
2019-01-30冯定雄李志涛
冯定雄, 李志涛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罗马国家起源于台伯河畔,通过经年累月的争战,逐渐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公元前146年,罗马灭亡了最后一个希腊城邦科林斯,公元前31年,当屋大维击败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统治者安东尼和克里奥巴特拉的时候,整个东部希腊语区也落入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之手,这样,地中海也就成了罗马的内湖。但是,正如奥古斯都的桂冠诗人贺拉斯所注意到的那样,“被征服的希腊人,把他们的艺术带到了土气的拉丁姆,用这种方式征服了他们野蛮的征服者。”[1]无论人们怎样理解这段话,[2]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罗马艺术既是对希腊艺术风格的继承,也有新的发展。
古罗马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人生活与现实的反映。古罗马表现黑人①的艺术品不仅数量众多,表现主题也非常丰富,因此,它是我们研究古罗马人对黑人态度的重要材料,其价值有时候甚至比文献资料的价值还要高,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作为人类学资料信息的来源,艺术品在某些方面比文献更具价值,因为它能告诉我们比文献更多的关于凸颌的数量或者缺失的情况,更多关于阔鼻和嘴唇外翻的程度以及脸型的比例和发型的情况。”[3]22不仅如此,古罗马艺术品中的黑人绘画主题还反映了罗马人对待黑人的态度,这对于考察西方古代社会是否具有种族主义歧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就考古发现的涉及黑人内容的古罗马艺术品进行探讨,分别考察罗马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罗马艺术品中所表现的黑人主题及罗马人对待黑人的态度。
一、罗马共和国时期艺术品中黑人形象
当希腊文明,特别是雅典文明在走向辉煌的时候,罗马国家还在意大利半岛徘徊,“实事求是地说,只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以后,希腊人才发现了罗马人、克尔特人和犹太人。”[4]但是,一旦罗马人与希腊人接触,他们即被希腊文化所陶醉,而此时恰巧是希腊的希腊化时代,因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希腊化时期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罗马艺术品中的黑人形象也与希腊化时期的黑人艺术风格直接相关。
来自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无釉赤陶小面具是一件描绘黑人形象的写实艺术品。[3]162-238该头像虽然头发卷曲程度不突出,但其扁平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却是黑人典型的面部特征表现。黑人在古代世界里经常以杂技演员的形象出现,希腊化风格的罗马大理石雕像表现了他们用胸和手保持平衡,而把双脚倒立于空中。老普林尼曾告诉我们:“在尼罗河的右岸有一支人类部落,他们以其所居住的腾提鲁斯岛(Tentyrus,即现在的Denderah,邓德拉)被称为腾提鲁斯人(Tentyritae),他们是这一怪物(鳄鱼)的天敌。他们身材矮小但唯有在这件事上能头脑清醒且很著名。这里说的这个动物(鳄鱼)对于面对它就逃跑的人是很可怕的,但它会从追逐它的人面前逃跑。但是,这些腾提鲁斯男人却敢独自面对这些鳄鱼,事实上,他们会跳到水里骑在它们的背上,就像骑在马上一样。当它们张开大口,头向后咬的时候,他们就在它们的嘴里插上一根木杆,并用左右双手紧紧抓住木杆的两端,就像用缰绳一样把它们往岸上拖;或者通过大声喊叫只是吓唬它们,迫使它们从嘴里吐出刚刚吞食的尸体用以埋葬。”[5]可能正因为如此,黑人爬在鳄鱼背上的场景就成为艺术家们的重要表现主题之一。有两尊来源于希腊化风格的罗马雕塑其造型几乎完全一样,都描绘一位作为杂技演员的黑人男孩倒立在鳄鱼背上的场景。[3]79-244两位黑人男孩头发呈螺旋状卷曲,宽阔扁平的鼻子,高颊骨,厚嘴唇,属于典型的黑人。当然,是不是属于老普林尼所描述的腾提鲁斯人,我们只能进行推测了。发现于意大利佩鲁甲的小男孩青铜雕像制作于罗马共和国晚期或者帝国早期,该青铜雕像位于一座基座上,皮肤漆黑,身材苗条,但体格健硕,头发卷曲,鼻子扁平,嘴唇较厚但并不外翻,属于尼格罗类型的黑人。该男孩手持灯笼,很明显是一位主人的侍从。[3]90-187
罗马共和国时期关于黑人的艺术品的典型特征是它对希腊化时代的描绘主题和风格的延续。从描绘主题上看,这一时期的黑人艺术品基本上集中于现实世俗世界,与早期希腊、古典时期的希腊的描述主题大异其趣,与希腊化时期的描述主题却是一脉相承,如对普通民众(甚至低贱阶层)的关注,描述对象的多样化等。在风格上也是对希腊化艺术风格的延续,如前述的面具、雕像等,无论是制作尺寸还是制作手法都与前述的希腊化风格极为相似。在具体内容方面,这一时期的黑人艺术品也与希腊化时代的情形如出一辙,它特别强调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的关注,如两件极为相似的倒立于鳄鱼身上的杂技演员,虽然捕捉鳄鱼的场景在罗马不一定能见到,但老普林尼的记述所描述的情形却在罗马社会生活中广为人知;②再如位于基座上的小男孩青铜雕像,从其动作判断,应该是演说者或者舞者,这些都是罗马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
二、罗马帝国时期艺术品中的黑人形象
到帝国时代,罗马艺术中关于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描绘与希腊化及罗马共和国时代的描绘特征是相延续的,只是到帝国中后期,其主题范围更加广泛。特别是基督教在罗马社会日益流行起来后,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宗教艺术占据了罗马社会和民众生活的主流地位,其主题和风格与此前的希腊罗马宗教艺术相比均有较大变化,作为基督教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黑人主题艺术也逐渐地走向了为基督教艺术和宗教服务的道路,体现着罗马艺术的转型。
与希腊黑人艺术一样,罗马帝国时代的艺术中,宗教神话始终是艺术的重要描绘主题之一。伊西斯崇拜不管是在埃塞俄比亚本土还是在埃及都受到埃塞俄比亚人的高度重视,因此,那些身居异乡(包括罗马)的埃塞俄比亚人在仪式中延续他们的兴趣是理所当然的。如前面提到的发现于雅典的公元前1世纪半期或者公元1世纪前半期的黑白混血人种的头像就被认为是埃及异族人为了自己的崇拜所需的本土祭司;来自希腊化时代的Aphrodisias闪长岩或大理石小雕像也是一位伊西斯祭司(Isiacus)。来自尼禄时代的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壁画中,有描绘伊西斯仪式的雕像群,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白人,还有一些人是黑人。除了其中的一个,其他的很难仅从面部特征看出艺术家的准确的面相意图,因为他们只是大致勾勒出了脸型。但是,这些半身雕像中的其中一个很明显是来自于黑人类型或者埃及类型的整体场景。罗斯托夫采夫认为这些黑人是祭司的侍者,[6]他们穿着从腋窝到脚的长袍,而白人崇拜者的长袍则是从肩到脚。在这尊雕像中,这位黑人崇拜者右臂向前伸出,站立在人群中央,这些人群站在中央的两旁,做着崇拜的姿势或者手持摇鼓。[3]189-252来自阿里恰(Ariccia)附近的阿庇安大道(the Appian Way)上的公元2世纪早期的坟墓③中的大理石浮雕也明显地与伊西斯和塞拉皮斯(Serapis)崇拜紧密相联。[3]23-242浮雕中有三位臀部特别肥大的黑人妇女,她们正在翩翩起舞,神情甚是陶醉,很明显是祭祀仪式中的场景。这些黑人妇女的夸张舞蹈包括屈膝和向后摇头,她们所进行的动作毫无疑问在喜剧中是很普遍的,这也与古典作家的记载相吻合。据说,舞蹈在一些埃塞俄比亚人中是如此地盛行,以至于在战争中,在他们跳舞前他们是不会射出他们的箭的。“他们头上戴着圆形圈袋,里面装着箭,箭羽朝里而箭头向外,就象太阳的光芒一样。在小的战斗中,他们很容易从箭袋中拔出箭,像萨梯一样跳跃起舞,然后攻击敌人。”④除了与埃塞俄比亚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伊西斯崇拜外,在罗马宗教的其他崇拜中,也有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艺术表现。如在公元180—200年的大理石棺上的描绘巴库斯(Bacchus)的胜利的绘画中,有两个黑人男孩骑着一对豹子,他们乘着巴库斯的胜利马车。该石棺来自于一个家族墓地。左边两个穿着神的豹皮的年轻人被认为是为巴库斯神服务的新成员,是天真无邪的年轻人的象征。艺术家选择黑人男孩作为胜利之神这种角色是有原因的,据狄奥多罗斯说,狄奥尼索斯(Dionysus)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他还给所有虔诚于他的男人以指示并在他的仪式范围内培养这些人的公正的生活,还使他们理解他的神秘,而且,他还在各地举办盛大的节日集会和音乐竞赛。总之,他调解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争吵并在有民事冲突和战争的地方建立和睦和平安。……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他给那些遵从他的神圣天理的人以优越权力,惩罚那些对他不虔敬的人,要么是使这些人疯狂,要么就让这些人依靠女人的双手生活在痛苦中;在另外的情况下,他会通过令人吃惊的军事装备破坏那些反对他的人。”[7]在希腊罗马传统(或者说荷马传统)中,埃塞俄比亚人是世界上对诸神最虔敬的民族,因此,石棺上的黑人可能正是艺术家源于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虔诚与公正这一传统灵感。浮雕中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野蛮人的小孩子与石棺上的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罪人与劫掠品一起被绑在大象身上。该浮雕把埃塞俄比亚人作为虔诚与公正的象征,反映的可能是狄奥尼索斯神在取得胜利后,在他从世界最南极的地方返回欧洲的行程中,给予了这两个黑人男孩以荣誉的特别地位。[3]149-229
在表现传统的宗教神话题材之外,罗马帝国时期关于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艺术更多地则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题材。在罗马把地中海变成内海的过程中,罗马的“伟大”得到了彰显,反映罗马使臣、高级官吏等上层贵族阶级的外交活动的艺术内容也不少。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罗马青铜像,卷发长条梳理,宽鼻子,高颊骨,鼻下前突,厚嘴唇,拥有八字胡和络腮胡子,它的身份应该是罗马的一位高官。弗拉维王朝时期真人大小的大理石半身雕像,身披一件覆盖物,头发卷曲,目光有神,嘴唇很厚,面带微笑,该男子被认为是作为使臣或者人质来到罗马的黑人,可能是在他停留罗马期间制作了他的雕像。来自约公元100年的麦罗埃的道路里程碑上的黑人头像,其黑色画面上有白色的眼睛,嘴唇有疤痕。该黑人被认为是罗马官员送给麦罗埃国王的礼物。在泰里亚替斯(Thyreatis)发现的公元160—170年的潘泰列克大理石(Pentelic marble)头像,可能是阿提库斯(Atticus)的被监护人门农。该头像头发短而卷曲(羊毛性效果),鼻子虽然已经被破坏但明显很宽阔,厚嘴唇。⑤门农被认为是希罗德·阿提库斯⑥的一个儿子,阿提库斯是继基督之后,公元2世纪最有影响的国际贵族人物。他是著名的智者和悼念门农之死的资助人,也是他视如己出的另外两个代养的孩子的庇护人,因为这两个孩子是高尚的、具有荣誉的青年,他们喜爱学习,值得在他的家庭长大成人。⑦另一个来自公元250—260年的雅典的年轻男子潘泰列克的大理石头像,该头像头发短平,因此看上去不是特别卷曲,鼻子被破坏了,嘴唇略厚,可以肯定是一位黑人;其身份不能确定,可能代表了上层社会阶级的一位绅士。[3]81-249
在描绘上层贵族生活的艺术题材中,上层妇女的生活也是艺术家们乐此不疲的重要的内容。罗马文献及其他材料中对黑人妇女的赞美性描绘是很丰富的,如维吉尔对黑人梅那伽的爱慕,[8]7对黑人阿敏塔的爱情;[8]46奥维德与黑人西帕西斯的爱情;[9]马尔提亚明确地写道他宁愿喜欢黑人姑娘也不喜欢白人姑娘:“我想要的女孩是要比夜晚还要黑的,比蚂蚁还要黑的,比沥青还要黑的,比乌鸦还要黑的,比蟋蟀还要黑的。”[10]卢克索里斯称赞迦太基竞技场的黑人英雄奥林庇乌斯具有“珍贵的乌黑”“宝石之光”。[11]在庞贝城郊区一个农庄的墙壁画中,作者宣称:“无论谁喜欢黑人,就像烧成漆黑的木炭的黑人,反正当我看到黑人时,我都很高兴吃黑莓。”[12]公元2世纪下半期,富裕的罗马人可能通过黑人妇女头像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爱,这些黑人妇女美好的身材在黑色大理石雕像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1947年发现于雅典阿哥拉(Agora)的大理石妇女头像上,该妇女长头发,头发盘成卷用以装饰脸,两端拧成绳链一样,鼻子有些扁平,嘴唇很厚。这应该是一位雅典黑人妇女被处决的头像。有学者认为“这个小型的大理石头像……揭示了精巧手艺以熟练的技能和富有的同情心对待外来类型的情形。宽阔的鼻子、很厚的嘴唇以及凸出的颊骨都标志着这位妇女具有黑人血统。软帽式的发型(bonnet-like coiffure)是图拉真时期宫廷女士的温和的穿戴风格”。[13]斯诺登则认为:“我对该大理石雕像的考察使我坚信,毫无疑问这是黑人混种人。”[3]93不管怎样,该黑人妇女应该是罗马上层社会女性的代表之一。另一尊黑人妇女大理石头像可能属于哈德良时期,该头像头发浓密卷曲,鼻子略宽,嘴唇很厚。该妇女如果不是贵族,至少也是富人。[3]93-254
罗马帝国时代反映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的艺术品最多的是反映他们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职业者。亚历山大里亚港口作为地中海世界与东方海域的中转站,极大地增加了希腊罗马人与埃塞俄比亚人之间的联系。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各色人等聚集到亚历山大里亚港口,这些埃塞俄比亚人参与到说着各种语言的人群生活之中。他们还可以通过从亚历山大里亚港口定期出发到地中海世界的各港口的船只抵达意大利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罗马博物馆中的无釉赤陶曾是古老海港的房屋和坟墓中的装饰品,它们生动地展示了罗马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生活。这些描绘黑人的收藏品不仅生动地反映了黑人的各种职业,而且对研究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有好几尊雕像反映的是持灯笼的黑人。还有一尊由提着灯笼的奴隶陪伴的年轻醉酒者雕像,该雕像制作于公元前30年之后,黑人奴隶一手持着灯笼,一手吃力地扶着醉酒的主人,形象生动逼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现实生活状况。比较有特色的一件艺术品是一位潜水者雕像,它的造型生动地描绘了一位黑人潜水者在水下的动作。帝国时期,罗马境内还有大量描绘其他黑人职业的艺术品,如来自公元2世纪早期的阿里恰的大理石浮雕上的舞蹈和鼓掌场景,上面描绘的黑人妇女的夸张舞蹈,包括屈膝和向后摇头,而她们所进行的动作在希腊罗马喜剧中是很普遍的。在发现于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尊白色大理石的黑人半身雕像中,该雕像的黑人身披短托袈,下身裸露,表情自然,被认为是公元2世纪的一位歌手或者演员。来自公元前30年之后的一尊雕像,描绘了一位黑人小男孩站立在葡萄藤中,双脚在踩阿基米德螺线(Archimedean screw)。来自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大约公元1世纪的大理石浮雕描绘了一位正在驱赶双马双轮战车(biga)的黑人,他紧贴头的卷发,宽阔、扁平的鼻子,厚嘴唇,鼻下前突,是典型的黑人肖像,其神情严肃专注,手臂肌肉发达,明显地正在用力;另一位武士则手持武器走在马前。来自庞贝城的无釉赤陶描绘了一位黑人象夫正骑着大象。[3]78-250公元1世纪的罗马诗人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曾比较详细地描述过迦太基军队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和努比亚人,[14]因此,这件无釉赤陶雕像的灵感可能是来自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埃塞俄比亚象夫,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黑人(埃塞俄比亚人)只有在汉尼拔的迦太基军队中才有,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其他类型的黑人象夫同样存在。
在古代社会,“和平只是一个空名”,[15]战争是一种“无情的规律”,[16]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它不仅贯穿整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在文化中也有明显反映。作为战利品的战俘,通常也会成为艺术家们的创作题材。罗马帝国的艺术品也一样,有大量作品反映战争场面和战俘情况。在罗马征战埃塞俄比亚的过程中,那些被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作为俘虏出售的埃塞俄比亚人到了罗马世界的各地区。全副武装的黑人武士的无釉赤陶为罗马帝国早期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身体类型提供了重要证据。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罗马博物馆中的无釉赤陶藏品包括有这些方面的生动例子。藏品中最大的一件是一位穿着短衣(可能是皮制品)的人物形象,短外套钩在肩上,右手握着双面斧的手把,扛在右肩上,另一个人物形象则左手拿着椭圆盾牌,右手拿着双面斧,第三个人物被描绘成一位角斗士或者士兵,穿着长袖拖袈,身上有胸甲、宽阔的双刃短剑或匕首以及方形盾牌。[3]134在柏林的一对铜像可能是受到了佩特罗尼乌斯战役的影响,它们可能代表了战争中被俘获的埃塞俄比亚战俘。这些埃塞俄比亚战俘双手被反绑,神情紧张。发现于迦太基的安托尼努斯(Antoninus)温泉的道路里程碑上的黑人很可能属于凯旋性质的纪念碑上的内容,他们被认为是公元2世纪中期被罗马人在奥兰·撒哈拉(Oran Sahara)北部俘获的战俘。[3]134-227
罗马帝国时代的黑人艺术品仍然延续了希腊罗马的宗教神话传统。宗教在古代社会中占有首要地位,这几乎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在中国,早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印度,掌管宗教的婆罗门要比包括国王在内的刹帝利地位高,在埃及,法老虽然本身就是“神”,但祭司阶层对法老的影响甚至限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早期犹太民族中,国王虽然掌管有最高的世俗权力,但真正对民众生活产生实际控制的还是宗教的力量。希腊罗马社会宗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们没有专门的、显赫的祭司阶层,但宗教在它们国家中的地位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征战、媾和。罗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帝国时代的艺术品也同样延续着希腊艺术的特征,宗教神话主题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地,这一时期涉及黑人的艺术品也与罗马宗教题材紧密相联,如前面提到的与伊西斯女神和塞拉皮斯神的崇拜相关的艺术品,不仅在艺术主题,而且在艺术形式、表现风格等方面都直接沿袭希腊传统。
三、罗马黑人艺术形象与种族主义
无论罗马共和国还是帝国时期关于黑人的艺术品的典型特征都是对希腊化时代的描绘主题和风格的延续,但其主题选择却更加广泛多样,从而使得这些宗教题材的艺术作品在整个艺术品中的比例似乎在下降。这并不是说宗教题材的艺术品绝对数量在减少,而是由于其他题材的艺术作品在不断地出现和增加,从而使得宗教艺术作品在整个艺术作品中的比例显得不如最初的希腊艺术作品的比例那么高。
其次,罗马时代(特别是帝国时代)关于黑人的艺术品在反映罗马现实社会生活方面数量不断增加。这不仅体现在它们绝对数量的增加上,更主要的还体现在它们的主题更加多样化。如反映罗马使臣、高级官吏等上层贵族阶级的外交活动、反映上层贵族生活等,特别是关于帝国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职业者生活,如持灯笼者、潜水者、歌手(演员)、武士、驾车者、象夫、战俘等等。这些广泛的艺术品描绘对象,一方面反映出艺术对罗马社会生活的丰富写照,展示出罗马社会生活的多面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黑人(埃塞俄比亚人)在整个罗马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分布,从而体现出他们这样一个在罗马社会不占主流和主导地位的人群(族群)成为整个罗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在罗马时代关于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的艺术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与罗马诸神相共生的黑人,也看到作为罗马高官贵族或富人的黑人,还有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当然也包括奴隶和战俘。从这些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的地位,我们并不能得出在黑人并不占主流和主导的罗马社会中,他们作为少数民族(亚民族)在整个罗马社会受到歧视或偏见的结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在讨论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时,认为艺术品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在罗马社会中地位低贱。1929年比尔兹利专门研究奥林索斯考古艺术的著作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专著。她认为,野蛮种族埃塞俄比亚人能持续地引起希腊罗马艺术家的兴趣,其原因是由于埃塞俄比亚人在希腊的卑贱地位,伟大的雕刻家不会把埃塞俄比亚人作为足够高贵或足够重要的主题。表现埃塞俄比亚人地位低下的场景在所有的花瓶中都表现得很清楚,如在沐浴场景中埃塞俄比亚人给主人涂油、送酒壶;作为奴隶手持鸟笼跟随侍候年轻女主人等;作为黑人的埃塞俄比亚人在花瓶艺术中最主要的两个特征则是他们皮肤的黑性和头发的卷曲性。[17]64-66对于罗马时代的艺术品,她认为,“在罗马,埃塞俄比亚人头像最通常得以使用的,是它对小灯饰的适用,不管是在铜像还是无釉赤陶中都是这样。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的头靠在一个水平位置,灯芯的孔要么是埃塞俄比亚人张开的嘴,要么是从他的嘴里伸出的管嘴。”[17]121这里,作者明确认为,埃塞俄比亚人的头像只是适用于古代罗马的小灯饰的艺术品中,换句话说,埃塞俄比亚人的形象是不会在其他大型艺术品中出现的,或者说它登不了大雅之堂;而且特别强调灯芯的孔只从其嘴里出来,似乎在强调埃塞俄比亚人的面相特色是很适合这种小灯饰品的特征的。其实,作者在这里明显带有一种偏见,联系她前面关于希腊艺术品涉及埃塞俄比亚人的作品的论述,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作者的观点:“没有任何一个野蛮种族会像埃塞俄比亚人那样持续地引起希腊罗马艺术家的兴趣。古典世界对其他已知种族的写实肖像几乎没有,即使有也通常属于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另一方面,在希腊艺术最具节制和理想化的时期里,黑人是对种族类型的最忠实的表达。阿提卡花瓶的制作者很满足于通过几乎没有任何种族区别标志的服饰来表达东方人,但他们在描绘埃塞俄比亚人的卷发和厚嘴唇的时候却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从这种表现形式的最早时候开始,这种类型的流行就从没有在古典艺术的任何多产时期中衰落过。由于埃塞俄比亚人在希腊的卑贱地位,也鉴于现实主义通常会局限在很小的主题上这一事实,伟大的雕刻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人作为一个有足够高贵或足够重要的主题,因为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头像和雕像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小主题的流行数量却非常巨大,这可以从古典遗址中大量的小雕像、花瓶、宝石制品、钱币、灯饰、量码、指环、耳环、项链及面具中看出。”[17]9作者给出结论很明显是要证明埃塞俄比亚人(黑人)在古代社会是低贱的人种,就连在艺术品中的反映,他们也只能出现在小的灯饰品之类的杂件中,他们不仅与其他野蛮人属于同类,甚至比其他野蛮人更低贱,因此这也成为古代罗马人对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种族歧视的依据。
从前面我们关于罗马艺术中反映的黑人形象的实际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比尔兹利的看法与历史实际大相径庭。首先,比尔兹利认为“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头像和雕像几乎是没有的”这一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罗马时期涉及埃塞俄比亚人(黑人)的真人大小的艺术品是有的,如弗拉维王朝时期作为使臣或人质的大理石半身雕像。其次,她认为“伟大的雕刻家没有把埃塞俄比亚人作为一个有足够高贵或足够重要的主题”的结论也是明显错误的。从前面关于涉及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的艺术品的主题看,黑人贯穿整个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与诸神共舞到达官贵人,从市井小人到战俘罪犯,无不存在于罗马社会的每个细胞,而且他们经常与罗马原著民(罗马人)同时出现,除去战俘、罪犯、奴隶,难道与伊西斯女神或塞拉皮斯神一起出现不算是“足够高贵或足够重要的主题”吗?从这些明显的事实中,作者却得出极端的结论,显然并不是科学精神使然,而是因为作者是带着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进行观察的。这种把牵强现象与古代社会的种族偏见、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古罗马社会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依据,恰好反映出作者本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倾向,而这种倾向正好迎合了当时欧洲盛行的“白种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潮,也是其组成部分之一。
注释:
①鉴于古希腊文献及艺术品中通常把埃塞俄比亚人和黑人相通称,故本文也把二者通用。
②这种罗马人从未见过但在罗马社会广泛流传的传说很多,如对特洛伊城的好奇、对介于神话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俾格米人的兴趣、对塔西佗提到的埃及巨大石像门农的向往等。(冯定雄:《罗马道路与罗马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1-254页。)
③从罗马共和国时代起,罗马人就喜欢把自己家族的墓葬群集中在主要的罗马大道沿路,如沿着通往伊达拉里亚的各城镇的路上,家族墓葬群排列得十分规则;在从阿尔通往意大利的道路上,有罗马西部地区最为著名的墓葬群之一阿里斯坎普墓葬群;邻近罗马的阿庇安大道和诺门塔纳大道的地下墓葬群则颇有特色,它与跨台伯河地区的蒙特韦尔德地下墓葬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深受希腊化和罗马化的影响,后者则是保守的传统犹太风格。罗马墓葬群成为罗马道路上很独特的景观。(冯定雄:《罗马道路与罗马社会》,第110-112页。)
④参见HELIODORUS的Aethiopica一书,http://www.elfinspell.com/HeliodorusBk9.html.
⑤格兰多认为,这是混种题材,但偏向于北非、努比亚或阿比西尼亚的黑人类型;(P. Graindor, “Tête de nègre du Musée de Berlin”,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hellénique, 1915, vol. 39, p.402-412.)皮卡尔则把该头像描绘成是黑人或白黑混血儿。(C. Picard, La Sculpture antique de Phidias à l'ère byzantine, Paris, 1926, p.444.)
⑥希罗德·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公元101-177年)是一位著名且富有的希腊贵族和智者,罗马元老院议员,公元143年被任命为罗马执政官。他是第一位被正常选出作为罗马执政官的希腊人。据斐洛斯特拉图斯说,阿提库斯是第二次智者运动的著名倡导者。(Philostratus, Lives of the Sophists, 2.1[2017-10-06][http://thriceholy.net/Texts/Lives.html])芬利把他描写成为“艺术和文学的赞助人,帝国大规模的公共慈善的资助者,不仅在雅典,而且在希腊的其他地方以及小亚细亚,他都拥有很多重要的职位,是皇帝的朋友和亲戚”。(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p.100.)
⑦“他们准备在邻近的村庄暂歇下来,那个村庄离被贤人占领的高地没有几个斯塔特(1斯塔特=167米)的距离。他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向他们跑来,这是他们见到过的最黑的印度人,在他的眉毛之间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新月状的斑点。但我知道,后来,同样的特征也出现在智者希罗德的养子门农(Menon)的身上,他是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他的这一特征在他青年时表现了出来,但当他长大以后,他的这一特征逐渐减弱并最终随着他青春的逝去而消失了。”(Philostratus, 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The Epistles of Apollonius and the Treatise of Eusebi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 C. Conybea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III, XI.(Leob)Philostratus, Lives of the Sophists, 2.558[2017-10-06][http://thriceholy.net/Texts/Liv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