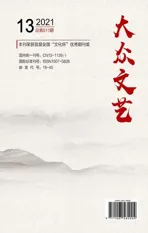作为抗战档案的口述史料研究
2019-01-28张艾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00875
张艾琪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875)
口述史学是近些年方兴未艾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口述的方式,获得的声音和文字是一种新的史料形式。现代口述历史首先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实验室成立,随即第一批口述历史档案馆和实验室在欧美建立起来。目前,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口述历史研究已越来愈多的出现各种研究领域之中,也极大推动了有关历史史料的研究范畴。
一、《我的抗战》中的口述史料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口述史料收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口述历史整理紧迫性的增加,抗战口述史创作成果越加丰富,研究方法也越加规范。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就是利用口述史方法进行创作的重要纪录影片。该片由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制作。2005年,时值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这一团队开始对抗战口述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2010年,这一团队推出了32集电视专题片《我的抗战》与同名图书,被认为是抗日战争口述历史研究中影响很大的作品。
口述史料作为口述历史作品的基础,需要经过选择才能构成完整的作品。可以说,口述史料的选择决定了口述作品的历史价值。
《我的抗战》对口述史料的选择首先体现在口述对象的全面性、典型性上。根据《我的抗战》创作者的叙述,在资料采集的过程中采访的对象在3000人以上,而这些口述者必须经过选择才能出现在作品中。据笔者统计,在32集的《我的抗战》电视片中,使用了约190位口述者的素材,其中女性37位,口述者的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这些口述者大多数是抗日战争亲历者,也有极少数抗战亲历者的子女。既有直接参与战斗的国、共两党的军官、士兵、地下工作者,乃至伪军、日本士兵,也有各行各业,经历或参与过抗日战争的人,包括但不限于:军属、演员、学者、学生、普通市民……这些人的讲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全面性。
这些口述者分别为从战士、普通市民的角度讲述了自己对“七·七”事变的记忆,二十九军战士张可宗见证了赵登禹师长的牺牲;阮捷成当时作为军训学生,并未真正上战场,却因住在营区,目睹了二十九军士兵的营区“变成空房子”。刘良惠对于日军进驻北平城,要求百姓欢迎的屈辱印象深刻……这些记忆来自不同视角而又互相印证,如战士张可宗、居民黄成祥都提到赵登禹牺牲时所乘坐的轿车被机关枪打得千疮百孔,在力求全面的同时折射出口述历史的真实。
二、口述历史与史实
历史学的本质是求真。尽管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进程是不可再现的,但在传统的史学编纂的观点中,向这一真实的历史不断靠近,是历史学的本质任务。口述史的真实性受到大量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口述者的因素,这又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口述历史来源于历史记忆,而口述者的年龄往往较大,如《我的抗战》,采访对象平均年龄高达九十岁,而在《我的抗战》项目搜集口述材料时,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对于口述者来说,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得模糊、不确定,在时间、地名上可能会时常搞混。另一方面,口述者本人大多是士兵、低级军官和普通百姓,本身也不一定了解所经历事件的全貌,因此在描述上可能有所误差,这就需要整理者进行考证。
主观上,口述史的价值判断、与访谈者的关系和对口述后果的判断,都会影响口述史的真实性、全面性。口述历史作品是由口述者和口述史的访谈者、整理者共同构建的,因此,这些创作者的专业素养、个人倾向和对口述史方法的掌握程度也同样影响着口述史作品的真实性。一方面,访谈者的干预可能会影响口述者讲述的内容。另一方面,整理者否选择适当的口述资料并积极进行考证,也影响了口述历史作品的真实性。在口述史中,难免会出现错误。有学者评价《山西抗日口述史》,就发现其中有把地名弄混,而整理者未纠正的错误。
尽管口述史被认为是口述者《我的抗战》的历史顾问李继锋认为,《我的抗战》是“在史实上较真的”,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将每一集都看了许多遍,“许多集最后的审片意见还是惊人一致的:本集未发现问题。”但是,崔永元的团队成员很少有历史专业背景,在片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史实性的错误。在第五集《白山黑水》的字幕、解说词中,将抗联叛徒程斌的名字误作“陈斌”,在有人指出这一问题后,创作团队对此进行了改正。1在电视片中,许多文献的引用没有完整标注。《我的抗战》中引用了大量“纪录片”资料,但大部分没有标注是实景拍摄还是情景还原。在平型关战斗一节,使用了一张描述战士们过河的图片,但该图片并非平型关战斗的实景,只是在情景上有所相似,该片中也没有特别说明。从历史著作的角度来说,这并不符合学术标准。
口述历史走向大众媒体,一方面有助于其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口述历史的可信性和准确性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口述历史以亲历者讲述作为主要材料,但如果不进行与大量文献档案、影像史料的印证,就会与史实出现偏差。这也是非历史专业的口述历史研究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三、口述历史与真实感构建
“口述历史,就是带着强烈的个人视角。但至少,每个人的讲述汇集起来,就会更加接近真实。”2从影像史学的尺度衡量口述史纪录片的真实感构建,会发现这一“真实”分为几个层次,笔者把其分为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
首先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不可能实现,但必须追求。以口述历史来说,其来源于亲历者讲述的记忆,而记忆必然是个人的、主观的,这样的记忆有时能导向文献中所没有书写的真实,有时却与真实背道而驰。口述史的真实,要求口述史的工作者不仅要搜集丰富多元的个人记忆,还要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辨别和比对。除此之外,纪录片还通过运用大量的影像史料、文献档案来构建这种真实感。
其二,是艺术的真实。历史纪录片包括真实的历史资料与后期的演绎成分,在演绎中,必然会存在想象和虚构的成分。“艺术虚构”的形态是对“历史真实”的把握,是对“艺术真实”的显现。前文中所论述的“情景还原”,当然,在历史纪录片中,艺术表达必须符合历史逻辑,以史料和研究成果为基础。
第三,是情感的真实。《我的抗战》以微观的视角,关注个人的、细节的历史,挖掘出口述者关于抗战的个人记忆和情感。在历史中所见的这些感情,在每个观众的一生中都可能经历或看到或听到,因此,观众也更容易理解历史。电视片中传达的真实历史情感,如家国情怀、患难爱情,是观众们可以接收到的,观众也在这种细腻的情感中,体验到了历史的真实感。
福柯认为,历史是“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而口述史作为典型的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历史事件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许多记忆已经逐渐成为“一己之词”。记录个体的、独立的、微观的口述记忆,并从中发掘集体的、联系的、宏观的历史,正是口述历史需要解决的问题。传承历史记忆与历史意识,成为口述史的重要功能。口述史与纪录片的结合,有助于历史记忆的传承。
《我的抗战》选取细节化、传奇性、抒情性的口述史料作为全篇的叙事内容,以历史记实资料和版画风格的情景再现搭起框架,以充满历史信息的解说词穿针引线,构建成了一部微观视角的宏大历史,表达了创作者的历史情怀,并通过影像的媒体和网络的媒介,使大众更易于接受。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我的抗战》具有局限性。纪录片中的论述仍然停留在历史情感的层次,只追求情感的渲染而没有追求,甚至说刻意回避了对历史之“真”的追寻。口述历史的探索,需要的不仅是“求真”的意识,还需要历史学的方法,需要更多专业历史学者和史学界之外的人士的共同努力。
注释:
1.王同彪. 我和崔永元就《我的抗战》瑕疵交流[M]. 王同彪著.发现抗战.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2.
2.郭晓明. 故事背后那些未完的故事[M].《中国传奇2010之我的抗战》节目组. 我的抗战.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