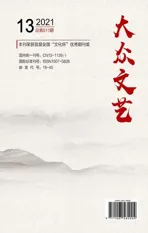当代山水画中的写生与创新
2019-01-28林沛锐广州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518000
林沛锐 (广州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518000)
写生是山水画创作中一个源远流长而又历久弥新的话题。当山水画步入一种陈陈相因的境地时,写生总是可以作为一种革新求变的工具,在山水画创新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厘定写生在中国传统山水画语境中的含义,让写生在当代山水画的创作中继续发挥革新中国画的作用与目的,是当代山水画家不得不面对的时代课题。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于历代写生概念流变的研究,从中推导出写生与当代创作、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希望从中探寻到对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新的启示。
一、写生概念的流变
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写道:“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李将军李中书) ,树石之状,妙于韦偃,穷于张通(张璪)。1”能穷尽树石之状,唐代画家张璪无疑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画家,朱景玄评其山水就说:“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若逼人而寒,其远也,若极天之尽。2”从这个描述来看,张璪作品里的山岩喷泉,有如实境,有很强的感染力。张璪曾提出“师造化”的概念,对中国画影响非常大。但这个概念是以故事流传下来的。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第三卷记载:“张璪,……尤工树石山水,自撰《绘境》一篇,言画之要诀,词多不载。初,毕庶 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3”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由此影响了传统中国山水画观念一千余年,而传统写生观念更多是与“造化”联系在一起,在这里“造化”一词指的是作为学习对象的万物,根据外在形象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和整体趋势,但并没有投射出主体的精神与情感。根据张璪的概念,只有将“造化”内化为“心源”,写生才既是画家对自然对象、造化万物的一种理解与全面鲜活的把握,同时也体现出自己的世界观及修养、心性、心境。这一观点后来为北宋范宽所阐发。他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和张璪不同的是,比起“师诸物”,他更强调“师诸心”,但问本心,莫向外求,写生也就变成内心对于世界的体验、感悟。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动荡、思想变革以及视觉经验革新等影响,山水画被赋予更多全新的含义,它从以前文人士大夫游心骋目的心灵感悟与修养训练增添了关注现实、反映生活的时代课题,创作思路的改变也反映于写生中的题材、手法、媒介等方面的改变。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傅抱石、关山月等大师吸收西方绘画理论,深入观察自然,诞生了诸多新的风格,使山水画重新注入生气,将山水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例如,傅抱石和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大气磅礴,开创了国画巨幅山水的先河。新的视野带来新的题材,从黄土高原到西北大漠,从江南水乡到西藏雪山,从祖国山河到异国风情,山水画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
二、写生与创新
南朝齐、梁的艺术理论家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论,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古画品录》逐渐成为后世整个中国画的品评标准。用六法来看今天的写生,启发同样非常大。“气韵生动”这条纲领,决定了中国画重“神似”。“骨法用笔”说线条,“应物象形”重形态,“随类赋彩”关注色彩,“经营位置”讲构图,“传移模写”说的是临摹,“应物象形”与“随类赋彩”无疑都可以和写生概念挂起勾来。
古代写生概念中和今天相近的也并不罕见,北宋画家赵昌自号“写生赵昌”,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有记载说:“又有赵昌者,汉州人,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遶栏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人谓赵昌画染成,不布采色,验之者以手扪摸,不为采色所隐,乃真赵昌画也。其为生菜折枝果尤妙。4”清晨有露水的时候,对着花木调好颜色来作画,和今天的写生何其相似!赵昌有一幅《写生蛱蝶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使我们今天仍能欣赏到他笔下翩翩起舞的蝴蝶的曼妙身姿,更能想见他写生的美好情境。
赵昌的写生使他的作品充满细节,富有生气,这样的方法无疑是有利于创新的。苏轼就曾写诗说“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然而过分强调细节,往往又不易跳出细节来营造自己的特点。同样是写赵昌,欧阳修就说“昌花写生逼真,而笔法软俗,殊无古人格致,然时亦未有其比。”虽然肯定赵昌的地位,却也批评他笔法软俗。赵昌是花鸟画家,笔下所绘与山水画家又大不相同。山水画家在面对优秀传统,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作出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作品?这是摆在每个山水画家面前的课题。我认为在写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彰显时代的气息已经成为山水画家突破传统的必由之路。理解前人的方式方法、寻找自己独特的语言符号、抒发自己强烈的情感是当代山水画家的创作路径。传统山水画的写生讲求“目识心记”,以不同的角度对自然进行观察,分片段记忆,最后再回到案头进行记忆创作,而传统西方的对景写生,用画框的概念对眼前之景进行如实的记录。中西这两种方式并没有孰高孰低之别,但对于我们当代人观察自然、描绘自然却提供了很多元的角度,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融合中西的写生方法,在这点上,我认为我的恩师许钦松先生给我作出了很好的精神表率,他一直都致力于中国山水画的革新。他敏锐地感受到人们对于景观的感知变化,以更为坚实肯定的线条、阔大的结构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大山大水,其作品形神并重,堪称“气韵生动”的时代强音。
三、写生与创作
关于写生与创作的关系,清代著名画家石涛提出“搜尽奇峰当初稿”的山水画创作主张,画家在创作山水画中应该直面客观的山水景物,通过主观的感受,理解和熔铸,把自然风光变为胸中丘壑,即达到“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的境界,从而创作出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优秀作品。这一点充分证明画家在创作出优秀作品过程中写生的重要性。在当代山水画家的心目中有着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写生是一个收集素材的过程,是创作的前置与准备阶段,写生创作过程是一个片断,一个局部,不能完整地把艺术呈现出来;另一种则认为写生即创作,写生是对着有依据的、独特的、特别的创作,可以有表现,可以强调创作性,强调写生本身的特性。
脱离写生的创作有如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古往今来,成就大家者必然在写生上着力颇多。五代画家荆浩《笔法记》记载说:“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数亩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钲山四望,……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5”他隐居太行,触景生情,写生数万本,才把握到山水之真。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写山水诀》里面亦曾记载他“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随身携带描笔,见到好景色马上画下来,这不是写生是什么?只有细致地观察摹写世界,下笔才如有神助,也才会“分外有发生之意”。
那写生是否就是一种创作呢?对此我不能苟同。我个人更认同第一种看法,“写生是一个收集素材、加深对自然印象以便之后创作的过程,也是对检验自身写生能力的过程。将写生作为创作,会因为增添效果而遗失掉一些写生中最鲜活的场景,同时也会掩盖掉自身在写生过程中不足,不利于日后查漏补缺”。当然,无论是将写生作为创作的前置或者是写生创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在写生过程中把握住那种直面自然的鲜活感与生动性,也就是所谓“生涩”的感觉,或者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但却能最真实将现场的感受保存下来,这是写生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我不认同写生就一定是“生涩”,而创作就是“成熟”的,新中国以来关于“圣地山水”的写生作品中,很多都是同一角度同一对象的惯性“摹写”,很多画梅、画竹的“高手”在面对实景时依然如在案台一样程序化挥洒,这种写生作品在我看来是“成熟”的,是一种技术的重复,已经丧失了写生的意义,更遑论创作的意义了。正如一代山水画大家黄宾虹曾经所说的,“天地之阴阳刚柔,生长万物,均有不齐,常待人力补充之。”一味地摹写,画得再像也不过是写生,只有把自己的心像投射到景物之上,创作出“师造化”而又“出造化”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创作”。
注释:
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p16.
2.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P11.
3.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p99.
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p667.
5.荆浩撰.《笔法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3月第一版,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