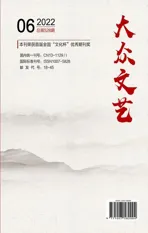新时期文学的苦难意识及救赎
2019-01-27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
(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871)
苦难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境遇,虽然其本身并非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但是在感受、承担和反思苦难这一客观事实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一种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换句话说,当苦难从一种客观事实上升为一种人类所独有的自觉意识——苦难意识——的时候,人们便会从浮华的现实苦难表象潜入深沉的人生底蕴,从而体验人类生命的独特价值。因这种特殊价值,苦难意识与文学艺术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成为众多文学家与艺术家常用的创作主题。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许多作家对苦难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探索,并以多种方式来超越苦难,寻求救赎。
一、严肃式苦难救赎
随着“寻根”思潮的出现,一种现代精神层面上的苦难意识开始被中国当代作家们重视。自此之后,苦难成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在对苦难的直面追问与对救赎的勇敢探寻中,一些作家从民族文化、历史、人性等宏大角度对苦难意识进行了严肃式的反思与救赎。
张承志因其在异国他乡的漂泊经历而产生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他在散文《无援的思想》中提醒国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在世界文明的战场上实际处于弱势,我们应该怀有民族危机意识,不能沦为新的殖民地,即文化的殖民地。他期盼着民族文化战士的出现:“我一直想,文明的战争结束时,失败者的废墟上应当有拼死的知识分子”1。于是张承志救赎民族文化苦难的方式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他高呼“今天需要抗战文学。需要指出危险和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2。同样对民族文化怀有苦难意识的还有贾平凹。贾平凹在《废都》、《秦腔》等作品中反思的是在商品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乡土沦丧之后所遭遇的精神苦难。他在这些作品中为传统士大夫精神和乡土文化唱出了最后的挽歌。
张炜的苦难意识则主要来自于历史的罪恶:“思考历史是沉重的,这是因为它本身的滞坠与苦涩,因为所有的历史选择并非遵循后人看来一目了然的理性,而是按照每个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模糊的可能性”3。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对生命的贱视、对人性的扭曲,都是张炜的苦难意识的来源与反思对象。面对历史苦难,张炜选择的救赎方式是铭记历史、拒绝遗忘。这在他的作品中被反复强调:他在《柏慧》中写道,“我多么憎恨‘遗忘’。我认为这是人类最可怕的劣性,最可耻的疲痴。没有了记忆,也就丧失了理性。一切丑恶与污浊都是在模糊的记忆之言的遮蔽下肆意侵犯的”4;他在《家族》中感叹,“可怕的遗忘啊,它是迷人的婴粟花结出的果实,可惜它在我们的心田里总也不能结籽”5。
余华对苦难的探索与救赎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余华的早期作品以建构奇异、怪诞、隐秘和残忍的文本世界为长,以血腥、暴力与死亡为主题,尽显人性之恶。但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只是单纯地暴露苦难,而是以简练的笔法和饱满的情感,为苦难探寻救赎之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活着》。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面对苦难的生存态度,即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小说的主人公福贵在经历了生活的大起大落、亲人们的离世之后,仍旧没有放弃生活,而是以超越苦难的达观态度平静悠然地活着。这种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救赎方式,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是从深层面对人性的回归。
二、戏谑式苦难救赎
当苦难意识成为一种价值标杆和崇高的代名词时,一个以“边缘人”自称的“文学混混”出现了。苦难在他的笔下成为了嘲笑和玩弄的对象,被其他作家高捧在上的珍品碎成了一地渣子。他就是王朔。
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中国社会带如价值有待重定的转型时期。文学的“历史化”书写受到冲击,对历史进行祛魅成为创作潮流,更加偏向个人化的写作也不可能再同1980年代那样可以引导和凝聚社会精神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家王朔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成为一种“现象”引起了众多争议与讨论。
在王朔的众多作品中,《顽主》无论在语言风格还人物塑造上,是经典也是标志。所谓“顽主”,其实就是“地痞无赖”,但是在《顽主》中,“无赖”却有了新的定义:无赖就是无所依赖,无赖了就会真快活。“顽主”就是一群“无所依赖”的、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社会边缘人,他们没有确定的社会职业,对体制既怀着不能进入的怨恨,又带着随遇而安的真快活。“顽主”可谓是王朔小说中人物的总括。在语言风格上,《顽主》也将调侃、反讽和荒诞发挥到了极致,完全剔除了生活中原有的崇高感与价值规范。名人名言被随意篡改,前后之间没有任何语义上的联系,表现出的只是莫名奇妙的荒诞感。而这种荒诞感正是王朔所要表达的一种“新的世界观”,这就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的认同。在王朔那里,生活没有什么崇高可言,更没有什么完整性可言,活着的人们都是不完整的,没有英雄,也无所谓反英雄,所谓的“正派人物”都是在装腔作势假正经,而不完整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王朔的这种反崇高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不满,王晓明抨击王朔式的调侃是“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他认为,在王朔的小说中,不仅文化成为废墟,连嘲笑文化废墟的嘲笑者本人也是废墟,“一旦嘲笑者本人也成了废墟,那么,他就不能指向任何外部世界,于是便只有在玩弄语言的亵渎与嘲笑中获得一种自慰式的快感”。6在王晓明看来,“王朔现象”表现出的正是中国人精神素质的恶化,人文精神的危机。王蒙对此却有不同的认识,他肯定了王朔对多年来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7的刻意颠覆,肯定了王朔对神圣与崇高的躲避和消解。
王蒙所讲的“崇高”,指的就是苦难意识。王朔通过调侃与反讽来躲避崇高,剔除价值规范,其实是在努力消解新时期以来一直被大家反复咀嚼品味的苦难意识。社会在转型,时代在改变,沉浸迷醉并执着于苦难,在王朔看来也许是一种故作姿态的做作。而王朔对苦难的解构,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苦难的救赎与超越方式呢。
三、结语
新时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其对苦难救赎的深度化与多面化思考也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基石。从张承志、张炜等作家的严肃式反思,到王朔的调侃与戏谑,苦难意识在多种思想的碰撞中不断迸发新的意义与价值。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坛也以更加开放和多元的姿态来面对苦难意识,对个体生命与人类命运进行着不懈探索。
注释:
1.张承志.无援的思想——思想随笔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92.
2.同上,82.
3.裴毅然.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36.
4.张炜.柏慧[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310.
5.张炜.家族[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296.
6.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J].上海文学,1993(6):63-71.
7.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J].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95(7):7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