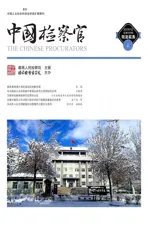互联网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的认定*
2019-01-26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文
一、问题的提起
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不少是以单位名义组织实施的,一个案件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是检察官准确适用法律的重点,同时也是控辩双方在庭审中争论的焦点。
涉案单位是否合法是判断单位犯罪的要件之一。合法单位既要满足形式要件,即依法设立,拥有公司营业执照,也要符合实质要件,即在营业执照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经营行为。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 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该条文中“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规定内容看似清楚,但笔者通过座谈、调研、查阅判决书等方式发现,检察官办案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该条文在司法实务中的理解和适用。
二、成因分析
(一)《解释》第2 条制定的前提和基础有待商榷
规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初衷是有些犯罪分子,基于规避法律严厉制裁的心理而实施的以公司、企业的正当经营活动作掩护的犯罪行为,其犯罪心理是即使案发被追究刑事责任,所受到的刑罚处罚也不重。[1]另外,也有观点指出,刑事司法实务一般都将单位犯罪列为刑事辩护的一个重要思路……单位犯罪比自然人犯罪定罪数额的起点高[2]。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值得商榷。同一罪名,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孰轻孰重,应从立案追诉标准和法定刑两方面进行比较后才能得出结论。“一般而言,互联网金融犯罪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互联网金融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如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二是互联网金融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等;三是互联网金融作为犯罪工具的犯罪,如洗钱罪等”。[3]其中,可以构成单位犯罪的有8 个罪名: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洗钱罪、集资诈骗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笔者对上述罪名梳理后发现:一是大多数罪名单位和个人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相同。只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2个罪名单位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高于自然人犯罪,其余6 个罪名的立案追诉标准两者相同。二是绝大多数罪名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等于或者重于自然人犯罪。有5 个罪名行为人以自然人犯罪的名义与以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名义承担刑事责任相对应的法定刑是相同的,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洗钱罪,自然人犯罪法定刑最低甚至为单处罚金,而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最低却为拘役。仅有集资诈骗罪,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重于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三是单位犯罪单位需另外缴纳罚金。对互联网金融领域单位犯罪进行处罚时,均规定了“双罚制”,尤其当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与自然人犯罪一致时,单位还需另外缴纳罚金,刑事责任显然要重于自然人犯罪。综上,在互联网金融犯罪领域,单位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与自然人犯罪基本一致,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的法定刑与自然人犯罪基本相同,甚至更重。
(二)《解释》第2 条“或者”前后标准不一
“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实施犯罪”(下文对此内容简称“设立前”)即行为人犯罪的主观故意在单位设立前已产生,行为人设立单位的目的即为了实施犯罪,可以说单位成为犯罪工具,完全是一种摆设,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与自然人犯罪无异。
“公司……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下文对此内容简称“设立后”),笔者认为,该规定会因行为人犯意产生时间点的不同,以及单位设立后从事正当经营行为与犯罪活动的比例差别而有所区别。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单位设立后行为人即产生犯意,之后一直从事犯罪活动;第二种情形,单位设立后从事过正当经营行为,从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点开始从事犯罪活动;第三种情形,公司设立后,正当经营行为与犯罪活动相混合。这三种情形,只有第一种情形与“设立前”,无论行为人的行为模式还是主观恶性两者基本一致。从行为模式而言,公司设立后即开始从事犯罪活动。从主观恶性而言,设立的单位只是其实施犯罪的工具。“设立后”的其余两种情形与“设立前”的行为模式、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从行为模式看,前者有正当经营行为的存在,后者没有。从社会危害性看,后者危害性更大。从主观恶性看,后者是有预谋的犯罪,主观恶性更深。因此,《解释》第2 条直接将两者等同规定,有违公平。
(三)《解释》第2 条实务操作性不强
该解释意图以单位设立后实施的正当经营行为与犯罪活动的比例作为单位犯罪的划分标准,但什么是“主要”?具体比例应当设置为多少?有观点认为,对于“主要活动”的把握,不应仅仅局限为“数量”“次数”等简单的量化指标,还应综合考虑犯罪活动的影响、后果等因素,以作出准确认定[4]。但这种比例认定法在实务中应当如何操作并不明确。200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 条、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 条对该问题都有所涉及,两个司法解释虽然针对的是走私、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办理,但“在没有其他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办理其他刑事案件中也可以参照适用”[5]。笔者认为两个司法解释与其说是审查判断标准,不如说是侦查取证指引,主要解决了侦查机关应当主要围绕哪些方面收集证据,并没有从实际解决应当如何理解和适用“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规定。例如,行为人设立公司后有生产经营活动,但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集资款,对该问题,在具体案件认定上法官间存在理解上的不一致。有的法官认为集资行为属于公司设立后主要从事犯罪活动,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有的法官认为集资是一种融资行为,款项也主要用于公司经营,应认定为单位犯罪。
(四)证据收集难度较大
笔者认为,既然可参照适用的司法解释已经作出了规定,那么,每起案件的办理,侦查机关应查明犯罪情况以及单位正当经营情况,但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往往仅从单位纳税数额多少、单位意志有无、违法所得归属等角度来认定单位设立后是否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对单位正当经营情况的证据不予收集或者收集不到位。另外,上述司法解释中提及的如犯罪的次数、频度、持续时间等证据,也较难取证,“虽然《解释》第2 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但是公安、司法机关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该条的规定,需要收集到虚假公司……设立后的违法犯罪活动证据,而在具体办案过程中,这些往往难以收集”[6]。
三、应对路径的选择
通过对“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规定在司法适用中面临困惑及成因分析的梳理,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一)上级层面及时回应
1997 年《刑法》从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和单位犯罪的处罚两方面对单位犯罪作出了规定,但在实务办案中陆续出现了对单位犯罪主体范围的界定、单位犯罪中主从犯的区分以及单位实施只能由自然人构成的犯罪如何处理等疑难问题。以上问题,已逐步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予以解决。同样,《解释》第2 条规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该条应如何理解,实务中应如何适用,亟待上级层面出台更细致的规定。
(二)以严格限定为原则,做到“或者”前后标准“同质化”
单位设立后,行为人立即产生犯意,之后一直从事犯罪活动。此时,虽然单位是合法设立的,但从行为人的行为来看,其只是利用了单位的“框架”,目的是便于其个人实施犯罪,可以说,单位设立后没有任何正当经营行为可言,那么,此种情形与“设立前”基本一致,与自然人犯罪没有区别,可以直接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三)根据案情结合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认定
在互联网金融犯罪领域,单位设立后从事正当经营行为,经过一段时间才开始实施犯罪、正当经营行为与犯罪活动相混合等情形因有合法经营活动的存在,无需且难以查清正当经营行为与犯罪活动的比例,应从案件如何才能妥善处理的角度进行通盘考虑,具体而言可以从是否有利于确定打击范围、是否有利于区分行为人的地位作用、是否有利于有力指控犯罪、是否有利于追缴违法所得等方面具体把握,依法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该观点也得到“e 租宝”案的证实,该案并未深究涉案单位设立后有无从事正当经营行为,而是从追赃挽损以及社会维稳的角度作出相应裁判。
(四)以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指导办案
“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是司法人员对个案适用法律的具体诠释,是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参照方案。”[7]案例指导制度既能弥补成文法的滞后性,也能将抽象的司法解释具体化,还能保证相同案件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检察机关得到同样处理。基于此,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单位犯罪,相关检察机关应及时关注本院或者辖区范围内的经典案例,将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法律适用、政策把握、办案方法等方面具有指导、典型意义的案件及时筛选、上报,便于上级检察院掌握情况,通过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等形式来推进解决实务办案中的疑难复杂问题,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注释:
[1]参见孙军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刑事审判参考》1999 年第3 辑。
[2]参见林荫茂:《单位犯罪理念与实践的冲突》,《政治与法律》2006 年第2 期。
[3]郭华:《互联网金融犯罪概说》,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78、83、86 页。
[4]同前注[1]。
[5]陈增宝:《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司法确认与否定》,《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 年第1 期。
[6]邹涛:《单位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研究》,《公安研究》2004 年第2 期。
[7]孙国祥:《论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人民检察》2011 年第1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