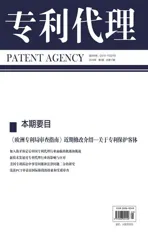论创造性判断中的“成功之合理预期”标准
2019-01-26余颖
余 颖
一、引 言
2018年9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下简称“CAFC”)做出判决,维持专利审判和上诉委员会(以下简称“PTAB”)此前的决定即Broad研究所等(以下简称“Broad”)涉及CRISPR在真核细胞中应用的专利与加州大学等(以下简称“UC”)的一项专利之间不存在抵触(no interference-in-fact)。理由之一是PTAB和CAFC均认同CRISPR的真核应用相比UC早期公开的CRISPR体外应用是非显而易见的①参见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road Institute, Inc. (Fed. Cir. 2018).。然而,在中国,同样的CRISPR真核应用专利申请、遭遇同样的对比文件、申请人提交类似的争辩后却仍难以克服显而易见、不具备创造性的审查意见。以上在美审理程序中、相关案件的中国审查程序中,争议的焦点都曾不约而同的落在:鉴于CRISPR/Cas9系统体外应用的早期揭示、鉴于其他基因编辑工具在真核细胞中的应用成果,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能够预期该系统将成功应用于真核细胞。PTAB和CAFC均认为这样的预期不成立,中国审查员则认为这不过是将前人的展望付诸实施,是顺应技术发展趋势所为,其结果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预见的。笔者在专利代理实践中发现,“成功之合理预期”(“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success”)在欧美创造性审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权利人击破“显而易见”论断从而确立创造性的最有利的论证方式之一。然而,中国创造性判断的规范中对此没有明确要求,审查员对此没有论证的义务,申请人或权利人就此提交的论证也不具备当然的挑战效力。结果常常令申请人对中国的创造性标准和审查标准感到困惑,甚至产生质疑。鉴于此,笔者比较和研究了欧美有关“成功之合理预期”的规范设定和实践运用,体会其在创造性判断中的地位和权重,并提出了在中国规范和实践中引入这一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成功之合理预期”的别国规范与实践
(一)美国专利局MPEP中的相关规定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SR②参见美国最高法院判决KSR Int'l Co. v. Teleflex Inc., 550 U.S. 398 (2007).案中的认定,MPEP规定创造性判断必须基于Graham事实调查:(A)现有技术的范围与内涵;(B)权利要求与现有技术的区别;(C)相关领域普通技术水平;(D)必须予以考虑的相关客观证据(有时亦称“次级考量(secondary considerations)”),这包括商业上的成功、长期存在但未能满足的需求、别人的失败和出人意料的效果③参见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MPEP) § 2141.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41.html.。在此基础上,根据KSR的要求必须清楚、明确地完成“初步推定显而易见(Prima Facie case of Obviousness)”的论证。对这一论证,MPEP进一步规定了以下证成要件和标准:(1)对现有技术进行修改或合并之启示和动机;(2)必须存在成功之合理预期(“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Success Is Required”);以及(3)必须对权利要求中所有要素予以考虑。④参见MPEP § 2143.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43.html.
对于“必须存在成功之合理预期”,MPEP进一步强调这是初定显而易见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即使现有技术公开了权利要求的全部要素、即使证得存在对现有技术进行修改或合并的启示或动机,仍然不能初步推定显而易见,除非证明存在成功之合理预期。在证明程度上,虽然不要求绝对可预见性,但必需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同时,如果申请人提交证据足以否定指称的成功预期,则是为创造性成立的理由。MPEP进一步提示,成功预期的判断标准是有技术领域间差异的(whether an art is predictable);必需还原到发明形成之时的阶段水平进行判断(determined at the time the invention was made)⑤参见MPEP § 2143.02.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43.html.。
至于做出这一判断的主体,MPEP采用KSR中的设定:“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是机器人,而是具有普通创造能力(ordinary creativity)的;他能够类似拼图一样对现有技术进行组配;还会想到运用推理和创造⑥参见MPEP § 2141.03. https://www.uspto.gov/web/offices/pac/mpep/s2141.html.。
以上可见,美国在规范中对于成功之合理预期的论证制定了刚性的要求,同时在宽严尺度上则技术性地留取了相当的灵活性,使之在众多案例中成为争议的焦点。
(二)PTAB和CAFC的案例法
在前述UC vs Broad⑦参见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road Institute, Inc. (Fed. Cir. 2018).一案中,UC较早公开了CRISPR/Cas9系统的体外(in vitro)应用,并提交了专利申请。Broad的专利主要涉及CRISPR/Cas9系统在真核细胞中改变基因表达的方法。UC称,鉴于其早期的公开和涉案专利,Broad的转用方案是显而易见的。Brord则提供专家证言称,真核细胞与原核细胞的胞内环境存在诸多差异,导致无法预期CRISPR/Cas9系统在真核细胞能稳定留存,进而有效工作。UC的专家亦承认虽有CRISPR/Cas9在人和动物细胞中的常识,但遭遇了失败。同时,虽有其他原核系统转用于真核细胞获得成功,PTAB考虑后认为这些成功有限且艰难,各自依赖于为特定技术特别研发的特殊策略,这进一步证明了原核系统转用于真核生物能否成功难以预见。最后,综上所述成败难论的证据(mixture of evidences),PTAB认为Broad的真核应用方案缺乏成功之合理预期。CAFC对此表示认同。
UC曾出具专家证言称,CRISPR/Cas9在体外环境中(in vitro)获得的结果提示了该系统用于真核“令人激动的可能性(exciting possibility)”。而PTAB认为这至多表明了对成功的渴望,但不证明存在成功的合理预期。CAFC对此表示认同。
UC还曾举证称,在其最早发布了CRISPR/Cas9相关论文(“Jinek 2012”)之后不久且在Broad最早的申请之前就有多个其他团队着手开展将CRISPR/Cas9用于真核细胞的研究,这显然是受到了成功预期的激励,并且证明这一转用仅是常规技术运用的产物。PTAB则认为这些研发行为能够证明存在转用于真核细胞的“动机”,但不能证明在实验完成前就已存在“成功之合理预期”,因为立项或开展研究不证明本领域技术人员知道完成项目存在障碍且知道解决方案。CAFC对此表示认同。
联 想 此 前 在“Purdue Pharma L.P. v. Depomed,Inc.”⑧参见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Purdue Pharma L.P. v. Depomed, Inc. (Fed. Cir. 2016).一案中,虽然被挑战专利的总共五项特征被同属药物制剂领域的两篇对比文件全部公开,但CAFC同样确认了PTAB维持专利有效的决定。CAFC认同PTAB的认定:挑战者没能证成对于现有技术合并存在成功的合理预期。具体来说,CAFC认同PTAB的认定:挑战者没有充分解释“如何及为何(how and why)”将对比文件中的特征组合得出本发明技术方案。尤其,PTAB还指出,根据本发明的技术特征来认定从现有技术角度出发的技术问题是后见之明的表现。对此,CAFC则表示,挑战者没能证成客观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技术已知的(known in the art)或是可由现有技术直接得出的(derived directly from the prior art)。
以上可见,PTAB和CAFC确认了“成功之合理预期”的论证是创造性判断的必需要件,是事实问题。并且,应当将成功的“渴望”、谋求成功的“动机”与成功的“合理预期”严格区分开来。“成功之合理预期”需要基于事实进行全面、严谨的逻辑和技术论证,尤其是在技术层面上就实际存在的问题、障碍以及是否已知或可知解决方案等问题进行查实和论证。正如更多其他案例法例如O’Farrel⑨参见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In re O'Farrell, 853 F.2d 894, 903 (Fed. Cir. 1988).、KSR、kubin⑩参见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In re Kubin, 561 F.3d 1351 (Fed. Cir. 2009).中指出的,“成功之合理预期”不要求绝对的预见性,需要考察的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引导之上付出了何种程度的创造性劳动才得以完成一项发明创造。
(三)EPO审查指南中的相关规定
欧洲专利局(EPO)著名的“能—会”判断(“Could-would approach”)中指出:“关键不在于技术人员是否能够通过调整或修改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从而得出本发明,而在于他是否会去这样做,而会去这样做的原因在于现有技术提供了这样做有希望解决目标技术问题或预期有某种改进或优势的促动力”。⑪⑪ 参见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GVII-5.3.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i_5_3.htm.⑫ 参见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GVII-3.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i_3.htm
至于做出这一判断的主体,EPO的设定是:“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具有相关技术领域一般(average)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能够获得现有技术中所有信息,尤其对比文件;拥有对该领域普通的(normal)、用于常规(routine)工作和实验的手段和技能;这可以是指一个团队而不一定是个人⑫⑪ 参见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GVII-5.3.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i_5_3.htm.⑫ 参见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GVII-3.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i_3.htm。技术上诉委员会在决定T500/91中进一步指出:“一般水平的技术人员没有创造性思维能力(creative thinking)”。
(四)EPO上诉委员会的判例法
在EPO,更大程度上,“成功之合理预期”是通过上诉委员会的判例法确立的。
决定T296/93在决定理由7.4.4段中指出:“‘成功之合理预期’不能与‘对成功的期望(hope to succeed)’混为一谈”;“‘成功之合理预期’意味着技术人员能够基于项目开始之前的现有知识合理预期在可接受的时间限度内成功完成该项目”;“具体技术领域的开发程度越低,预测成功的难度就越高,成功的预期就越低”。
决定T207/94在首页的前言中就点明:“任何诉称动摇成功之合理预期的因素都必需以技术事实(technical facts)为基础”。决定理由第31段指出:“‘成功之合理预期’不能与‘对成功的期望(hope to succeed)’混为一谈…前者只是一种愿望的表示(expression of a wish),后者则必需是对事实的科学的分析(scientific evaluation)”。理由第34段进一步确立了论证的标准即“所有关于妨碍成功的推测或假设都必需以事实为基础⑬⑬ 参见EPO技术上诉委员会决定T0207/94.⑭ 同⑬.⑮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GVII-5.2.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i_5_2.htm.”,并且“若无证据证明某特征可能阻碍方案的成功实施则既不表示该发明不能成功也不表示能成功⑭⑬ 参见EPO技术上诉委员会决定T0207/94.⑭ 同⑬.⑮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GVII-5.2.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i_5_2.htm.。
决定T078/95在理由第14.3段中评论称,即使将对比文件组合“本领域技术人员仍然不确定该怎么办(uncertainty as to what to do)”,以至于“虽然可能对成功有某种程度的期望,但不成其为案例法确立的成功之合理预期”。
决定T0333/97在理由第7段中指出:“如果现有技术存在动机和启示,貌似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地有径可循,则此时的问题是基于对事实的科学分析来考察本领域技术人员是否存在‘成功之合理预期’”。
以上可见,EPO同样认为“成功之合理预期”的论证是创造性评价中的必要条件。并且,这一论证必须建立在事实、证据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而以上例举的每个决定也的确都在证据与事实的基础上对是否存在成功之合理预期,从技术上和法理上进行了扎实而严密的论证,因此在其后的诸多决定中被援引和参照。
三、中国创造性判断的规范与实践
中国现行《专利审查指南》(2010版)(以下简称为“《指南》”)规定了创造性的判断标准,即著名的“三步法”:(1)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2)确定区别特征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3)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关于判断的主体即“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指南》的设定为“假定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
不难看出,以上第(2)步即技术问题的确定对于“成功之合理预期”的判断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对此,《指南》规定为“根据该区别特征所能达到的技术效果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并“应当根据审查员所认定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重新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在《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中可以找到几乎与此完全相同的规定和表述。然而,现行《指南》却没有EPO此后关于“后见之明”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客观技术问题的确定不得包含任何指向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因为,技术问题认定中若包含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则就该技术问题分析现有技术时,势必造成对创造性判断的后见之明”⑮⑬ 参见EPO技术上诉委员会决定T0207/94.⑭ 同⑬.⑮ EPO 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GVII-5.2. https://www.epo.org/law-practice/legal-texts/html/guidelines/e/g_vii_5_2.htm.。联想前文PTAB和CAFC在“Purdue Pharma L.P.v. Depomed,Inc.”一案中关于技术问题认定的评述,与此颇有呼应之意。
以上第(3)步是《指南》在创造性判断中提出的论证命题。对此,《指南》进一步规定:“要确定的是现有技术整体上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启示,即现有技术中是否给出将上述区别特征应用到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其存在的技术问题(即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启示,这种启示会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是最接近欧美“成功之合理预期”的表述了。然而,此处“启示即启示”类似同语反复的循环定义作为操作指导未免缺乏明确性。或因如此,实践中常见审查意见和决定对何以“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缺乏论证。
既有判例中,格列卫用于胃肠基质肿瘤(GIST)用途发明专利的无效决定和两审判决都对成功之合理预期有颇多论述。
其中,专利复审委员会的无效决定认为:“至于STI571治疗GIST能否具有成功预期,虽然证据1没有明确公开STI571针对GIST的具体实验类型和实验数据,但综合证据1作者在证据1上下文中公开的信息可知,证据1的作者推测组成性激活的c-kit受体酪氨酸激酶是合理的靶点,这条治疗途径属于新的治疗途径,加之实验范围已经扩大到与全球其他的研究中心合作,以及作者对于‘非常早期的结果看起来令人兴奋’的记载,本领域技术人员得到的信息是采用STI571治疗GIST是具有合理的成功预期的。针对专利权人提出的抗肿瘤药物研发成功率低的问题,以及现有技术中没有单一药物靶向治疗实体肿瘤的成功先例的问题,并不影响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从证据1合理预期到ST1571能有效治疗GIST的结论,创造性判断中只需要对成功具有合理的预期即可,并不需要绝对的成功预期”。⑯⑯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复审委员会第27371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⑰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73行初985号.⑱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京行终2871号.
一审法院认为:证据1中“‘令人兴奋’的表述会带给本领域技术人员足够的动机,促使其将STI571用于GIST治疗的临床试验,并对这一途径的成功性具有合理的预期”。原告主张:肿瘤药物的研发成功率极低但现实需求极大,因此即使在没有成功预期或成功预期极低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仍可能会考虑尝试研发;但是,在没有任何科学、实证依据(例如试验数据)的情况下,无法使本领域技术人员产生合理的成功预期。对此,该院认为:“正是鉴于肿瘤药物研发的复杂性,本领域技术人员往往会对一些积极的信息产生极大的关注度,并据此进行有益的尝试,因此,虽然证据1中未明确公开具体的实验类型和实验数据,但结合其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认知能力和证据1全文的描述,应认定其可以根据证据1所披露的信息,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联想到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故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⑰⑯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复审委员会第27371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⑰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73行初985号.⑱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京行终2871号.
二审法院关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STI571治疗GIST是否具有成功预期的争论完全支持并直接采纳了以上复审委的观点。⑱⑯ 参见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复审委员会第27371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书.⑰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京73行初985号.⑱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京行终2871号.
虽然个案的决定和判决有其具体案情、历史阶段性特征使然的价值取向因素,但可以预见这些论述和观点将会在以后的创造性判断实践中被广泛参考、引证和采用。
四、思考与讨论
以上所见,在欧美实践中,创造性判断中的“成功之合理预期”之证是第一性的事实问题,是必需满足的证成要件。然而中国现行《专利审查指南》(2010版)尚没有此类论证要求,实践中或论证不足、或论证不利。目前的专利审查似有重检索、轻论证的倾向,在判断显而易见性时,往往赋予了“本领域技术人员”不应有的过高的创造能力。《指南》对于防范“事后诸葛”虽有明确提及,但仅此区区一句警示,没有落实为方法论上可执行、可检验的规范和标准。因此,这一警示即没有对审查主体形成有效的约束,也未能授予申请人/权利人有力的申辩武器。
笔者认为,在创造性判断中不妨引入“成功之合理预期”标准,对论证提出要求、制定规范。例如,EPO上诉委员会T078/95决定中的“怎么办(what to do)”之问、美国Purdue一案中的“如何及为何(how and why)”之问就颇具可操作性,值得借鉴。这样的提问引导判断主体返回到发明完成之前的现有技术,角色代入到当时的普通技术人员,好比站到与本发明遥遥相对的现有技术之彼岸,审视从那里到本发明的距离和阻隔。这样的提问还能够引发更贴近研发实践的问题和思考。例如,发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是否容易?有时,“以问题为抓手”本身就是发明创造对现有技术最大的贡献。又例如,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构想的落实、达到期望的技术效果是否存在技术障碍?现有技术对此又是否已有解答,或可找到某些指引?这种寻求解答和利用指引的过程又是否符合“本领域技术人员”不具备创造能力的人设?正如前文所述,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还原现有技术、查明技术事实、科学分析方能解答。与此过程中,通过争辩双方就此进行的证据、观点和论证交锋,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发明形成本来的过程,避免落入后见之明和反向工程的陷阱,同时对本发明在现有技术基础之上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和贡献形成客观的评价和判断。如此,“事后诸葛”之禁方可得以落实和体现,审查意见和决定也会更言之有物,更令人信服。
科学的创造性审查标准促进专利创造、提升专利质量、激励创新与共享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要求完成“成功之合理预期”的论证,可能会错误地低估一项技术发明的创新与贡献。例如,一项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创新方案可能会因为一些非常早期上游基础性发现的公开、甚至一些无法复制的虚假公开而被视为显而易见,无法获得授权。这会挫伤创新主体参与专利创造和运用的积极性,甚至会对“公开换保护”的制度导向和效用产生怀疑,转而采用技术秘密等其他形式保护其研发成果,这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多赢局面。
诚然,相比有愈来愈多工具辅助的检索,要完成一项严密的技术和逻辑论证实在要难上许多。这要求判断主体全面掌握事实查证、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的把握和运用、技术理解和科学分析以及逻辑论证等诸多技能。或许还需要一点对现实中技术研发的风险、波折与艰难的基本认知和同理心。但是,中国专利事业发展至今,这些正是对于审查员和专利代理师提出的新的、却也是基本的素养和技能要求。只有确立规范,提出要求,才能引导和驱策审查员和专利代理师通过实践与磨练实现进步与提升。
五、结 语
现行创造性判断中对于“成功之合理预期”这一标准的缺失其实是对论证要求的缺失。这导致了许多现有规定和标准,例如“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力的认定、“显而易见”的判断、“事后诸葛”的防范在执行中失准,甚至失效。笔者认为,引入“成功之合理预期”标准对创造性的论证提出要求不失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且籍此标准确立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实现高质量审查、高质量代理、高质量专利的发展目标。另外,在授权标准上与发达国家看齐也符合对外开放、技术引进、成果共享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