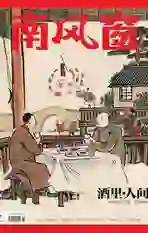赤水河畔的酱香叙事
2019-01-25何子维
何子维

山高,崖陡,河谷深秀。
赤水河的两岸,分布着茅台镇、习酒镇、二郎镇……糟香飘溢,一刻不散,因为酿酒车间,24小时不停工。
小镇往往位于山坡上,甚至贴着崖壁生长,一排排整齐的车间,如三军列阵,粗暴,雄壮。
车间里氤氲缥缈,又热火朝天,酝酿那“杯中之王”,中国酱香。
老师傅
酒糟刚出甑,直冒白烟,散发出浓重的糟香。
老蒋将裤腿高高挽起,光着脚站在酒糟上,用铲子把酒糟翻开、摊平。那姿态像正在耕地的农民,标记他工人身份的,是他那身洗得泛白的灰色工衣。
老蒋43岁,这个年龄按现在的标准还算青壮年,但他却已经被制酒车间的其他人叫老工人了。
老工人就可以成为师傅。因为制酒工龄超过10年,厂里也安排他负责指导新工。
在酱香酒的酿造车间工作,需要耗费大量体力,更需要技巧,对于新工是一种挑战。性子温润的老蒋总是以自己的故事作为教学案例,新工们都耳熟能详了。“小”蒋刚刚进入车间的时候,全靠蛮力挥舞手里那把十几斤重的铲子,结果肩胛骨拉伤,一周后才恢复。
经过10年的磨炼,酒神的力量仿佛注入了老蒋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铁铲握在手心,肌理就会起条件反射。臂膀和腰会匀速持续地发力,一铲下去,铲多少料,举多高,再在空中画出多大的弧度,散落何地,就像机械臂一样精准,无需脑海中做出计算。
好多人问过老蒋,当时拉伤为什么不停止工作,就像好多人问过老蒋,为什么不离开这河谷。
“停下?离开?”老蒋的神色比问他的人还诧异,因为他根本没想过。
喀斯特地貌把贵州的高山河谷分割成一块块面积不大的坝子。壩子围着山,山围着坝子。本来“地无三里平”了,又被赤水河劈成两半。一个个小镇被逼上河的两侧,在峭壁上铺开,人的活动只有“上”和“下”。这种从地理上看来几乎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蛮荒之地,却是而今名满天下的制酒小镇。
对于早先居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回报的确有些迟到,但越是迟到的回报越是丰厚。而对于这些小镇来说,最早改变其苦熬命运的还不是酒,而是盐。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盐的珍贵了,而且交通和技术的进步已经使盐成为廉价的商品。但对300年前的赤水河谷人而言,它却是上天赐给的礼物。
乾隆年间,贵州总督张广泗修赤水河道,蜀盐入黔。工人在赤水两岸休憩、补给。本来以酒换劲,是下苦力之人的上乘之选。赤水河畔“老酒仙”的自酿酒,一旦开坛,满屋飘香,弥久不散,简直就是琼浆玉液。这给敏锐的商人提供了商机,他们迅速作出了反应。船到小镇,官盐进山,再装酒离镇。降低成本,两全其美。
酒香,不怕巷子深,更不怕河流长。相反,长长的河道铺成了河谷两岸生存之道。建立新中国后,汇集了成百上千酿酒的“老酒仙”的赤水河谷,小作坊逐渐演化为颇具规模的酒厂,酿酒业异军突起。最后酿就了名扬四海的茅台,以及习酒、郎酒等。
老蒋的留下是一种理所当然,是把制酒手艺“搞”下去的理想,也是在大山里被称为勇气的信标。
流动的盛宴
在遵义,几乎人人都知道“重阳下沙、端午制曲”这一口诀。
“沙”是高粱,是酿制酱香酒的主要原材料。
高粱是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农作物。把高粱磨成粉,可以做成日常的面、饼、糕,“甜杆”则还可以做成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粱与小麦、水稻等共同奠定了许多国家的粮食基石。随着技术的发展,高产美味的小麦、玉米、水稻替代了皮厚、粒小的高粱。尤其是因高粱中含有单宁物质,口感似青柿,不宜作为主食,逐渐被舌尖犀利的中国人放弃。
被主食“嫌弃”的红高粱却在川黔交界之地坚韧存在,供不应求。尤其在与贵州接壤的川南地带,成熟的糯红高粱被收割上船,沿着赤水东进。
一个个小镇被逼上河的两侧,在峭壁上铺开,人的活动只有“上”和“下”。这种从地理上看来几乎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蛮荒之地,却是而今名满天下的制酒小镇。
运送糯红高粱的船经过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梯子岩,先到贵州仁怀的茅台镇,然后掉头向北,到达贵州习水。就这样,在四川无人问津的高粱被赤水河谷的酒厂以高于其他地方2.5倍的价格收购下来,与贵州富含矿物质的水、群山环抱气流而稳定形成的独特菌落形态,构成了中国酱香酒的自然要素。
老蒋夸赞,只有糯红高粱才能完成酱香酒繁复的酿造过程的考验—两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高温制曲,高温取酒,一年一轮回,熬过二十四节气,还要储存三到五年,方可勾调面市。
和当地人一样,老蒋把“糯红高粱”叫作“红缨子”。这种亲切的称呼,是老蒋认为红缨子对酱香酒的酿制居功至伟,也有对红缨子的“身世背景”心生怜惜之情。
赤水河一河隔两省,向南贵州,向北四川。老蒋自打孩童年纪起,每个月都会走几公里碎石和泥泞交替的山路,到渡口乘船去赤水河对岸坐汽车,去四川省泸州市古蔺二郎的哥哥家。
老蒋的哥哥在古蔺酒厂工作,每次去,哥哥都会带着到酒厂里玩。老蒋觉得自己自幼就和酒厂有不解之缘。成年后,进酒厂工作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同事们几乎都像老蒋一样,闻着酒糟香味长大,是他们的集体记忆,他们甚至无法想像没有酒糟香味的日子怎么过。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无论小作坊,还是大酒厂,或多或少都有商业竞争的关系,但对于他们而言,酒是他们为生存而制造的一种产品,也是连接着他们内心的莫名需要,是融入他们血液里的味道。
地理的阻绝,地缘的封闭,使得贵州人总会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安土重迁的思想,在今天虽然已经不被待见,但老蒋却不愿意作出任何反应,只管自顾自地埋头喝自己的酒。那滋滋的啧啧的声音,仿佛只一抿,便如卸却了身后的一座座大山。
“这里头有家乡的味道。”老蒋举起酒杯,眼睛里泛着光。
看来,光有酒还不够,这酒还必须够味。就像远在他乡的人点了一份家乡菜,光有菜名相同还不行,味道足够贴近才能填补想家的滋味。
小的时候老蒋只能看家里的长辈们喝酒,但是那种持久绵长的酱香味道一直刺激着他的神经。等到成年,可以喝酒了,老蒋第一次向自己的身体里注入酱香酒,那种儿时刺激着神经的味道瞬间从舌尖散开,肆意地铺满整个口腔,轻滑入喉,弥散整个鼻腔,他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索然无味,什么叫回味无穷。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好酒竟然唾手可得。
2018年,老蒋唯一一次离开赤水河在外地喝到酱香酒。即便没有老乡同席,彼此也可以借着一杯酱香酒,把彼此当作“莫愁前路无知己”的沟通共同体。直到桌上的众人皆醉,哪里还问来时的路,哪里还分你与我。这时候,老蒋发现自己所有的情感都是经过赤水河发酵的。
尽管在中国,酒的味道与喝酒的动作总是被人作为叙事的开场白,以显示叙事之人的成熟与伟大。但相比而言,赤水河畔生长的人却拥有一种不可傲藐的身份—酱香酒共同体的身份。他们选择粮食作为巨大的叙事空间,选择源于胎教般记忆力的耳濡目染,让以酒的味道与喝酒的动作作为叙事开场白的人们,从现代的喧嚷退回到孤立的分散,退回到土壤的封闭,退回到农耕的浪漫。
此地山水
看似普通的赤水河,因为两岸酒厂云集,而被誉为“美酒河”。
表面上看,美酒河仅仅为沿线酒厂提供蒸煮制曲的水而已,但沿线酒厂总产值以千亿计,促成了百万之众就业,满足了中国各地数以亿计的酱香酒消费人群的需求。以最知名的茅臺为例,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249.80亿元居“2018贵州企业纳税100强”首位。因为待遇好,当地人有谚语说:“一人进酒厂,全家就脱贫。”
小镇赚钱了,就像捏着进入现代化的入场券。首先是改善旧居。居民的小院被分割成两块,住在后面的老房子里,由一个侧门进入,而前面新起的房子已经不再顾及“地气”,基本没了院子,由青瓦房直接变成了水泥楼房,一排排连成一片,蔚为壮观。
比居民改造自己的房子更大变化的,是酒厂展开规模型建筑。整齐划一的厂房、宽敞整洁的酒店、丰富多样的娱乐休闲区域,和以酒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像无数浮在海面上的花瓣一样,在山谷中起伏流动。
他们无需对生活中的柔软善意卸下伪装的盔甲,他们也无需对生活的凛冽艰险抱以冬天终将过去的姿态苦苦熬着。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但在老蒋看来,过去赤水谷底人的生活,从来不需要设计。
让老蒋始料未及的是,大兴土木不仅改变了小镇的面貌,也冲击着赤水河畔人的思维。老蒋仍然怀念过去那种礼俗性的社会和个人生活,人人都有一个小小的圈子,相互了解,节奏稳定。他们总是以“我很满足”的状态感恩生活,他们一家三代甚至三代以上以酒为生,他们没有想过走出山谷。他们也无需走出山谷,他们无需对生活中的柔软善意卸下伪装的盔甲,他们也无需对生活的凛冽艰险抱以冬天终将过去的姿态苦苦熬着。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但在老蒋看来,过去赤水谷底人的生活,从来不需要设计。
老蒋也知道,他和他的乡亲们随着酒厂向现代企业逐渐转型,正在适应新的变化。比如,制酒业务链被拆分成若干过程,小镇的人慢慢学会了承担专门的角色。但这样也容易被人遗忘或疏忽,以致有的人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家里无事可干。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将日子过得井井有条。他们知道,现代化意味着优胜劣汰,意味着选择,也意味着被选择。
“剩下的酒糟拿去喂牛。”他们仍然按照传统的作法,把人的粮食残余部分再加工,变成动物的粮食。这些看似简单的运用,却是赤水河谷的人的智慧与生生不息的缘由。
小镇里的人不会把自己不用不要的东西直接扔进赤水河,甚至连孩子也不会去河里嬉戏游泳。这些无意识的克制举动,就像担心惊扰了神明,他们一脸虔诚地讲,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不希望自己赖以生存的赤水河当作被征服的对象。
在崇尚科学的今天,有多种考证和研究想看清楚酱香酒的形成,究竟是充足阳光和朦胧月光的催熟,还是南北季风的来回慰藉。但酱香酒的形成,仍是个谜,充满传奇色彩。不可否认的是,酱香酒也成为重塑小镇居民生存状态的另一种力量,这使得自然的敬畏心在赤水河畔得以延续。
赖水为根的人们相信,神明为他们关了一道门,就为他们开了一扇窗。酒,有千种风味,而一旦失去敬畏,毁掉的就是世上独一无二的酱香酒。
在赤水河这个仅有的位置上,他们生活的质地和纹理,比显眼大城市的布景更切实。这是由于他们贴近生存地面的在世方式,比以消费体系为目的的人更为舒适更为可靠。
在赤水河这个仅有的位置上,因为偏僻而被标本化,因为完整而被注意,因为映射人的内心而获得生机。
赤水河谷的人,头上晴天少,杯中酒还多,他们为坚韧的力量,作无言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