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点能留下来的事
2019-01-23邱磊
邱 磊
被逼出来的研究
教师好好备课、上课、改作业,有这 “三板斧”就行了,搞什么虚头巴脑的 “教科研”呢?写什么矫情的文章!——这是很多老师的想法,可能也包括不少学校管理者。但在 “教育”这一行走多了看多了,会发现, “事非经过不知难”,每天忙前忙后、起早贪黑地伺候这 “三板斧”,指望着它,仰仗着它,却也有失灵的时候。
2008年,我所在学校的高三“二模”成绩出来后,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满脸困惑地诉苦:为何我们天天起早贪黑,狠抓死拼,考得却乏善可陈,黯淡如故?细一想,从听课指标化、备课模式化,到全覆盖监控和捆绑式考核, “一模”之后的所谓 “革新” “思痛”,恰如某种不为人知的负强化,隐迹于每天冠以科学之名的各种 “数据表报”和 “分析座谈”中,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下破灭了校长和主任们的黄粱美梦。
“真的心灰意冷了”,副校长有点懊恼地说,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像想到什么似地慨叹: “或许我们当初把体育课、活动课、艺术课都上足上全,结果就不一样了。”高三以来,学校削减了大部分的体育课和户外活动的机会,甚至连一日三餐的时间都被精心计算好,以免“浪费”和 “虚度”。但百密一疏的是,考前两周,几名学生因身体不适而在家休息,还有位临时变卦的“单招生”(即本该参加大专院校单独选拔的学生),均未全程经历所谓的 “二轮复习”,却无一例外地发挥超常,远优于那些汲汲苦撑的同窗。有一位主任后来向我透露,校长已收到多名学生申请,要求“在家晚自习”或 “周末多休息”。
听到这里,我想到的第一个句话,便是 《黄帝内经》中的评语:“以妄为常”。这句两千多年前的箴言,穿越时空地投射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和警示。毫不夸张地说,这几位不用“朝五晚九”的落网之鱼,只是幸运地睡足过几次觉、短暂地享受过家庭生活的余裕和身心释然的闲适——所谓考试,不过是场正常地发挥而已,何曾有过什么灵异的神来之助?但在一个 “以妄为常”的教育逻辑中,在一个擅长以 “爱”之名禁锢和扭曲人的默认秩序里,他们相比那些每日煎熬18个小时的同窗,已是剑走偏锋的传奇。
或许有人以为,这几个孤例,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遑论说明什么问题。需要承认,这些未曾预料的旁逸斜出,确是低概率事件,可正如马克思所说, “它不一定说出某种真实的东西,却真实地说出了某种东西”。我们不是断言,在家休息两天,或停止高强度的机械训练,一定能考得更好;而是提出,教育在时间轴上疯狂地攫取本不属于它的部分,在过度挥霍人们对它的期待和希望的同时,弗洛姆口中的 “控制欲”是否已经膨胀到足以泯灭其 “初心”的地步呢?
正是在这样毫无情面、彻彻底底的挫败下,学校开始冷静下来反思:只仰仗无以复加的 “三板斧”,填满孩子的一切时间、精力,到底错在哪里?教学测评中,一切以硬碰硬的数据说话,并产生相应的整改和强化措施,又何错之有?大家思来想去,最后终于看到一个事实:对教育规律的敬畏、对 “人”本身 (诸如生理机能、情感表征和心理需要)的尊重,对文化滋养的重视,才是一切工作的基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科研也好,写作也好,才恰恰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摸索、反思、建构的理性累积期。
我们把这样的例子,缩小到每一个教师的职业生涯中来说,道理也相近。如果日复一日地吃着当年意气风发时的老本,以 “劳苦功高”自居,拿 “披星戴月”说事,借 “能力有限”遮掩,那教二十年与教二年,除了多些油滑、世故与怠倦,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区别来。要想让生命不被辜负,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年都有新尝试、新感受、新成就。这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初恋般的感觉,来自哪里?答曰:来自将课堂、教材、教法,将德育、智育、美育,将行政和专业,统统给横切、纵切、斜切,直至看到层层叠叠里面的核,体会到教育的每一个细胞都饱含智慧和潜力。而要做到这一切,归根结底,来自于我们对 “治学”和 “研究”的正确看待和价值归回。
你最重要的任务,是炼好自己这块钢
没有一点治学的精神,靠蛮力和经验行事,终将被时代逼到墙角。那做教育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写文章吗?我倒不是这样认为,观念的改变是所有改善的基础。比如,对数据的迷信——相信任何问题总可以从一张张的统计表、函数图中一窥究竟;相信 “量化考核”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出路……这种 “精确到每一个毛孔中”的工业化思维,几乎删掉了教育的精神品质,所谓兴趣,所谓意志,所谓努力,其生存土壤都必须附着于考试机器的承认。
观念的改变是最难的,但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对治学来说,最容易上手的起点是阅读。我们会有趣地发现,临近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学校都必须上完第8课才肯罢休,其潜台词是:每次少上一节课,一学期下来, “损失”就大了。但教育果真是如此“计算”出来的吗?恐怕远非这样简易。雷蒙德·E·卡拉汉在 《教育与效率崇拜》中启示我们:工厂的流水线,可以将原料准确切割和组合,在美国加工的肯德基和在中国生产的KFC,完全可以等质化。但学校不能,它的“产品”,即便是从培养技术工人的角度看,也无法被全然控制;这也不是数量级的问题,而是涉及教育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理性和感性、物性和人性的深层探讨。再如,当我们运用 “举例法”或 “案例法”来授受新课时,布莱尔、施瓦茨等人在 《科学学习》中研究揭示:所有的案例举证,只有呈现 “对照组”时,孩子才有更深刻的学习刻痕。而单一的案例法,除了在课堂上增强感官刺激外,并不能长久地改变学习效率。
也即是说,阅读所带给我们的,完全是另一种 “课堂”。这种课堂,会冲击我们所谓的 “常识”,扣问我们因循守旧的行为及其后面的动机,在多学科、多领域的系统思考中,重新定位自己。美国 《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有本畅销书叫 《失控》,其中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单个的蜜蜂或蚂蚁,所拥有的意识是有限的,所传递的信息也是简单的,而一旦形成蜂群和蚁群,则具有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比如,当食物出现时,蚁群总能神奇地沿着最短路径将之搬运回巢,但它们其实没有谁是 “总指挥”,一切只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着。这种群体智能的涌现,与当下 “去中心化”的 “大数据” “云计算”的时代潮流倒有几分相像,但前提有一点:不能刻意控制任一个体,须让他们拥有足够的自由和发展空间。

所以,这让我们想到:教育不也是如此吗?当每个人得到了个性伸展的可能,群体才能作为一种欣欣向荣的 “生命场”,催生出无数美好的因缘和社会的持续进步。但在今天越来越紧的钳制和管控中,学生被带戴上统一的面具,符号化地生存于一个巨大的筛选系统中。他们是数字化时代的 “土著”,天然地畅享于PC、ipad、iphone之间;却又是数字的奴隶,整个中学时代的价值基座都建立于对最后一次筛选结果的鉴定和度量。这两种身份间的悖谬,斫断了教育与未来间的联系,将作为 “社会关系总和”的 “人”单维化和空心化,将来走出校门的,只是戴上另一套面具、生活于一个更大的牢笼中的人。
有了这一层面的阅读、思考,想到自己未来的路,心里才可能激发起改变、改善的想法,准备在“分数”之外,做一点可以留下来的事。真正的教育生命,可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生发出来。所谓的学术,从来不是为了评定职称、为了暴得大名、为了利益至上,而是有着现实的变革需求;所谓的写作,这时候才有了其应有的必要性。一言以蔽,教育教学的学术性思考与研究,其初心必发自于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想给孩子更真的、更美的、更善的东西,想以最小的伤害代价,帮助他们走过人生的花季雨季,那么最最重要的事,就是赶紧炼好自己这块 “钢”。
搞点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于普通教师来说,似乎不大敢相信,但所有做过的人会告诉你,这是一件 “人人皆可成尧舜”的事。这不是件端坐在实验室、趴在文件堆里、睡在办公室里疯狂烧脑、自娱自 “嗨”的活儿,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去炼一炼,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块好钢呢?我自2009年开始写博客,动因源于一次考后反思,首篇名曰《大考之后,大爱之前》,即一气呵成地写下千言,渐渐累积而能形成习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中国信息技术教育》上的 “博客介绍”,虽只有短短一版,却道出了自己对当下教育生活的思考,同时亦是不断坚持写作的回报与鼓舞。有了最初的尝试,次第而来的种种 “因缘际会”,便是无法预料的。当我把阅读心得、课堂反思、治班困惑等种种 “吐槽”化作文字,文字又成为互联网海量数据的一部分,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些反应如同一只只触手——每一只都可能联结到一个全新而未知的知识网、人脉网、信息网中,如此,将来自己所致力的研究领域 (课题)也许正孕育其中了:遇到陶行知、遇到蔡元培,遇到杜威、遇到卢梭……每一个人,无论东西方,均以自己的学术结晶,化成后人知识结构乃至心智结构中的宝贵营养。譬如,陶行知的“小先生制” (课上让孩子讲给孩子听),是实现生本课堂的典范;杜威的“从做中学”是解决行知分立的原则;卢梭的 “教育即浪费论”(教育要留给孩子自由生长的时空)是提醒后人分清 “效率主义”(知识最大化)和“效能主义”(能力最大化)的区别。
做一点能留下来的事
多元的联结和丰厚的素材,让老师们不再对聒噪的现实盲听盲信,而渐渐有了个人的教学主张,基本的行业底线和坚实的教育信条。自己这块 “钢”终于开始成型。一代又一代的先人,可能走完一辈子,也只能留下一本书、一个主张、一句话。而我们现在,之所以能 “立”于课堂中,在于汇集了无数人的智慧和创造——那我们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后世呢?也许,可以做一点能留下来的事 (或抱此至愿,心有所向)。利用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根据自己的课堂建设,加之兴趣、时机、政策等,做点“留痕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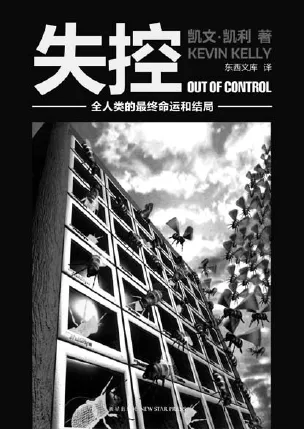
以我而言,一直以为教材的生本化不足,“不好好说话”乃至“说听不懂的话”是孩子最厌恶之处,于是想办法自己 “写”套教材,按照个人所长、孩子的年龄段和时代风貌,参照港台日美的资料,以大主题的形式,一路串接必备的知识网络,锻铸核心素养。比如,我以 “光”“水”“气”“电”等自然主题,“地名”“文字”“诗词”等人文主题,还原了地理的知识生成、观念建立、价值取向的过程,实践怀特海 “过程即意义”的哲学主张,在教育领域的书写。虽然探索的过程,尚有种种不足,但每每新写完一稿,内心的欢愉感和满足感,都是十足的。尤为幸运的是,创作受到教育媒体的支持,不远的将来,作为一种资源,或以视频、音频、图书 (绘本)等形式留存。
这样看,我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建设者、开创者。所以,做教育教学研究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它不是让你当古板的当老学究,也不是令人皓首穷经地做惊天动地之举;能唱则唱、能画则画、能写则写、能辩则辩,每个老师充分地发挥特长,不断汲取古今中外 “大咖”的智慧,让自己长大、长高、长壮,看到更多、更远、更精彩的世界,并在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上,结出弥久芬芳的果实来。教育的世界,一直在改变,我们若不能主动迎接,就会受之碾压;但教育的世界也有很多沉淀下来的公理和常识,成为盲动和乱流中的制衡者。让我们都成为这个聒噪时代的阅读者、写作者、研究者吧,都成为坚韧不乏、持之以恒的 “钢之炼金术师”吧!做这一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的生命,为了不辜负每一个孩子的信任,以及他们身后的整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