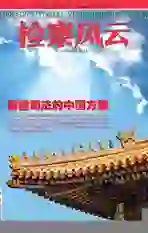侠与《侠隐》
2019-01-21张宁
张宁

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因被姜文翻拍成电影《邪不压正》而名噪一时,然而从文字到影像,两部作品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审美旨趣。
看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改编的《邪不压正》,彭于晏一出场,我就感到不妙——这个片子和“侠”没什么关系了。甚至,无关北平,无关1937,无关张将军,这只是姜文借了北海先生原著的壳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欲望与权力的故事。那么《侠隐》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在谈《侠隐》之前,要了解“侠”以及“侠文化”。
关于“侠”的含义及其起源,许多学者早有论述,如刘若愚的《中国的侠》、侯健的《武侠小说论》、田毓英的《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汪涌豪与陈广宏合著的《游侠人格》、叶洪生的《论剑》、鄭春元的《侠客史》、王立的《武侠文化通论》等。总的说来,侠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而在《侠隐》故事发生的时代,“侠”的存在的诸多条件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如冷兵器时代走向终结、法制社会成为历史潮流、传统道德观渐趋瓦解,等等。没有了生存土壤,“侠”这一群体的没落成为必然。
对于“侠”在中国文化中的命运,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代大师金庸先生就已经在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做出判断。在那部所谓的武侠小说中,没有武,也没有侠——主人公韦小宝既不会武功也不是侠客,他唯一擅长的武术技能是逃跑;而作为江湖最后一位大侠,陈近南稀里糊涂、窝窝囊囊地死掉——这甚至是“反武侠”的。如果说金庸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武侠小说文类的现代化转换,那么张北海的《侠隐》则实现了对武侠小说审美意境的再造。诚然,我们不必纠结于《侠隐》到底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因为,如果《侠隐》不算武侠小说,那么《鹿鼎记》更不是武侠小说;而所谓武侠、言情抑或其他种种分类,更多是研究者为了便于研究所做的归纳,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本本身说了什么。
小说情节说起来并不复杂,就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太行派掌门人顾剑霜一家被他的大徒弟朱潜龙勾结日本人杀害,太行派灭门,唯一侥幸逃生的是后任掌门的弟子李大寒。在美国驻华医生马凯的帮助下,李大寒赴美进修并整容,五年后化名“李天然”归国报仇。故事围绕李天然复仇展开,这是武侠小说最常见的情节构制模式。然而与以往众多武侠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张北海道出了在一个新旧交替时代,在武林走向消逝的乱世,“侠”的迷惘与反思。
作者将李天然回国的时间点卡在了卢沟桥事变前夕,在那个国将不国的关口,李天然复仇的最大心理障碍,并不是电影中表现的胆怯、懦弱、无法面对现实与自己,而是内心对侠的行为和侠的信仰的怀疑:在新的时代,侠的行为准则还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不为非作歹、不投靠官府”吗?在民族危亡面前,个人复仇与行侠仗义在何种程度上还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与官方合作到底是违背了江湖规矩还是国仇与家恨的殊途同归?在一个被火药文明征服的世界,侠的出路又在何方?作者对主人公的塑造和情节的铺陈冷静而克制,所以整个故事读起来总能不时引人遐思。李天然既是曾经的太行派年轻掌门,又是留美归国新闻编辑,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少了江湖草莽气,多了几分斯文,他的诸般思索也便合情合理。
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复仇大业,李天然都产生了自我怀疑。当他和年轻的寡妇关巧红在路边馆子避雨吃羊杂面的时候,被人指戳嘲笑。李天然想教训那两个伙计一顿,可是一想那又怎样?这么大一个北平就这么两个混蛋?从小就听惯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包括这种人间羞辱吗?没流血,没死人,这算是件小事吧?李天然找到朱潜龙的时候,朱潜龙摇身一变已经成为警察局的便衣组长,后又升任侦缉队长。这很值得玩味,因为警察机构和组织在现代社会代表的是法制,与“以武犯禁”的“侠”形成尖锐对立。从自然法哲学的视角看,无疑是李天然代表正义,但站在实证法学的立场上说,李天然则是法制的破坏者,反而朱潜龙身后是现代法制。这一点,姜文在其电影《邪不压正》中进行了放大,朱潜龙在影片中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打击犯罪惩恶扬善赢得群众爱戴的“好”警察,当他举枪把囚犯的脑袋崩开花,围观的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警察是持枪的国家武装力量,武功为“侠”带来的特殊象征意义在枪口之下被消解。
其实马大夫有几句话更说中了要害:“……你想想,就算你报了这个仇,那之后呢?就算法律没找到你,也是一样,那之后呢?这个年代,你一身武艺又上哪儿去施展?现在连你们的镖行都没有了,你还能干什么?天桥卖技?去给遗老做护院?给新贵做打手?……跟我们去美国走一走吧,出去看看世界……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大,大过你们武林,大过你们中国……”在已经变换的时空里,武侠注定落寞。
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代表蓝青峰适时向李天然抛来橄榄枝,李天然犹豫过,因为与官家合作是“侠”的大忌,因为那会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侠”所倚重的自由。然而他很快发现,世易时移,如果不借助蓝的力量是很难报仇的;同时他也在思考,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救国救民是不是“侠”的分内之事?当他看到一向养尊处优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蓝田大义凛然上了前线,又为国捐躯,他被震撼了——“一个大少爷,半年训练就能上场,而浑身武艺的他,此时此刻,反而全无用武之地”。掌毙羽田,断臂山本,李天然一度以这种快意恩仇为“侠”之英雄本色,可是与原本看起来有点幼稚的蓝田比起来,似乎幼稚的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养父马凯及其夫人,作为国际友人他们亦投入抗战救亡的洪流之中,身为中国人的自己还能无动于衷吗?在更深的层面上促使李天然与蓝青峰合作的是,与太行派一起正在走进历史烟尘的,还有他一度以为是家的古都北平。
作者用大量笔墨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北平。前门东站熙来攘往的人群,哈德门大街上的有轨电车,晒在身上暖呼呼的太阳,一溜溜灰房,鼓楼、雍和宫、什刹海,从干面胡同西口到东交民巷……张北海笔下的北平很是地道。作为离开中国多年、与北平分别多年的旅美华人,张北海对老北平的生动再现,既是小说中人物李天然对旧日时光的留恋,也是他自己对往昔的怀念,对传统生活与文化的怀念。
“夕阳无语,可惜一片江山。”正如北平再也回不来了,太行派还能重回江湖吗?江湖已经不复存在,“侠”的出路似乎只有归隐。在小说结尾,一代豪侠隐迹古都,热血青年投身抗战。然而,这依然不是革命叙事传统上的浪漫主义觉醒,在更大程度上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无奈探索。在创作上,这一探索的意义是为武侠在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过渡中的存身寻求一个可能;从武侠小说史上看,这其实是对以“北派五大家”为终结的民国武侠小说在时空上的再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