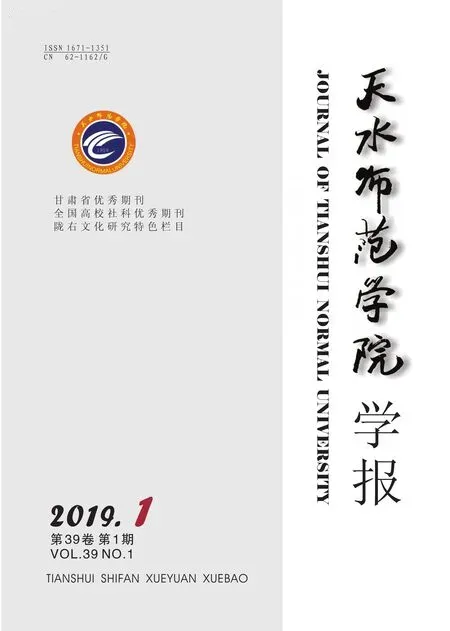北朝墓志文学中的佛教信仰
2019-01-20杨柳
杨 柳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北京 100011)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入华后快速传播的时期。在北朝多元文化相激荡、相融合的背景之下,佛教在北朝的影响渐趋深入、广泛,历史上多有北朝帝王崇佛的记载,佛教向各个阶层渗透,成为一些个人的信仰选择,甚至也成为一个家族群体的信仰取向。北朝墓葬也受到了佛教的冲击与影响,墓葬装饰中开始出现莲花纹、莲座摩尼宝珠、散花等具有明显佛教特征的图案(高润墓壁画中,墓道两壁的上沿绘有忍冬、莲花等纹样组成的装饰花边;[1]娄睿墓壁画中,也有摩尼宝珠、莲花、金翅鸟等[2]),还有些人物画像,如建德元年(572)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墓墓室北壁绘有一手持柳条、有须的男子形象,[3]恐怕也与佛教有关。而佛教话语也已渗透到了墓志书写中,如,北魏《孙辽墓志》:“少怀净行,长而弥洁,悟三有之元(笔者按:恐应为“无”)常,体四趣之沉溺,洞达苦空,超鉴十相。是以童丱之年,信心三宝,厥龄十八,禁酒断肉,修斋持戒,心无染缚,善能开化,方便导物。……一仪无像,四天传则,灵剎开神,梵堂启或。伊我君公,秉心渊默,深覩正真,妙达通塞。淹回圣迩,寝息神光,裁辩权实,离析旧章。十尘外遣,五阴内忘,蒸斯沉溺,作彼舟航。”[4]147-148这里,三有、四趣、苦空、十相、三宝、禁酒断肉、修斋持戒、善能开化、方便导物,以及灵剎、梵堂、十尘、五阴等,均为佛教中常用的词语,可见墓志书写者对佛教用语等已经相当熟稔。本文拟对墓志所载北朝时人的佛教信仰状况、奉佛动机,以及佛教对北朝社会和个体的影响做些探讨。
一、关于志主佛教信仰的记述
在对志主生平叙写中,时或涉及志主的佛教信仰。一些志主的名、字中,便包含明显的佛教“元素”,如,《北齐处士马公瑾故妻元氏墓铭》:“讳摩耶,河南洛阳人也。”[5]242北魏《张整墓志》:“君讳整,字菩提”[4]43北周《独孤藏墓志》,称藏:“字达磨,朔州人也。……本性刘,汉景帝之裔,赤眉之乱,流寓陇阴,因改为独孤氏。”[6]295可见,佛教影响已深。
佛教的修行方式在北朝墓志中多有记载。佛教提倡茹素少荤,使人神清气爽,头脑清醒,有利于参悟修为,奉佛之人往往都要持斋以达到念佛的清心境界。诵读佛经也是主要的修行方式:“崇信佛法,戒行精苦,蔬食洁斋卌余载,行坐读讼,晨昏顶礼。”(《李敬族妻赵兰姿墓志》)[6]379“于是寄情八解,凭心七觉,炳戒珠于花案,发意树于禅枝。”(《杨敷妻萧妙瑜墓志》)[6]526此外,还写到志主的布施、写经、造像等北朝人常用的积德修行方式:施舍如北齐武平七年(576)《崔幼妃墓志》,志文称其:“回心释典,刻意法门,洞识苦空,悬鮓常乐。帷屏象马之翫,罗绮玉帛之珍,施舍无遗,藏篋俄尽。”[4]477造像写经如北周大象二年(580)六月《梁嗣鼎墓志》:“其人孝敬慈善,志尚玄门……以周大象二年六月廿一日临终,愿舍敕赐衣物,造金银像两区,涅盘经二部,卒于洛阳里。”[4]491
佛教义理也受到了北朝时人的欢迎。学界通常认为,南朝佛玄互相影响,以义理为主,北朝佛教则重禅修。如,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谈到:“自此以后,南北佛学,风气益形殊异。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此其原因,亦在乎叠次玄风之南趋也。”[7]但本文认为,不可绝对化地理解为北朝佛教义学衰绝。后秦姚苌、姚兴、姚嵩的佛学议论,颇为深入,且具文采。姚嵩的《上述佛义表》,理致颇深。北魏献文帝、孝文帝和宣武帝亦好尚佛理,并提倡佛教义理研究。《洛阳伽蓝记》载:“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沙门论议,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迎驾于新门。”[8]为方便前往佛寺于沙门谈讲,而专辟城门,足见孝文帝于佛教论议之热情。又《魏书·韦纉传》载:“高祖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纉掌缀录,无所遗漏。”[9]1014《魏书·释老志》载: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9]3042杜弼在佛教义理方面颇具造诣,曾与魏帝辨析佛性和法性的问题。[10]北朝墓志中也记载了不少志主生前好谈佛理,如《元举墓志》:“洞兼释氏,备练五明,六书八体,画妙超群,章勾小术,研精出俗,山水其性,左右琴诗。”[4]215《元鸾墓志》:“少标奇□,长而弥笃,虚心玄宗,妙贯佛理。”[4]46
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家族奉佛的不乏其例。据史载,崔光家族信仰佛教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崔光“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其弟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其从弟长文“专读佛经,不关世事”。[9]67河东裴氏的裴植一家亦是虔诚奉佛者,史载“其母年逾七十,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植弟瑜、粲、衍并亦奴仆之服,泣涕而从,有感道俗。”裴母虽年过古稀,但对奉佛的热诚不减,不仅舍身为婢,供寺院洒扫,后来干脆出家为比丘尼,“入嵩高,积岁乃还家”。裴植本人也长于释典,善谈理义。临终,遗令子弟为自己“翦落须发,被以法服,以沙门礼葬于嵩高之阴”。[9]1571刁雍因“笃信佛道,著教诫二十余篇,以训导子孙”(《魏书·刁雍传》)。[9]871将佛教作为训导子孙的重要内容,可见佛教已成为其家庭文化的重要部分。
二、关于奉佛动机的书写
从墓志可以看出,北朝人奉佛,有诸多复杂的原因。
北朝皇室后妃中,出家的不少。除极少数是出于喜爱佛教的原因,其他更多都是因为残酷的宫廷斗争而被迫出家。据研究者统计,北朝后妃先后有18位出家为尼。如,北魏孝文幽皇后、孝文废皇后、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等,而这些后妃大多是在被废后强令为尼或不得不为尼。北魏胡太后即曾出家为尼。武泰元年,尔朱荣称兵渡河,太后尽召肃宗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发。最终胡太后和幼主还是被尔朱荣并沉于河,太后妹冯翊君收瘗于双灵佛寺。洛阳瑶光寺,即是众多后妃名族处女出家的场所,《洛阳伽蓝记》卷一载“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仪此寺。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归诚一乘。”[8]47孝文帝废皇后冯氏,即终于瑶光寺。宣武皇后高氏,在明帝时亦居于瑶光寺。
而天下多虞,是许多人遁入佛门的重要缘由。《魏书·释老志》记载道:“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盛,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狠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9]3048动荡的社会中,多有依附佛寺立身者,《魏书》卷四十三记载,刘旋之死后,其妻许氏携二子法凤、法武入国,“孤贫不自立,并疏薄不伦,为时人所弃。母子皆出家为尼,既而反俗。”[9]969因家庭的变故,孤贫不自立,并疏薄不伦,为时人所弃,无奈之下只得出家。《魏故比丘尼慈庆墓志铭》也记载:“尼俗姓王氏,字锺儿,太原祁人,宕渠太守更象之女也。禀气淑真,资神休烈,理怀贞粹,志识宽远。故温敏之度,发自龆华;而柔顺之规,迈于成德矣。年廿有四,适故豫州主簿行南顿太守恒农杨兴宗。谐襟族,执礼中馈,女功之事既缉,妇则之仪惟允。于时宗父坦之出宰长社,率家从职,爰寓豫州。值玄瓠镇将汝南人常珍奇据城反叛,以应外寇。王师致讨,掠没奚官,遂为恭宗景穆皇帝昭仪斛律氏躬所养恤,共文昭皇太后有若同生。太和中,固求出家,即居紫禁。”[4]146王钟儿因逢战乱,没入奚官,后为景穆皇帝昭仪斛律氏养恤,再后来出家为尼,其身世经历,映射出北朝社会的动荡不安。
对无常命运的困惑,也是北朝时人投身佛门的重要原因。离乱之世,人生尤显无常,佛门乃是救赎,是难得的依托。《高殷妻李难胜墓志》云:“……乃悟是法非法,如幻如梦,厌离缠染,托情妙极,遂落兹绀发,归心上道。三乘并运,六度俱修,慈解日深,法性增益。以毗尼藏,摄彼威仪,用修多罗,开其方便,精行乐说,众所推重。方当主持我玄虚,栋隆我净法,而众生福尽,乃失导师。”[6]194另有寡居守志的女性,以佛教为精神寄托。《萧妙瑜墓志》载:“夫人孀居守志,无劳匪石之诗;昼哭缠哀,自引崩城之恸。寄情八解,凭心七觉,炳戒珠于花案,发意树于禅枝。”[6]526又如,《元纯陀墓志》记叙,志主初嫁穆氏,穆氏去世后,在兄长的强求下,又嫁于邢氏为妻,不久邢氏又谢世,这样的变故,令元氏连受沉痛打击,十分悲苦,志载其“思成夫德,夜不洵涕,朝哭衔悲”。对这样凄惨无常的命运,她应当是有过深沉的省思:“吾一生契阔,再离辛苦,既惭靡他之操,又愧不转之心,爽德事人,不兴他族,乐从苦生,果由因起。”可见,省思的结果是:这样多舛的命运,是“果”,“因”则是自己“爽德事人”。由此因果顿悟,她“便舍身俗累,托体法门,弃置爱津,栖迟正水,博搜经藏,广通戒律,珍宝六度,草芥千金。”[4]261出家为尼,投身佛教活动之中。——佛教因果报应,为女性多舛的命运提供了一种解释。这也是女性会投身佛门的较为深层的原因。
三、墓志所见佛教对北朝社会和个体的影响
从北朝墓志书写,也可看出佛教对北朝社会和个体的影响。
佛教在北朝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作用,是融入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为亡父母追福,吃斋念佛,更甚者,舍宅为寺、为亡父母造像。如,景明初年,宣武帝令大长秋白整仿照代京灵严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灵太后所建永宁寺,也是为其父乞福。《元郁墓志》记载:“祠子安明年卅五,奄丁穷毒,痛悼崩毀,躬沉庐下,扳号慕上。朝粥夕溢,余期弗改。斋施勉力,倾储追福。令僧尼持宝結路,运货终辰。昔大拏好施,抗称前代,今王子捨宅,流孝后世,所谓今俗超然,岂悉达之能伦,痛悼善孝,诸宗雅其慈。”[11]3元郁志盖:“仰為亡妣用紫金一斤七兩造花冠双钗,并扶颐,若后人得者,为亡父母减半造像,今古同福,安不慕同。”[11]2“倾储追福”乃是孝行,孝道至此有了新的内容。为父母尽孝也成为北朝时人奉佛的理由。《王普贤墓志》载:“夫人痛皋鱼之晚悟,感树静之莫因,遂乘险就夷,庶恬方寸。惟道冥昧,仍罗极罚,茹荼泣血,哀深乎礼。”[4]70王普贤即感于“子欲养而亲不待”,故持斋念佛,为父母修福。
葬俗亦受佛教影响,葬期和墓葬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北魏王朝把厚葬作为一种“孝行”加以倡导,不到葬期而匆匆下葬,或者该迁葬而不迁葬,则有可能招致不孝之嫌。相反,《魏书》载,河东闻喜人吴悉达因迁葬之诚,而被表彰:“因迁葬曾祖已下三世九丧,倾尽资业,不假于人,哀感毁悴,有过初丧。有司奏闻,标闾复役,以彰孝义。”[9]1885但因为佛教的融入,葬期便随佛缘而大大缩短。东魏佛门大师慧光卒于元象元年(538年)三月十四日,十七日葬,丧期为三天。[12]北周梁嗣鼎身为武将兼通佛经,其于大象二年(580年)六月二十一日卒,其月二十三日葬,仅停二天。[4]491二人均为卒后即葬。北魏《张略墓志》载:“兴和元季十一月十七日卒于家,时季七十三。粤以兴和三季八月庚子朔廿二日辛酉藏以玉塔,奉以床帐,葬于豹寺之西韩司空墓右。”[5]175-176且不仅安葬时间短速,墓葬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信奉佛教,志主“寝疾发心,誓不棺椁”,卒后果然以不以棺椁装殓,而将灵骨(骨灰)藏于塔中,而床帐等生前物品另葬于墓中。北魏正光五年《孙辽墓志》载,孙辽笃信佛教,卒后,其子息追述亡考精诚之功,于墓所建造浮图,“愿令事与须弥等寿,理与日月齐明,永流懿迩,式传不朽”,其墓志名亦作“浮图之铭记”。[4]147佛教毫无疑问也影响了北朝人对于两性关系的理解。出于修道之心而夫妻别葬的时有出现:如,元纯陀(法字智首),遘疾弥留之际,“子孙号慕,缁素兴嗟。临终醒寤,分明遗托,令别葬他所,以遂修道之心。”而其儿女果然式遵,不敢违旨。[4]261-262
从前文论述可见,佛教也影响到了北朝时人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建构。从北朝墓志可见,有些奉佛者乃是出于对人生真谛的追寻而靠近佛教,甚至笃信佛教,身体力行。如,《魏故持节征虏将军营州刺史长岑侯韩使君贿夫人高氏墓铭》记载:“至景明三年,宣武皇帝以夫人皇姨之重,兼韵动河月,遂赐汤沐邑,封辽东郡君。又以椒帏任要,宜须翼辅,授内侍中,用委宫掖。献可谏否,节凝图篆。夫人以无生永逸,有陋将危,志腾苦海,舟梁彼岸,故裁谢浮虚,敬仰方直。于是金花断意,宝蕤离心,物不中度,未曾观揽。”[4]153-154志主以皇姨的身份被封辽东郡君,又被授以内侍中之职,而夫人不以为意,以人生为苦海,而“志腾苦海,舟梁彼岸”,于是“裁谢浮虚”、“敬仰方直”。孙辽“浮图之铭记”记载,其年少之时,便怀净行,长而弥洁,悟三有之无常,体四趣之沉溺,更以十八之龄,禁酒断肉,修斋持戒。甚至,曾烧两指而尽身供养,不以支节之痛,以示无我之念。供佛之心,不可谓不诚,而从其生平来看,以童丱之年便归信三宝,可见志主不是因为世积乱离,或坎坷的人生经历,方才遁入空门,而是心内有着对人生的终极追求,而于佛门寻找依归。
对以上这几位志主而言,佛教修行真正影响了其人格建构。但总体而言,真正以佛教的终极追求为目标的志主并不太多。从大多数与佛教有关的北朝墓志可以见出,在人生价值、死亡意识等深层次的观念上,佛教尚未形成重大的影响。
终极价值上,佛教的影响有限,主要还是儒家存善留名的思想。如,孙辽墓建有浮图,而其墓志名亦作“浮图之铭记”,铭记道:“有子显就、灵凤、子冲等追述亡考精诚之功,敬造浮图一,置于墓所。愿令事与须弥等寿,理与日月齐明,永流懿迩,式传不朽。”铭文云:“浴余小子,末命将沦,构兹宝塔,缀此遗尘。崇功去劫,树善来因,舟壑虽改,永□天人。”“崇功去劫”,“树善来因”,虽然渗透了佛教话语,但在生死观上还是秉承了传统的从化形销,在人生的终极价值上,仍是儒家的立善留名思想:“事与须弥等寿,理与日月齐明,永流懿迩,式传不朽。”[4]147如《张略墓志》:奉承遗勑,不违生愿,依俗所造,布施三宝。但露草不停,奄随物化……兴和元季十一月十七日卒于家,时季七十三。”[5]175-176这都说明,佛教的生死观,并未触及北朝人生死观的根本。死亡,即便对佛教中人,也是一去不复返的铁定的事实。《慈义墓志》:魏瑶光寺尼慈义,“长辞人世,永即幽泉”,[4]102可见,虽然用到了佛教的一些表述,但其生命观却并未受到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对于死亡的巨大悲感,甚至会令书写者感叹,奉佛之举,实亦枉然。如《东魏官讲法师刘集墓志》载:
尼讳集,俗姓刘。冀州灌津人也。独悟之心,超然自远。年十三出家,舍副笄之饰,袭多罗之衣。总持十二,如瓶泻水。自大魏理运,道冠前王,像法之兴,于斯方盛。时年廿五,魏宣武帝所宠。为官讲法师、文宣大寺主。
铭文:
悠悠物理,茫茫世路。独有哲人,依空高步。法船既逝,德音难续。徒奉牛头,空之鸡足。[5]210-211
“法船既逝,德音难续”,令书写者感慨,志主年十三出家,虔心奉佛,但最后不过是“徒奉牛头,空之鸡足”。
而佛教的核心教义轮回转世之说,在北朝墓志书写中几无痕迹。这与同时期造像记所体现出来的生死观念,有较大差别。如,永平三年(510年)九月四日尼法庆造像记云:“为七世父母所生因缘敬造弥勒像一躯,愿使来世托生西方妙乐国土,下生人间王公者,远离烦惚,又愿己身□□□与弥勒俱生莲华树下,三会说法,一切众生永离三途。”[13]普泰元年(531年)八月十五日龙门尼道慧法盛造观世音像也云:“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师僧眷属,愿不堕三途,□诸□难。”[14]此中都蕴含典型的佛教转世思想。但在北朝墓志书写中,却几乎不见类似的表述。在北朝墓室画像中,莲花是一种常见的装饰纹样,如河北磁县湾漳北齐墓墓道地面绘有八瓣仰莲,山西太原徐显秀墓墓室四壁上部和神怪瑞兽周围都穿插着飘逸飞动的莲花图像,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的第四过洞进口上方绘红彩莲花图案,北魏大同智家堡石撑墓彩绘中,更是出现了手持莲蕾的侍从。论者以为,虽然莲花在佛教传入前就作为装饰纹样存在,但考虑到北朝佛教的兴盛,莲花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墓葬装饰中,也许是墓主借以表达“愿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化生”的美好愿望。[15]按:从墓志书写来看,恐并非如此,莲花图案恐怕主要还是作为一种装饰元素而出现的。通过考察北朝葬具画像,郑岩论道:“除了一些装饰性的莲花图案,佛教思想、教义和相关礼仪,并没有大量融入这些葬具画像中。”[16]
北朝墓志书写中,也可看出,在实践层面,北朝佛教修行与儒学修养往往并行不悖。如,《杨无丑墓志》:“禀灵闲惠,资神独挺,体兼四德,智洞三明。该般若之玄旨,遵斑氏之秘诫”,[6]84该志中“该般若之玄旨,遵斑氏之秘诫”等语将佛典与传统女子教育典籍并举,“体兼四德,智洞三明”和铭辞中“行该四德,志达三明”等表达也是同样的意思。将儒家要求女性的“四德”与佛家的“三明”(菩萨明,诸佛明和无明明)相对,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儒家学说在当时与佛教经常是结伴而行的。《魏前将军廷尉卿元公妻薛(慧命)墓志铭》亦是将儒行与禅练对举:志主薛慧命“且诫则有章,斑母恧其先;礼修台赞,鲁宫惭其昔。敬上接下,娣姒贵其仁;尊佛尽妙,禅练尚其极”,铭文云“古今所传,有矩有规。洞鉴妙法,化耋效畀”。[4]214-215
而在理论层面,佛教又显现出与玄学的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之初期,佛教呈现出与玄学相交融之势,这在北朝墓志中也有体现。《高猛妻元瑛墓志》:“加以披图问史,好学阁倦,该柱下之妙说,核七篇之幽旨,驰法轮于金陌,开灵光于宝树。”[6]118说明志主对老庄之学和佛教均有接触、学习。
甚至,佛教的终极目标是成佛,但在一定程度上,佛教的成佛与神仙学的成仙,在大众的视野中似也并无太大差别。佛教与神仙学在北朝墓志书写中也常常相提并论。如,《魏故使持节侍中司空公安乐王妃李氏墓志铭》(志主李宪之女):“兼且德越胜缦,度超末利,投心法界,尚想玄门,方冀沐浴香雨,乘舟利涉,长捐火宅,永弃铁城。故乃散宝招提,贱聚沙之业;布金买地,同长者之心。然虽灵桃可饵,赤龙之驾难追;巨枣易寻,白云之乘方远。死生相续,灭恶无常,如泡如幻,孰云能免?铭曰:天地匪固,随劫销亡。生如石火,世匹萤光。既明实相,深悟无常,唯遵正觉,是曰舟航。经天西逝,带地东流。一言从化,聚骨崇丘。”[5]146-147这段叙述中,叙述者在佛教与神仙学话语之间进行了自由切换:前文详述志主平生奉佛种种,而谈及死亡,叙述者马上换了神仙学话语,“灵桃可饵,赤龙之驾难追;巨枣易寻,白云之乘方远。”随后,又马上切换回佛教话语:“死生相续,灭恶无常,如泡如幻,孰云能免?”说明,在墓志书写者心中,志主对于佛教的追求,与仙家企图长生不老、修炼飞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划上等号的。《董仪墓志》亦云:“兼及笃信三宝,妙闲二谛。指彼岸而将登,出尘罗而愿往。忽驭周女之云车,从葛妻而蝉蜕。”[5]291-292这就如同道教、佛教混合造像碑,显示出在造像者心目中,道教与佛教的界限极其淡薄,对道教造像与释迎、弥勒、观世音和无量寿等佛、菩萨像一视同仁,而道教像的造像记也与佛像的造像记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