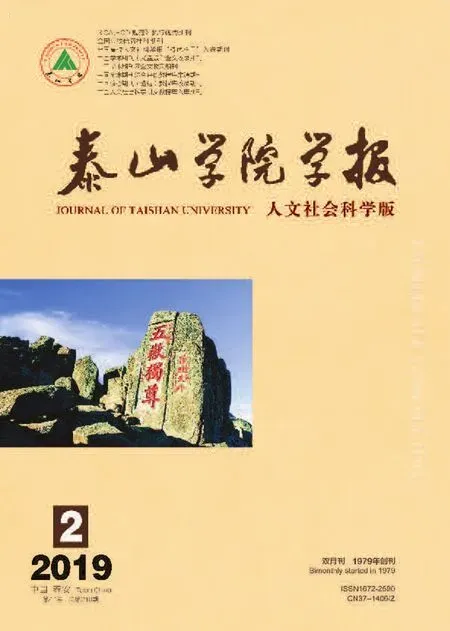课程研究中的自传方法
——派纳与福柯自传思想的比较研究
2019-01-20戎庭伟
戎庭伟
(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引言
“从自传和传记文本的角度理解课程的系统尝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在自传和传记研究中有三个流派:自传理论与实践、女性主义自传、从传记和自传的角度理解教师[1]。自概念重建运动后,自传何以成为当前课程领域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尽管历史上课程界一直强调‘个体’,派纳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标语,是不具备具体生活的一种抽象……课程领域忘记了实实在在的个体。单单专注于公众世界、可见的世界、设计、序列化、实施、评价以及课程材料,课程领域忽视了个体对这些材料的体验”[2]。
研究者的眼光过多停留在个体外部,秉持外部环境变化—个体自然变化的机械因果观,导致课程领域长期见物不见人。我们需要“除了注视着外部以外,还要注视我们自己的内部,并开始尽可能诚实和具体地描写我们内部的经历是什么”[3]。“我们内部的经历”的外部表现就是我们的生活史。
教育空间中的个体是通过教育真理的界定与权力关系的调节而形成的,这种方式生成的具象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体性变得从属于某种规范性的准则,凝固为僵硬的结构,或缺乏向与自己不同方面流动的能力。”[4]这就使得主体性局限于某一种“规范性准则”而变得僵硬与固化,使得主体性面临一种危险:即主体性等同于同一性的身份,主体变成“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与我国“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标显然存在矛盾,我们需要开辟主体性的新维度。
所以,无论对于个体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于生产主体性的多种力量而言,主体对建构自身力量的自觉与体认,既是深化与巩固主体性的必要机制,也是个体进一步超越既定的身份界限、创造想象中自我的前提与基础。派纳将自传方法引入课程研究,“旨在帮助课程领域的学生学习如何描述学校知识、生活史和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达成自我转变。”[5]
让个体理解自我,并寻求期待性的改变,是派纳引介自传的初衷,也是福柯的生活方式。福柯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一直想让我的著作成为我自传的一部分。我的著作一直都是关于我对于疯狂、监狱和性的私人问题……我每一部作品都是我自己传记的一部分。”[6]与福柯的假设相一致,派纳认为理解自我特别是当下自我的处境、确认形成自我的各种内外部因素,是改变自我的必要前提。个体可以而且有必要对自己复杂的心灵状况进行深入审慎地理解,这可以“产生更加准确,以及最终更加全面的社会的或教育的观察,并且对于研究者本人来说,可能会带来心灵上和教育上有益的结果”[7]。因此派纳的自传方法,可作为福柯“自我的技术”①“自我的技术”作为一种主体化方式,是主体在自我力量或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作用于自己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旨在改变自己,达到某种“幸福、圣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境地”(Foucault,Michel.Technologies of the Self,in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Martin,etc.eds.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8:18)。中认识自我的方式,目的在于将自我“内在的真实”讲述出来。只有通过对“内在的真实”的关注,才能达到自我关怀。问题在于,什么是儿童“内在的真实”?福柯和派纳对“内在的真实”的认识是一致的吗?
二、自传的目的:先验论与形成论
派纳曾问到,“存在一个真实的自我吗?”他认为,“个性是社会性的表达与构成;它与自我既整合又分离”,自我的“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的问题便处于这一整合与分离的运动中”。“如果个性与自我相分离,代表了自我的否定、歪曲或其他形式的变体,那么我们可以说自我(个性)是不真实的。……相反,行为表现出与自我相统一的流畅性与平和性的人可称之为真实的。”[8]在此,他并没明确回答是否存在真实的自我,但他接下来的分析却试图表明,自传的目的在于达成自我的“流畅性与平和性”,以解决由于异化或压抑造成的自我的不真实。因为“逐渐成年是一个把自己丧失到角色中,丧失到一个人与人之间、政治、经济影响的复杂结构中的过程”,如果人不能发展一种基于自身生活史的批判性理解能力,那么就会“被尘封在一种线性—理性的模式里,不可能看到运动和再生的可能性”。[9]通过深入挖掘历史,我们获知自身身份的选择与排除机制;通过将我们目前之所是与所不是进行比较,从而为过渡到所不是的压抑部分打通了道路,摆脱了受困的困境,实现了“真实的自我”——“这种令人瞩目的现象足可以用‘解放’一词来表达。”[10]
而在福柯看来,与“所不是”部分的联合带有危险性和局限性,因为它所坚持的同它所反对的遵循同一逻辑:都将二元论中的一方升格为主导,另一方压制为附属;都承认我们的先验存在②主体先验存在论的一种形象表达即是(海德格尔意义上)“回家论”。王红宇认为,女性的旅途首先应该是一个向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失去了的声音和无形的东西的踪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回家的旅途,是为了归还被压制、被排斥、被异化的东西(Wang Hongyu.The Call from the Stranger on a Journey Home:curriculum in a third space.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4:5)。尽管笔者承认“向内的过程”的价值,但并不认为我们先验地存在着“失去了”的和待“归还”的东西,也并不认为有“家”可归。。主体压抑论者常常强调要通过确认被压抑的部分而解放主体,如“揭示教育经验中未被意识、处于压抑状态的部分……是要确认有哪些部分被压抑了,哪些没有被言说。当遭受压抑的部分逐渐显明,并且压抑的原因和方式明了的时候,人便能够清楚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只能通过回溯个人受教育的历史以及展望未来来实现。”[11]其实,主导与附属中的任一部分,都不比另一部分更为真实;我们的存在方式并不局限于在主导与“他者”之间进行二元选择的范围内。
与其确认被压抑或被异化的部分,不如关注主体的形成过程与方式,这不仅因为并非所有主体都是通过压抑而产生,还因为主体的形成过程是自我认识(包括自传方法)的核心任务。福柯式思维强调,任何本质性的或先验论的“自我”都不存在,个体是话语推论、权力生产与伦理建构的结果。[12]并不存在先验的或压抑的自我;如果存在“真实的自我”,那也只能是自我的历史的“真实”。自我的“真实”,表明我们“认识自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历史”的真实,则意味着我们的方法论必将是从儿童主体的“地方”(place)[13]出发,以一种个性化、情境性、具体性的方式去考察儿童。自传作为这样一种方法论,其目的显然不是揭示压抑部分以凸显先验存在,而在于揭示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和偶然性,并以此为基础去创造新的存在的可能性。
自传首要分析的,是由社会关系构成的儿童主体性的有意识或个体性部分,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其无意识内容或前个人性方面。主体性的个人特点与社会特点,意识领域与无意识领域之间的对立,在此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分析家庭与学校等这些形成儿童主体性的社会因素,考虑性别、政治、民族等话语对于儿童主体建构的内涵,揭示这些复杂的事实对于重构儿童主体性所具有的寓意,根本目标是要认识到:“我”被界定成什么样的人?“我”对这种界定该做出如何反应?
三、自传的过程:RPAS与谱系学分析
为了还原个体“所不是”的部分,派纳提出自传方法的四个步骤或环节,即回溯(re⁃gressive)、前进(progressive)、分析(analytical)、综合(synthetical)。回溯阶段,运用悬置和自由联想策略,遵循心理分析的技巧,回忆过去,扩展并转变我们的记忆。前进阶段,展望未来,期待现在尚未存在的,因为未来像过去一样,居住于现在之中。分析阶段,学生考察过去与现在,如现象学上的保持距离一样,一个人与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保持距离,从而给予现在更多的自由。综合阶段,我们重新进入现在。[14]
回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回答“我是谁”、是什么促成了现在的我之类的问题。派纳发展的悬置和自由联想两种方法就是致力于从内部深层次地理解构成个体的经验。何谓过去的经验?派纳认为,回溯是“对描述即时的、前概念的体验感兴趣,然后运用‘距离化’和‘悬置’的现象学过程去进行描述。”[15]“即时的、前概念的体验”是现象学术语,这种体验如果能为个体“去进行描述”,就已经说明它不是“前概念”性质。同时,对能够“描述”出的“前概念的体验感兴趣”,本身说明对一种先验状态的迷恋。
与派纳的认识不同,福柯认为回溯的意义并不在于去揭示主体的某种先验状态,而在于对形成主体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历史经验本身或许包括派纳意义上的“前概念体验”(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但前者包涉的内容远比后者广泛和深刻。对回溯目的定位不同,相应的悬置和自由联想策略的作用和意义也将发生改变。
单就悬置而言,其作用是先暂时性摆脱想当然的儿童身份及相关的概念世界,用一种反思的方法来探究蕴涵在儿童教育经验中的意义。在保守的学校情境中,儿童(包括家长和教师也类似)非常容易认同他们的角色,接受当时的教育专家所提供的解释,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外部的对于自身的论述话语中,尤其是在家长的配合下,儿童成为既定理论的忠实实践者,而很少能够倾听自己内部的声音,反思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别人论述中的我。儿童所遇到的这种情况,派纳称之为“压制、潜意识、角色认同的行为,理智和心理的被捕。”因此,儿童的多数反应是习惯性的,儿童“活生生的经验”就成为“习惯”的附属品和支配的对象。悬置,就是打破这种附属和支配的情形,它让儿童暂时逃离公共的“习惯”,在“活生生的经验”的刺激下,并开始追问公共“习惯”形成的过程和原因。
假设在20世纪初期,接受霍尔的发展阶段论的儿童,很可能按照各个阶段的特征对照和比较自己,观察自己的发展现实是否和阶段论特征相一致。如果二者类似,他们才会安心,因为自己的发展符合科学研究的结论,表明自己的生物学特征在复演种族特征方面的成功。在此过程中,派纳认为,儿童丢掉了自己的内心体验,压抑了自己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可能异于霍尔发展阶段论的“活生生的经验”。而学会使用悬置方法的儿童,并不会削足适履式地与公共的“习惯”——霍尔的发展阶段论——去匹配与比照,而是先将阶段论置于一旁,寻找自己在不自觉地匹配与对照过程中所压抑掉的与阶段论不一致的特征——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对其进行研究,从而解放了“真实的自我”。
但运用福柯式思维的儿童可能会向内求索被压抑掉的东西,但更倾向于思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霍尔及其阶段论思想,并用这种思想来表征我的发展过程?他提出这种思想的背景是什么,我是这种背景中的因素吗?有没有其他的理论也是来描述我的发展?这两种或多种理论之间矛盾吗?在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后,福柯式思维的儿童将会得出这种结论:霍尔原是位代言人,他的发展阶段论只不过间接地影射着种族发展论和种族至上主义[17]。作为个体的我,只不过是这一思想的承载点和媒介,我没有必要完全依据这一理论去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为了兼听则明,我还要思考一下桑代克关于我们发展的理论,因为至少它构成了对霍尔发展论的挑战。正如我不会完全信服霍尔的理论一样,我也不可能完全采纳桑代克的理论。事实上,最妥当的做法是,在理解这矛盾性的理论之上,我要去反思作为个体的我的发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幸运的是,他们的理论为我打开了两扇窗户,但从哪个角度观看,最终还是取决于我自己。
福柯式儿童的上述独白,就体现了自传中“悬置”技术的应用方式。儿童将凝视对准于自己的内部经验,“把反思性注意的目光投注到己经成为过去的经验整体的某一部分上……自我经过这种凝视或者反思性注意,便通过意向性运作把意义创造出来;因此,意义存在于自我对其意识流之某一部分所持的态度之中,各种特殊经验的意义都是由相应的注意活动构造的。”[18]意向性运作,即是悬置的根本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重新审视过去的经验对于当前主体身份的建构意义,主体需要在理解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表明自己对经验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者说主体新的自我意识,才是自传的核心目的,因为它是在重新评估建构自我的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它的诞生,标志着儿童主体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觉。不管是积极地接受目前的自己(强化当前身份)、默认目前的身份,还是要拒斥当前的身份,这一意义统一体至少让儿童在这三者之间初步具备了自我选择能力。
四、自传的结果:“真实的自我”与历史偶然性
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自我”及“真实的自我”的特征,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派纳认为,通过自传,我们能够挖掘被压抑的部分(被塑造部分的对立面)和无意识材料(通过梦、幻想等),并能够将此“出身”与当前现状以及未来整合起来——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回家”,“回家”的过程能够解决自我的真实性问题。通过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及悬置自然主义态度,主体能够发现自我的“真实声音”,能够在心理上进行政治和文化批判,这一过程具有政治以及认识论与教育学的意义。派纳说“自传是一种致力于把人从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即自传)能够帮助融化,如果你愿意,理智的受阻碍或僵化的区域,并允许理智的运动……这个运动发生在个体生活史的情境中;当它发生的时候它就是教育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研究课程在教育经验中的作用[19]。通过自传,个体自身就可以检视自己在社会政治生活的种种弊端中的共谋角色;借助自传,实现理智在受阻或僵化区域之间的流动,自我就可以“回家”。
对于福柯来说,并没有一个可以返回的家。他认为,重构自我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于排除与压抑之境内,因为这种做法仍然遵循二元论思维,只不过变换了侧重的方面。本质上,二元论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比另一方更为真实或符合人性。没有可以返回的家,根源在于并不存在先验意义上的“真实的自我”。福柯研究了主体在机构中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监狱、精神病院以及学校,在生产出正常人的同时,扼杀了其他的非正常的人。[20]但是,这两种类型的人在福柯看来,都不能代表“真实的自我”,所以,它也不可能为机构的“规训”与“惩罚”方式所遮盖与歪曲。相反,权力能够压抑与遮盖主体—权力的生产方式,但其主要功能还是生产主体,生产现实与真理机制。主体是由机构生产出来的,尽管是以非正常人的出现为代价。
不存在“真实的自我”,也就不存在“可以返回的家”。如果说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回家”能够找到最真实的自我;那么,对于福柯而言,唯有通过流浪才能体会到最真实的存在。“一个人所曾经成为的与现在正是的个人总是‘包含’着他所没有成为的与现在不是的成分。一个人曾被拒绝与压制的方面,与其自觉接受与整合的方面对界定或可能界定自我发挥着同样彻底的作用。”[21]这是心理分析的基本逻辑。对于福柯而言,建构新的自我可能也需要通过与边缘化群体相认同而得到解决,即所谓的疯人、穷困的人——各种处境不利的群体—这是心理分析的出发点和核心假设,但却不是福柯建构意义的全部内容,因为在他看来,相对于拒绝与压制来说,权力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其生产性,而权力的生产并不指向于先验的人性的丰盈与完善,而是将个体的生产力与自己的目标相匹配。
在福柯看来,我们迫切需要做的,莫过于认识自我,揭示自我建构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在由谱系学理解所开创的空地上,个体自主地选择与创造新的生存方式。在这方面,派纳的自传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自我的很好范例,但福柯式思维需要对其核心假设进行修正,因为我们能够重新找回我们自己分离的碎片……并重新合并他们;但在找回分离的碎片时,切不可只留恋于被抑制的一方,否则就将继续陷入一元论思维之中。正确的态度是,利用并超越“被抑制”的“他者”,甚至是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最大程度上扩展主体性的社会方面,形成世界性的主体性(cosmopolitan subjectivity)。而自传既揭示了主体性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两方面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也为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
五、结语
从派纳当前的思想来看,之前他的“是否存在真实的自我”这一提问略显蹊跷。这种思路主要受到福柯前期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疯狂与文明》中关于边缘群体的成因分析,尽管对福柯的这种理解存在着偏颇)。区别于政治压抑性的自我概念,派纳近年来更倾向于分析世间性(worldliness)的或世界主义的(cosmopolitanism)主体性[13]。这种思路与最近出版的福柯后期作品的思想相一致,即权力不仅具有压抑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生产性功能。“真实的自我”尽管存在,但是历史性的,它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化中。据此推测,派纳可能会将上述问题改为: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自我”?
要回答这一问题,在于正确处理权力塑造的身份和自我描述的身份之间的关系。前者可以成为我们批判的标签;进而依据自身对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尽力地去形成自我,塑造社会可接纳的主体性风格。这种自我指涉的能力,让主体有可能在两个自我之间建立一定的距离,即反思的(或“我的”)自我与权力建构的自我(尽管是根本性的)。这体现了福柯在思想的前、后期对于“主体”这一术语所分析的理论范式发生的转变。早期倾向于真理主体与权力主体,而后期则倾向于我的主体(或伦理主体)。与许多福柯研究者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并不能说福柯早期的分析模型没有涉及主体的问题,只是侧重于主体的方面不同。福柯理论范式发生的转变,不是从忽视主体转到面对主体,而是从集中论述强加于主体的外部因素,转到同时考虑个体在权力运行中的关键缓冲点的角色。[22]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研究转向,它为分析主体化过程,为重构个体主体性,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