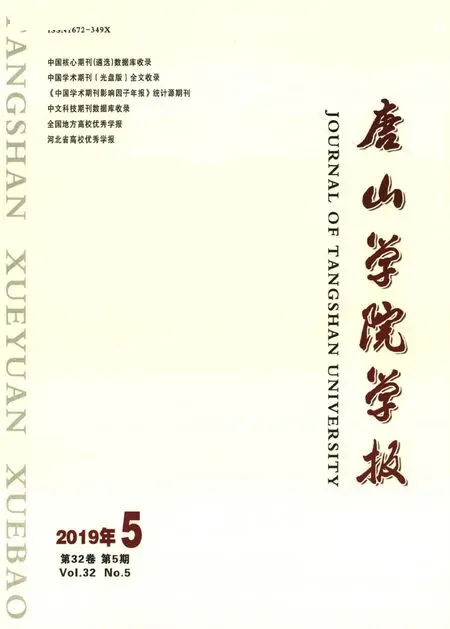手枪:词与物交织的文本实验
——欧阳江河名诗《手枪》解读
2019-01-20毛靖宇
毛靖宇,陈 婉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旅游分院,浙江 义乌 322000)
一、词与物之辨
《手枪》[1]一诗是著名诗人欧阳江河久享盛名的名作、佳作,同时它也是一首语言诗学的实验之作,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先锋实验运动,今天的人们往往倾向于作出较低的评价。事实上,从《手枪》一诗丰富深刻的内涵,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验诗人在当时就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起点。
这是一首很短的精致的诗,但同时也是一首难懂的诗。尽管前人对它的关注甚多,但笔者仍然认为其谈论过于零碎,而且在文本本身的解读上,尚不够完整深入。
这首诗为什么难懂呢?艾青、穆旦、卞之琳,他们的诗不会让人觉得难懂,或者,他们的诗的难懂和《手枪》的难懂不是同一种性质。比如说在艾青的诗里,礁石就是礁石、太阳就是太阳、手枪就是手枪,虽然这些东西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解。而在欧氏诗歌中,手枪可以拆开,这个好理解,但是为什么又拆成两个党,这就很令人费解。对此相关的评论很多,都指出这是手枪的政治隐喻,或是词与物的对应关系等。然而这些评论大多没有落实到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层面,虽有洞见,不免浮光掠影。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写的艺术内涵在哪?对于这些基础性问题,却没能提供多少参考。因此,读者看了这些解释,往往还是困惑不解。
事实上欧阳江河的诗与艾青等人的诗,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写作。他们的不同,根本上在于对词语意义理解的不同。欧氏诗歌中的手枪,当然可以指一种武器,但又不仅仅是一种武器。这其实涉及到欧氏诗学中最重要的一些思想,比如一些概念对:现实与虚构以及词与物等。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的解读中,欧氏诗中的落日就是落日、草莓就是草莓、女儿就是女儿,如此等等。
《词与物》是著名法国学者福柯的名著,福柯的名声可能对“词与物”这对概念在当代诗学界的走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欧氏的《手枪》写于1985年,而福柯作品的汉译本,应该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出现。就算当时像欧氏这样的少数人能从某种渠道看到1966年首版的法文原著,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欧氏诗学中词与物的概念不是来自于福柯,而是来自于作为福柯思想源头之一的索绪尔语言学。
索绪尔将词语分为能指与所指两部分,这一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为人熟知,但是我们也许难以想象像欧阳江河这样的诗人有如此巨大的理论创造力。笔者相信欧氏正是接触了这个有关能指与所指的理论,才发展出了他后来为人熟知的现实与虚构、词与物等诗学理论。
索绪尔的理论的确是石破天惊的、天才的,值得高度评价。正如笔者在其博士论文[2]中所指出的,在索绪尔之前,人们普遍持有的是一种指称论的语言观念:词语指称某物,而它本身隐而不显。但是索绪尔揭示了语言的秘密,他指出了真正科学的语言学洞察:词语分为能指和所指两部分,那个以前被人们忽略的、透明的能指现身了,语言“说话”了。
这样的洞见对欧氏诗学的探索应该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读者来说,缺乏这样的洞见,也就很难进入欧氏的诗歌世界。事实上,欧氏的诗不能按照寻常的思路来解读。在笔者看来,欧氏的诗歌正是在现实与虚构、词与物的交织之间发生的。欧氏诗中的每个词语,有时是所指,有时是能指,有时是现实,有时是虚构,有时是词,有时是物,产生了一种扑朔迷离、令人目眩的艺术效果。很多读者可能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上出现过一种叫做“立体画”的艺术品。对于这种画,你从上面观看到的图景与你的眼球聚焦点有关。当你调整眼球的聚焦点的时候,会从图片上看到不同的具有立体效应的图像效果。欧氏诗歌就是这样一种立体画,是一种多层面、多维度交织缠绕的文本织物。比如《手枪》这首诗,我们将会看到,它有时的确是指一种便携式武器,有时又是以一个词的面目出现。至于它到底什么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不是什么,这个并没有现成的规律可循,而是完全取决于诗歌文本织就的语境。
二、手枪:物性与诗性
综上所论,欧氏的写作是在词与物的界面上进行的,是在现实与虚构的界面上进行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欧氏的诗歌是脱离现实的。相反,欧氏的很多诗歌都是立足现实、从现实出发的。回到对《手枪》一诗的解读,我们就要先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是手枪?的确,在这首诗的一开始,我们的确是将手枪理解为一个物,一种现代武器。可见这首诗是从这种作为物的手枪开始的。但是为什么一首诗从一把手枪开始?难道手枪有什么诗意、诗性吗?
这个问题其实暗含了欧氏研究中两个重要的主题:物性与诗性。在这里我们对这两个主题进行集中并置的研讨。这两个主题是对欧氏诗学探索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关注面,是欧氏所有诗歌写作实践的出发点。具体来说,欧氏本人对诗歌历史的判断、对诗人身份的定位、对诗歌写作的定性,显然是和汪国真这样的诗人,乃至艾青、穆旦、卞之琳这些诗歌史上鼎鼎有名的大诗人,都是有所不同的。
很显然,欧氏不是一个随便写几行就当作是诗去投稿发表的诗人。笔者相信在他的诗歌生涯伊始,首先就有一个身份定位问题。他首先是将自己作为一个现代诗人来定位的。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当然要写现代人在现代世界的感受和经验,这是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应有之义。但是欧氏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对构成现代诗人写作资源之一的古典诗歌传统、对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个传统的现代汉语,抱着现象学悬置式的怀疑态度的。欧氏多次在不同地方强调过,古典诗歌传统是与一种农耕文明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今天,这种农耕文明已经遭到破坏了,被一种工业文明取代了。因此,那样一种写作也就不复有效了。
这样,欧氏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实验运动中,采取了一种相当激进的诗学立场。但实际上这种立场和当时一种空洞的“反传统”的“pass朦胧诗”之类的立场相比,却保守得多。对于欧氏而言,他不满足于像一些现代诗人那样采取对传统诗意、传统资源“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创新模式,而是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宽广的传统诗学中认为是非诗意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整个非诗意的现代社会现实,而其中一个最集中的区块就是物质性。现代社会的最显眼的特征不就是物质性吗?就这样,在传统诗学中处于对立两端的物质性与诗性,在欧氏诗学中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联姻。
手枪作为一种现代的物,它具有坚硬、暴力、可射击、可拆卸等物质性。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些物质性在诗中是如何表现的。
(1)手枪是钢铁制作的,坚硬方正,短小便携,而这些也正是《手枪》这首诗的特征。这首诗用汉字写成,汉字是方块字,它们的外形在本诗中具有手枪的整齐方正,短小精悍,它们的读音在本诗中具有钢铁的坚硬与射击的短促有力。
(2)手枪是一种现代器械,具有可拆卸、拼装的特征。这一点被欧氏充分利用,在诗中重复地写到了“拆”。欧氏对手枪拆装以及射击的兴趣,让我们想到了他长达十年的职业军人经历。毫无疑问,他对枪应该非常熟悉。即使是我们这样没有摸过枪的人,也可以从影视作品中得到一些对枪的了解。笔者就对影视作品中那种子弹上膛、拉栓,当然还有射击,所发出的整齐、干脆的声音特别着迷。而本诗第一段“手枪可以拆开/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一件是手,一件是枪/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手涂黑可以成为另一个党”,具有枪支拆装的声音与节奏,其中“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中的“变长”,让人想到拉动枪栓使枪管变长的动态与节奏。
(3)手枪的瞄准。开枪射击的时候需要瞄准,瞄准的时候挤眉弄眼,样子非常滑稽可笑。笔者记得中学军训的时候,那些女生看到教官眯眼示范射击的动作就忍不住偷笑。本诗中也有对瞄准的描写:“眼睛压进枪膛”“子弹眉来眼去”,等等,给诗歌增添了几分别样的幽默风味。
(4)手枪可以射击,而射击体现了一种对外在世界、事物的远距离操控。神枪手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目标应声而倒,效如桴鼓,达到这样高超的射击技艺,似乎在枪手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逻辑关系。诗歌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短平快的、肯定的因果逻辑关系,比如“一个人朝东方开枪/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
(5)手枪对世界的控制,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因此手枪也与政治及暴力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从诗歌中看出来,而且以前的研究者也谈得较多,这里就不更多赘述了。
以上列举的这些手枪的物质性,在传统诗学中显然是没什么诗意而言的。但是欧氏偏就将这些毫无诗意的内容写进诗里,使它们具有丰富、深刻的现代诗意。欧氏处理这些物质性所使用的艺术手法,也完全是他独立的自创,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称之为“仿型”[3]94。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仿型,不但可以仿外形,还可以仿声音、动态、质地。而且早在写《手枪》的1985年,他的这种艺术手法就已经运用得相当醇熟了。
三、《手枪》文本通读
以上两部分的分析,揭示了欧氏诗歌两个方面的特征,这两个方面在诗中相互纠缠,令人目眩神迷,使得阅读欧氏的诗歌文本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既是一种艰难的历险,也是一次有趣的旅行。下面我们对《手枪》进行一次通读。这里所说的通读并非细读,因为这首诗歌虽然本身并不长,但是其文本含义盘根错节,头绪繁多,想要在细读的思路下字字解析,条条理顺,显然并非易事。所谓通读则是一种解读的策略,它放过了细读要求的滴水不漏的严谨,仅在整体上对全篇含义有个大致的梳理。事实上,本论文前面两个部分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对本诗部分内容的解读,为进一步的解读提供了必要的铺垫。而在下文中我们将要获得的是在前面理解的基础上对该诗的整体性概观。这首诗全诗如下:
手 枪
手枪可以拆开
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
一件是手,一件是枪
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
手涂黑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党
而东西本身可以再拆
直到成为相反的向度
世界在无穷的拆字法中分离
人用一只眼睛寻找爱情
另一只眼睛压进枪膛
子弹眉来眼去
鼻子对准敌人的客厅
政治向左倾斜
一个人朝东方开枪
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
黑手党戴上白手套
长枪党改用短枪
永远的维纳斯站在石头里
她的手拒绝了人类
从她的胸脯里拉出两只抽屉
里面有两粒子弹,一支枪
要扣响时成为玩具
谋杀,一次哑火
从整体来看,该诗一共才四个小节。这四个小节之间构成一种松散的转喻关系。这种转喻关系在欧氏另一首诗中也有体现:(警车快得像刽子手)/快追上子弹时转入一个逆喻[4]。简单来说,第一节、第二节之间关系密切些,都是围绕“拆”字展开的,因这个“拆”字引出“东西”一词,这个词同时也是第三节的关键词,只不过在第三节中被“拆”开了:“一个人在东方开枪/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在第四节中,诗转入逆喻:手枪成为玩具,谋杀成为哑火。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在这里一开篇就提到“拆”,这种可拆性是手枪的一个重要物性,对“拆”的谈论成为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在阅读本诗的前两句“手枪可以拆开/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这时我们以为诗歌写的就是作为物的手枪,然后通常的阅读经验引领我们产生了某种阅读期待。但是读到后面三句,我们不禁困惑不解,习惯中的阅读期待全部落空了。事实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物的手枪与作为词的手枪被混在了一起,在诗行的展开中偷偷地完成了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过渡。最后,“手枪”成为一种亦真亦幻、亦词亦物的双关之物,产生的是一种虚实相间、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表达效果。
这种词的手枪与物的手枪的并置,体现了一种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一种以前人们没有玩过的语言游戏,是一种全新的写作实验。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物的手枪的可拆性与作为词的拆字法,单独看来都是一种显而易见同时也是没有什么诗性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熟知这样的事实,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诗意并进而发展出了一条诗学探索的新路径。作为诗歌的批评者,笔者缺少一种原创的能力创造这种诗意,但却能通过解读分析出这种诗意。笔者认为这种诗意产生于两种异质事物的并置,这种并置用欧氏后来使用的概念来说那就是“反词”[3]19。这是一种与传统古典诗意不同的具有异质混成性质的诗意。在目前我们讨论的物的手枪与词的手枪之可拆性的并置中,可以发现在其中包含了维特根斯坦的世界与命题相对应的哲学思想;包含了一个职业军人对手枪的熟悉与迷恋;包含了一个汉语诗人对汉语的熟悉与迷恋;包含了一个现代人对物质、重量、线条、节奏等感觉材料的现代体验……总之,在此前,还没有人这么写诗。而在此后,欧氏在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诗学理论文章中所阐述的,事实上正是这种诗学思想。
另外,在第一节中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它暗含了物的手枪的另一个功能:瞄准,而这个瞄准的功能进一步衍生出另外的诗行。比如,在第一节中最后两句“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手涂黑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党”,这两句诗中的两个“党”字,处于诗行的最末端,从手枪仿型的意义来看,就像枪管远端处的准星。而这个准星就跳过第二节使诗行延伸到第三节:
人用一只眼睛寻找爱情
另一只眼睛压进枪膛
子弹眉来眼去
鼻子对准敌人的客厅
政治向左倾斜
一个人朝东方开枪
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
在这第三节中,一开始说的是“人”,似乎从诗歌“手枪”的话题上岔开去了,但实际上这一节说的还是枪。准确地说,这一节说的是人是怎么使用枪来瞄准与射击的。诗中将人的一双眼睛一分为二,一只眼睛寻求爱情,一只眼睛压进枪膛。这让我们联想到瞄准的动作,我们瞄准的时候正是睁着一只眼睛看目标,闭着一只眼睛好像它被压进了枪膛。而后面一句“子弹眉来眼去”写的是射击,更让这种形象化的描写产生了一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效果;但接下来一句“一个人朝东方开枪/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前一句是因,是瞄准,后一句是果,是射击,两个句子之间有一种立竿见影的逻辑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枪的黑色幽默:一种看起来滑稽可笑的瞄准动作,却产生了残酷无情的暴力结果。
这种黑色幽默的反讽,看起来仅仅是诗歌字面意义对比的结果,没有什么深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诗歌让我们看到这种反讽在词与物的层面都有其根源。这个根源就是“东西”。“东西”是本诗中另一个关键词,它在诗中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说:“手枪可以拆开/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读到这里我们当然将这个“东西”理解为:某种东西、某种事物。但事实上“东西”在这里是“手枪”的同位语。如果说“手枪”存在着偷偷的置换与过渡,存在着亦词亦物、亦真亦幻的双关性的话,那么“东西”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当这个词在第二节中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它的另一个层面的含义得到了强调,这个时候“东西”成为“东”和“西”两种相反向度的组合,并且这种组合甚至获得了世界的存在论意义上的高度:“东西本身可以再拆/直到成为相反的向度/世界在无穷的拆字法中分离。”这几句诗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世界就是由像“东西”一样内在地包含着“东”“西”的矛盾(相反向度)的东西构成的。而当这个“东西”在第三节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它已经从第二节的哲学层面转移到了本节的政治层面,以“一个人朝东方开枪/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的形象直观地阐述了第二节中的有关“东西”的哲学领悟。
这种有关“东西”的哲学领悟,与上文提到的欧氏的“反词”思想也是一致的,它也构成了欧氏诗歌结构的一个深层基础。在接下来的第四节中,维纳斯的出现正是构成了手枪的反词。如果说美神维纳斯代表的是艺术、美与和平的话,那么手枪则代表了暴力、丑恶与战争,这一节中两者的并置,体现了欧氏相当深刻独到的见解。首先,诗中写道:“永远的维纳斯站在石头里/她的手拒绝了人类。”这里表达了一种通常的反战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手”很有意思。米洛的维纳斯的断臂,被说成是对好战的人类的拒绝,也暗含了对战争工具“手枪”的瓦解。这种通过改变语言从而改变世界的操作,也许正是早期“非非”语言革命的一个片段。不过,接下来的诗句则改变了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诗思引向更为深刻的维度,其思想的基础仍然是上述的“反词”哲学。诗中“从她的胸脯拉出两只抽屉”,这实际上影射的是超现实主义者达利的画。达利画过很多胸脯中拉出抽屉的女人像,这种画法本身就是一个容易产生多种阐释的艺术创新,欧氏对这个意象的引用是否符合达利的本意,这个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时候这个意象已经受到了欧氏诗歌语境的限定与改写。根据本诗的语境,笔者解读这个带抽屉的维纳斯具有如下几层含义。第一,抽屉的几何形状与手枪相似,都是一种现代的、方正的几何形体,而与维纳斯乳房的圆形形成对立。这种对立反映的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对立,也反映了欧氏诗学中传统诗美与现代诗美的对立。第二,从维纳斯的胸脯中拉出抽屉,而抽屉里面取出来的是作为谋杀工具的枪和子弹。这个意象是达利原画所无,是对达利原画的创造性延伸(笔者见闻有限,没有见过达利画中有类似意象)。在这里美神与手枪的并置被换了个方向,手枪代表的暴力又变成是美的结果。这种思想和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不无相通之处,它们都是触及了世界与事物内部的深层逻辑:对美的追求,走上了暴力争夺的反面。第三,诗歌最后指出这支枪只是一种“玩具”,谋杀只是一次“哑火”。这种处理实际上又将诗歌的所指带回了诗歌文本自身,也就是说,诗歌这里谈论的还是诗歌写作这件事本身。诗人认为这种写作创造了真实感的幻觉,但毕竟和真实的世界不同。因此,就算是诗歌中的手枪,也和真实的手枪不同。但是,诗人费尽心思想要写出的不正是一把尽量逼真、让人难以分辨的手枪吗?因此,这里诗歌在结尾处的处理,实际上有一种魔术师自揭谜底的作用。这种自揭谜底非但没有降低诗歌的魅力,相反却为读者对诗歌的赏析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参照层次。
四、结语
欧阳江河是当代著名诗人,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登上诗坛,至今已有四十余年诗龄,特别是最近几年,更是频频推出新作。相比于欧氏的丰产,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却要滞后得多。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在诗歌研究领域,对欧阳江河的研究目前集中于诗歌文本阐释和诗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一方面,诗歌文本的阐释主要包括对具体文本的细读,……由于欧阳江河诗歌技巧的繁复和思辨的复杂,提升了他诗歌阅读和研究的难度,所以对其作品分析的成果并不占很大的数量,……另一方面,对欧阳江河的诗学理论进行研究,和对其整体风格进行论述的成果更为重要,但也更为缺乏。”[5]
笔者认为,欧阳江河诗歌是世界现代艺术运动的产物,也是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它虽然在很多方面与传统新诗写作有所不同,但绝非一些没有下过功夫研究的人所批评的那样是故弄玄虚、病句体、唯脑论写作之类的。笔者深知欧阳江河诗歌研究是个全方面、整体性的工作,绝非旦夕之间即可奏功。在此,选择欧氏早期成名之作《手枪》作为谈论对象,指出了它立体画般迷人的艺术魅力,也指出了它在短短的诗行中所蕴含的丰富意蕴以及深刻哲理。尽管如此,由于诗歌写作性质的某种变化,笔者并不奢望在一篇单篇文章中“一口吸尽西江水”,完满地处理所有问题。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本意,仅在于管窥一斑、抛砖引玉,保持充分的开放性,引起学界对欧阳江河诗歌的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