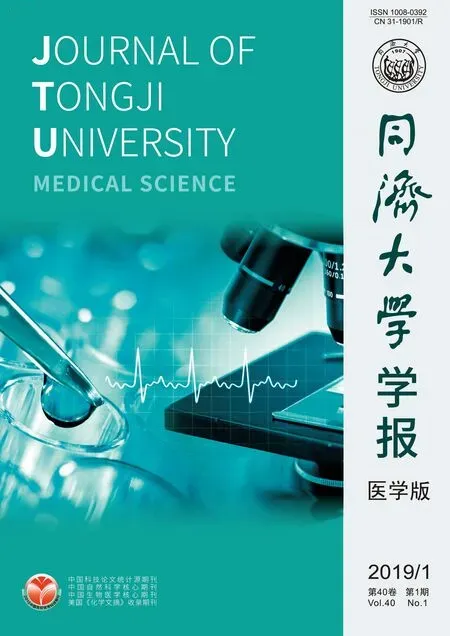肺动脉高压诊治现状
2019-01-19刘锦铭
刘锦铭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肺循环科,上海 200433)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是一类常见肺血管疾病,其主要病理生理学特征是静息状态下肺动脉压力升高,合并不同程度右心功能衰竭。PH指各种原因导致的肺动脉压力升高,包括毛细血管前性PH、毛细血管后性PH和混合性PH(肺动脉和肺静脉压力均升高)。PH血流动力学诊断标准为: 海平面状态下,静息时右心导管测量肺动脉平均压(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mPAP)≥25mmHg(1mmHg=0.133kPa)。正常人mPAP为(14±3) mmHg,上限为20mmHg。毛细血管前PH的血流动力学诊断标准为mPAP≥25mmHg,同时肺小动脉楔压(pulmonary artery wedge pressure, PAWP)≤15mmHg及肺血管阻力>3 Wood单位。毛细血管后PH的血流动力学诊断标准为mPAP≥25mmHg,PAWP>15mmHg。2018年2月在法国尼斯召开的第6届世界PH会议再次更新了PH的临床分类,其中第一大类PH通常也被称为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PAH),与左心疾病所致PH、呼吸疾病和/或缺氧所致PH、肺动脉阻塞性疾病所致PH和未知因素所致PH构成了目前PH的临床分类。
德国医师Ernstvon Romberg报道了首例PH病例,在尸检时因无法解释此种肺血管病变,故将其命名为“肺血管硬化”。20世纪40年代,Cournard用心导管直接测量肺动脉压力,人们开始从血流动力学角度认识PH。此后,Dresdale首次报道了1例原因不明的PH患者,并将其命名为原发性肺动脉高压(primary pulmonary hypertension, PPH)。20世纪60年代因减肥药阿米雷司在欧洲引起PH大流行,这引起了整个欧洲医学界乃至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在阿米雷司事件的促使下,世界卫生组织于1973年在日内瓦举行首届WHO会议成立肺动脉高压专家组,制定PH的病因及病理命名。欧美十几位权威专家在第1届PH会议上,将PH分为原发性PH和继发性PH两大类。此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血液研究所(NIH)启动了全美多中心PPH注册登记研究。自1998年第2次世界PH会议首次将PH临床诊断划分为五大类,虽然每年在不断更新,但始终延续既往五大类分类原则。第一大类PAH;第二大类左心疾病相关PH;第三大类呼吸系统疾病和/或缺氧所致PH;第四大类肺动脉阻塞性疾病所致PH以及第五大类未知因素所致PH。其中第一大类PAH也是临床最需要使用靶向药物治疗的类型,又细分为特发性PAH、遗传性PAH、药物和毒物相关PAH、相关因素所致PAH(其中以结缔组织疾病、先天性心脏病、门脉高压为主)、肺静脉闭塞病/肺毛细血管瘤、新生儿持续性PH[1]。
PAH的发生发展过程与肺血管结构和/或功能异常(即肺血管重构)密切相关。肺血管床内膜损伤、中层肥厚、外膜增殖/纤维化导致肺动脉管腔进行性狭窄、闭塞,肺血管阻力不断升高,进而导致右心功能衰竭甚至死亡。其中PAH主要累及直径<500μm的肺小动脉,特征性病理改变包括肺动脉中膜肥厚、内膜向心性或偏心性增殖和纤维化、外膜增厚纤维化、血管周围炎症细胞浸润及管腔内原位血栓形成等,严重患者可见复合病变,如丛样病变、扩张型病变等。但PAH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现认为,肺血管重构是遗传因素、表观遗传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种血管活性分子、多种离子通道、多条信号通路在肺血管重构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2]。
目前超声心动图是疑诊PH时一线无创诊断方法,但右心导管检查是确诊PH的“金标准”,也是进行鉴别诊断、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建议对疑诊PH的患者首先考虑常见疾病如第二大类的左心疾病和第三大类的呼吸系统疾病,然后考虑慢性血栓栓塞性PH(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CTEPH),最后考虑PAH和未知因素所致。对疑诊PAH的患者应考虑相关疾病或危险因素所致,仔细查找有无家族史、先天性心脏病、结缔组织病、HIV感染、门脉高压、与肺动脉高压有关的药物服用史和毒物接触史等。
PAH的药物治疗进展近几年也是突飞猛进。1995年之前的年代称为PAH传统治疗时代,临床医生用传统药物例如洋地黄、利尿补钾药物、降压药治疗PH,死亡率极高。1987年和1991年NIH分别发表了该注册登记研究的基线资料和患者预后。PPH发病率为1~2/百万,中位生存时间为2.8年,预后差,死亡率高。1995年欧美等国批准注射依前列醇上市,正式拉开了PAH靶向治疗时代的帷幕。随着PH研究机制的进展,不同作用途径的靶向药物陆续上市,肺动脉高压治疗进入了口服、吸入、皮下注射和静脉滴注等多元化治疗时代,PAH患者预后因此也得以逐渐改善[3-4]。
目前PAH靶向治疗药物主要有三大经典途径,包括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波生坦、安立生坦和马昔腾坦)、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西地那非、他达拉非和伐地那非)以及前列环素类药物(依前列醇、伊洛前列素、曲前列尼尔和贝前列素),广泛应用于第一类PAH,显著改善了患者预后。其他类型PH的治疗除了充分治疗原发疾病,部分临床表型也需要PAH靶向药物治疗。此外,新型药物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利奥西呱已在国内上市,是目前唯一具备PAH和CTEPH双适应证的靶向药物,且在既往临床试验中表现出令人鼓舞的治疗效果。口服选择性前列环素受体激动剂司来帕格即将上市。这些新型药物的问世为PH患者的治疗带来更多的选择和希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大类即CTEPH的治疗在近几年有很大的进展,该类型也是目前唯一可能治愈的PH。对所有确诊CTEPH患者首先进行肺动脉内膜剥脱术可能性评估,肺动脉内膜剥脱术适用于血栓位于主干或肺动脉近端分支的患者,通过手术治疗甚至可以达到治愈。目前国内已有多家中心可行此项手术。此外,日本学者将改良经皮肺动脉球囊扩张术(balloon pulmonary angioplasty, BPA)治疗慢性血栓栓塞性PH推向全世界,目前全国多家医学中心开展了经皮肺动脉球囊扩张术治疗CTEPH,对于无法手术的患者有了更多选择[5-6]。临床实践观察CTEPH患者经BPA治疗后其血流动力学、右心功能等显著改善,疗效有时优于口服PAH的靶向药物。
治疗的快速进步推动了第2、3、4、5、6届世界PH大会于召开,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的概念被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取代,PH分类进一步细化,新药治疗策略及PAH危险度分级不断完善,对我国肺动脉高压的筛查、诊断与治疗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对规范临床医生的诊疗行为、提高我国肺动脉高压临床诊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美国胸科医师学院在其官方杂志Chest上发表了全球第1个PH临床指南,2004年我国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发表了PH现代分类最早的中文版本。2007年3月Chest在线发表了历史上第1个中国肺动脉高压注册登记研究,该研究表明2007年之前中国肺动脉高压5年生存率仅为20%左右[7]。2006年波生坦和伊洛前列素在中国相继上市,西地那非和伐地那非治疗肺动脉高压的临床研究也开始启动,标志着中国进入靶向药物治疗时代[8-10]。2007版肺动脉高压筛查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的发表积极推动了PAH临床规范化工作。从2007年全国只有一两家肺血管疾病专科诊治中心,至今11年来,陆续发展成为数十家肺动脉高压专科临床诊治中心,越来越多的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风湿免疫内科、心血管外科以及儿科医生投入到肺血管疾病的诊治工作中,肺血管疾病专科医师和医疗中心得到蓬勃发展。
这期间国内外PH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学术研究的发表,不断更新对PH的认识。从流行病学、诊断分类,到新的致肺动脉高压药物的发现、遗传基因突变以及诊断标准,旧的知识体系正在接受更多的挑战,新的理念正在更新。从10年前的单药治疗,到序贯联合治疗策略(初始治疗单药病情加重后加用其他途径的靶向药物),目前初始联合治疗策略(即采用两种或三种不同途径的靶向药物)已越来越被临床医生推崇,对于PAH这种明确有多个致病通路的疾病,理论上联合治疗较单药治疗效果更好。AMBITION研究以及其他联合治疗关键研究陆续发表,使PAH早期干预、危险分层以及初始联合治疗等策略逐渐得到公认[11],联合治疗地位逐渐增高。2018年第6届世界肺高压大会建议将危险分层为中危或高危的患者均推荐联合治,序贯联合治疗和起始联合治疗均可显著减少PAH患者临床恶化事件[12]。
迄今为止,2018年第6届全球PH大会汇总,目前已有70多种化合物正用于肺动脉高压药物研制的临床实验中。肺动脉高压靶向药物及治疗等飞跃发展,促进中国大量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学术会议的广泛推广及普及,促进越来越多不同专业医生投入到肺血管疾病的诊治、研究工作中,推动中国在PH领域逐渐进入群雄并起局面。我国肺血管疾病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并以此推动了《中国肺高血压诊断和治疗指南2018》问世。与2007年版中国专家共识31篇文献中仅有4篇中国文献相比,本次更新的指南共引用的186篇文献中有61篇来自中国自己的研究,反映了我国PH诊治经近10年的飞速发展,逐步赶上世界的脚步。
尽管中国肺血管疾病领域蓬勃发展,但我们也深刻意识到目前有大量工作亟需解决,例如“孤儿药”的医保问题,中国PAH创新药物研发,PAH科普工作等等。期待未来不久,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