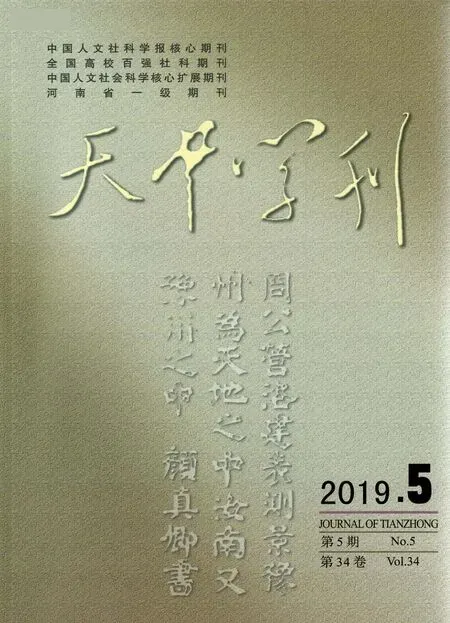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中的古典小说研究
2019-01-18赵东旭
赵东旭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出现较晚,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通史,是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Vasiliev,1818―1900年)院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2。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末松谦澄(号青萍,1855―1920年)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属于先秦断代文学史[2]194。对国内影响较大的日本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是盐谷温(1878―1962年)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英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年)的《中国文学史》。这些海外汉学家从不同视角撰写中国文学史,不仅编纂体例有很大差异,而且对中国古典小说也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思考海外汉学家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呈现出的不同小说观念及其启示意义。
一、不同的中国文学史编排体例
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体例编排并不相同,都有自身特色,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不同范例。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现藏于俄罗斯喀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最早由北京大学教授李明滨于1987年在苏联进行学术考察时发现并介绍给学界。瓦西里耶夫是俄国著名汉学家,自取中文名字“王西里”,在汉学研究上造诣颇深,被誉为“汉学奇才”。这部中国文学史用“十月革命”以前的旧俄文字印行,大32 开,共163 页,译成中文约10 多万字[3]163,1880年由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出版。作品封面右上角有作者亲笔题字:“佛洛林斯基惠存 谨表敬意 作者赠。”[4]92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以后主要供学生阅读,并未翻译成其他语言,也没有流传开来,因而在中国、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并未产生影响,也没有得到应有关注。
初看起来,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更像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5],里面包含很多与文学不太相关的内容,仅在最后两章论述中国的雅文学和俗文学。这部文学史总共 14章:第一章开宗明义,即总论;第二章介绍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第三章介绍中国文字和文献的古老性问题以及中国人的看法;第四章介绍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孔子及其实际贡献、三部最古老的儒家文献《诗经》《春秋》《论语》;第五章介绍《孝经》《礼记》《书经》;第六章介绍佛经;第七章介绍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第八章介绍非儒思想家以及道家;第九章介绍佛教;第十章介绍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史地著作;第十一章介绍中国的律学;第十二章介绍语言学、评论、古董;第十三章介绍中国的雅文学;第十四章介绍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6]7。就目录本身来看,这部文学史大部分论述的是儒家文献、佛经等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实际上,《中国文学史纲要》确是一部中国文学史,并非文化典籍史。19世纪70年代末,俄国著名报人兼文学史专家科尔什开始组织撰写俄国历史上第一套大型《世界文学史》丛书,瓦西里耶夫应邀写作中国文学部分[1]1。因此,瓦西里耶夫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文学史而非文化典籍史。再者,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学史纲要》第一章“开宗明义”中,也很清楚自己的写作目的,他说:
并不是任何一位懂得对象国语言且从事某领域学术研究的学者都善于普及自己的学识,因为与其是需要懂得运用自己的知识,毋宁说应该知道那些有文化的读者希望了解的问题。比如,他们可能希望我先讲或多讲所谓的雅文学,介绍一些史诗,况且希腊人和印度人都有自己的史诗。希望我多讲讲戏剧、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演说术等等。[6]20
由此可见,瓦西里耶夫明白自己写作的是文学史,意识到读者希望自己多介绍雅文学,多讲讲戏剧、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演说术等。不过,瓦西里耶夫有自己清晰的文学观念,他坚持将文学放在最后两章,而且在前面先用较大篇幅详细介绍儒学等相关内容①。
由于文学史的主旨不是要确定一个民族的精英才俊应该创作什么作品,而是要认识他们的创作成果,而这也正是文学史的素材,所以有必要坚持一种次序,即异域文学赋予其作品的一种层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以及浩如烟海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的基础是儒学,而儒家甚至使反对者,以及所鄙夷的作品(小说)也接受了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我们又如何能抛开儒学而先言他?[6]21
瓦西里耶夫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学的基础,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他觉得坚持一种次序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先论述儒学,才能真正能让读者理解中国文学。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已经渗透进中国人的身体、血液甚至骨髓之中。儒学尽管不像是一种宗教形态,但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学等都有深刻影响。可见,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学有深入认识。
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01年,也是其重要代表作。翟理斯是英国著名汉学家,1867年来华,1893年因身体原因回国,1897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在汉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在英国汉学界也具有重要地位,为汉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和瓦西里耶夫类似,翟理斯的这部《中国文学史》也是他应邀为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筹划出版的一套“世界文学简史”(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而作[7]15。他在《中国文学史》序言开篇中自称:“这是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中,第一次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尝试。”[8]5这说明翟理斯并不知晓瓦西里耶夫1880年已经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
相比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在体例编排上有所进步,他基本按照西方文学史的编排方法,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7]15。这部文学史第一次以文学史的形式,向英国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学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概貌——虽然尚有欠缺与谬误,但它向英国读者呈现了一个富于异国风味的文学长廊[9]。翟理斯以朝代更迭为序,将中国文学史分为8 期,分别是先秦、汉代、三国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和清代文学,同样是一部中国文学通史。
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章节目录与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有相似之处。翟理斯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内容也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文学,还涉及很多中国文化的部分。他在文学史中不仅论述诗歌、小说和戏剧,还介绍了孔子、孟子以及铭文、历史、词典编纂学、佛学、经学、活字印刷术、字典、百科全书、法医学、中药学、农学百科全书等相关知识,其中很多内容也超出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范围。文学史家郑振铎很早就对翟理斯收录很多与文学无关的内容进行了批评:
一方面把许多应该叙及的人,都删去不讲。一方面却又于文学史之中,滥收了许多非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作品的范围本来不易严密的划定。但有许多文字,如法律条文,博物学书之类,一看就可以决定他不是文学作品的,Giles 则连这种书也都收了进去,而且叙述得很详细。[10]1
可见,郑振铎并不特别认可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他在文学史中“滥收”很多与文学不相干的内容,特别是把法律条文和博物学等也写入中国文学史中,这些与文学相距甚远。同时,他还指出其“疏漏”的弊端:
“创始者难”,我们自然不能十分的求全责备他。但我读了这本书后,我心中却禁不住有许多话要说;我觉得Giles 的叙述有许多地方未免太误会了,有许多地方并且疏漏得厉害。我们故不能由理想的文学史的标准去批评他,但就中国文学而论,他这部书实在是没有完全的研究,他的谬误颠倒的地方,又到处遇得见。[10]1
郑振铎认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疏漏严重,缺失很多内容,而且在许多方面对中国文学有所误会。不过,他也实事求是地意识到,对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不能过于求全责备,不能以理想的文学史标准批评它。王国维是晚清民国时期较早使用“纯文学”的学者之一[11]81,他在1905年发表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说:“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恉。”[12]早期国内学者如林传甲、窦警凡、黄人、王梦曾、张之纯、曾毅和谢无量等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均包含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文化而非文学的内容,甚至有学者认为很多早期中国文学史是学术史而非文学史[13]。可见,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也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因此人们应该站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看待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毕竟,当时视域下的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并不一样,文学概念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正处于从杂文学向纯文学方向发展的时期[14]148。
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同样具有自身特色。盐谷温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研究专家,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曾留学德国和中国,也是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15]106。《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是盐谷温1917年夏在东京帝国大学讲稿基础上,又花了一年半时间主要修正、增补小说和戏曲内容之后,于大正七年(1918年)十二月完稿,1919年由日本雄辩会出版[16]16。该书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述对我国的小说研究启发很大。它最早由陈彬龢(1897―1945年)于1926年译介到中国[17]167,后来留学日本的孙俍工(1894―1962年)在1929年6月再次将其译介到国内,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3年6月已经发行到第5 版,可见其传播之广泛,深受读者欢迎②。
相对瓦西里耶夫和翟理斯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侧重于阐释中国文学的性质和种类,分上下篇,共6 章。第一章“音韵”分为中国语的特质、四声及百六韵两节内容,第二章“文体”分为总说、辞赋类和骈体文三节内容,第三章“诗式”分为总说、古体和近体三节内容,第四章“乐府及填词”分为乐府、绝句的歌法和填词三节内容,第五章“戏曲”分为序说、唐宋之古剧、元之北曲和明之南曲五节内容,第六章“小说”分为神话传说、两汉六朝小说、唐代小说和弹词小说四节内容。正文末还有附录、附表和插图。从章节目录上看,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论述的内容与文学关系更加密切,基本上属于文学讨论的范围,最后两章戏曲和小说的内容所占比例最大,可见作者对这两种文学体裁的重视。这也是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与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和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最大不同之处。可见,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日益朝着纯文学方向靠拢,文学观念在不断进步。
从瓦西里耶夫、翟理斯到盐谷温,他们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分别代表了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范例,对随后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他们写作中国文学史的方法并不相同,这与他们各自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关系密切,同时也反映出文学观念一直朝着纯文学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古典小说在海外中国文学史 体例中的位置及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在海外中国文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海外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中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编排,也逐渐朝着规范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对后世学者编纂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部分产生了深远影响。瓦西里耶夫首次将中国古典小说写入中国文学史,并将小说放在最后一章“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中。他提到的小说既包括文言小说,也包括白话小说。其中文言小说4 部,依次是西汉刘向的《列仙传》、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宋代的鸿篇巨制《太平广记》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话小说12 部,依次为英雄传奇《水浒传》,世情小说《红楼梦》和《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和《玉娇梨》,言情小说《品花宝鉴》,志怪小说《白蛇精记》,历史演义小说《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七国演义》《战国》《三国志》。瓦西里耶夫非常重视长篇小说,对《红楼梦》和《金瓶梅》介绍较多,但并未按照朝代顺序论述中国古典小说。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由于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在当时影响很小,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述影响也很有限。
翟理斯则遵循朝代顺序,在元明清文学中分别介绍了中国古典小说。他主要以白话小说为主,展现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面貌,有助于读者把握中国小说流变的基本规律。在元代文学中,翟理斯将小说单独放在第三章论述,介绍了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和神魔小说《西游记》。在明代文学中,翟理斯将小说和戏剧一起放在第二章介绍,主要涉及言情小说《金瓶梅》、历史演义小说《列国传》、神魔小说《镜花缘》、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平山冷燕》《二度梅》和话本小说《今古奇观》。在清代文学中,翟理斯在第一章重点介绍了《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相比瓦西里耶夫,翟理斯论述的中国古典小说数量大大增加,小说也是其论述的重点。
郑振铎对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小说的编排既有批评,也有积极肯定。他认为翟理斯对小说的编排“详略不均”:
清文人中不甚重要之蓝鼎元反占了十页以下不过二页,袁枚也占了八页,《红楼梦》则几占有三十页。尤其奇怪的是蒲留仙之《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中并不算特创之作,事实既多重复,人物性格亦非常模糊,而Giles则推崇甚至,叙之至占二十页之多,且冠之于清代之始,引例至五六则以上。《笑林广记》多无稽猥琐之言,事实既不感人,文笔也不足列于文坛之上,Giles 虽知其为并无价值之小说,而仍引例多至十一则。至唐代之短篇小说,宋世之诸词家,皆至美之作品,反不得于此书之中占一二页的篇幅。[10]1
从郑振铎的评论可知,他并不赞成翟理斯过于推崇《聊斋志异》,而且认为这部小说并无多少创新之处,事实重复,人物性格模糊,价值并不是很大。《笑林广记》则多猥琐之言,并不感人,翟理斯却多次引用。可见,郑振铎和翟理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认识有所不同,这与二人的小说观念及中西文化差异密切相关。不过,郑振铎对翟理斯把小说写入中国文学史中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全书中最可注意之处:(一)是能第一次把中国文人向来轻视的小说与戏剧之类列入文学史中;(二)能注意及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两点足以矫正对于中国文人的尊儒与贱视正当作品的成见,实是这书的唯一好处。[10]2
可见,郑振铎认为翟理斯把中国文人一直较为轻视的小说写入中国文学史,对于改变中国文人传统的小说观念,重新审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有着积极意义。
与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不同的是,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在当时传播很快,影响很大,并且再版多次。1919年,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已经被译成西班牙文。到1928年,该书已经发行到第6 版。英国汉学家波乃耶(J.Dyer Ball,1847―1919年)评论这部《中国文学史》时说道:
对于本书的问世,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相信它能够激发汉学学生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学之广袤领域的热情;同时,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让那些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的人了解在中国“文学”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18]207
波乃耶认为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有助于国外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学,是学习中国文学的重要媒介。
相对而言,盐谷温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述最为规范和体系化,标志着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编排逐渐走向成熟。他在书中将中国古典小说分为4 节,首次按照神话传说、两汉六朝小说、唐代小说和诨词小说的顺序来介绍,既涉及文言小说,也包括白话小说。可以说,盐谷温初步建构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框架[15]106,对国内的小说研究也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影响深远。值得一提的是,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引发一桩学术公案,至今还有学者对此进行讨论。1925年,陈源(即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暗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19]9。对此,鲁迅特意发表声明予以澄清: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所说还时常相反……[20]
可见,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的确参考了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但显然是在借鉴而非“剽窃”。盐谷温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对国内小说研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海外汉学家把中国文学传统中地位较低的中国古典小说写入中国文学史中,并逐渐朝着规范化和体系化的方向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地位,对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和国内的小说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中国古典小说带来全新的研究视角。
三、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
最早将古典小说写入中国文学史的是海外汉学家。鲁迅很早就注意到海外汉学家所著中国文学史中的古典小说,他说:
中国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21]
鲁迅这里所说“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显然即指海外汉学家所著中国文学史。鉴于鲁迅曾在日本留学,与日本学界关系密切,因而他所指的很可能是日本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1882―1912年,日本至少有14 位学者撰写20余部中国文学史[2]210,可见日本学界对中国文学史著述之多。作为“他者”,海外汉学家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阐释,往往与国内的小说观念有一定差异,这与其所处的不同文化视域关系密切,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早期海外汉学家都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地位较低,不过,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中却对中国小说予以积极肯定,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这对于改变当时国内落后的小说观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西方人在谈及“文学”时,首先想到的是诗歌、小说和戏剧[22],因此海外汉学家在写作中国文学史时,便把小说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瓦西里耶夫在其《中国文学史纲要》中介绍中国古典小说时,一开篇就指出小说在中国国内地位很低,甚至遭到蔑视:
我们终于讲到这种在我国称得上是雅文学的文学类别了。呜呼!这种文学受到了中国人的完全蔑视,我们在任何学术目录中均找不到此类书籍和作品的踪影,因此也难考其源流和作者。尽管有许多作者的名字也为人所知,但有时却是虚构的,这是因为作者耻于承认这种在中国学究们眼中的粗俗之事是他所为。在中国文人甚至难以启齿说他曾经读过某些名剧作或名小说,尽管他也许就读过这些作品,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民众(中国的贵族无足轻重)之中,不可能感受不到民众的趣味。这是传统上的迂腐之气将知识分子从民众中分离了出来,漠视人民的欢乐和痛苦。中国的迂腐文人所依仗的是陈腐的语言和荒谬的内容。[16]207
瓦西里耶夫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小说在中国的地位之低。在瓦西里耶夫看来,这些几乎是荒唐之举。他对迂腐文人忽视小说表示愤慨,认为实际上他们自身依仗的是陈腐的语言和荒谬的内容。瓦西里耶夫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地位低下归因于儒家思想,认为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禁锢,才导致小说被视为伤风败俗的文学:
如果我们关注到了儒学极力捍卫其思想控制权的立场,便可以理解这种对立现象了。儒学看似不是宗教,可没有哪种宗教能够展示和证明其具有用某种思想禁锢一个民族两千年的能力。经典文献中既不包括戏剧,也不包括长篇小说(可《左传》中却有大量传说),所以,这是一种空虚的伤风败俗文学(是他们将戏曲和小说变成了真正的伤风败俗文学)。[16]207―208
瓦西里耶夫从儒家思想的视角解释小说在中国文学中地位较低的原因,将其归咎于儒家的话语权[23]85,其认识可谓非常深刻,抓住了思想层面这一根本原因。
同样,翟理斯也意识到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不高:
所有的中国文学都是纯文学。小说和故事并没有被划为文学的范畴,作者也没有意愿为这些作品署其真名。他们担心,如果将小说和故事当作文学,或者将小说署上真名,就会导致文学的标准大大降低。甚至是《红楼梦》,也被认为包含一些损害其整体美感的章节。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它是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但是却忽略了普通人的常见弱点,这就会使得作品的描绘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8]43
翟理斯指出,在中国国内小说并非属于纯文学,小说作者也不愿意署上自己的名字,认为这样就会使文学的标准降低;即使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这部小说被认为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
盐谷温也注意到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一直都比较低,他在介绍汉代小说时一开篇就说:
所谓小说之语见于《汉书艺文志》算是最初。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③然亦弗减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所谓稗官注云:
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准是以观则小说是读如字面一样是闾巷底细言了。[24]323―324
可见,盐谷温同样意识到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地位不高,被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为“刍荛狂夫之议,细碎之言”,难登大雅之堂。而且儒家对于小说也持轻视态度,认为小说是“末技”,虽然有可以观赏之处,但会妨碍远大的事业,君子不应该写作小说,以免沉溺其中而耽误自己。
瓦西里耶夫、翟理斯和盐谷温都注意到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不高,但他们仍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积极肯定。这些汉学家将全新的小说观念传入中国,颠覆了传统文类体系及其价值观念[25],对于提高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改变传统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促使国内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小说,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早期海外汉学家都意识到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价值在于透过小说可以了解中国的社会风俗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追求及其国民性特征,这也是国外读者普遍的阅读需求。瓦西里耶夫特别看重中国的长篇小说,他认为长篇小说有助于认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及其生活观,这是欧洲读者仅凭观察和阅读儒家文献所无法代替的。例如:他认为读者通过阅读《红楼梦》,可以了解中国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诸如熟人聚会、谈吐或者饮食,还有如何庆祝初雪降临等情景;《金瓶梅》则揭示了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暴露了肉欲横流和下流龌龊的一面;《品花宝鉴》描写了富丽的宫殿、极其贫困的茅舍和肮脏的小店铺,读者从中还可以了解中国居民的习俗、情感和追求[6]214。翟理斯则认为《水浒传》对研究中国习俗风尚颇有价值,而《红楼梦》描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全景,读者几乎所有能够想象到的中国社会特征,都在这部小说中一一呈现出来[8]281。同样,盐谷温也认为借助《水浒传》有利于研究中国的国民性及其社会风俗。他还特意列举了“吴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认为“其神出鬼没不可端倪之处,也可以窥见诡谲阴险的国民性的一面”[24]422。对于《红楼梦》,盐谷温指出读者透过这部小说可以感受到中国乃文明之旧邦、文化烂熟之地,人情风俗充分发达,但发展之极则流为享乐,遂终于颓废。他进一步说,《红楼梦》还表现出中国人极其复杂的性情且辞令精巧,小说中虚饰之多又反映出中国国民的复杂性。对于小说《金瓶梅》,盐谷温则认为这部小说极其写实,非常逼真地描写了市井小人的生活状态,曲尽人情之细微机巧,是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史料。
可见,瓦西里耶夫、翟理斯和盐谷温都特别注意透过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像《红楼梦》和《水浒传》等著名的长篇小说,去了解中国的人情风俗和社会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中国古典小说是了解中国社会特征和人情风俗的重要窗口。实际上,早期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的途径之一便是将中国古典小说视为重要中介。因此,很多西方来华传教士都竞相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并逐渐传播国外,使国外读者借此了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话本小说《今古奇观》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被译成英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它拉开了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小说关注、翻译和介绍的序幕,在西方广为流传,成为西人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参考,并为西人借鉴和模仿,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26]。海外汉学家也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外译现象。瓦西里耶夫提及欧洲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长篇小说,如《好逑传》《玉娇梨》《白蛇精记》。不过,他认为这些极尽绮靡矫饰的小说并不能反映中国真实的现实生活。翟理斯注意到《今古奇观》已经有多个译本在欧洲流传。盐谷温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外译介绍得最为详细,不仅涉及小说在欧洲的译介,还包括其在日本的译介情况。他提到《水浒传》的日译本和德文节译情况,还曾提到《好逑传》的英译本,《玉娇梨》《平山冷燕》的法译本,以及《红楼梦》的英文节译情况。
第三,相对来说,早期海外汉学家都比较重视中国的长篇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这部在海内外知名度较高的小说,三位汉学家均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瓦西里耶夫在文学史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红楼梦》,认为这部小说反映了中国的上层社会生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小说。他评价《红楼梦》的语言纯净雅致,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有很多续作。翟理斯则用更大篇幅介绍《红楼梦》的故事情节,认为它是一部原创的而且产生深远影响的爱情小说,是所有已经提到的中国小说的顶峰之作,堪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8]356。盐谷温也在文学史中重点介绍了《红楼梦》,他认为这部小说华丽丰赡,不仅可以在中国小说界鼎力争霸,而且在世界文坛也毫不逊色。可见,三位汉学家都由衷喜爱《红楼梦》,而且都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们将中国小说置于世界文学范围之内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其他一些著名的中国长篇小说,早期汉学家也有很多独到见解和精彩评价。例如,瓦西里耶夫详尽地介绍了《金瓶梅》的故事情节,认为小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面貌,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瓦西里耶夫则认为《三国演义》是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其叙事艺术和优美文辞备受推崇,引人入胜[6]214。翟理斯也对《三国演义》积极肯定,认为它可以从众多小说中脱颖而出,《西游记》是一部以流行和畅快风格写成的最受人喜爱的小说,《金瓶梅》风格简洁明快。盐谷温认为《水浒传》豪宕博大,可立足于世界文坛,《西游记》幽玄奇怪,可与世界优秀的小说相媲美。早期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积极肯定,也与早期中国一些眼界开阔的知识分子不谋而合。例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通俗小说高度肯定[27]12。
第四,早期海外汉学家都注意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问题。瓦西里耶夫认为《红楼梦》的第一个版本最为精美,为其他大众书籍所不及,还提及小说的稿本出现后,抄本价格极为昂贵。翟理斯注意到《聊斋志异》有多种版本并存,认为但明伦评论的版本最好。相对以上两者,盐谷温对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的关注最为全面,而且他还注意到版本及作者的真伪问题。在介绍汉代小说《汉武内传》和《汉武故事》时,盐谷温认为两书作者虽署名班固,但应为后人假托。他的判断依据是,班固是有名的历史学家,是《汉书》的作者,而两书描写的也是《汉书》中的故事,因此假托班固较为合理,且《隋书·经籍志》均收入二书,但不曾说是班固所撰,这就更加印证自己的看法,进而推测此两书可能是六朝词人所作。他还指出《搜神后记》虽署名陶潜,其实也是后人假托。盐谷温在介绍《水浒传》时,注意到李卓吾批评的百二十回本(也有百回本)和金圣叹批注的七十回本[24]416,可见其研究态度之严谨。
总而言之,虽然瓦西里耶夫、翟理斯和盐谷温分别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但他们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都表现出一些相似的特征。例如,他们都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在中国国内地位较低,并对小说积极肯定,而且都对《红楼梦》予以高度评价;三位汉学家都非常注意透过中国古典小说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情风俗以及国民性特征;他们都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注意到中国小说的版本问题和外译情况。他们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对于提高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改变国内陈旧的小说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国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是开先河之举,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海内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基础。
注释:
① 实际上,1887年,瓦西里耶夫还石印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资料》,这是他为中国文学史课程编写的讲义。这部书主要由“中国文学资料”“中国文学史附录”“书目”三部分组成。见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阎国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 页。
② 孙俍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再版多次,初版时间是1929年6月,1933年6月发行第5 版。
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句话虽出自《论语》,但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说的。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见杨伯峻编《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