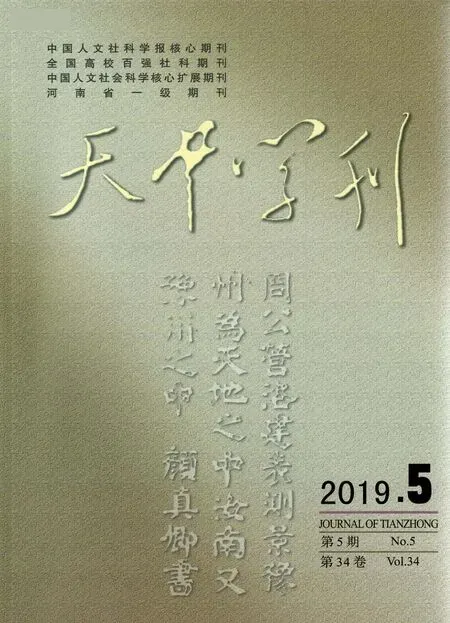清代赋学特征三论
2019-01-18潘务正
潘务正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赋学发展至清代,受社会政治文化、学术思想及文学自身的演进等因素影响,呈现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特征。诸如赋学的地域化倾向、家塾赋学教育的普及导致的赋法精细化以及律赋疏离科举考试而呈现对此种文体的突破等。这些并不见得是清代赋学的根本特征,但绝对是清代赋学有别于前代的显著之处。清代赋学作为中国赋学“集大成”的节点,我们有必要对其特征进行总结概括。
一、赋学的地域化倾向
与诗、词、文和作家个性密切联系的文体不同,散体大赋与科举律赋体现的是高度一统的国家意志。大赋最初亦具地域属性,汉代初年,辞赋作家分布于各藩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汉书·贾邹枚路传》);淮南王刘安“招宾客著书”(《汉书·地理志》)。藩国文学“既远绍先秦地域文化特征,又具有时代的新祈向”[1]。在此情势下,辞赋具有地域性特征毋庸置疑。然而,武帝行推恩之令,藩国衰落,中央大一统政权加强,导致藩国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转化。司马相如是这一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他前期在梁孝王文学集团中作《子虚赋》,描写楚使子虚先生向齐乌有先生夸言楚之云梦,继而乌有先生以“吞云梦者八九”之气势扬齐压楚。二者之间的竞赛,恰恰彰显藩国文学的地域特征。然相如进入宫廷之后,为武帝作《上林赋》,又力压楚、齐诸藩国,弘天子上林“巨丽”的声威,体现大一统政治形势下宫廷文学的气象。自此,汉大赋形成了“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喻”的传统,即使“抒下情”,也并非一己之情感,而是具有讽喻性的政治意味之情感,共性远远大于个性,甚至淹没个性。由此,汉大赋成为宫廷文学的典型代表,而完全偏离了地域文学的特征。
定型于唐代的律赋作为考试文体,自然也不允许个性及地域性特征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限韵的唐代应试诗赋,不仅可以考察士子的文采及思维应变能力,也暗含着培养士子习惯于接受一定制约的用意。同时,在作品主旨上,只有契合统治者心理方能得到阅卷官的首肯,录取的概率才大。因此,表达对王朝及其统治者的效忠之心是此类作品的共同特性,至于个性与地域性,也在排斥之列。因此,当明清时期诗、文、词乃至戏曲等文体的地域性增强,地域文派随之出现之时,赋则始终未能形成地域性派别。长期的献赋及考赋传统,导致此种文体始终与国家礼乐及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而少有个性及地域性特征。
但是,至于清代嘉道以后,尽管赋体仍未出现地域性流派,但随着文学地域意识的增强,这一文体的个性及地域性特征也随之凸显。随着辞赋对制度的偏离,尤其是道咸以下国运多艰,王朝制度控制力的削弱,士子虽习律赋,却很难再以此种文体获得功名利禄,光绪三十一年蒋萼云:“近因时局多艰,育才兴学,方且奉明诏罢制科,登高能赋,固已无所用之。”[2]一方面家塾对赋学教育的重视和教育的普及,使得习赋人口增多;另一方面,科举录取人数的固化,且还有着不断缩小的趋势,大部分士子习得律赋却无用武之地。这种情况下,律赋的工具性逐渐减弱,而文学性相对增强。同样是将赋与诗相关联,汉代“赋者古《诗》之流”是以讽谏的政治功用建立二者渊承关系;清代则是从文学性角度着眼,朱一飞移严羽论诗之极致“入神”于赋中,云赋之致为“传神”[3],予赋以诗的特性。晚清时期强调赋体“神韵”特性的尚有李元度、余丙照诸人。既然此体的文学性增强,则其与诗、文、词的体制相似,亦逐渐滋生出地域性特征。虽然赋之传统导致此体并未出现地域流派,但其地域性特征的增强却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以地域命名的赋集开始出现。这类赋集有刊于道光年间的欧阳厚均《岳麓赋钞》、杨景曾《澄江赋约》,编于同治六年的姜学渐《资中赋钞》,刊于光绪年间的杨浚《闽南唐赋》、李恩绶《润州赋钞》,以及具体年代不详的《淮南赋钞》《竹西吟馆赋钞》等①,正是这股思潮的体现。这类赋集,一是收录作家毫无例外集中于本地,如《澄江赋约》收嘉道时期江阴赋家季芝昌、王苏、夏柔嘉及编者杨景曾诸人律赋70 篇,《润州赋钞》收镇江130 余位赋家240余篇赋作;二是所收之赋,虽多为应试之体,但亦有铺陈本地风光的赋作。赋本来就有“代类书”的功能,因此散体大赋中描写帝国山川风貌的部分拆散而为律赋或小赋,很容易就成了一篇地域赋,这在清代文集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润州赋钞》就收有冷士嵋《登金山赋》,贺鉴、彭澧、王仲骏《练湖赋》,鲍皋《兰溪赋》,王文治《铁甕城赋》,魏晋贤《宝晋书院赋》,冯煦《新修金山寺赋》,赵辑《北固山望江赋》,张崇兰《焦山读书赋》《海岳庵赋》,钱之鼎《砚山园赋》,张灏《蓴湖赋》,颜崇名《寄奴泉赋》,周寿朋《登海云楼观日出赋》,郭元《李牟瓜州吹笛赋》,吴台章《草长江南莺乱飞赋》,李士□《焦山古鼎赋》,陈国藩《焦山待月赋》,鲍上宗、孙庆甲《北固山多景楼赋》,杨正钧、丁传靖《辛幼安京口北固亭作永遇乐词赋》,等等。许多赋集以地域命名,亦收录本地文人所写本地风光的作品,由此突出赋的地域倾向。
其次,在赋学研究中贯穿地域流派的学术思想。赋至清代作为研究对象,不同学术流派会以各自的学术思想对其进行探讨。如阳湖文派尤喜古赋,张惠言不仅作《黄山赋》,且编成《七十家赋钞》。阳湖文派特点是主今文经学,词学创作强调“意内言外”,词学批评注重“作者之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词体的这种比兴功能在赋中亦得以发挥,张惠言在《目录后序》中说:“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因此,所选古赋多数具有“寓意”,他是以这种方式发挥批评时政的功能。就是以“七十家”名赋集,也暗含着踵孔门“七十子”之志意将乖离的“大义”重新梳理清楚的学术抱负。当然,似此彰显赋学地域特征的流派在晚清仅此一家。
最后,在赋集与赋话中凸显地域流派的文学主张。将赋视为文之一体,则地域流派的文学主张也会投射在赋体之上。如晚清湘乡派中人李元度编《赋学正鹄》,在所分十类中,特重“气机”。湖湘一地,由于地理原因,民性多流于刚强倔强,为文亦重阳刚之气。该派代表人物曾国藩谓:“行气为文章第一义。”[4]与醇厚老确的平正文风相比,曾国藩更重雄奇瑰玮之气,他在教导弟子张裕钊时,建议以汉赋之气体药其古文体弱的弊病。李元度也认为“赋以气机为第一义”[5],推崇“笔力纵横跌宕,顿挫淋漓”之致的赋风。同时,李氏也接受了桐城派姚鼐所倡的合阳刚与阴柔为一体的审美境界,融合发展而提出“潜气内转”的理论,因此他反复用“向背”“反振”等揭示形成“潜气内转”的笔法因素。至于蜀中赋家,又多向往先贤的赋风,因此姜学渐《资中赋钞》以胎息扬马之类的比拟评价赋家高超的艺术成就。于是,赋的地域性又融入了地域传统的因素。
二、赋学普及与赋法的精细化
随着律赋重新作为选拔人才的工具,为在科考中脱颖而出,对赋法的探寻成了士子研讨的重点。清人揭示赋法的著作主要有三类,即赋选、赋话与赋格。讨论赋法的单篇文章并不多,有的亦被收录在这些著作中。这三种类型的赋学著作又分别与时代相对应,清代前期赋话尚未出现,赋法通过赋选传达;中期赋话开始现身,与赋选共同承担传播赋法的功用;后期则赋选、赋话与赋格三位一体地行使赋法分析与教学的功能。且后期几种媒介结合得更为紧密,赋选中录有赋话,姜学渐《资中赋钞》卷一目录后有小字云:“附赋学赋话若干条。”这若干条分别是“味竹轩赋学一则”“味竹轩初学律赋一则”“味竹轩赋话数则”、江海平《律赋说》一篇等。赋选中选录赋话条目最多的当数汤稼堂《律赋衡裁》,此书卷六附有“余论”48 条,属清代较早的赋话。潘遵祁《唐律赋钞》卷首录有其中的10 则,潘世恩《律赋正宗》录有12 则,而程祥栋《东湖草堂赋钞》所录多达41 则。赋格与赋选有时也相结合,如朱一飞《律赋拣金录》选赋209 篇,前又载《赋谱》10 条,阐述具体赋法,属赋格类文字。赋话、赋格与赋选互相依附,以理论直面创作,编者意图以此更好发挥指导功能。
纵观清代赋法研究的趋势,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线索,即清初倾向于虚的一面,不注重具体的法度,而是倾心于赋之风格的品味,中期以后具体的法度分析加强,后期重点落在赋法层面。这种变化,与赋学著作面对的读者密切相关,读者的水平不同,赋论家关注的重点自然有差异。
清代前中期,赋选的编纂主要是为士子进入馆阁或应付翰苑考试服务。康熙二十四年同时出现的王修玉《历朝赋楷》、陆葇《历朝赋格》及赵维烈《历代赋钞》,都是应六年前博学鸿词科考试及上一年翰林院大考之运而生。参加这类考试的人员,或者是文名卓著的诗赋家,或是熟谙诗赋创作的馆阁中人,因此,编者不需要对赋作之法作详细而具体的说明,只要提供典范之作即可。尽管陆葇《历朝赋格》以“格”名书,且云:“格,法也。前人创之以为体,后人循之以为式,合之则淳,离之则驳。”但全书并未就赋法进行揭示,即使在书前列有凡例十三则,也多是针对赋学源流及编纂宗旨而言,关于具体的赋法并没有涉及。王修玉及赵维烈二人之著亦是如此。
清代中期,赋选的重镇是馆阁之作,一方面备翰苑之掌故,一方面为词垣众臣提供应对翰苑馆课、散馆及大考等诸种考试之用。所以习赋者都有很好的赋学创作基础,如翰林院出身的钟衡编有《同馆课艺》,在此基础上,又“与二三儒彦,家门隽英,讨律赋之源流,作士林之矩矱”[6],成《律赋衡裁》一书。尤其是书后所附具有赋话性质的《律赋衡裁余论》48 则,对赋法已有一定的涉及,但总的来说还比较概括,非具体性的分析。如举唐太宗《小山赋》“松新翠薄,桂小丹轻,才有力以胜蝶,本无心而引莺。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及《小池赋》“牵狭镜兮数寻,泛芥舟而已沉。涌菱花于岸腹,劈莲影于波心。减微涓而已浅,足一滴而还深”两句,后总括云:“渲染‘小’字工妙乃尔,可见才大者心必细。”这充其量只是起到提醒学赋者诠题时注意题中字样的作用,而非具体法度的分析。与嘉道以后关于诠题的探讨相比,钟衡的揭示显得简单。总而言之,《律赋衡裁余论》作为一部赋话,感悟性语句较多,分析性语句较少。李调元作于学政任上的《雨村赋话》之《新话》不仅大量采纳钟氏之语,且论述方式亦与之相同。
与上述赋法探讨的论著相比较,朱一飞所编《律赋拣金录》所附之《赋谱》出现了明显转变。汤稼堂《律赋衡裁余论》、李调元《雨村赋话》等赋话的惯常方式是通过摘句示以大体的法度,而《赋谱》则抛弃句例,直接示人以法。该卷开头有一段总括性介绍云:“律赋之法有五:一辨源,二立格,三叶韵,四遣辞,五归宿。其品有四:曰清、真、雅、正。其用工有九:曰起接,曰转折,曰烘衬,曰铺叙,曰琢炼,曰连缀,曰脱卸,曰交互,曰收束。其致则一:曰传神。神传,蔑以加矣。赋又有六戒:一曰复,二曰晦,三曰重头,四曰软脚,五曰衰飒,六曰拖沓。”以下就对五法、四品、九用功及六戒作详细的说明。如论“接法”云:“接有接法,如用‘尔其’‘懿夫’等调,非无意义,须相机势斟酌用之,不得沿为习套。至于硬接,尤须神气一线为佳。”只介绍“接法”的具体方式及注意事项,并未列举相关的赋例。其后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将赋格与赋话相结合,既有具体法度的说明,也列举有代表性的馆阁之作示例。这种著述形式,到余丙照《赋学指南》达于极致。
清代赋法呈现的具体化,是律赋逐渐进入低等级科举考试之中导致。清代前中期,律赋主要应用于博学鸿词科及翰林院的各项考试,中期以后,翰苑出身的学政出于为馆阁储才的目的,在督学地方时,有意识地在观风试及童生试中增加律赋一项。此项考试的成绩虽不直接决定岁科试及乡试的前途,但名列前茅者能得到学政的青睐从而会有更多的机会。因此,士子也须在这种文体上下功夫。于是,嘉道以后,更多的家塾选本出现,希望对家族成员从小就进行律赋教学,正如王雅南《赋学指南叙》所云:“国朝稽古右文,无体不备。故自膠庠及村塾莫不以赋学课生徒。”[7]1由于孩童年幼,普通文士又不如馆阁中人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很难自己揣摩典范赋作,必须明示以具体的赋法,因此这类选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各种法度进行详细的说明,并辅以对应的赋例。余丙照《赋学指南》“欲为无师授者示迷途”,故此“不惮缕晰言之”,该书分为十法,“又别为碎目数十条,每条引佳构若干以为程式”[7]6。显然,律赋考试由中央到地方、由成人到孩童的普及,是清代赋法精细化的主要原因。
余丙照《赋学指南》是一部赋法的集成之作,由这部赋话可以看出清人尤其是清代后期赋家着力之点。此书将赋法分十类加以介绍,分别是押韵、诠题、裁对、琢句、赋品、首段、次段、诸段、结段及炼局。这十类赋法可以概括为押韵、诠题、裁对、风格、句法、段法及篇法七个部分,除去赋品属于风格的层面,其他六种均属技法范畴。清人的赋法研究,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是押韵。“作赋先贵炼韵”,故此书将其置于篇首。押韵之法,著者又特别注重押虚字、因韵法、出色韵及押人(地)名。其中所谓因韵法,即“遇一典故,顺押不得,用倒押;整押不得,用拆押。总要意灵笔活,就韵生情”。此法分顺押、倒押及整押、拆押,其中拆押之法就是为了押韵,故意拆散成语,如华庭桂《黄牡丹赋》云:“竞夸天下无双,魏应居后;谁占人间第一,姚合称王。”将《群芳谱》“姚花真可为王,魏花乃后”与皮日休《牡丹诗》“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拆散,以此来与所押之韵谐和。
第二是诠题。诠题之法又可分绘景、写情、情景兼到、传神、体物、刻画、点醒、陪衬、烘托、比例、双关、串合、映带、疑审、释义、议论、搓法、旋风笔、撞法、算法、前后着想、题前翻跌、段末收束等。其中所谓“搓法”,就是“上句炼出一字,一手握定,下句即从此一字生出意义,回环变换,如搓绳然”,故名。如齐召南《月中桂赋》云:“惟水生木,实为坎水之精;有木干云,更出青云之上。”第一句炼出一“水”字,第二句即由此字生发;第三句炼出一“云”字,第四句即由此生发。又如与之相近的旋风笔,则是“拈一字于一句之内,灵变取致,如一丝之萦绕”,故名。如周系英《庚子拜经赋》云:“铭遵考父,一命伛而再命偻;受比丹书,三日斋而七日戒。”分别拈出“命”“日”二字,宛转萦绕。再如撞法,“上半联另借他件作出,下半联仍就本题作对,撞起一联,共成绝对”,如宋言《学鸡鸣夜度关赋》云:“念秦关之百二,难起狼心;笑奇客之三千,不如鸡口。”上一联借他事与鸡鸣度关相撞,而成一联,即属撞法。诸多法则,眼花缭乱,且差别细微,若非精心于此,难以分辨得如此之清晰。
第三是裁对。对仗之法又可分卦辞对、干支对、数目对、反正对、流水对等。卦辞对“实足为通篇生色”,干支对“最易生色”,数目对“簇簇生新”,而流水对则“既避重复,且有生动之趣”。正因如此,著者于此也是颇多用心。
第四是句法。关于句法,著者特别强调炼短句、长句、起结及运用沉郁、叠字句等。炼短句又有间字炼法、顺递炼法、倒装炼法、古致炼法、圆活炼法、炼颜色字法、炼数目字法及炼叠字法等。炼长句又有顺炼、曲折炼、古致炼、呼应、流水、滚炼、反正比例、反剔、撞法、逆挽诸法等。
第五是段法。段法分首段、次段、诸段、结段。首段之法有直起、陪起、题前起、对起、翻起、颂扬起、暗笼、明擒诸种;次段之法有溯源、顺拍、逆翻、映合;诸段之法则有铺叙、互勘、提起、点染、停顿、反正、折落、开合、浅深、推原、推论、赞叹及旁衬等;结段之法则有颂扬、怀古、寓意、推原、推论、赞叹、旁衬、扎题、压题、翻题等。
第六是篇法。余丙照称之为“炼局”。篇法的总体原则是“活”“紧”“曲”,“总宜相题立格”,如长题有截做法、串做法;扇题有分疏法、交互法;古题有叙在题前法、述在题后法;时题有因时制宜法、援古证今法;短题有溯古法、写景法;比拟题宜处处双关夹写,抉出题眼。不管何种题型,均以“层次清楚为要”。
由如此之多具体精细的“法”,可以看出清人对此的热衷。律赋至清代中后期变得有法可循,这既是士子为举场中获隽而求新求异使然,也是律赋教学普及化的结果。对律赋之法的精心揣摩,是赋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三、文体错位的美学意趣
中国古代的文学体裁,各自有其功能,如诗言志、词为艳科、文以载道等,每种文体都需遵循一定的规范,如此才视为得体。在辨体意识最为发达的明清时期,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又有逾越规范者,故意打破文体之间的界限,将两种不相容的文体之根本部分融于一处,即以一种文体描写该体所禁绝的另一种文体的成分,从而形成“错位”的现象,比如以古文辞为小说、以词为诗、以曲为词等。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从属于破体为文的范畴;但文体“错位”与破体为文又不完全相同,后者是一种文体有意识地吸收品位比自身或高或低的另一种文体的某些特征,以达到改造本身的目的,而前者则是一种文体故意将与之不相容的另一种文体的某些成分纳入其中,其目的并非为改造本身,而是在两种文体的冲突抵牾中制造出别具一格的美学效果。
就律赋而言,作为科举选拔人才的工具,要求其内容纯正,风格典雅,一切与之不符的观念与格调均被排斥在外,故侯心斋云:“律赋本意应制,一切悲忧愁叹等不吉字面,及一切香艳字句,近词曲者,俱不可用。”[8]其实不仅律赋,一切应试文体均需如此,故“清真雅正”成为时文、律赋及应试诗共同的风格要求。张廷玉说:“夫应制之篇,以和平庄雅为贵,气虽驰骋有余,而音之厉者弗尚也;音虽跌宕可喜,而格之奇者弗尚也;语虽新颖巧合,而体之佻者弗尚也;辞藻虽丰,征引虽博,而言与事之凡俗者弗尚也。鞞铎之振厉,不足语云门韶濩之铿锵;林壑之幽深,不足语建章鳷鹊之巨丽;雉头蝉翼之瑰异,不足语山龙黼黻之文章。”[9]说的虽是应制文章,实际上亦适用于应试之体。
较早以文为戏者要数韩愈,其《毛颖传》被林纾称为“千古奇文”[10]443,柳宗元赞之以为“若捕龙蛇,搏虎豹……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不过亦有如裴度贬之云“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11]42。不管是赞美还是贬斥,聚焦点都在其“有意规抚《史记》”[10]442。这也是一种文体的错位,即以正史的传记体裁写滑稽的小说内容。表面的严肃性与内容的诙谐性在碰撞中产生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而此种创新则为正统士大夫所排斥,裴度就是从文章体制的角度反对韩愈如此作文。
清代,“以文为戏”成为突破文体规范的常用手段。乾隆时人缪艮将己作名为《文章游戏》,明目张胆地强调以游戏为文章宗旨,自序曰:
仙吾知其游戏神通,佛吾知其游戏三昧,吾儒独无所游戏乎?虽然,吾儒不得以游戏著也,可游戏者,其惟文章而已。陶唐氏之文,仲尼氏之文,道也,戏于何有?经纬之文章,谟训之文章,所以载道也,亦戏于何有?文章而我得纵其游戏,游戏而仍名之为文章,惟吾党风前月下,浇书掷剑,情往兴来,更唱迭和,不摹古人,不薄今人。方且手忘笔,笔忘墨,乌知所谓文章?乌知所谓文章游戏?夫文,文采也;章,章法也。文采章法,果灿然斐然,则仙之吐蜂噀酒,戏也;佛之弹指须弥,戏也;而此风前月下,更唱叠和,谓非戏乎?《诗》有之,“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游戏而归于文章也,戏之正者也。以几案为戏场,以笔砚为戏具,可以破闷,可以忘倦。爰集风前月下情往兴来之作,目曰《文章游戏》,以悦观者,观者其予我否?[12]250
他以诗、文、赋等体制,书写其日常生活,中间充满幽默诙谐的风趣,他在自序中道其写作策略云:“半生阅历之境,不能无言,遂率尔操觚,不过借打油、订饺伎俩,自抒胸臆而已。”[12]249此与阮葵生之言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阮氏之语云:“高沙孙舍人护孙选《古文华国编》,专取馆阁一派,颇具规则……近日学子每薄制体不为,徒从事于吟风弄月,为急就之章,‘胡钉铰’‘张打油’,宁不自镜其丑耶?”[13]他推崇馆阁之体制,指责以文章为游戏。这种游戏文学的风气正是由于“薄制体不为”导致,是对科举的偏离所致,也可视为挑战正统秩序而生。显然,缪艮的“自抒胸臆”,是根本于其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甘心游戏人生的精神追求。《新妆赋》对于“闺中情态”之“入神”描写,《慨贫赋》(以“酒色烟赌人烦大”为韵)以律赋写穷态[12]3,正与律赋的规范相违背。作者就是以此种“游戏”之笔,表露其对正统秩序及文体的反讽。
嘉道时人沈谦《红楼梦赋》亦是如此风格。其中所收系列律赋,描写小说中闺阁女子的生活、情感,既是以律赋写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又是以此种科考文体描绘“艳情”,这一文体的错位,正带有游戏的性质。沈谦擅长律赋,是为参加科举步入仕途做准备的,然而科考的失意,进身之途已被阻断,此种文体实际上已无用处,以其抒写穷愁劳苦,并借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寄托忧愤,无奈之中包含着调侃。以律赋写小说,一方面高贵文体的品位被拉低,另一方面低贱文体的品位被抬高。高雅与俚俗,庄重与艳情,有用与无用,大达与小道,这些对立面在错位中产生碰撞,从而形成文体的张力,产生丰富的审美趣味。最终高雅的旨趣被消解,成了可笑的一面;俚俗的兴味得到提升,成了尊崇的一面。
沈谦《红楼梦赋》借用律赋写小说,肯定小说之类的俗文学、嘲讽律赋这种考试文体的态度,可与嘉道时期《红楼梦》支持者借“红学”调侃“经学”之举进行类比。徐珂《清稗类钞》的记载人所熟知:
曹雪芹所撰《红楼梦》一书,风行久矣。士大夫有习之者,称为“红学”。而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曾寓目者几九百种,尤熟精《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大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盖“经”字少“巛”,即为“红”也。[14]
朱子美以“红学”调侃“经学”,将一直以来神圣的经学拉下祭坛,同时也赋予不登大雅之堂的红学以崇高的地位。沈谦《红楼梦赋》以科举之律赋写艳情、愁情、悲情之小说,显然也带有类似的意图,都是在文体错位之中,发现至味弥永的美学意趣。
随着清政府统治力的削弱,士人对科举也逐渐表现出一种疏离,曾经主要用于翰林院大考、散馆、馆课及学政选拔生童等系列考试中的律赋,成了一部分士子所拥有的无用之长物,而经多年的揣摩研习,士人便放开手脚,以此体描写一直以来被视为律赋禁忌的内容与风格。旧的范式被打破,文体也在突破中发生衍变,获得别样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