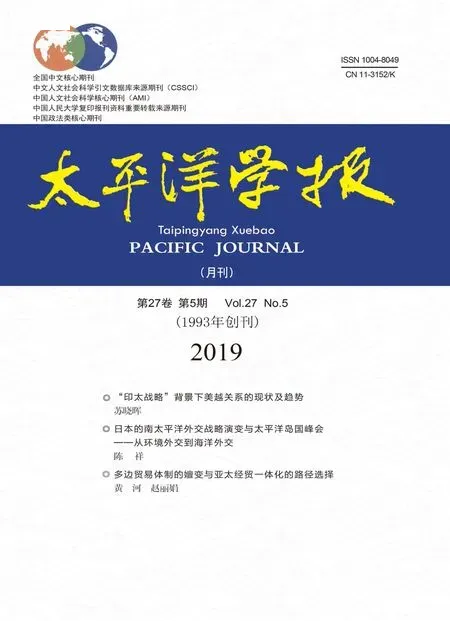东亚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同盟政治与领土争端
——以中日钓鱼岛争端和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2019-01-18李途
李 途
(1.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3)
领土争端是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是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除了与印度及不丹之间的陆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外,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方向还面临着海上领土争端,其中既包括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也包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主权争端。这两个争端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属于二战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与20世纪70年代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争夺密不可分,美国均牵涉其中。1951年9月,旨在解决日本战后政治地位以及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美国联合英国等国家单独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其中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所有权利、权利根据与请求权”。①“Peace Treaty with Japan”,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September 8, 1951,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36/volume-136-i-1832-english.pdf.但是,日本拒不承认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属于“旧金山和约”规定的日本应当放弃的领土,反而主张钓鱼岛作为美国战后托管的“日本领土”,随着《归还冲绳协定》一并“归还”给了日本。“旧金山和约”第二条还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权利根据与请求权”,但未明确规定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归属,这也为后来的南海争端埋下了隐患。菲律宾据此主张,“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南沙岛礁的主权权利后,南沙便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无主地”①Mark E.Rosen,JD,LLM,“Philippin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Legal Analysis”, Center for Navy Analyses, August 2014, 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iop-2014-u-008435.pdf.,为其后来非法侵占南沙岛礁提供依据。
此外,美国还因与争端当事国日本和菲律宾存在正式的同盟关系而进一步牵涉其中。作为日本和菲律宾最为重要的盟友,美国在这两个主权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值得特别关注。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公开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多次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关于“共同防御”的规定适用于钓鱼岛,美国还一再声称其立场始终如此,从未发生改变。但在中菲南沙岛礁争议问题上,美国刻意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否涵盖南沙争议岛礁的问题上保持模糊态度,一再拒绝在是否协防南沙的问题上向菲律宾作出明确的安全承诺。
同样作为美国的亚太地区盟友,同样针对中国,为什么美国愿意向日本做出明确的同盟承诺,而拒绝向菲律宾做出明确的同盟承诺?对此,吴志成与陈一一提出,可以从美菲与美日同盟条约、美国战略目标差异以及菲日两国对美政策影响力等制约双边关系的基本因素来进行分析,这为理解美日、美菲同盟差异提供了一定的思路。②吴志成、陈一一:“美国在黄岩岛与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缘何不同?”《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第35-40页。但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同盟关系的存在如何影响同盟一方与第三方的领土主权争端?一国会在什么情况下介入同盟国与第三方的领土争端?同盟的介入或者不介入又会对争端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同盟政治与领土争端
领土争端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对同一块领土均宣称拥有主权从而造成的冲突和纠纷。领土争端一般都涉及敏感的主权问题,如果争议领土还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的话,争端当事方很难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妥协和退让,因领土而起的争端也就具有持久性和破坏性的特征,容易引发国家间的敌对和冲突。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争端解决结果,争端双方都会试图提升本国的军事实力,加强对争议领土的控制,威慑对手不要采取进一步侵占行动。
军事实力的提升,既可以通过加强军事部署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强化同盟来实现。同盟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③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1,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68, pp.268-271.同盟关系一旦组建,当盟国与其他国家发生争端或冲突时,一国就有义务对其盟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这种援助既可以包括外交方面的支持,比如积极声援或严守中立,也可以包括军事方面的支持,比如提供武器装备或直接军事介入等。同盟国一旦违背自己的援助义务,不仅会对盟友及同盟一方的生存与安全利益造成损害,还可能对本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以至于将来在本国受到攻击时不能获得其他盟友的援助。
关于同盟关系如何影响领土主权争端,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同盟内部的领土主权争端。根据保罗·胡思(Paul Huth)的研究,领土争端分为三个部分:产生、升级和解决。尽管同盟关系的存在并不足以阻止领土争端的产生,也就是说,即使是同盟国家之间也可能存在领土纠纷,但是,同盟关系能够缓和彼此之间的对立,加强相互的沟通与协调,防止领土问题发展成为长期的、严重的军事冲突。此外,同盟关系还有助于领土争端的解决。因为双方存在着共同的安全利益,而领土问题上的妥协是维持同盟关系与加强安全合作必须付出的代价。①Paul K Huth, Standing Your Ground: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160-163.
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共同的威胁消失,同盟一方不再认为对方对本国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时,领土问题上的合作需求就会大大降低。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中越两党结成了“同志加兄弟”的友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也多次表态支持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公开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军撤出越南,苏联加强对越援助,中越矛盾越来越突出,实现统一的越南很快背离了原来的立场,派军占领了原为南越当局侵占的南沙岛礁,并进一步扩大到对中国西沙和南沙全部岛礁提出主权要求。②相关研究参见唐慧云:“1950—1979年间中越同盟中的苏联因素”,《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7-12页。
另一种是同盟一方与第三方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这种情况更为复杂,既包括同盟内部的分歧,也包括同盟与争端第三方之间的冲突。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争议领土是否属于同盟义务规定的范围?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存在着共识?同盟双方在如何解决领土争议问题上是否存在着一致的看法?是通过武力实现还是主张和平谈判?同盟一方是否会介入盟友与第三方的领土争端?同盟一方如何平衡受盟友牵连的风险与被盟友抛弃的风险?同盟的介入,以及通过何种方式介入又会对领土争端的未来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激化争端还是缓和冲突?
传统威慑理论认为,同盟关系本身便是一种威慑,同盟关系的存在可以向对手传递彼此合作的信息,增加威慑的可信度,减少领土冲突的风险。托林·怀特(Thorin Wright)和托比·赖德(Toby Rider)指出,防御性同盟能够有效地威慑敌对方的侵略行为和进攻意图,因为同盟的存在增加了敌对方挑起冲突和战争的成本。即使是在领土争端这种涉及重大利益、极易引发冲突的问题上,防御性同盟也能够对敌对方的进攻行动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③Thorin M.Wright and Toby J.Rider, “Disputed Territory,Defensive Alliances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31, No.2, 2014, pp.119-144.但在保罗·胡思看来,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同盟关系的威慑作用非常有限。因为争端国一旦在领土问题上遭到挑战,其盟友很难在短时间内向其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争端对方的意图并不是发起大规模的、全面的军事进攻,而只是为了实现有限的领土目标。④同①,pp.118-119.换言之,如果争端另一方的目的只是为了占领特定地区的争议领土,那么,除少数情况外,这种行为一般不会对同盟的生存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军事介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不会那么强烈。
除威慑作用外,同盟关系的存在还可能激化现有的领土争端,提升冲突与战争的风险。一方面是因为,当争端当事国在领土问题上寻求外部联盟的援助时,容易造成争端另一方的不安全感,从而产生安全困境,提升了威胁的感知和冲突的风险。⑤John Vasquez, The War Puzzle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68.另一方面,同盟关系的存在还可能会鼓励盟友主动采取武力升级措施,或是在领土谈判中要价过高,因为它会期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盟友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剧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同盟国家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迫卷入与自己无关、但涉及盟友的领土主权争议中。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同盟的功能除了共同抵御外部威胁外,还包括约束盟友的行为,约束的目的在于防止盟国采取有损本国安全利益的行为。比如,在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认为,国家间结盟是安全(security)与自主(autonomy)之间的交换。大国在向小国提供安全保证前,会要求对小国的行为施加一定的控制,从而减少同盟牵连的风险。⑥James D.Morrow, “Alliance: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No.1, 2000, p.79.金(Tongfi Kim)也提出,同盟陷阱(entrapment)在现实政治中是很少见的事情,受到同盟连累的国家往往是小国和弱国。因为在不对称同盟中,大国如果担心受到小国盟友冒险军事行动的牵连,因其本身具备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它会在同盟条约中对同盟义务的性质和启动同盟的条件进行明确的规定,以避免日后受到连累。①Tongfi Kim, “Why Alliances Entangle But Seldom Entrap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20, 2011, pp.350-377.
从上述分析来看,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影响是复杂和多重的,同盟关系的存在,无论在威慑对手方面还是在鼓励盟友方面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其效果取决于同盟介入的程度和介入的意愿。而同盟介入的程度和意愿又取决于其如何权衡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领土争端是否属于同盟义务规定的范围?第二,同盟一方能否从介入争端中获益,特别是在同盟条约没有明确规定援助义务的情况下?第三,同盟一方如何评估介入争端可能产生的同盟牵连风险?只有当盟友的领土争端涉及本国重大的安全利益时,同盟一方才会介入争端,主动承担同盟牵连的风险。
首先,同盟具有不同的类型,同盟条约规定的差异决定着一国是否有义务介入盟友的军事冲突。②Brett Ashley Leeds, “Do Alliance Deter Aggression?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Alliances on the Initiation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47, 2003, pp.427-439.如果同盟条约对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援助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那么该国介入领土争端的可能性会更高,在领土问题上支援盟友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同盟的建立和维持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愿意履行同盟承诺的国家才会组建同盟。③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4, 2003, p.805.另外,根据布雷特·利兹(Brett Leeds)等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盟友都会履行援助义务。同盟的可靠性基于同盟条约明确规定了启动同盟义务的条件以及应当采取的行动。④Brett Ashley Leeds,Andrew G.Long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 Reevaluating Alliance Reliability: Specific Threats,Specific Promi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4, No.5,2000,pp.686-698.如果一国在条约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拒不履行同盟义务,它将面临着较高的违约成本,这对大国和小国来说都是如此。大国拥有更多的盟友,一旦失信于某一盟友,它将付出极高的声誉代价;小国高度依赖大国的安全保护,一旦不履行同盟承诺,容易面临被大国抛弃的风险。
反之,如果同盟条约没有对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援助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即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行动空间,那么该国介入领土争端的可能性会降低,在领土问题上支援盟友的可能性也会减少,这点对于大国来说尤其如是。比如,王石山等基于其研究提出,美国是否援助危机中的盟国是附带条件的,当危机并不直接涉及美国的同盟义务时,或者说美国在是否履行同盟义务的问题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时,美国援助盟友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⑤王石山、韩召颖:“美国为何援助国际危机中的盟国(1946—2006)”,《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第107-134页。
其次,同盟一方是否会介入盟国的领土争端取决于它能否从介入争端中获益。一般而言,一国是否会履行同盟承诺介入盟国的冲突,主要取决于介入的收益是否会超过介入的成本,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果军事介入的成本较低,也就是说,介入能够轻易地帮助盟友取得胜利,那么该国介入的意愿就会越高。二是,如果介入的收益越高,该国介入的意愿也会越高。三是,如果不介入的损失较大,比如同盟关系遭到破坏甚至失去盟友,那么介入的必要性也会增强。⑥James D.Morrow, “Alliance: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No.1, 2000, pp.63-83.
如上所述,如果同盟条约对援助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那么盟国介入领土争端的可能性越高。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履约将面临较高的声誉损失,还因为履约有助于维持和强化同盟关系,巩固双方在争议问题上的合作。如果同盟一方违背其同盟义务,拒绝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援助盟友,可能会承担损失盟友的风险。同盟关系越重要,盟国履约的意愿就越强烈,介入争端的积极性也越高。
反之,如果同盟条约没有对援助义务进行明确规定,但是同盟一方认为维持同盟关系至关重要,或是介入争端能够获得显著的收益,且不介入的损失较大,那么该国介入争端的可能性也越高。以美国出兵朝鲜战争为例,二战结束之际,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军,并将南朝鲜划在美国的太平洋“环形防线”以外,南朝鲜一旦遭到攻击,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和联合国的集体行动”,即否认了美国对南朝鲜的援助义务。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认定北朝鲜的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因此改变了原来不予援助的立场,决定立即进行全面军事干预以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①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36-55页。
最后,在介入领土争端的问题上,同盟一方除了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外,还需要承担必要的成本,特别是同盟牵连的风险。同盟一方最终是否介入争端,取决于其如何评估同盟牵连的风险和成本。同盟牵连指的是一国因为同盟义务不得不援助盟友从事代价高昂、但获益甚少的事业。②Tongfi Kim, “Why Alliances Entangle But Seldom Entrap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20, 2011, p.355.同盟牵连的实质是一国出于道德、法律或声誉上的考虑选择维持同盟承诺,卷入盟友的军事冲突,通常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③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4, 2015, p.12.
一般而言,如果盟友的领土争端与本国的利益关涉不大,或者说盟友的重要性不够突出,那么为了减少同盟牵连的风险,同盟一方会尽力逃避同盟义务,或是尽可能地维持同盟承诺的模糊性,避免直接介入盟国与第三方的领土争端。这点对于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提出,大国可以通过在盟约中设定规避性条款、逃避代价过于高昂的同盟义务(比如只提供外交而非军事援助,只提供空中掩护而非地面部队)、维持同盟的多元化(一国的挑衅性行为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共同约束),以及使用明确的同盟承诺来威慑对手并阻止盟国主动挑起冲突等,降低本国卷入盟国军事冲突的风险。但是,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不会因为同盟而卷入军事冲突。只是表明,大国在选择军事介入时,同盟义务并不一定是其主要的考虑,大国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以美国为例,二战以来的六十余年间,美国一共与60多个国家签署了同盟协定,但只有五次清楚地表明美国被卷入盟国的军事冲突中,分别是1954年和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越南战争、20世纪90年代的波斯尼亚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在这些屈指可数的案例中,美国援助盟友都是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对同盟的义务。④同③,pp.7-48.
反之,当盟友的领土争端涉及本国重大的安全利益时,即当争议领土的价值或者同盟的重要性超越了同盟牵连的成本时,那么无论盟约是否规定或者如何规定,该国都会选择介入争端,主动承担同盟牵连的风险。比如一战前夕,德国向俄国宣战后,法国履行其对俄同盟义务也向德宣战,但作为协约国的一方,英国迟迟未能宣布参战。直到德国违背《伦敦条约》入侵低地国家比利时、直接威胁英吉利海峡的安全时,英国才最终下定决心向德国宣战。战争态势的变化对英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决定了英国参战态度的转变。
以中日钓鱼岛问题和中菲南海争端为例,尽管美国一再表示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主张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美国事实上对日本和菲律宾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多次公开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另一方面,拒绝将南沙岛礁及黄岩岛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美国之所以在两个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同盟条约规定的差异。《美日安保条约》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均规定美国共同防御的义务为日本/菲律宾管辖下的领土,但是美国基于“第27号令”和《归还冲绳协定》承认钓鱼岛为日本管辖下的领土,从而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围。相反,美国从未正式承认菲律宾对其主张的部分南沙岛礁①菲律宾称“卡拉延群岛”。和黄岩岛拥有主权或管辖权,从而将它们排除在美菲共同防御的范围之外。第二,同盟的性质以及利益上的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支援盟国的意愿。在南海问题上,由于菲律宾实力较弱,在分担美国全球及地区战略重任方面有限,美国并不愿向菲律宾做出明确的安全承诺,以免日后承担过于高昂的同盟牵连风险。相反,从当前来看,无论是美日同盟,还是钓鱼岛本身,对美国的战略价值都远远超过了美菲同盟和南沙岛礁。这也意味着美国介入钓鱼岛问题的意愿和程度都远远超过中菲南海争端。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利益,都促使美国自愿承担同盟牵连的风险,甚至随着局势的变化进一步强化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支持态度。下文将分别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具体说明。
二、美日同盟与中日钓鱼岛争端
钓鱼岛问题原本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主权争议,但是钓鱼岛问题的出现与美国二战后的对日政策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美国是钓鱼岛争端的“直接参与者”。②M.Taylor Fravel, “Explaining Stability in the Senkaku (Diaoyu) Islands Dispute”, in Gerald L.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Jisi Wang eds.,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 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0,p.147.尽管美国一再淡化它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角色,认为这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深度介入”了钓鱼岛争端。正是因为美国占领琉球群岛后,有意通过行政管辖和相关军事活动将钓鱼岛和琉球群岛捆绑在一起,才造成了今天的中日钓鱼岛纠纷。③Jean-Marc F.Blanchard, “The U.S.Rol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1945-1971”,the China Quarterly, No.161, 2000, p.120.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还多次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公然违背其在主权问题上的中立立场。
美国承诺钓鱼岛属于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围,首先是源于同盟义务的规定。因为从同盟条约内容的解读来看,《美日安保条约》规定共同防御义务涵盖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而美国承认钓鱼岛为“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因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一看法不仅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共识,也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这也是美国无法在钓鱼岛问题上置身事外的重要原因。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虽未明确提及钓鱼岛问题,但二战结束后钓鱼岛作为美军的训练基地一直处于美国的军事托管之下。到了1953年12月,美国代表琉球民政府发布“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限的公告”(即“第27号令”),错误地将钓鱼岛划入美国托管琉球群岛的地理范围。这一公告将钓鱼岛问题与琉球群岛的未来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也成为后来中日主权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0年1月,美日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U.S.and Japan,以下简称《美日安保条约》),修改了两国曾于1951年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日安保条约》除了确认美国继续享有在日本驻军和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外,还废除了美军干涉日本内部事务的条款。其中第五条还规定,双方认为,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上针对缔约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都是对本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双方承诺将根据本国宪法规定的条款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④“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nuary 19, 1960,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q&a/ref/1.html.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日本国内要求“冲绳归还”的舆论呼声也越来越高。1971年6月,经过近两年时间的谈判,美日最终达成《归还冲绳协定》(Okinawa Reversion Agreement),规定美国将琉球群岛及大东群岛的行政管辖权归还给日本,并在《谅解备忘录》中按照琉球民政府“第27号公告”的内容,以经纬度坐标的方式将钓鱼岛明确标识在归还的地理范围内。面对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称,虽然美国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交还日本,但是美国在岛屿主权争议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美国将行政管辖权交还给日本并不表明美国偏向争端中的任何一方①Mark E.Manyin, “ The Senkakus ( Diaoyu/Diaoyutai)Dispute: U.S.Treaty Oblig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2761,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October 14, 2016, https://fas.org/sgp/crs/row/R42761.pdf.。美国国务卿威廉姆·罗杰斯(William Rogers)还表示,《归还冲绳协定》并不影响这些岛屿的法律地位。协定生效之后,这些岛屿的法律地位与协定签署之前的法律地位保持一致。②Jean-Marc F.Blanchard, “The U.S.Rol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1945-1971”,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1, 2000, p.120.
尽管美国做出了上述中立表态,但是美日同盟条约所确立的美国援助日本的义务明确将美国与钓鱼岛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美国通过“第27号令”以及《归还冲绳协定》承认钓鱼岛为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因此符合《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规定,一旦有第三方使用武力夺取日本实际管辖和控制的钓鱼岛,美国就有义务援助日本。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也没有逃避其对日同盟义务,多次公开表态承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有分析称,美国自小布什政府时期才开始承认钓鱼岛为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围③郭永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第111-117页。,但事实上早在1971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态。197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威廉姆·罗杰斯在参议院关于“归还冲绳协定”的听证会上明确表示,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归还给日本的领土,其中包括钓鱼岛。④Tongfi Kim,“US Alliance Obligations in th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Issues of Applicability and Interpretations”,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Report, No.141, 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2016, p.8, https://www.hsfk.de/fileadmin/HSFK/hsfk_publikationen/prif141.pdf.
在随后出现的数次钓鱼岛危机中,美国的上述立场一再得到确认和证实。1996年7月,日本右翼组织“日本青年社”登上钓鱼岛,建立了一座太阳能灯塔,并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其为正式的航标。8月,日本另一右翼组织登上钓鱼岛,在灯塔附近竖立一面日本国旗。9月,中国香港和台湾民间群体多次组织赴钓鱼岛的保钓运动。这一系列行动引发了新一轮的中日钓鱼岛纷争。9月,《纽约时报》引用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话表示,美国军队没有义务因为《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介入钓鱼岛的争端。这一表态引发了日本方面的担忧。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和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副助理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均对此作出了反驳,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问题。⑤同④。
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先后与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日本海上保安厅随后以“涉嫌妨碍公务”为由逮捕了中国渔船船长。中国对此提出严正抗议并与日方多次交涉,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局面。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会见日本外相前原诚司(Seiji Maehara)后公开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是美国对日承诺的一部分。⑥Hillary Clinton,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U.S.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7,2010,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 /10 /150110.htm.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后,中国随即采取反制措施,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定期巡航,并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岛屿的领海基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2014年4月,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表示,美国对日本的同盟承诺是毋庸置疑的,《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日本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其中包括钓鱼岛,这也是美国总统首次就钓鱼岛问题作出这样的公开表态。
其次,美国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不仅是美日同盟条约的规定使然,也是因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利益,无法对中日纠纷置之不理。具体来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有赖于日本提供军事基地和各种辅助设施,其中琉球群岛的作用不可忽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就开始在日本驻军,将琉球群岛视为其远东战略防线的重要环节,并私自将钓鱼岛也纳入其中。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作为美国军事后勤基地的作用更为突出,也加速了美国对日媾和的进程,“旧金山和约”确立了美国对琉球群岛等岛屿的托管制度。在美国看来,将这些岛屿置于战后美国的托管之下而不是交给日本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极为重要。为此,美国需要获得对琉球等群岛的“排他性战略控制权”。因为“一旦琉球落入苏联或共产主义中国手中,将会危及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网络。”①Jean-Marc F.Blanchard, “The U.S.Role in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1945-1971”, the China Quarterly, No.161, 2000, pp.102-109.美国军方还认为,这种排他性的控制权应当包含整个琉球群岛。任何一个小岛一旦被分割出去,都会对美国在关键岛屿的军事存在构成严重的威胁。②同①,p.104。这也是战后美国将钓鱼岛划入琉球群岛地理范围的重要原因。
20世纪60年代,美国之所以同意与日本就“归还琉球”问题进行谈判,也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利益密切相关。因为面对日本国内不断要求“归还冲绳”的舆论压力,美国意识到冲绳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对美日安全合作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美日安保条约》将于1970年到期,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去留将成为问题。为了防止日本本土及冲绳岛内的反美情绪影响到《美日安保条约》的存续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美国同意尽快归还冲绳。1969年11月,尼克松与佐藤荣作发表联合声明,约定美国将在其军事基地功能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归还冲绳。③王新生:“佐藤政权时期‘冲绳归还’的政治过程”,《日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154页。
1971年6月,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事实上肯定了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这明显是偏袒日本的表现。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继续维持美日安保体制。尽管当时尼克松政府已经在谋求改善对华关系,但是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改变。事实上,美日在签署《归还冲绳协定》的同时还秘密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规定美国在归还岛屿的“行政管辖权”后还可以继续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其中就包括钓鱼群岛中的黄尾屿和赤尾屿。④崔修竹、崔丕:“美日返还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施政权谈判中的钓鱼岛问题”,《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第19-22页。
其二,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基石,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钓鱼岛问题也成为美国拉拢日本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与美菲同盟不同的是,美日同盟不再是冷战初期“美国提供安全保护、日本提供军事基地”这种单向的依附性同盟,日本对美国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日本能够为美国提供东亚的军事基地,还体现在日本能够积极配合美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联合军事行动。⑤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第12-13页。这从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经历的三次大调整中就能看得出来。每一次调整都扩大了美日同盟的适用范围,从最初的专守防卫扩大到“周边事态”,再扩展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⑥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第29页。,日本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同盟内部的影响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冷战期间被共同安全利益掩盖的美日经济矛盾逐渐突出,克林顿政府奉行贸易优先政策,在贸易和市场问题上频繁向日本发难,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一度遭到质疑。然而,朝核问题和台海形势的发展,促使美国重新审视日本的战略价值。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出台了《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日关系是美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对实现美国太平洋地区安全政策和全球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并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推行亚太安全政策的关键”。①“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03052174.1996年4月,美日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重新定义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将美日同盟的目标从冷战时期的“遏制苏联扩张”发展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②“Japan-U.S.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pril 17, 1996,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1997年9月,两国公布了新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提出了“周边事态”的概念③“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Defense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September 23, 1997,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19970923.html.,大大扩展了日本军事力量在日本周边地区活动的范围和方式。
小布什政府时期,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通过修改国内立法,突破了“和平宪法”关于直接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限制。此外,日本还积极配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三法案”。2004年2月,日本向伊拉克派遣550人组成的陆上自卫队以执行人道救援任务,这也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通过反恐合作,美日同盟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美日安全合作的范围也从日本的“周边事态”扩大到印度洋和中东地区。
奥巴马上任初期,美日同盟曾因为普天间机场搬迁、民主党追求对等外交等问题出现过短暂的“漂流”,但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后,积极向美国靠拢,全力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同盟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升级。④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第26页。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和财政预算削减的情况下,美国也鼓励盟友日本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2015年4月,美日公布了新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解除了日本自卫队行动的地理限制,将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并强调了两国从和平时期到紧急事态各个阶段的无缝合作,其中就包括日本极力主张的“灰色地带事态”,这也意味着美国几乎无法在中日钓鱼岛冲突中置身事外。⑤Ian E.Rinehart, “ New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Deepen Alliance Cooperation”, 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 Reports,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April 28, 2015, https://fas.org/sgp/crs/row/IN10265.pdf.
其三,除了安抚日本外,中国因素也是美国介入钓鱼岛争端的重要考量。尽管钓鱼岛问题与美日同盟强化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中国崛起无疑是美日同盟强化的重要诱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钓鱼岛问题是“重塑美日同盟的外在动力”。⑥苗吉:“日本钓鱼岛政策及其走向”,《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1期,第50页。钓鱼岛是中国突破西太平洋岛链的咽喉⑦史春林、李秀英:“美国岛链封锁及其对我国海上安全的影响”,《世界地理研究》,2013年第2期,第6页。,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维持介入的态势,将对中国形成有效的制衡。此外,美国还担心,一旦在钓鱼岛问题上置身事外,美国的安全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按照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的观点,一国在决定是否介入盟国的军事冲突时,除了需要考虑介入的成本与收益外,还需要考虑不介入可能造成的损失。如果不介入的损失较大,那么该国介入的必要性也会相应提升。⑧James D.Morrow, “Alliance: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No.1, 2000, pp.63-83.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果美国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向日本提供支援,就会引发地区国家对其同盟承诺可信度的担忧以及对其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能力的质疑。一旦地区国家对美国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失去信心,就可能抛弃美国,选择追随中国。美国还担心,如果不对中国在东海地区的行为及时采取针对措施,就会鼓励中国在南海地区也采取类似的“过激”行动。⑨Bonnie Glaser, “US Interests in Japan’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s wi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7th Berlin Conference on Asian Security, Berlin, July 1-2,2013,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https://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projekt_papiere/BCAS2013_Bonnie_Glaser.pdf.因此及时表明美国的立场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来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强化对日承诺的重要原因。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日援助承诺存在漏洞,日本对此也深感担忧。因为按照同盟条约的规定,美国对日同盟义务包括“日本管辖下的所有领土”,但是美国要求日本承担保卫其领土的首要责任。也就是说,一旦日本失去了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美国就可借此逃避对日援助义务。①Yoichiro Sato, “The Senkaku Dispute and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Pacific Forum, No.57, 2012, p.1.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后,中国大幅增加了钓鱼岛附近的海上巡逻和海上执法行动,实现了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常态化护渔巡航。中国这一做法意在挑战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是对美国对日同盟承诺可信度的一种考验。②Mrak E.Manyin, “The Senkakus(Diaoyu/Diaoyutai) Dispute: U.S.Treaty Oblig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2761, October 14, 2016, p.7, https://fas.org/sgp/crs/row/R42761.pdf.
为了缓解日本方面的担忧,美国一再偏离其在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进一步强化了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多次声明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领土现状的行动,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2012年,美国国会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明确表示,任何第三方的单边行动都不会影响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拥有行政管辖权的立场,美国遵守《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的对日同盟义务。③United States Congress,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3, Public Law 112-239, January 2, 2013, U.S.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https://www.gpo.gov/fdsys/pkg/PLAW-112publ239/html/PLAW-112publ239.htm.2013年1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会晤到访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时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反对任何损害日本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④“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Fumio Kishida After Their Meeting”, U.S.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9, 2013,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3/01/203050.htm.2013年11月,美国批评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行为是在“改变地区现状”,只会“引发地区危机和冲突”。⑤“Statement on the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U.S.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23,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11/218013.htm.
三、美菲同盟与中菲南海争端
菲律宾对南海岛礁的侵占始于“二战”结束之后。1956年,菲律宾人托马斯·克洛马(Tomas Cloma)宣称“发现”了南沙群岛并占领了其中33个岛礁,将其命名为“卡拉延群岛”(Kalayaan Island Group)。自1970年开始,菲律宾政府先后占领了南沙群岛中的马欢岛、费信岛等8个岛礁。1978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布第1596号总统令,正式将南沙33个岛礁纳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置于巴拉望省行政管辖之下。同钓鱼岛问题一样,美国在南沙主权争议问题上持中立立场,支持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然而,在同盟义务问题上,尽管菲律宾多次主张将南沙岛礁纳入美国对菲同盟义务的范围,但是美国一再拒绝做出类似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所获得的同盟承诺。一方面是因为美菲同盟条约的模糊规定,赋予了美国在同盟承诺问题上的灵活操作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菲律宾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及日本,美国协防南沙群岛的意愿并不强烈,不希望为此承担同盟牵连的风险。
1)课堂互动系统主要是建立教师计算机与学生手机之间的通信联系,实现对手机的屏幕广播、手机屏幕监看、教学互动、答疑指导等功能,达到对课堂教学的组织与实施[3]。
首先,从同盟条约的解读来看,《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沙争议岛礁存在着模糊性。⑥Tongfi Kim,“US Alliance Obligations in th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Issues of Applicability and Interpretations”,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Report, No.141, 2016, p.3, 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https://www.hsfk.de/fileadmin/HSFK/hsfk_publikationen/prif141.pdf.美国国会研究报告也指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没有明确规定美国必须在争议海域问题上援助菲律宾。⑦Thomas Lum and Ben Dolv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U.S.Interests-201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May 15, 2014, p.12,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s://fas.org/sgp/crs/row/R43498.pdf.这也意味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逃避同盟义务的空间。从实践来看,无论是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还是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美国给予菲律宾的只是有限的外交支持,拒绝将美菲共同防御义务扩大到南海争议岛礁。
1951年,美菲缔结《美菲共同防御条约》(U-nited States-Philippines Mutual Defense Treaty),其中第四条规定“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任何一方的武装进攻会被视为对本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双方承诺将根据本国宪法规定的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从内容上看,《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美日安保条约》相差不大,但是细节的差异决定了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和中菲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美日安保条约》将共同防御的范围限定为“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由于美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因而自然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共同防御的范围。但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五条将美菲共同防御的目标限定为太平洋地区“对缔约国本土的进攻”“对缔约国管辖下的太平洋岛屿的进攻”,以及“对缔约国在太平洋上的军队、船舶或飞机的进攻”。
由于美国从未认可菲律宾对南沙争议岛礁或黄岩岛拥有主权或管辖权,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菲律宾主张的南海岛礁并不符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五条中前两项“菲律宾的本土”或“菲律宾管辖下的太平洋岛屿”的定义。特别是菲律宾直到1978年才正式宣布将其主张的“卡拉延群岛”划入菲国土范围内,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于1951年签署,所以美国完全可以主张它的条约义务不包括南海争议岛礁。至于第五条的第三项,即菲律宾驻守在南海争议岛礁上的军队遭受攻击时,美国也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定。1975年6月9日,基辛格在发给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及美驻菲使馆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只有当这些军队是出于集体防卫的目的并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美国才会进行援助。基辛格还进一步指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没有给予任何一方绝对的安全保证,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都不能指望,当其部署在太平洋任意地区的军事力量受到第三方攻击时都能获得对方的援助。①Jay L.Batongbacal, “EDCA and the West Philippine Sea”,Rappler, December 12, 2014, http://www.rappler.com/thoughtleaders/77823-edca-west-philippine-sea-america.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美国对华制衡力度的加大,美国进一步明确了在第五条第三项上的立场。2019年3月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在与菲律宾外长洛钦(Teodoro Locsin)会晤时表示,由于南海是太平洋的一部分,任何对菲律宾在南海的军队、飞机或船舶的武装进攻,都将触发美菲同盟条约的共同防御义务。②Michael R.Pompeo, “ Remarks With Philippine Foreign Secretary Teodoro Locsin, Jr.”, U.S.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3/289799.htm.这也是美国高层官员首次做出这样的表态,但是这一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为菲律宾在南海的行为“广开绿灯”。只有菲律宾在南海遭受其他国家的“武装进攻”时,美国才会根据国内宪法规定的程序启动同盟援助义务。因此,只要中国避免首先在南海问题上对菲直接使用武力,美国是否协防南沙、如何协防南沙就是未定数。鉴于此,洛钦在同一场合也表示,“太过模糊的承诺会导致人们质疑承诺本身的可靠性。目前来看,帮助菲律宾发展自我防御能力才是正解。”③同②。
鉴于条约规定的模糊性和可操作空间,美国一直拒绝将菲律宾主张的南海岛礁纳入美国对菲同盟义务的范围,这从历次南海争端升级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1995年“美济礁事件”发生后,菲律宾加强了在其主张的南沙岛礁上的军事部署和附近的军事活动,中菲南沙争端明显升级。美国国务院随后发布了“南沙及南海政策声明”,表明美国在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强调其利益在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丝毫没有提及美国对菲同盟义务的问题。④Christine Shelly, “U.S.policy on Spratly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U.S.Department of State, Daily Press Briefing, May 10,1995,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l.2012年4月,中国海监船和渔政船与菲律宾海军护卫舰“德尔皮拉尔”号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发生对峙事件。在中菲对峙期间,正值美菲举行首次“2+2”会谈,菲律宾希望借此获得美国在黄岩岛问题上援助菲律宾的承诺,但是这一努力显然没有成功。①Tongfi Kim,“US Alliance Obligations in the Disput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Issues of Applicability and Interpretations”,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Report, No.141,2016, p.21, the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 https://www.hsfk.de/fileadmin/HSFK/hsfk_publikationen/prif141.pdf.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会后重申了美国的利益在于航行自由与地区和平稳定,她还表示美国将与菲律宾就这一事态进行紧密磋商,但仍然没有提及军事援助问题。②Hillary Clinton, “Remarks with Secretary of Defense Leon Panetta, Philippin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Rosario, and Philippines Defense Secretary Voltaire Gazmin After Their Meeting”, U.S.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30, 2012,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4/188982.htm.
事实上,菲律宾方面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菲律宾学者称,菲律宾很难从美国那里获得像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那样的安全承诺。因为如果美国想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积极和坚定,它早就会与菲律宾制定出类似《美日防卫合作指针》那样的文件来明确其承诺。③Maria Ortuoste,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Out of Time, Out of Options?”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1, 2013,p.244.
其次,如上文所述,当领土争端超出同盟义务的规定时,美国是否介入取决于风险与收益的考量。只有当介入的收益超过牵连的成本时,美国才会考虑将同盟承诺扩大到南沙争议岛礁。菲律宾由于军事实力较弱,在美菲同盟体系中一直居于从属地位,并没有向日本那样发展出与美国逐渐对等的同盟关系。菲律宾过去不仅严重依赖美国的外部安全保护,甚至在内部安全问题上也需要美国帮助打击国内的恐怖主义和叛乱势力,比如美军曾协助打击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极端主义组织等。在不对称同盟中,只要美国掌握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如何解释它的同盟义务就取决于美国的利益需要。
从美菲同盟演变的历史来看,菲律宾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步下降,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一度将军队撤出在菲律宾的基地,直到2014年才通过轮换部署的形式重新回到菲律宾。即便如此,美菲军事合作的水平和程度也远不及美日合作。此外,菲律宾宪法还禁止外国军队在菲律宾设立军事基地,也进一步限制了美菲军事合作的深化。因此,与美日同盟和钓鱼岛问题相比,美国协防南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不强烈。
具体来看,冷战期间,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曾是美国西太平洋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在遏制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菲律宾还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菲关系日渐走向疏离,双方的战略目标也出现分歧。美国希望借助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抗衡苏联的势力,但在马科斯及其继任者阿基诺看来,美国的军事存在更像是一种要求美国援助的筹码,而不是维护菲律宾国土安全的保障。④Richard D.Fisher, Jr., “ Rebuilding the U.S.-Philippine Allianc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No.12, 1999, p.3.同时由于忙于应对国内的叛乱和政变,菲律宾越来越难以在军事上向美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分担美国地区和全球战略重任方面作用有限。
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对美国的重要性大为降低。1990年,菲律宾政府借“美菲军事基地协议”到期需要重新谈判之际,要求美国提高驻菲军事基地的租金和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但事实证明,菲律宾错误地高估了冷战后它在美国全球军事部署中的重要性。⑤Renato Cruz De Castro, “Special Relations and Alliance Politics in Philippine-U.S.Security Relations, 1990-2002”, Asian Perspective, Vol.27, No.1, 2003, pp.144-146.美国拒绝了菲律宾的要求,将军队完全撤出了菲律宾,结束了在菲律宾近一个世纪的军事存在,美菲同盟也陷入停摆状态。
1995年“美济礁事件”发生后,菲律宾重新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存在对维持东南亚地区均势的重要性。1998年2月,经过两年多的谈判,美菲达成《访问部队协议》(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这一协议允许两国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并准许美国军舰访问菲律宾港口。双方还借此恢复了中断数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菲律宾公开支持美国的全球反恐行动。2002年11月,美菲签订《后勤支援互助协议》(Mutual Logistics Support Agreement),规定菲律宾可以为在菲领土范围内外行动的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保障。2003年6月,菲律宾向伊拉克派出人道主义救援团队。然而在2004年7月,阿罗约政府因“伊拉克人质事件”决定提前撤军,遭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厉批评,美菲关系再次受挫。“伊拉克人质事件”凸显出美菲同盟的利益分歧。这也从侧面说明,菲律宾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和实力不足的限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开展和推进助益有限。①Mely Caballero-Anthony, “Beyond the Iraq Hostage Crisis:Re-assessing US-Philippine Relations”, IDSS Commentaries, July 28,2004.
直到奥巴马政府宣布将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之后,菲律宾对美国的重要性才再次得到凸显。阿基诺三世政府积极配合美国的“再平衡”政策,美菲同盟关系得到强化。2014年4月,美菲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规定美军可以通过轮换部署的形式进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强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也正是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程度不断加深,公开声明南海航行自由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②“Speech of Hillary Clinton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larger ASEAN Regional Forum”, U.S.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3,2010,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 /07 /145095.htm.。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也拒绝在协防南沙的问题上向菲律宾做出明确保证,充分说明菲律宾重要性的提升程度还不足以让美国扩大对菲的安全承诺。
与钓鱼岛问题不同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兴趣是近些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以及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才逐渐变得突出的。美菲同盟强化以及菲律宾重要性的提升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调整的结果而非原因。美国介入南海争端主要是因为担心中国的“断续线”主张和南海岛礁建设会损害其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而非对菲同盟义务。当前,美国主要通过“航行自由行动”来挑战中国的南海主张,并不愿意因为同盟义务而被迫卷入中菲之间的领土冲突。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排除通过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介入南沙争端的可能性。因为一旦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存在危及美国的航行自由和海上霸权地位,美国就有可能借助美菲同盟的名义扩大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和安全承诺。正如蓬佩奥近期在美菲同盟义务上的最新表态③Michael R.Pompeo, “ Remarks with Philippine Foreign Secretary Teodoro Locsin, Jr.”, U.S.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3/289799.htm.所显示的那样,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全面开展,以及菲律宾“疏美亲中”倾向的加剧,美国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对菲同盟义务,以试图拉拢菲律宾配合美国在地区范围内制衡中国的行动。但是,美国未来将如何履行这一同盟承诺,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结 语
美国的海上霸权地位依赖于全球公共海域的开放及其军事力量的自由投射。东海和南海作为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美国自然不会置之不理。美国时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在参议院作证时指出,美国在东海和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利益,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畅通无阻的合法贸易、尊重国际法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他还表示,美国在主权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是争端解决的方式影响着美国的国家利益。④Daniel R.Russel,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U.S.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5, 2014, https://2009-2017.state.gov/p/eap/rls/rm/2014/06/228415.htm.尽管做出了上述中立表态,美国还是通过对日和对菲同盟义务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
美日同盟和美菲同盟均起源于冷战初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美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介入程度却不尽相同。美国在承认钓鱼岛为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同时,拒绝将菲律宾主张的南沙岛礁和黄岩岛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美国之所以在盟国的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上采取不同的协防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美菲同盟条约留下了不同的解释空间,美国完全可以借此逃避其在南海问题上的同盟义务;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同盟利益和安全利益要远高于美国在中菲南海争端问题上的利益,这也意味着,尽管存在同盟牵连的风险,美国介入东海争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远高于南海争端。
那么,美国的同盟承诺以及同盟承诺的差异又是如何影响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争端呢?傅泰林(Taylor Fravel)提出,美日同盟的威慑效应,是中日围绕钓鱼岛争端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关键原因。①M.Taylor Fravel, “ Explaining Stability in the Senkaku(Diaoyu) Islands Dispute”, in Gerald L.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Jisi Wang eds.,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 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0, p.160.莱谢克·布斯恩斯基(Leszek Buszynski)也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维护南海局势稳定,防止领土争端升级的主要原因。②Leszek Buszenski, “ASEAN, the Declaration on Conduct,and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5, No.3,2003,pp.343-362.但是,这种观点过于夸大了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效应,低估了争议领土问题上同盟牵连的风险,也忽视了同盟承诺的差异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安迪·叶(Andy Yee)就指出,美国在领土争端上对盟友的支持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即在促进南海争端当事国加强谈判与合作的同时加剧了东海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冲突。③Andy Yee,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No.2, 2011, p.189.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也表示,美菲同盟条约的模糊和含混,不仅不会对对手构成有效的威慑,反而会在危机出现时制造困惑和混乱。④Paterno Esmaquel II, “Lorenzana-Locsin Clash over Mutual Defense Treaty Heats up”, Rappler, March 5, 2019, https://www.rappler.com/nation/224962-lorenzana-clashes-locsin-philippines-us-mutual-defense-treaty.
事实上,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作用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同盟条约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一国是否会介入盟友与第三方的领土争端取决于其如何权衡介入的收益与风险。在不对称同盟中,只要主导国家掌握更多的权力和资源,如何解释它的同盟义务就取决于其利益和偏好。无论是美日同盟还是美菲同盟,其建立的目标都不是为了帮助日本或菲律宾实现它们的领土主权主张,而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安全利益。因此,除非美国的利益牵涉其中,否则美国会尽量避免介入争端,防止同盟牵连的风险,保持承诺的模糊性。
尽管不应过分强调同盟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威慑作用,但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利用其亚太同盟体系介入地区事务,的确改变了地区安全格局,进一步激化了地区海上争端。南海问题的升级正是发生在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背景之下,阿基诺三世仰仗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中国,造成中菲关系严重恶化,南海局势骤然紧张。而美国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只会推动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相反,无论是“美济礁事件”后中菲达成“磋商联合声明”,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是杜特尔特上任后中菲关系全面转圜,中国与东盟就“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取得突破性进展⑤“王毅:‘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形成,证明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达成共同遵守的地区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 年 8 月 2 日,http://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 /gjldrhd_674881 /t1582564.shtml。,以及中菲签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都说明地区国家和相关当事国完全有能力管控和解决好地区问题。域外大国出于自身利益介入地区争端只会推动问题走向多边化和国际化,加剧争端解决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