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的陪伴
2019-01-15冯浩
冯 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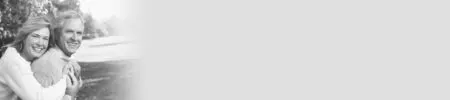
阳春三月,一向身体尚好、饭量较大的父亲突然生病了,很出乎我的意料。
26日早晨,我接到二弟的电话,说父亲腹痛住院了。我责怪二弟没有早点把父亲送去就医。放下电话,我直奔医院。着急地等了两小时后,我终于见到父亲,他脸色不佳,走路微颤,我大惊,赶紧大步迎上去和二弟一起搀扶着父亲。
78岁的父亲在镇中心幼儿园做门卫六年了,他尽职尽责,连周末、假期都守在园里。十天前,我回老家。父亲知道我回来,连夜从幼儿园赶回老屋,仅仅为了看看我。一夜北风呼啸,仿佛回到寒冬。凌晨,屋外一片漆黑,父亲戴着帽子,穿着厚厚衣服,手执电筒,与我打招呼后急匆匆地赶回幼儿园。黑夜中,父亲在逆风中独行,不远处,传来阵阵狗叫。一小时后,接到父亲已到幼儿园的电话,我才安下心来。
然而仅仅十天,父亲的变化这么大。抽血、插胃管、做心电图、做CT等等,所有检查都磨人,等待结果更是痛苦。医生的诊断结论是,父亲得了肠梗阻。
炎症导致父亲高热。看着父亲在输液,鼻子里插着胃管,我心痛不已。我默默地守在床边,希望父亲快点好起来。听说父亲在村卫生室挂了一天一夜针,疼痛未消,才不得不给我打电话。看着憔悴的父亲,我不由得想起了他的艰辛:少年丧父,青年生病,中年我们哥俩读书让他不堪重负。此刻,父亲能承载这次苦难吗?
昏沉的父亲嘴里含糊不清:“钥匙……开门……栅子门锁了吗?”我望着父亲干枯的嘴唇在翕动,还不时地睁眼用混浊的、极其疲倦的目光盯着我,仿佛我是陌生人。我一阵心酸,也很无助。留置针漏了,我小心地用一根棉签摁在父亲的胳膊上。才发现他光着脚,我忙脱下棉袜给他穿上。二弟昼夜守护,我的妻子负责洗衣送饭,我协助二弟给父亲擦身、掖被、换衣,就像父亲照顾儿时的我一样。每天,我乘公交车去医院,两次给老家的母亲电话,晚间徒步回家。
两天后,父亲高热退去,能贴耳与父亲进行简单的交流,我的心这才稍稍平静了些。我开始给父亲洗手、搓脚。自从成人后,我不知跟多少人握过手,可握父亲的手,还是头一次,生疏极了。父亲躺着,手伸开来,任凭我清洗,父亲粗糙而温暖的手上布满了老年斑,我不自觉地摊开自己的手,光洁细软,我这双握笔的手是父亲给的。父亲静静地躺着,我将父亲宽大的脚揽入桶中搓洗,父亲的脚有树皮的厚度,有水泥板的结实。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要下地干活,总是光着脚,戴着帽。忘不了他身穿雨衣,打着赤脚从田间插秧归来的身影;忘不了他肩挑白菜赶集时大步流星的步伐;忘不了他在雪地里挑着课桌送我上学留下的串串足印;忘不了他冒着酷暑,穿着多年一成不变的解放鞋为我上学借钱归来的深夜;忘不了他扛着沉甸甸的蔬菜从百里之外赶来,上楼时厚重的足音……他用坚实的脚印丈量着深沉的大地。
这双脚,承载着父亲一米八五的身体,迈过了近八十载沧桑岁月,踏出了子女的前程。擦干脚,我为父亲轻揉脚底的穴位。父亲似乎被我的举动惊住了。一会儿,他冒出了清晰的声音:“你坐一会儿。”我弯着腰,依旧轻轻地按摩,认真打量着这双脚,只见青筋外露,足底一条条清晰的波浪般的白细纹,宛如父亲踏浪而行的一生。
当初,父亲亲手修葺的台阶和后院的水泥路被我们踩得光亮如镜。如今,他亲手栽的银杏树已长成参天大树。他却老了,语速慢了,牙掉了,胡子白了,背也驼了。可他遒劲的毛笔字没变,他的美文《装房的经历》被视为我家珍宝。父亲清晰的思维、果敢与创新的劲儿没变。
四天后,父亲可以喝米汤了。医生讲,大便通畅之日便是肠梗阻解除之时。我渴望这个时刻早点来到,骤听父亲的好消息,我喜极而泣。父亲下床不便,我将便盆放在床上,然后拿来手纸清理,打来热水替父亲擦洗。一连几天,我乐此不疲,即便给父亲翻身费劲,全身冒汗,我也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这次父亲住院,是我工作以来陪伴父亲最长的一次。在我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父亲都无条件地陪我,这几日,是父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九天后,父亲康复出院,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过的特别的一段时光。
父亲跨过了生命中又一道坎,也挥别了镇中心幼儿园,再次回到那充满温馨的老屋,与母亲携手在村头,看夕阳染红天边。正所谓“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一个人无论诞生在多么贫瘠的地方,也无论去一个多么富裕的地方,都会深深眷恋故土家园。这次陪伴父亲,我悟出了两个幸福:一是父之福——孩子们整日围着父亲,他是幸福的;一是我之幸——于我,伺候父亲,是做儿子的福分,父亲能重现舒心的笑容,我亦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