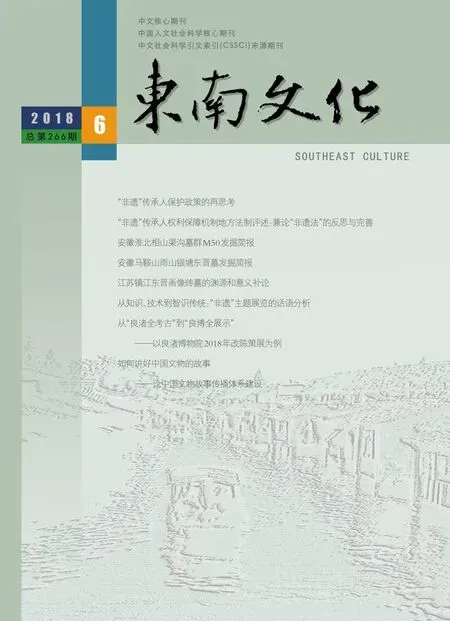江苏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渊源和意义补论
2019-01-15朴南巡
韦 正 朴南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江苏镇江东晋画像砖发掘简报曾从历史背景出发,简略指出镇江东晋墓兼具山东和先秦楚文化特点。在简报认识的基础上,再补充若干重要实例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六朝时期今镇江地区自成文化圈,镇江东晋画像砖墓是观察汉晋文化嬗变之迹的典型材料。
迄今发掘的东晋墓葬中,江苏镇江南郊畜牧场东晋画像砖墓仍然是图像资料最丰富的墓葬。墓葬为横前堂的前后室墓,通长8.95、宽3.93米。前后室都镶嵌有画像砖,发掘出的画像砖共54幅。画像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画像砖,人首鸟身即千秋画像砖、兽首鸟身即万岁画像砖、兽首人身执刀持钩镶即方相氏画像砖、兽首噬蛇人物画像砖和虎首戴蛇画像砖(图一),还有楔形兽面砖、人面兽脚珥蛇画像砖、男性裸体画像砖[1]。这座墓葬从形制到图像,都比较独特。依据文献记载和当时有限的考古资料,早年的发掘简报《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对墓主的原籍、图像的来源等问题进行了简略的猜测,今日看来,猜测基本是可靠的,但通过补充相关材料,可以深化对这一墓葬的认识,本文即由此而作。
一、与山东地区的关系
与镇江相距不过数十公里的今南京是东晋政权的首都建康所在地,那里发现了大量的东晋墓葬,但几乎没有一座是双室墓。建康地区东晋墓葬有较强的一致性,学术界有所谓“晋制”一说,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需严格界定,但差强可以用来描述建康地区的东晋墓葬:单室、平面形状为宽度较大的长方形,大型墓顶早期流行四隅券进、晚期流行券顶,双棺并列置于墓室两侧壁下,墓砖多为素面、少数使用花纹或画像砖。镇江画像砖墓显然不属于所谓的“晋制”系统,但该墓的形制和画像砖均非仓促之作。发掘简报的执笔者对墓主身份有一段推测文字,颇有价值:“东晋司马氏王朝偏安江南,北方大族纷纷南下,强占江南人民的土地和山川。镇江地处南京外围,成为当时南下大族争霸的重要地方,如山东大族刁协到镇江,则‘京口(镇江)山泽尽刁家’。……这座规模宏大的墓葬,其墓主很可能是南逃的北方大族之一。”简报的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属于典型的横前堂前后室墓,这种形制在东汉晚期中原地区非常流行。进入西晋,横前堂前后室墓在中原核心的今河南境内基本消失了,但在今山东等地区还有所保留,可以举出的例子有山东邹城西晋元康八年(298年)刘宝墓[2]、滕州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墓[3]等(图二)。东吴西晋时期南方地区保存着东汉时期的厚葬之风,前后室墓比较多见,少数墓葬大致可认为是横前堂前后室墓,如南京江宁张家山西晋墓[4]、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5]。但这些地区的墓葬进入东晋以后几乎都变成单室,这与这些地区的南渡官僚贵族主要来自于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地区有关,洛阳及周边地区西晋时期就已以单室墓为主了。东晋镇江地区的主要外来人口为鲁南淮北人士,这些人士的力量在南朝早期还十分强大,而不像其他来自中原北方地区的人士与南方地域社会较深地融合了。因此,从渊源上考察,将镇江东晋墓的性质追溯到山东地区是合适的。镇江地区发掘的东晋墓数量可观,在另一则材料集中发表的简报《镇江东晋墓》中,简报执笔者总结:“镇江东晋墓主多数是北方侨民和武官。其显属侨民者,如兰陵太守墓、郯县刘剋墓、临淮谢氏墓、□□王氏墓及谢氏、刘氏家族之墓就达十余座之多;显属武官者,如徐司马墓、嘉禾六年(237年)铭文铜弩机主人墓及出有较多兵器的土坑墓,也有相当的比例,这一特点正是东晋时期京口的侨民性和军事性的反映。”[6]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形制不是从南京地区的东吴西晋墓流传到了镇江,而是汉末东吴西晋时期就从山东传播到镇江本地,并在东晋晚期还有所运用。

图一//镇江东晋墓画像砖
在墓葬形制方面还可以找到支持上述推测的例子。镇江句容孙西村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墓是一座前后室墓[7],两个墓室都呈弧方形,这种形制在南方地区很少见,在山东地区则是比较常见的类型,如山东临朐大周庄西晋咸宁三年(277年)墓[8]、山东诸城西晋墓M1[9]是前室接近方形的前后室墓,墓壁外弧。更有甚者,山东龙口东梧桐东晋墓M1的年代为东晋泰元廿年(395年)[10],墓葬形制基本同临朐大周庄墓和诸城西晋墓M1,只是后室的后壁呈弧线形态,明显是在早先形制基础上的演进(图三)。魏晋南北朝历史错综复杂,墓葬文化的播迁现象也很常见,如果仔细爬梳,可以发现南北方不同地点之间的对应关系,镇江与山东地区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镇江东晋画像砖墓》还说:“根据考证,《山海经》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楚民族的好巫尚鬼的关系很密切;而鲁南北方大族受楚文化影响较多,南逃以后,很可能保持了传统的习俗,在墓中图画《山海经》上的神怪故事。”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认识。镇江东晋画像砖的图像也支持与山东地区有关系的推想。其中的兽首噬蛇人物画像砖和虎首戴蛇画像砖在鲁南淮北地区东汉画像石中都能找到类似图像。董良敏对此有所研究,其论文《“神人操蛇”汉画像石考释》中说:“神人操蛇形象在汉代并未消亡,在山东地区、淮北地区和四川境内的一些汉画像石中时有发现。”[11]董文所举例证中,与镇江东晋墓兽首噬蛇人物画像砖最接近的是安徽淮北梧桐村汉墓的神人操蛇图(图四∶1)。四川地区则与长江下游,特别是与镇江地区东晋墓建立不起有效的联系。淮北与山东本为一个大画像石区,因此,通过这两幅画像砖将镇江东晋画像砖墓与山东地区直接关联起来是可信的。

图二// 西晋的横前堂前后室墓例

图三//弧方形前后室墓例

图四//画像砖纹饰拓片
兽首人身执刀持钩镶的画像砖也支持今镇江与鲁南淮北地区具有密切关系。钩镶属防护类兵器,在山东、淮北地区汉画像石中常见,也有不少出土者,最大的一件就出土于江苏徐州地区。这种兵器在东晋时期未闻出土,文献中也没有记载,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兵器了。兽首人身形象代表的是方相氏,执刀持钩镶表现的是方相氏正在打鬼的场景,这种场景在汉画像石、壁画中也屡见不鲜,但在东晋墓葬中罕见,甚至可以说,兽首人身执刀持钩镶画像本质上不属于东晋时期的图像,只是由于镇江地区人口的特殊来源,而被长期保留了下来。
二、先秦楚文化的残留影响
《镇江东晋画像砖墓》中将镇江东晋画像砖的文化渊源与包括《山海经》在内的先秦楚文化联系起来,尽管只是印象式的,但这是又一具有较高价值的认识。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东晋距先秦楚的灭亡已有数百年之久,中间又隔了秦、两汉、东吴、西晋若干朝代,先秦楚文化为何得到保存?哪些因素被保存下来?随着更多考古材料的公布,现在进行阐释的条件要优于早年,下文即尝试加以阐释。
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于镇江东晋墓画像砖本身进行讨论。这批画像砖为浅浮雕,图像饱满,姿态生动,是中国古代画像砖中的精品。这批画像砖的制作不宜只作为丧葬用品看待,而应视为艺术品,工匠们在制作过程中必然投注了很大的热情才能如此。画像的内容也不宜只作为一种习俗性的题材看待,而应该在墓葬所属的东晋晚期得到人们的较强心理呼应才能如此。尽管在已经发掘的东晋墓葬中,类似画像砖为仅见,但检索新旧考古材料和相关文献,我们仍可推测画像砖所代表的思想与内容在东晋晚期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只是在墓葬之中表现不多而已。
在此不能不提及的就是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中第一首中有诗句“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至为著名。这句诗中提到了“周王”即穆天子,但整个十三首诗谈的基本都是《山海经》,而与《穆天子传》没多少直接关系,足见陶渊明所重视的主要是《山海经》。陶渊明的生卒年月为约365—427年,《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创造年代为陶渊明中晚年,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时代为隆安二年即398年,这两个年代是较为接近的。陶渊明的生活足迹基本不出今江西境内,镇江地处长江下游,可见《山海经》在当时的影响范围甚大。这里又不能不提及郭璞(276—324年),他是注《山海经》的第一人,还撰写了《山海经图赞》,他的这些著作皆传于世,后代的经籍志类书目中也都有载。郭璞又是两晋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占卜家,他的著作的影响力不可低估,陶渊明所读者有可能就是郭璞注过的本子。郭璞生活的时代在两晋之际,入东晋后基本在建康地区活动。这样,由郭璞、陶渊明与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可知《山海经》在整个东晋时期,地域范围上至少从镇江到今江西九江一带,都具有较大影响,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发现,不仅可以看作山东地区移民活动对南方地区的影响,也提示我们《山海经》在东晋前后时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遵循上述思路,可以发现有些考古材料可能也与《山海经》有关,如江苏宜兴周处墓有一类墓砖为人面纹(图四∶2),其性质当为镇墓之用。这个形象与镇江东晋墓的戴蛇虎首形象较为接近,人面的额头有皱纹、面有须,似乎为老者形象,嘴部特别大,可能也表示的是啖蛇功能。类似的人面纹墓砖还出土于南京蛇山西晋墓,人面形态与周处墓的非常接近,右侧人面似乎也有一个小耳朵(图四∶3)。人面的轮廓看上去更像一个面具,嘴部则有猛兽的獠牙特征[12]。南京江宁胡村南朝墓砖上有一种“神兽纹”,为正面形象,“张开大嘴,吐出舌头,嘴的两边各伸出一爪(图四∶4)。此纹饰砖主要用于甬道壁及墓室壁三顺一丁组合中的横砖上。”[13]湖北襄阳贾家冲M1南朝墓一千秋万岁画像砖的端面也有一个类似的形象[14](图四∶5)。后两个形象可以看作镇江墓虎首戴蛇形象的简化。
近年发掘的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晚期墓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山海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忻州地处太原北部,长期为北方民族控制地区,北朝晚期更是尔朱氏以及高欢家族严密控制的地带。很久以来,这一带都被认为是北方民族文化极其浓厚的地区,但九原岗北朝晚期墓的发掘极大地冲击了以往的认识。九原岗北朝晚期墓为北朝常见的凸字形,随葬品也是北朝晚期常见的陶瓷器,但令人惊诧的是,墓道两壁壁画近一半的题材可以与《山海经》直接对应(图五),这无疑就是一种《山海经》图,甚或郭璞、陶渊明所见的《山海经》图基本就是如此。这既让人们赞叹于考古发现之神奇的同时,也让人不能不重新估计《山海经》在当时社会上依然存在的影响。流传至今的南北朝文献中,涉及《山海经》的内容很少,但在忻州这样一个北方民族长期控制的山西高原上能发现如此精美的《山海经》图,可见其是南北朝时期民间信仰和风俗中的重要内容,其影响不仅及于汉族人士,可能也及于北方民族人物。这还提示我们,《山海经》已经化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基本因素,即使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甚少,也不能低估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分量。
一般认为,《山海经》产生于先秦楚地,因此,《山海经》大致可作为楚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但是,楚文化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将六朝时期仍然保留的楚文化内容揭示出来,是有助于对《山海经》在六朝时期流传状况的理解。与镇墓相关的考古材料我们可以举出在长江中游地区东吴西晋墓葬中常出土的人形镇墓兽,长江下游地区也有发现,其特点是拖着长长的舌头,这与先秦楚镇墓兽强调舌头是一脉相承。这种人形长舌镇墓兽在南方地区汉墓中几乎不见,在东吴西晋时才频繁出现,由此可以推测,楚文化的潜在影响一直存在,在适当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这种镇墓兽与汉代中原北方地区常见的那种额头带尖刺的走兽形镇墓兽不一样。但在这种长舌镇墓兽的额头有时也留有插尖状物的圆孔,这又是受到北方镇墓兽影响的表现,也由此将南北镇墓兽的差异表现得更加显著。长江中游的东吴西晋墓葬中还有站立状老虎形的镇墓兽,但在额头也留有插尖状物的圆孔,也是南北交融特征。但南方地区就是不采用北方特色额头带尖刺的走兽形镇墓兽,颇值得寻味。

图五//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
成都浆洗街桓侯巷成汉墓为玉衡二年(312年)纪年墓。其中共出土陶器百余件,包括很多陶俑,成都博物馆展览中的一件陶俑左手持锤、右手执长蛇(图六)。这种执蛇持锤或其他工具的陶俑在四川东汉晚期墓葬中多有出土。执蛇或啖蛇在《山海经》中多有描述,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漆棺画中多有执蛇或啖蛇的神怪形象,因此,可以看作楚文化的重要特征。先秦时期,楚国曾将疆域范围向西扩张到今重庆附近,楚文化对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地区发生很大影响,那么,直到成汉墓葬中仍然存在的这些执蛇的人物也可以看作为楚文化的影响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包括《山海经》在内的楚文化的影响直到六朝时期仍然是存在的,在各个地区的表现有所不同,四川地区承东汉而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在东吴西晋时期有楚文化的局部复苏现象,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楚文化因素则可能随山东的移民而来,这种异彩纷呈的局面正是与六朝时期由于移民、战争、商业互动等因素造成的社会剧烈变化之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对应关系,镇江东晋墓葬是一则典型材料。

图六//成都成汉墓陶俑
三、画像砖的布局和题材特点
镇江东晋墓画像砖的工艺精湛,内容也较丰富,可以认为是专门制作的画像砖,但在墓室中的排列情况却略嫌散乱。前室发现三块画像砖,简报没有交代画像砖的位置和题材,且墓室壁残高不足1米,因此,前室画像砖布局情况不明了。后室残留最高处达2.42米,从简报公布的后室三壁画像砖位置图看,墓壁残留的最低高度在1.3米以上,这两个数据表明,后室之中至少一半以上的画像砖被保留在原位,大致反映了原来的布局情况。简报准确指出了现存画像砖的几何分布特点:“后室的后壁下层为一幅,逐层向上为四、三、三、三幅,最上的三幅除中间对直,两边两幅拉至与四幅的两边的两幅相平,形成整个壁面上造象砖的排列对称,计五层十四幅,左右两壁下层为三幅,逐层向上为每层五幅,共各为五层23幅,上层与下层的造象砖都相错排列。”还需要补充的是,玄武画像砖只出现在墓室后壁即相当于北壁的位置上,这显然是有意为之。但是,就是在北壁,还出现了表现南方的朱雀。东西两壁的画像砖也出现这种不同方位砖混杂现象,一壁为青龙、白虎画像砖混杂,一壁为青龙、白虎、朱雀画像砖混杂。因此,除北壁之外,看不出画像砖题材与方位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这固然可能与墓室的空间设计与各种画像砖的计划数量之间有出入相关,但从现存壁面图来看,本来可以将代表方位的四神画像砖都集中到各自所本应属于的壁面上去。据此似可认为,镇江东晋墓的方位观点是存在的,但没那么认真,只是粗表其意而已。
尽管如此,镇江东晋墓葬四神画像砖的发现还是弥足珍贵。四神图像并不少见,汉代墓葬壁画、画像石上多有发现,魏晋时期的今中国东北、西北地区墓葬壁画中也不乏踪迹,但东晋政权控制范围内却鲜见,这个现象有必要加以关注。以笔者所知,东晋实际控制范围内,只有两处四神画像的发现,一处即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另一处是云南昭通霍承嗣墓[15]。霍承嗣墓为单室墓,四壁上部绘有四神,朱雀、玄武分别位于南北壁,青龙、白虎与通常的方位观相反,分别位于西、东壁,这在汉代墓室壁画中也可见到。霍承嗣墓的四神位置有章法的,比镇江东晋画像砖墓严谨。镇江东晋画像砖墓位于东晋政权的核心区域范围内,如果不是因为墓主与山东地区有关,大概也不会特地将四神制成画像砖而置于墓葬之中。因此,四神信仰实际上仍然存在于墓葬之中,只是没有得到表现而已,其原因也当如上文所指出,可能与东晋政权进行丧葬方面的管制有关。四神是西汉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社会信仰,六朝时期已经转化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墓葬空间有限,各个时代进行表现的重点有别,但不论是否得到表现,四神信仰的重要性不会减损。东晋时期虽然在文化上有一些新特点,但总体上维持汉晋时期的传统,这在很多方面都有充分表现,上至玄学的高涨,下至东晋人物的服饰,都可以看到与魏晋的强烈继承性。东晋在文化上没有创新,包括四神在内的社会信仰必然继续受到重视。因此,霍承嗣墓与镇江东晋墓虽然地理位置相隔玄远,但都是四神信仰在东晋时期普遍存在的标志。
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年代在东晋晚期,四神的存在表明东晋时期仍然继承了汉魏时期的文化传统,但进入南朝后,南方地区发现的画像砖就不在少数了。虽然在襄阳等地发现的南朝画像砖上,四神仍是主要题材,这仍可以看作是汉魏传统的延续;但在建康为中心的地区,画像砖的题材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帝王等高等级墓葬中,引人注目的是竹林七贤、羽人戏龙、羽人戏虎、仪仗出行等题材。在等级较低的其他壁画墓葬中,如江苏常州、邗江等地的南朝墓葬中,鞍马、牛车出行、人物、畏兽、莲花则是主要题材。四神的观念应该是继续存在的,但由于羽人戏龙、羽人戏虎或龙、虎都位于墓室之中而非墓道之中,并作为整个墓室壁画的引导,这无形之中就排斥了四神的存在。因此,就墓室壁画的具体表现而言,南朝与东晋差异很大,镇江东晋画像砖年代为东晋晚期,可以作为汉魏墓室壁画系统中四神题材的最晚作品来看待,因而就具有比较重要的时代意义。
镇江东晋墓画像砖的其他题材同样值得关注。上面提及的四神(24幅)、兽首噬蛇人物(6幅)、虎首戴蛇怪兽(5幅)、执刀持钩镶的方相氏(10幅)外,就只有人首鸟身的千秋(4幅)、兽首鸟身的万岁(5幅)了。这些题材可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第一,表方位的四神之外,保护墓葬的画像题材最多,有三种,即兽首噬蛇人物、虎首戴蛇怪兽和方相氏,所占比例也高,共21幅,占总共留存下来的54幅画像砖的39%;第二,千秋、万岁被单独塑造出来加以强调,这与汉代壁画中仅作为各种奇禽瑞兽题材中的一种明显不同。千秋、万岁是表吉祥的动物,其意义与保护墓葬的题材相反相成,正如孙作云先生所言,“汉代人‘打鬼’与‘求仙’思想,是一种迷信的两个对立面,消极的在打鬼,积极的在求仙。”[16]千秋、万岁出现在墓葬中既蕴含希望墓主地下美好生活永远延续之寓意,也表达了墓主早日升仙而不死的愿望。第三,没有出现一幅现实人物画像砖,这大概不能完全说是出于偶然,可能体现了墓葬设计制作者的理念,那就是表方位、保护墓葬和升仙内容比与现实直接相关的内容更重要。在墓葬壁画刚开始出现阶段,如河南洛阳西汉晚期的卜千秋等壁画墓葬中,现实人物也很少出现。因此,可以说,镇江东晋画像砖墓的题材比较忠实地反映了墓葬壁画最初创作时的思想,也说明这些内容才是墓葬壁画的根本性内容。
在上述题材中,还值得再谈一下的是兽首噬蛇人物、虎首戴蛇怪兽。在《山海经》和先秦时期的美术材料中,蛇是被经常描述和描绘到的,这与人们对蛇的认识有关,如《楚辞·大招》:“魂乎无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鰅鳙短狐,王虺骞只。”但秦汉以后,蛇在画像中的表现总体上变少的。虽然我们指出镇江东晋墓的兽首噬蛇人物、虎首戴蛇怪兽可能与墓主为山东一带的移民有关,但像这样强调蛇,大概既与南方多蛇的环境有关,也与这一墓葬的画像砖题材具有一定的初创性质,因而能够比较充分地表现墓葬的本原思想有关。
四、小结
镇江东晋画像砖墓虽遭破坏,但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在不流行画像砖的东晋时期,这座墓葬的画像砖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较多地表现了时人对墓葬空间和思想的构建状况。镇江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鲁南淮北地区,画像砖的内容也可窥见与鲁南淮北地区的联系。这座墓葬画像砖的题材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山海经》在内的楚文化的残留影响,在总体上则可以看作汉晋墓葬壁画的自然延续。这座墓葬的年代在东晋晚期,南朝开始长江下游地区的墓葬画像砖转以其他内容为表现主题。因此,这座墓葬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它大致标志着汉晋墓葬壁画系统的基本终结。
[1]镇江博物馆:《镇江东晋画像砖墓》,《文物》1973年第4期。最后三种画像砖见于林树中《六朝艺术》,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33页。林著没有附图,但对画像进行了描述。楔形砖上的兽面形象“在南北朝墓所见甚多,如常州南郊出土南朝晚期墓中的兽面砖,河南洛阳出土现藏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的北魏晚期石棺床支足上的兽面石刻”,人面兽脚珥蛇画像“作人面、圆眼、宽嘴,额上珥蛇,两蛇左右伸出。人身、裸体、兽爪。此形象似湖南长沙出土战国帛书画里的一个神的形象,也与楚文化地区内出土春秋战国时代某些珥蛇、踩蛇的青铜器花纹形象相联系”,男性裸体画像“作人头,头上长双角,张嘴露齿,双手上托,裸体,露男性生殖器,双腿如蛙,其下似一石头,有双蛇钻动,再下又有两蛇相交。在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与画砖中,曾出现裸体形象,如青海互助县高寨魏晋墓出土的裸体画砖,又如江苏苏州吴县咸康元年(335年)墓出土的男性裸体画像砖,其用意,颇费猜测。”
[2]山东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文物》2005年第1期。
[3]滕州市文化局、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西晋元康九年墓》,《考古》1999年第12期。
[4]南京博物院:《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
[5]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考古》1991年第3期。
[6]镇江博物馆刘建国:《镇江东晋墓》,文物编辑文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
[7]南波:《江苏句容西晋元康四年墓》,《考古》1976年第6期。
[8]宫德杰、李福昌:《山东临朐西晋、刘宋纪年墓》,《文物》2002年第9期。
[9]诸城县博物馆:《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10]烟台市博物馆、龙口市博物馆:《山东龙口东梧桐晋墓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4期。
[11]董良敏:《“神人操蛇”汉画像石考释》,《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0—298页。
[12]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40页。
[13]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胡村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
[14]襄阳市博物馆等:《天国之享》,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15]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
[16]孙作云:《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画幡考释》,《考古》197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