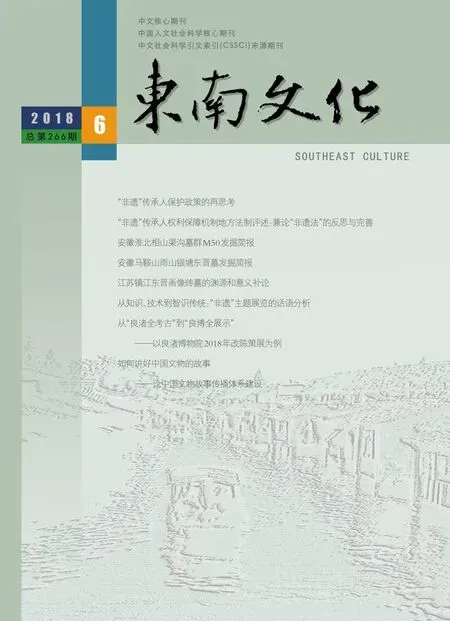江苏扬州双山汉墓墓主身份探讨
2019-01-15余国江
余国江
(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 江苏扬州 225008)
内容提要:双山汉墓即甘泉一号墓、二号墓,是扬州地区发现的两座东汉时期高等级墓葬。关于其墓主身份,学界有不同看法:一号墓墓主,或认为是广陵王刘荆家族中的某个成员,或认为是刘荆的王后;二号墓墓主,或认为是刘荆,或认为是东汉晚期的某一代广陵王。通过对两墓形制、器物的比对,可以确认这是两座东汉早期广陵王侯之墓;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形制的细微区别来推测,一号墓、二号墓墓主分别应该是广陵侯刘元寿、广陵王刘荆与王后。
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甘泉山一带,分布着大量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甘泉山之北不足一公里处,有东西相邻的土山,当地人称双山,实际是两座汉墓的封土堆。1975年和1980年,南京博物院先后发掘清理了西边和东边的墓葬,编号为甘泉一号墓、二号墓[1](图一)。一号墓被盗严重,出土了铜雁足灯等少量遗物;二号墓亦被盗,出土了虎纽玛瑙印、错银铜牛灯、鎏金博山炉、金胜、漆九子奁、铜雁足灯、玉翁仲等,后又在堆放二号墓盗洞填土的土堆里发现了著名的“广陵王玺”金印。
作为扬州地区的高等级东汉墓,双山汉墓的墓主身份一直受到关注,相关探讨也有一些。甘泉一号墓墓主,发掘简报中推测与东汉第一代广陵王刘荆有一定关系,应是刘荆家族中的某个成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一号墓是刘荆王后之墓,但未加以论证[2]。二号墓墓主,发掘者根据铜灯铭文、金印等推定是广陵王刘荆;后有学者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推测是东汉晚期的某一代广陵王,“广陵王玺”金印为东汉晚期或使用至东汉晚期的可能性都存在[3]。
笔者认为,对双山汉墓墓主的探讨,其实并不仅仅是单个墓葬的问题,更牵涉到对扬州地区其他东汉墓的时代以及“广陵王玺”等重要文物内涵的认识。所以不揣浅陋,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拙见陈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双山汉墓是两代广陵王侯之墓

图一//双山汉墓位置示意图
根据发掘简报可知,甘泉一号墓、二号墓形制极为相似:两墓均为砖室墓,由甬道、墓室、棺室组成;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券顶为重券,由前、中、后三个券顶构成,前、后券顶为南北向,中券为东西向。

图二//铜雁足灯铭文
两墓虽然被盗严重,出土遗物不多,但残存器物所体现的器类仍大体相同,都有铜雁足灯、陶猪圈、陶屋、鎏金铜泡、铜合页等物,铜器多鎏金。同类器物形制也较为类似,如陶盆,均为大口,口沿平折,浅腹,平底。尤其是两件铜雁足灯,更是惊人地相似:灯盏为圆环形浅槽,灯架为一雁足,下以圆盘作灯托,盘口沿分别铸有篆书铭文“山阳邸铜雁足短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廿”“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图二),显然是同一批次的特制产品。
两墓规模也相近:一号墓甬道长2.5、宽2.5、高4.24米,墓室长13.1、宽7.8~8.2米;二号墓甬道长2.6、宽2、高3.4米,墓室长9.6、宽8.8米。扬州地区发现的东汉大型砖室墓不多,甘泉山附近老虎墩东汉墓墓室前宽后窄,通长14.04米,最宽处8.65米,实际面积小于双山汉墓,该墓据推测是东汉中期的某一代广陵侯或者重臣之墓[4]。由此可知,双山汉墓墓主是广陵王侯的可能性很大。
再考虑到双山汉墓相距不远,均位于甘泉山之北,东西相对,又出土有“广陵王玺”金印等器物,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两座墓的时代十分相近,应是广陵王侯之墓。
东汉时期的诸侯王、王后的合葬形式,既受到帝陵的影响,也融入了各地的丧葬传统,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同穴合葬,其中有的同穴同室,有的则同穴异室,棺室之间有间隔;第二种,同坟异穴合葬,两墓位于同一封土下;第三种,异坟异穴合葬,各有独立的坟冢[5]。甘泉一号墓为单人葬,人骨架已朽,可见一些朽骨痕迹。二号墓有两个棺室,西侧棺室发现少许头骨和肢骨的残片,应该是夫妻合葬墓。如果一号墓为广陵王后墓,二号墓为广陵王墓,那二号墓中另一棺室的存在就难以解释了。而且,严格来说,一号墓墓室相较于二号墓要略大,王后墓大于广陵王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甘泉二号墓是某代广陵王侯夫妻的同穴异室合葬墓,一号墓则是另一代广陵王侯之墓。
二、双山汉墓的时代
甘泉二号墓出土了“广陵王玺”金印,是确认墓主身份的关键遗物。据史籍所载,东汉一代封广陵王者,唯有刘荆:“荆,上母弟也,性急刻,喜文法。初封山阳王。世祖崩,荆与东海王彊书,劝彊起兵,彊恐惧,封上其书。天子秘其事,徙荆为广陵王。”[6]至广陵(今扬州)以后,刘荆仍祝诅天子,永平十年(67年),“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7]四年后,永平十四年(71年),明帝“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元寿卒,子商嗣。商卒,子条嗣,传国于后。”[8]刘元寿只是广陵侯却能“服王玺绶”,主要是因为刘荆为明帝的同母胞弟,虽然有罪自杀,明帝却十分怜惜其子。《东观汉记》记载: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狩。……三月……幸东平王宫。上怜广陵侯兄弟,赐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舆马,悉赋予之。”[9]这是明帝对刘元寿兄弟的特殊恩遇,故而史书中特别载明其事。当然,这种特殊情况绝不是皇帝对待广陵侯的常制,两汉时身为侯而服王玺绶的,仅有广陵侯刘元寿一例。按照汉代制度,明帝和刘元寿去世以后,这种恩遇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又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棱字伯威,援之族孙也。……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10],即章帝章和元年(87年)时,广陵侯国已经废除,此后也没有复置之事。自永平十四年刘元寿封为广陵侯,至章和元年马棱为广陵太守,前后不过十余年,而刘元寿、刘商、刘条前后三代继嗣,并传国于后,似乎有不合理处。一种可能是,自广陵侯刘元寿后,刘商、刘条等均为列侯,已不得再“臣吏民”。也就是说,东汉一代能“服王玺绶”、使用“广陵王玺”金印的只有广陵王刘荆和广陵侯刘元寿,并不存在“广陵王玺”金印一直延续使用到东汉晚期的可能。

图三//甘泉二号墓平面图与复原图

图四//釉陶壶的比对
双山汉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也印证了这一点。先看墓葬形制。扬州地区西汉和新莽时期流行木椁墓,至东汉时期为砖室墓所取代。东汉早期的砖室墓多为单室或前后室的双室墓(或附耳室),券顶;东汉中晚期则常见前中后三室并附侧室的大型多室墓,多为叠涩顶或穹隆顶[11]。甘泉一号墓、二号墓均有短的甬道,墓室为单室,有前、中、后三个相连的券顶。一号墓棺室位于墓室中央,呈凹字形;二号墓墓室中段砌有三堵短墙,在两个棺室外形成回廊(图三)。这些都具有典型的东汉早期的特征[12]。或认为二号墓内部结构为黄肠题凑式,且仅仅只存黄肠题凑之意[13]。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扬州地区汉墓从木椁墓到砖室墓的转变过程中,砖室墓吸收或者说是残留了一些木椁墓的元素,是东汉早期砖室墓尚未发展成熟的表现。
再看随葬品。甘泉二号墓的釉陶壶等器物,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在扬州及附近地区其他墓葬中也有类似者出土。二号墓出土釉陶壶13件,简报将之分为三式。Ⅰ式,侈口,束颈,口外有一周宽边,长鼓腹,平底。肩部有蕉叶纹双耳,腹部密布弦纹,颈部加饰复道波浪纹。Ⅱ式,与Ⅰ式相似,而底部有矮圈足,腹部无弦纹。Ⅲ式,口部喇叭形,无宽边,有矮圈足,腹部密布弦纹(图四∶1—3)。扬州邗江宝女墩M104新莽墓出土了7件釉陶盘口壶、8件釉陶壶,无论从器型、最大径位置、耳部装饰等来看,都与甘泉二号墓相同或相似[14](图四∶4、5)。扬州仪征螃蟹地七号墓时代为新莽时期,出土的I式釉陶壶,侈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置蕉叶纹双耳,也与甘泉二号墓Ⅲ式釉陶壶相近[15]。

图五//铜博山炉
甘泉二号墓出土有三件铜博山炉,除一件缺盖外,另两件均通体鎏金(图五∶1、2)。螃蟹地七号墓出土一件铜博山炉(图五∶3),盖呈三角形,上部镂刻卷云纹,似山峦叠嶂,身为子母口,弧腹,平底,豆形足,下有承盘,口沿下和柄部有凸棱[16]。甘泉二号墓铜博山炉与之相比,造型大体相同,而体量更大,没有口沿、腹部等处的菱形、锯齿等纹饰,可能是同时或稍晚时代的产品。
甘泉二号墓还出土了4件青瓷罐,或认为其时代不可能早到东汉早期[17]。确实,按照《中国陶瓷史》的总结:“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应该是比较确切的。”[18]但是,关于瓷器起源问题备受学界关注,却一直未能取得完全的共识。以往一般认为浙江上虞地区出土的东汉晚期青瓷是最早的成熟青瓷,近年来这一看法也受到质疑[19]。吴小平等在对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进行研究时,把釉陶作为瓷器看待,将Ba型Ⅰ式瓷四系罐的时代定为西汉晚期,Ⅱ式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Ⅲ式时代为东汉晚期[20]。广西贵港深钉岭汉墓M7、M8出土了青瓷罐、青瓷双耳罐、青瓷圈足碗,发掘简报将其年代定为东汉早中期[21]。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一些东汉釉陶的釉与瓷釉几乎完全相同[22],则甘泉二号墓出土的这4件青瓷罐究竟是成熟瓷器还是接近成熟瓷器的釉陶器,似乎仍有探讨的余地,即使是瓷器,也不能轻易否定东汉早期的可能性。
总之,综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来判断,笔者认为发掘简报的判断不误,双山汉墓的时代应该是东汉早期,而不会晚至东汉晚期。
三、双山汉墓的墓主身份
在确定双山汉墓为广陵王侯之墓、时代为东汉早期后,两墓的墓主就只能是广陵王刘荆和其子广陵侯刘元寿了。
甘泉二号墓中随葬有“广陵王玺”金印,发掘简报将墓主确定为广陵王刘荆,这是比较合理的。史载刘荆“性刻急隐害”,但汉明帝对刘荆的不臣行为一忍再忍,先“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刘荆不思悔改,方才“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23]。从后来刘元寿兄弟的待遇来看,刘荆之死是格于国法,而明帝对其恩情仍在。因此,刘荆身死国除,“广陵王玺”金印随之而葬,是很可能的,与其合葬的当为其王后。
另外,双山汉墓在形制上有一些细微区别,如一号墓有墓道,作斜坡状,底宽2.5、上宽3、长约45米[24];而二号墓则没有墓道。甘泉顺利东汉墓时代约在东汉早中期,墓室前部的地层因取土扰乱,墓道情况不明[25];东汉中期的甘泉老虎墩汉墓,在略偏于墓门西侧有斜坡喇叭状的墓道[26]。仅从有限的材料推测,可能二号墓比一号墓略早,更多地保留了西汉新莽木椁墓的特征。时代越往后,砖室墓的结构越复杂,加长甬道,增设耳室,砖砌方式由单一到多样,而增加墓道可能也是表现之一。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山阳邸”铭文铜雁足灯等器物,则一号墓墓主就只能是广陵侯刘元寿了。
四、结语
扬州在东汉时曾为广陵国都城,多年来,发现有一批较高等级的墓葬,双山汉墓就是其中的代表。对其墓主身份的探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扬州地区东汉墓和相关随葬品的认识。双山汉墓距离相近,形制相似,出土遗物有很大的共性,时代特征也较为明显。根据墓葬、随葬品、史料等综合判断,我们认为双山汉墓是东汉早期广陵王侯的陵墓,二号墓墓主为广陵王刘荆与王后,一号墓墓主为刘荆之子广陵侯刘元寿。
[1]a.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b.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2]李健广:《江苏邗江甘泉顺利东汉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
[3]汪俊明:《扬州甘泉山二号墓年代献疑》,《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4]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县甘泉老虎墩汉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5]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60—361页。
[6]东晋·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卷一〇《孝明皇帝纪下》,中华书局2017年,第184页。
[7]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113页。
[8]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第1448—1449页。
[9]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二《显宗孝明皇帝纪》,中华书局2008年,第57页。
[1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62—863页。
[11]赵化成、高崇文等:《秦汉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另外,《江苏邗江县甘泉老虎墩汉墓》将扬州地区东汉砖室墓的演变规律总结为:“早期墓型单一,为长方形或正方形,有回廊、短甬道,券顶,平面布局还保留着西汉木椁墓的某些特点。以后甬道一般加长,置有对称的耳室,墓室具有明显的前堂后寝的布局,仍以券顶结构为多,但也出现了穹窿顶,到了晚期,耳室增多,甚至在主室两侧也设置耳室。”
[12]田立振:《试论汉代的回廊葬制》,《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13]同[3]。
[14]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墓》,《文物》1991年第10期。
[15]仪征市博物馆:《仪征新集螃蟹地七号汉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
[16]同[15]。这种錾刻花纹铜器,一般认为产于广西合浦一带,是汉代合浦郡工官所造。见吴小平、蒋璐:《汉代刻纹铜器考古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85页。
[17]同[3]。
[18]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19]王昌燧、李文静、陈岳:《“原始瓷器”概念与青瓷起源再探讨》,《考古》2014年第9期。该文认为:“以往学术界几乎公认我国上虞地区出土的东汉晚期青瓷残片达到了瓷器的标准。然而,这一标准既缺乏科学依据,又过于‘苛刻’,若以此为标准,则我国的青瓷几近绝迹。”
[20]吴小平、蒋璐:《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第1期。
[2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贵港市文物管理所:《广西贵港深钉岭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22]如湖南资兴东汉墓出土陶器的釉,全是玻璃质,开冰裂纹,透明光亮,特别是釉堆聚处,釉色晶莹,或碧绿、或银灰,与六朝瓷釉几乎完全相同。参见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23]同[8],第1446—1448页。
[24]实际清理部分约15米。由于墓道西邻有一座现代砖窑,未能全部清理,发掘者推测已发掘部分约为整个墓道的三分之一。
[25]同[2]。
[26]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