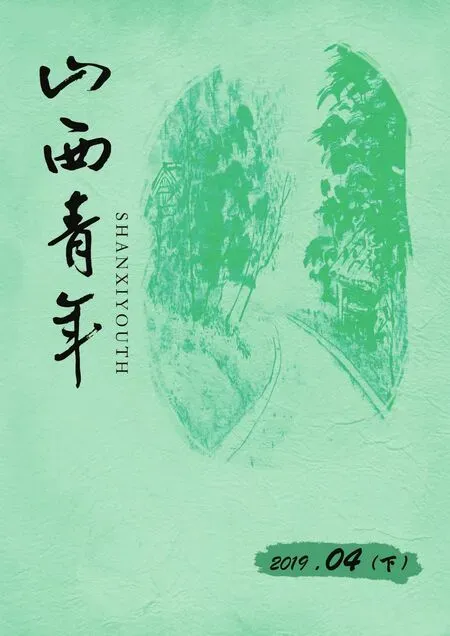古印度宗教文化的发展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2019-01-15张世霞
张世霞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00)
古代印度的法律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的扑朔迷离使印度的法律刻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婆罗门教、佛教与印度教先后以其独具特色但又存在共同的文化理念改写着印度这个国家的发展历史。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与法律融合的结晶与升华,种姓制度给印度人民带来了身份和归属感的同时,也带来的了歧视与不公,这种制度在印度发展史上经久不衰,扎根在了古印度人民的心中,尽管后来印度国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中一些非人性的规定,但这种文化的影响至今在一些地区依然被人们所遵从。这种古老、独特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将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①。依靠其宗教与法律的力量.将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神圣化、固定化和永久化,融通了宗教与法律桎梏人们思想达到至高境界。
一、古印度法律的宗教色彩
婆罗门教的教义作为古印度的立法依据,开启了古印度的法律深深打上宗教文化的烙印。据史料记载,在印度的历史上,曾经有6支不同的外族人入侵并统治过印度。分别是印度——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和英国人。其中波斯人和希腊人除了极尽掠夺外未留下牢固根基。而土耳其人和蒙古人把伊斯兰法的一个分支引进了印度,②也只对目前印度少部分信仰者人群有效。英国人最后进入印度,进行统一管理,引进了英国公法,私法仍由当地的不同习惯进行调整。因此,在6支外族统治过程中,只有印度-雅利安人也叫印度人,在大约3000年左右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被分为佛法和婆罗门法两个分支。佛法最早是阿育王用比梵语更古老的陀文记载,代表着印度现存最早的法律记录③。婆罗门法是用巴利语记载并保存,并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
(一)婆罗门教居于古印度的统治地位
雅利安人入侵后,便利用达罗毗茶人对自然力的崇拜,通过神权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提出了万物的生存都是宇宙创造者.即梵天支配的观点,雅利安人的祭司(梵语称婆罗门,婆罗门教由此而得名)还利用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茶人肤色和形态上的差异,编造了梵天(造物主)用自己的口、臂、腿、脚创造了四个不同种姓的神话,并在此基础上将吠陀教演变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宣扬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如果要想造善业,赢得好的来世而避免转生的恶报,就必须遵循“达摩”。印度人将法律称作“达摩”,但实际上“达摩”是法律、宗教与道德规范的混合体。这一时期的“达摩”就是法律与宗教合而为一的婆罗门教法。婆罗门教产生以后,很快流行于印度各地,并成为印度的国教,婆罗门教的种姓制被认为是立法的首要目的和宗旨,是古代印度法的核心内容,古代印度法正是以不平等的种姓制为基础构建的,法律的任务与目的就是确立各种姓的法律地位,规定各种姓的权利义务,保护高等种姓的特权不受侵犯。
(二)《摩奴法典》的“神化”统治激起其他等级的强烈不满
《摩奴法典》将人们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作了更为严格的区分,婆罗门是第一种姓,掌握神权,垄断文化;刹帝利是第二种姓,掌握军政大权;吠舍是第三种姓,主要从事农牧业和商业;首陀罗是第四种姓,绝大部分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有一些是失去村社身分的自由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奴隶。这种制度规定职业世代相承,永久不变;实行种姓内婚,种姓之间不相混杂;不同种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极不平等,在宗教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做了严格的区分,神圣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固定化和永久化了这种世代不变的“神圣制度”,其统治手段激起了其他等级人的强烈不满。
二、佛教以“人生而平等”掀起古印度历史风波
婆罗门教的神化等级统治,激起低下等级人不满的同时,对于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军事贵族等,也随着印度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对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的特权地位与腐化堕落强烈不满。公元前6世纪,佛教以宣扬人人生而平等,开始盛行于古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出身于刹帝利(武士)的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3年一前483年)④⑤,也就是后来人们赋予他的佛名—释迦摩尼。佛教主张众生在灵魂上平等,每个人都通过修行而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而毋须婆罗门祭司的引导。由于佛教教义通俗易懂、仪式简便、不崇拜偶像,收纳信徒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因而比婆罗门教更易被劳动群众接受,发展极为迅速。在阿育王统治期间,将佛教定位国教。阿育王为了传播佛教,大约在公元前270年时继位后,颁布了三十到四十多个诏谕,且把它们刻在石头上。⑥阿育王通过颁布诏谕使佛教得以宣传,也因此,阿育王经常被称为佛教的君士坦丁。阿育王的诏谕大多都很短,但能详细说明并宣传他的道德法律制度,并将这样宗教作为生活哲学,将“达摩”与佛教相结合形成新的道德宗教制度,阿育王将这种新佛教制度用摩掲陀文献记载,这种文献后来被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字“巴利”所代替,渗透到了印度疆土以外的地区,传入缅甸、暹(xian)罗、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成为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广的宗教。由于佛教宣扬人生而平等,没有等级差别等教义与古老的婆罗门教相对抗,故在公元400年至700年之间发生了一次彻底的社会与宗教变革,大约在公元800年左右,佛教在其发源地国印度销声匿迹⑦。而且,由于古印度的佛教从一开始就被刹帝利种姓所控制,这一由掌握国家军政要职的官员构成的阶层,也是统治和奴役印度人民的特权贵族,所以婆罗门教与佛教间的宗教文化斗争,其实也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斗争。阿育王死后,势力衰竭的婆罗门教又渐渐复兴,并在吸收了佛教的某些教义的基础上演变成了印度教。
三、印度教是集吠陀教、婆罗门教、佛教为一体的混合体
佛教对世界的影响最广,而印度教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最深,印度教义的制度化、法律化构成了印度教法,印度教法是印度教徒在宗教、世俗生活中一切行为规范的总称。⑧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其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对劳动人民提出应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对统治阶层则宣扬纵欲与享受。可以看出,印度教法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等级特权法。而且,印度教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教义,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经典,它是将印度文化的起源即“吠陀”文化作为吠陀教,借助吠陀教对多神以及日月星辰、雷雨闪电、山河草木、各种动物、英雄人物和祖先的崇拜,在婆罗门教中加入了某些佛教的因素,将两者有机结合。可以说,印度教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是哲学理论、多种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祭祀仪式、风俗人情的混合体⑨。它以婆罗门教的法经、佛教的三藏为经典和主要法律渊源,在印度封建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一)印度教的教义不对教徒进行强制遵守的规定
印度教没有明确的勾画出神学教义去要求教徒必须遵守,而是以各自的信念为基础,而这种信念具有某种宗教哲学的性质,所以使很多印度教徒以不同的方式对其接受,它不要求信徒通过接受关于神、灵魂、创世、得救等特定的宗教教义的共同认同而连结在一起。正是因为以宗教哲学这个根本信念为基础,使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这些宗教组织,被视为了印度教的分派或者独立的宗教。
(二)印度教的基本信条之一就是“轮回”和“业”
印度教认为来世的等级是由前世的功德所决定,虽然印度教同样将人分为四类:即婆罗门(祭祀或者贵族)、刹帝利(武士)、吠舍(商人)、首陀罗(仆役、工匠),人们不可能从一种种姓改为另一种姓,各种姓之间有层级关系,而且各层级之间必须保持这种秩序,于是产生了许多规则,如禁止同属于纯洁性较低的种姓成员结婚或者保持性关系,或者同他们共同进餐,甚至禁止他们接近。这种规定导致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不同种姓的混合婚子女如何判定婚姻的效力和子女的层级归属问题,所以在后期的印度立法中废除了种姓决定其法律效果是否发生的一切规则。当然,现实生活中印度的这种种姓制度似乎已成了惯例,虽然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比如寡妇在高级种姓成员之间的再嫁问题,几乎不存在)。但随着该国政治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在普遍、平等选举权的保障下,以及印度居民职业变动越来越大,传播媒介的影响和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加强,使得种姓制度也处在了深刻的变革之中。
(三)印度教法的发展
印度教法是居住在不同国家的人信奉印度教的社会的法,是属人法。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在《吠陀》⑩里的诗歌、祈祷词、赞美诗及箴言中,可以找见被称为规制人们行为规范的最初条文,印度教徒将其作为神圣的启示,同时把他作为宗教和法律的渊源。因此有人主张印度教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体系。但在印度最古老的文学文献中,一部称为《法律书籍》,梵文称为《传承经》⑪里,主要是老学者们或者祭司们所记忆的“判例”,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园后200年之间著成,这部书里最古老的内容是关于人们生活的重大事件中应当举行咒术的、宗教仪式的箴言式指示,勾画了印度初期宗教习惯做法的形象,几乎没有包含法律内容的规范。它所根据的是当时在宗教仪式和社会关系方面印度教徒所遵守的习惯作法。之后大约从公元200年起直到英国殖民统治时代,最重要的法律文献是汇编、摘编和注释书。这些都是与《传承经》相连的,不求独创,只是从事解说《传承经》,并且使《传承经》在实务上便于使用。许多著作者着手从中挑选摘抄与眼前时势看来特别有用的章节,条理清楚的编写出来,按照这种方式,《传承经》被“现代化了”,对过时的资料给予去除,有的著作者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注释书,因为《传承经》是有约束力的,这种解释实际上是著作者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形成的习惯和惯常作法,没有否认将印度教法中的习惯作为法源。而“法论”⑫,是紧随《传承经》之后出现的一部法律书籍,它的出现,使古印度的法律发展前进了一大步,这些法论由著作者将法的各种规则以韵文的形式广泛的写下集录,其中最著名的《摩奴传承》,是公元前2世纪传说是摩奴所述的集录。这部法论的开头,就将我们今日可能会列入私法和刑法的规则,井然有序、条理清楚的进行了处理,同样承认印度教法中将习惯作为法源,而且在实务中会被优先适用于规则。
(四)印度教法的法典化
传统的印度教法,既不是以世俗统治者制定的法律,也不是法院的判例,而是印度教徒之间正在实行的习惯法,英国统治印度后,对传统印度教法进行了修改,在立法方面,废除了关于寡妇禁止再婚的规定,废除了对于抛弃自己宗教的印度教徒,对逐出自己种姓的人剥夺其全部财产和继承权的原则等特别震惊的印度教法的规定。其次,是利用判例对印度教法进行修改,他们利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发展一些规则,而这些规则有意无意的受到普通法的影响,故传统的印度教法逐渐被所谓的“英—印法”取而代之,这种法律很快发展成不需要传统的法律文献,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判例法,且由印度法院运用这种判例。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向议会提出印度教法的“印度法典化”草案⑬,遭到保守派和已经形成一定法律习惯的人们的强烈反对,后来印度政府先撤销该草案,改成以个别的法律草案为对象逐个提案获得成功,在1955年,印度教婚姻法作为第一个适合现代观念的《印度婚姻法》的制定法实施了。1956年,《印度未成年人与监护法》、《印度继承法》和《印度收养和抚养法》三部法律也相继实施。印度教法大部分都编纂成了法典,而英印法只在一些没有立法规则且调整的不太重要的领域里起作用⑭,可见,印度教法不是印度国法,其法典化的根基源于教徒对宗教文化信仰与习惯。
四、启示
(一)文化信仰厚实古代印度政权根基
古印度民族对宗教文化信仰的习惯,推动了古印度法律制度的建设。古印度人民对宗教文化的信仰执着,致使宗教教义的最终法典化。婆罗教以其教义,一度掌握国家政权,使教徒在种姓制度的桎梏下遵从信仰。商业的快速发展,商人阶层的刹帝利阶层,创造了与婆罗门相对抗的世界性宗教即佛教,一度在孔雀王朝(公元前250),也就是国王旃(zhan)陀罗笈多(阿育王的祖父)的统治期间,领土从东部扩展到北部和西部,西至阿富汗,东到孟加拉,北抵喜马拉雅山脉,南及德干的中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权。⑮而印度教的出现,再次演绎印度历史,其印度教法的法典化,有力证明了印度的宗教文化对印度民族的影响至深。如论教义如何改写,如论政权如何更替,对宗教文化的信仰,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不管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最终都被印度民族定位国教,而印度教的最终法典化,更是体现印度宗教文化发展的最高沉淀,是印度民族对宗教文化信仰的升华,厚实了印度社会的政权根基。
(二)依法治国沉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
而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新理念,是国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从人治到法治,历经数代中华民族的智慧,沉淀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至高寓意,是对中国上下五千年治理文化的传承与升级,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沉淀到了至深境界,回避可能因政权更替动摇牢固的文化根基,这种不忘初心的治国理政新理念稳定了未来数年的国家发展新目标,用文化软实力强化治理手段,用“一带一路”的全球化理念铺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相结合的整体性思维。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这个地球,说明撬动地球的前提得有支点。佛教以婆罗门的相关教义为支点,精华了佛教教义,以“人人生而平等”的佛教文化鼎盛了孔雀王朝,成为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广的宗教。而印度教对佛教的取代,是因为印度教站在了婆罗教和佛教的肩膀上,结晶了婆罗教和佛教的精华,成就了印度教法的法典化。而中国,古丝绸之路禀赋给人类智慧巅峰的“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战略,将中国的依法治国新理念用现代化方式撬动了许多不了解中国的沉睡领域,用传统文化之精髓点燃了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指明了未来社会的治理手段与治理方向,让依法治国的治理理念和“一带一路”的治理方法或治理工具,伴随中国走向世界,协同发展,共享发展红利。古印度宗教文化、法律及政权更替,警示民族以史为鉴,精华过去,扎根现在,不忘初心,指引未来,用几千年的祖宗文化沉淀,绽放坚实辉煌的未来华夏大地。
五、结语
古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不同历史时期宗教文化的演变过程,对古印度法律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印度宗教文化法典化过程及其政权更替,有力的证明了宗教文化在古印度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性及其影响力。其宗教文化的演变导致的政权更替,宗教文化的发展导致最终的法典化,演变了古印度社会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启示人们,传统文化根基的牢固性可以影响千秋万代,传承传统优秀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增强现代文化自信,是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古代印度先后经历了6支外族人的统治,以不同方式传播其宗教文化,使这种对宗教文化的信仰扎根于印度民族的心中,构筑了印度教法法典化的坚实基础,也牢固了古印度的政权基础。
当今中国依法治国新理念,结晶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球化战略,正是站在上帝的视角,俯视全球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发展实际,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注入中国现代文化之魅力,禀赋给了世界了解中国的平台、路径与方法。
[ 注 释 ]
①叶秋华.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②[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册,214.
③[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册,226.
④[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册,175.
⑤阿育王诏谕.From the facsimile in James Burgess and George Buhler,“Archaeological Survvey of Southern India:the Buddhist Stupas of Amaravati and Jaggayyapeta”,Edict VI,plate LXIV and pag 123(London,Trubner,1887).
⑥阿育王诏谕.From the facsimile in James Burgess and George Buhler,“Archaeological Survvey of Southern India:the Buddhist Stupas of Amaravati and Jaggayyapeta”,Edict VI,plate LXIV and pag 123(London,Trubner,1887).
⑦欧东明.略论印度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南亚研究季刊,2004(4).
⑧王云霞.《比较法研究》.印度社会的法律改革,2000(2).
⑨[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册,313.
⑩这是古印度《摩奴法典》的渊源之一.——中译者注.
⑪天启者颁布给弟子并由弟子收集的法律——中译者注.
⑫梵文原意是指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传统中论述行为规范的学说,可以叫做“法学”或者按照我国古代梵文汉译传统译作“法论”.但由于早期法论的著作是用一种名为“经”的词句像歌诀那样简单的散文写的,故此处亦可译作“法经”,但并非法典之意——中译者注.
⑬[德]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545.
⑭[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册,225.
⑮[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册,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