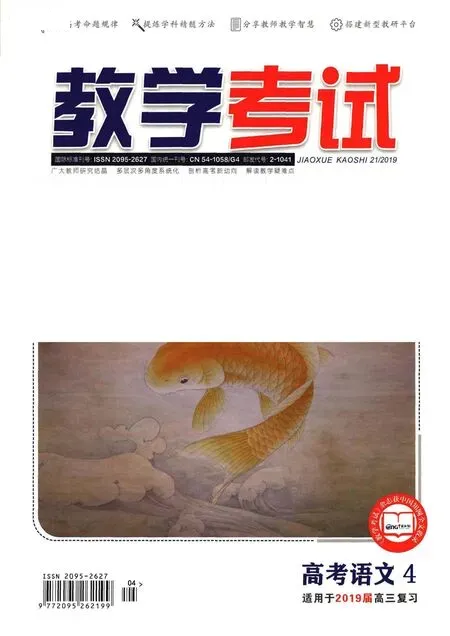思辨性阅读要从打破成见开始
——以“刘兰芝被遣归之原因”的探讨为例
2019-01-10安徽
安徽
笔者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发现,语文课堂阅读教学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缺乏思辨能力,而贴标签式的阅读方法却大行其道,这严重阻碍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提升。笔者将阅读教学中以政治观念、社会道德价值以及断章取义、主观臆断来解读文本的方法,都称之为“阅读成见”。比如,朱自清先生为什么“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答曰:作为知识分子的朱先生在1927年7月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内心充满矛盾和彷徨。再如,秦武阳在荆轲刺秦王时为何不助荆轲一臂之力?答曰:秦武阳被秦王的威严所震慑,不敢有所作为。还如,散文的特征是什么?答曰:形散神不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阅读成见”是思辨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的天敌,在解读文本时应该尽量避免。
笔者以《孔雀东南飞》教学中“刘兰芝被遣归之原因”的探讨为例,浅谈如何提升学生思辨性阅读能力,以期就教于方家。
笔者就“刘兰芝被遣归之原因”进行了文章检索,发现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有:①不顺公婆说;②无子说;③门第差距说;④焦母恋子情结说;⑤太守阴谋夺妻说。笔者在教授这一课时,为了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特地将上述五个观点作为思辨性阅读的“标靶”提供给学生。具体做法是将全班学生分为五组,每组分配一个观点,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各小组对分到的观点进行质疑和论证。现将学生的研讨成果小结如下。
[小组1]持“不顺公婆说”观点的论者往往举《大戴礼记·本命》中“妇有七去”为证:“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就刘兰芝“不顺公婆”而言,我们实难从诗歌中去证实。诗中焦母数落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刘兰芝在何事方面“无礼节”和“自专由”,焦母却含糊其词,并没有举证。另外,这也只是焦母的一面之词,不可不信,但更不可全信。相反,诗歌中描述刘兰芝离开焦家时有礼有节地向焦母辞别,语重心长地嘱咐小姑子好生奉养焦母,处处体现出她懂规矩、有礼貌,有良好修养。
[小组2]“无子说”更显牵强附会。诗歌中刘兰芝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一对总是聚少离多的年轻夫妇婚后两三年里没有生育,并不一定说明女方刘兰芝不能生育,更不能说是给焦家断了后。从刘兰芝和焦仲卿暂时没有生养孩子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刘兰芝不能生育的结论属于主观臆断;其次,我们有理由推断,刘兰芝如果真的不能生育,被遣回娘家后,县令和太守也不会派人前去为子求亲。
[小组3]东汉时期的社会已逐渐看重门第观念,但据此认为刘兰芝被遣归是因为刘焦两家门第差距大,无疑也是牵强的。细读文本,我们否定的理由有四:首先,文本中有“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这样的句子,说明刘兰芝也是出身官宦人家;其次,诗歌中共有两次提及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刘兰芝会女红不足为奇,但懂音乐、知书达理则显然不是蓬门荜户的家庭所能培养出来的;再次,刘兰芝如果出身低贱,县令和太守怎会派人前来求亲?并且求娶的还是一个被婆家赶回娘家的女子?最后,焦家娶了刘兰芝两三年后,再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要休掉刘兰芝显得滑稽可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小组4]“焦母恋子情结说”乍一看似乎很新颖,其实也经不起推敲。一是文本中我们看不到、读不出焦母溺爱甚至纵容焦仲卿这样的信息,更找不出焦母依恋儿子的蛛丝马迹;二是焦母声称儿子休掉刘兰芝后,她会替焦仲卿求娶东家之贤女秦罗敷,若焦母真的有“恋子情结”,难道她不担心新来的秦罗敷会“夺走”焦仲卿?遣走刘兰芝,迎来秦罗敷,结果一样“失去”儿子,焦母又何必多此一举?
[小组5]“太守阴谋夺妻说”则更像天方夜谭。持此观点者认为,焦仲卿为庐江府小吏,虽然是官,但焦仲卿对其母说自己在仕途上无太大的发展——“儿已薄禄相”。焦仲卿为太守衙门里的小官吏,其妻被太守第五子看中,于是太守以焦仲卿的仕途发展为条件,逼迫焦仲卿休掉刘兰芝从而达到让自己儿子娶到刘兰芝的目的。而作者在文中不便直接表达这一内容,所以让焦母出面充当了一回恶人。我们小组认为,这一观点严重偏离了诗歌的内容,是纯粹的主观臆断,我们从诗歌的字里行间是绝难发现支持上述观点的任何可信依据的。
不难看出,在笔者提供了思辨性、批判性“标靶”观点后,学生还是能够结合文本细读,有理有据地反驳既定成见的。思辨性阅读不能止步于批驳成见,更重要的是能够合情合理地建构自己的观点。建构自己的观点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在批驳对方观点的基础上,悦纳其合理之处,纠正其偏颇之处。因此,笔者进一步指导学生再综合思考学界影响较大的这五个观点,指出其合理之处。
细究以上五种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后三者难以自圆其说,存在明显的漏洞,不可取。考量前两种似存在可能性的观点,我们发现其共同点是“错”在刘兰芝,这也就意味着焦母的做法——逼着焦仲卿休掉刘兰芝——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认为《孔雀东南飞》一诗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焦母的,那么矛盾就出现了:焦母作为一个封建家长,因为儿媳刘兰芝的“不顺公婆”和“无子”,她要求儿子休掉媳妇就显得合情合理,是在按“规矩”办事,虽然这一“规矩”往往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换言之,一旦刘兰芝被扣上“不顺公婆”或“无子”的帽子,其被休只是时间问题,并且其在舆情上完全处于劣势。这样的话,因为“错”在刘兰芝,我们就无法指责焦母,更无法将刘兰芝的悲剧归结于焦母的蛮横和专制了。
如何对这一矛盾做出合理的解释呢?笔者给学生提供了一篇文章:《诠释与衡定——〈孔雀东南飞〉百年研究综述》。该文指出,20世纪关于《孔雀东南飞》主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反封建礼教和反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制度和歌颂爱情。在了解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后,师生一致认为不管《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是上述三个中的哪一个或者兼而有之,都有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那就是焦母在诗歌中是反面的角色,是被批判的对象。那么我们在探讨刘兰芝为何被遣归时,如果一味地将“过错”推到刘兰芝的身上,焦母这一专制、顽固的封建家长形象是不是被弱化了?因为刘兰芝的“不顺公婆”或“无子”,焦母的做法就显得顺理成章,而不是无理取闹。什么样的焦母才专制和蛮横?不分青红皂白,在刘兰芝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自己看着不顺眼、心里不痛快,就让儿子休掉刘兰芝,这样的焦母才专制且蛮横。
其实我们在细究刘兰芝被遣归的具体原因时,往往从刘兰芝身上找原因,而忽略了一个事实:刘兰芝在行为和性格上越是没有过错和缺陷越能体现焦母的蛮横和独断。
基于这样的考虑,回到《孔雀东南飞》文本,我们却发现刘兰芝身上根本就没有让焦母可指摘甚至将其休掉的缺点,可以说刘兰芝是一个合格甚或优秀的儿媳妇。她与焦母的矛盾,是婆媳之间因观念不同而产生的代际摩擦,这在中国的家庭中似乎司空见惯,古代是这样,现代亦然。社会家庭生活中公婆权限的越位和丈夫职责的缺位,往往使得家庭不和谐。诗歌中焦母对刘兰芝的挑剔(“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以及焦仲卿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府衙(“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少有时间陪伴妻子,这无疑是婆婆在家庭生活管理上的越位和丈夫在参与家庭生活中的缺位。在这种婆媳矛盾中,焦仲卿扮演的角色自然很尴尬,他在处理母亲和妻子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态度不坚定,方法也欠妥当,于是刘焦二人的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换句话说,作者不言明焦母要求儿子休掉刘兰芝的具体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这种婆婆对儿媳挑剔的情形在当时的社会中并不少见,要说儿媳的过错有多大多严重,往往又难以说清;要说婆婆有多么恶毒,其实也谈不上。婆媳二人都是个性极强的人,并且两人在性格上均有瑕疵,双方又不能换位思考去尝试理解、包容对方的缺点,作者这样写是对当时社会客观情况的实录。二是《孔雀东南飞》毕竟是经过作者加工的诗歌作品,其中不免有作者的艺术加工,同时也注入了作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这样处理的效果是明显的——刘兰芝越是优秀,焦母越是要将其“先逐之而后快”,就越发显示出焦母的专制和蛮横。
我们认为论者从文本中的只言片语去挖掘和推想刘兰芝被遣归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其实可能恰恰掩盖了作者的真实用意:遣归刘兰芝,焦母说不清道不明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就是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理由,更何况封建家长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往往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这样的话,一个态度蛮横、自私固执的焦母形象就呼之欲出了,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也就随之诞生了。
当然,我们探讨的结论也不一定正确,但在探究的过程中,师生拓宽了视野,训练了思维,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解读文本的一个重要方法——不轻信、不盲从成见,学会辩证地分析观点,看待问题;尊重作者并从文本出发,合理建构属于自己的观点。笔者也由此总结出思辨性阅读的一般路径: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合理建构。另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文本解读不能撇开文本,否则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确认是否准确,反而有哗众取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