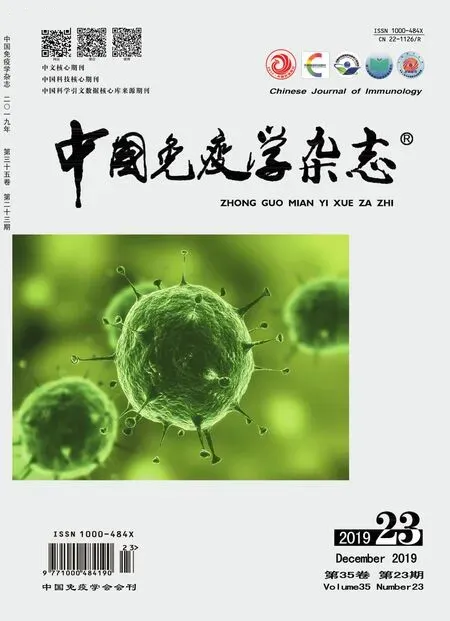肿瘤微环境及基于微环境的肿瘤治疗策略研究的若干新进展①
2019-01-10王建莉路小超赵同军
封 贺 王建莉 路小超 赵同军
(河北工业大学理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天津 300401)
近年来,对微环境在肿瘤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与肿瘤相关的微环境研究已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针对肿瘤微环境的靶向治疗也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2004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将肿瘤细胞及微环境相关研究作为重点资助项目,我国针对肿瘤微环境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肿瘤微环境主要由肿瘤细胞、细胞外基质蛋白(Extracellular matrix,ECM)、血管、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s,ECs)、神经和细胞外因子组成,这些微环境因素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1]。研究表明,肿瘤微环境不仅在肿瘤细胞增殖、免疫反应、血管生成、肿瘤复发与转移等肿瘤发展过程中的多个阶段和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癌症治疗期间机体的调节过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2,3]。对肿瘤微环境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肿瘤的发生发展机理,为临床实践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本文就近年来肿瘤微环境相关研究及基于微环境的各种肿瘤治疗策略加以综述。
1 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外基质
肿瘤的ECM是由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糖蛋白和蛋白聚糖等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大分子网络。这些大分子是由肿瘤细胞分泌到细胞外,并附着在肿瘤细胞表面或细胞之间。肿瘤细胞表面黏附的这些蛋白对肿瘤的侵袭与转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4-6]。在肿瘤发展的不同阶段,ECM会受到胶原酶、透明质酸酶、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s)、基质降解酶和金属蛋白酶抑制剂(Tissue inhibitor of matrixmetalloproteinase,TIMP)等多种酶调控,因而在功能上会有所不同[7]。这表现在,一方面ECM的存在能在肿瘤发展的早期预防肿瘤转移[8],另一方面随着肿瘤的发展,ECM的大量存在会削弱抗癌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另外,在转移的癌症中,破坏ECM可以提高抗癌药效[7]。
在针对细胞外基质的靶向肿瘤治疗中,纳米技术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其治疗策略主要有三种,破坏ECM、仿制ECM以抑制肿瘤的进展和干预ECM自然产生机制[4]。
针对肿瘤ECM破坏的方法大致包含三种。传统的方法通常是使用物理的手段,如辐照、高热和超声波等来达到治疗的目的[9,10]。然而物理方法会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对正常组织会造成潜在的物理伤害。相比之下,用某些酶或药物来扰乱ECM是一种更加可行的策略,这种方法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透明质酸酶(HAase)和胶原酶可以分解ECM[11],而使用重新编程的人类 HAase PH20可以提高抗癌的效率[12]。第三种方法是使用化学药剂如环巴胺。环巴胺可以破坏肿瘤细胞外的纤维蛋白,减少肿瘤血管并改善肿瘤的血液灌注率,提高抗肿瘤的效果。将含有环巴胺和紫杉醇的纳米聚合物(PEG-PLA NPs)作用于肿瘤组织,可以改变细胞外基质沉淀,改善胰腺癌肿瘤药物灌注并显著抑制肿瘤的生长[13,14]。
在肿瘤的发展早期,通过人工仿制ECM,加强ECM对肿瘤细胞的束缚,能够重塑肿瘤微环境,进而抑制肿瘤细胞的扩散和转移。例如,在乳腺癌和黑色素瘤肿瘤模型中,在肿瘤部位使用人工ECM(NFs)超过3 d,可以有效抑制癌细胞的转移[4,8]。
另外,干预ECM自然产生机制也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新领域[4]。最近研究表明,在小鼠乳腺肿瘤模型中,使用LOXL2抗体,可以干预原生肿瘤胶原蛋白的产生机制,进而抑制肿瘤的生长[15]。
2 肿瘤血管微环境
除了细胞外基质对肿瘤入侵转移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外,在实体肿瘤中,血管生成是肿瘤最为重要的标志,参与肿瘤的发展、侵袭、转移等各个阶段。
当实体瘤直径达到2 mm左右时,很难在周围环境中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肿瘤细胞便会分泌促血管生成因子进入肿瘤微环境诱导血管再生[16]。促血管生成因子中比较重要的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VEGF-A)、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 growth factor,PLGF)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16]。这些促血管生成因子共同作用激活周围血管的静息内皮细胞,并且通过调节细胞黏附分子如整合素等促进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和血管形成[16]。人们普遍认为,在肿瘤微环境中由VEGF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s receptors,VEGFRs)介导的信号级联通路,可以改变血管通透性进而促进肿瘤血管新生[17]。最近的研究表明,VEGF/神经纤维蛋白-2(Neuropilins-2,NRP-2)信号传导可直接促进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s,CSC)的增殖[18]。因为新生血管影响肿瘤生长,所以抗血管治疗被认为是有前景的癌症治疗方案。
2.1肿瘤血管微环境及肿瘤药物治疗 新生血管为肿瘤生长提供更多氧气和营养,使得肿瘤细胞数量短时间急剧增多。由于血管生成的过程受各种血管生成因子调节,使得不同肿瘤以及不同肿瘤区域形成的血管网络分布不同,形成的肿瘤血管微环境存在差异,对肿瘤生长的影响也会不同。此时,相对于肿瘤周边区域,肿瘤中心显示较高的细胞增殖速率。此外,新生血管还参与癌细胞扩散等活动[19]。
肿瘤内已形成血管与附近肿瘤细胞之间有一段距离,所以血管运输的药物打破血管屏障并能准确到达治疗区域是肿瘤药物治疗的关键[19]。由于形成肿瘤血管的内皮细胞间隙超过纳米大小,使得纳米尺寸的药物载体可以通过药物渗透贯穿血管壁,并积聚在肿瘤组织中释放抗癌药物,诱导细胞凋亡,进而阻碍肿瘤的生长[20]。其中,药物渗透是由血管内的压力梯度驱动并通过细胞间隙进行的[21]。但肿瘤微环境会限制药物的渗透性,导致肿瘤组织内药物分布不均匀、治疗效果不稳定。
2.2血管微环境中的内皮细胞 依据肿瘤血管微环境特性,可实施血管阻断策略治疗肿瘤。通过快速打破肿瘤内已形成的血管网络,阻断其对肿瘤生长过程中氧和营养物质的供应,对肿瘤细胞实行饥饿治疗,实现最终治疗肿瘤的目的[22,23]。实验表明,肿瘤微环境中ECs产生的血管分泌因子,如凹形(Notch)配体、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和细胞外因子(Wnt),对于组织和器官的维持起关键作用[24]。在肿瘤微环境中针对ECs的调控可能有效地破坏肿瘤血管,提高治疗的效果。许多制药公司依据VEGF特性,开发了VEGF靶向药物,其中包括针对VEGFRs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等[25]。
VEGF靶向药物最初不是用于破坏血管微环境,而是用于抑制肿瘤的血管生成。在动物实验时,单独将血管生成抑制药物用于荷瘤小鼠模型中能有效抑制其肿瘤生长。然而,除少数临床实例以外,单独将血管生成抑制药物应用于人类肿瘤治疗时则不能有效抑制肿瘤生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人类和小鼠体内新生血管对VEGF的依赖性不同所致[26]。而血管生成抑制剂与抗癌药物的联合疗法可能对肿瘤的治疗是有效的。在联合疗法中,血管生成抑制剂在破坏以前建立的肿瘤血管系统时,一方面降低血管的分布密度,限制氧和营养物质的供给,另一方面使得抗癌药物渗透到肿瘤深层发挥作用从而杀死癌细胞[26]。在晚期肾癌中,使用VEGF抑制剂阿西替尼和派姆单抗联合治疗,在Ⅰ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了良好效果[27]。通过VEGF诱骗受体(VEGF-grab)与放射疗法相结合,可以有效抑制VEGF-A和PLGF的作用,进而抑制肿瘤细胞的血管新生,使肿瘤血管正常化,最终达到良好的抗肿瘤效果。这种联合疗法为临床治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28]。
肿瘤血管网络的变化使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应答也发生变化。研究显示,VEGF抑制剂和前列腺素E2抑制剂都能抑制肿瘤中ECs的一种二型跨膜蛋白(Fas配体)的表达,使得CD8+T细胞浸润,调动机体免疫系统发挥作用[29]。另外,有报道VEGF信号传导抑制剂直接抑制T细胞中的PD1配体表达,并最终实现对肿瘤生长的抑制[29]。这些从ECs出发对肿瘤血管微环境调控,诱导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应答发生变化,其中涉及的微环境是实现抑制肿瘤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3 肿瘤微环境中的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主要来源于单核前体细胞,这些单核前体细胞通过趋化因子CCL2、CCL5、CXCL等被招募到肿瘤微环境中,形成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30]。TAMs占肿瘤组织重量的比例可以达到50%,大量巨噬细胞的浸润与不良预后密切相关[31]。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IFN-γ、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IL-4、IL-10、TGF-β、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和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等作用下可以大致极化为两种状态:经典活化的M1型巨噬细胞和替代活化的M2型巨噬细胞。M1型巨噬细胞通过吞噬作用实现对肿瘤的抑制。同时通过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免疫激活因子和趋化因子能够激活免疫系统,从而对肿瘤产生抑制作用。M2型巨噬细胞在组织修复和肿瘤进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由M2型巨噬细胞所分泌的VEGF、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bFGF、血小板源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等细胞因子能够促进肿瘤细胞的血管生成。M2产生的蛋白水解分子,如血纤维蛋白溶酶、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uPA)、MMP和组织蛋白酶B等可以直接重建细胞外基质[32]。此外M2型巨噬细胞还可以产生免疫抑制因子,包括PGE2、吲哚胺2、双加氧酶(IDO)、IL-10,这些免疫抑制因子导致免疫抑制。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对肿瘤明确的调控作用,促使人们将TAMs作为重要的抗肿瘤药物靶标探索治疗对策。
目前,针对TAMs的靶向治疗主要有以下几个策略:第一种是抑制TAMs向肿瘤部位的募集。使用单克隆抗体(mAbs)或化学药剂等药物可以抑制单核细胞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受体,进而抑制肿瘤的生长,这些治疗方法目前还在临床前和临床试验测试中[33,34]。其中某些药物,如CCL-2抗体、CSF-1 抗体、CSF-1R 抑制剂、FLT3抑制剂尚处于小鼠体内试验阶段。抗IL-6抗体、趋化因子受体CXCR4抑制剂等已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34]。第二种策略是减少TAMs的数量。减少TAMs的数量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减少血液中单核细胞的数量,而另一个则是减少肿瘤组织中已经存在的巨噬细胞数量。在小鼠体内使用的药物主要有双膦酸盐、豆荚蛋白、曲贝替定、阿仑单抗及抗毒素等。通过减少TAMs的数量,抑制肿瘤的生长、扩散和转移[35-37]。其中曲贝替定已进入Ⅱ期临床试验[38]。对M2型巨噬细胞重编程使其转化为M1型巨噬细胞是一种新颖的抗肿瘤潜在治疗方案。有几项研究表明,通过脂多糖、CpG和小干扰RNA(siRNA)激活的受体家族可以将TAMs转化为M1型巨噬细胞。此外,通过对核转录因子(NF)-κB或STAT3信号通路进行处理,可将TAMs转换为M1型巨噬细胞,如葡聚糖、索拉非尼等药物正在临床试验阶段[39-42]。还有一个可行的治疗策略就是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多数肿瘤会在其表面表达CD47“不要吃我”蛋白。CD47与巨噬细胞表达的信号调节蛋白α(SIRPα)结合,可以有效地逃避巨噬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使用Hu5F9-G4、CC-90002、外来体-SIRPα等可以抑制CD47与SIRPα相结合,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抑制肿瘤的生长[31,43]。
4 肿瘤微环境中的成纤维细胞
成纤维细胞来源于纤维母细胞及其他间质细胞,其主要功能是维持组织的结构骨架,在肿瘤组织中,成纤维细胞是肿瘤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微环境中,肿瘤细胞通过分泌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招募成纤维细胞,这些成纤维细胞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形成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44]。CAF的募集受到微血管损伤、细胞之间接触和可溶性因子、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以及ECM蛋白、蛋白酶、蛋白酶抑制剂等多种因素的调控。
肿瘤微环境中成纤维细胞对肿瘤生长的调控是多方面的。在早期阶段,CAF通过和活化的成纤维细胞形成缝隙连接对肿瘤产生抑制[45]。随着肿瘤的发展,CAF释放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DF1)、肝细胞生长因子(HGF)、VEGF以及PDGF促进肿瘤的生长并且介导肿瘤细胞的耐药性。CAF通过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PD-L2)和凋亡相关因子配体(FASL)诱导T细胞的凋亡,进而对免疫产生抑制[46]。此外,CAF还会分泌细胞外基质、蛋白水解酶、类肝素酶等可以促使细胞外基质重塑[22]。
以CAF为靶标的肿瘤治疗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一种重要的策略就是阻断由癌细胞和CAF激活的信号通路。例如在小鼠胰腺导管腺癌中,以过度活跃的黏着斑激酶(FAK)为靶标,使用FAK抑制剂(VS-4718)不仅可以减少纤维化,还可以减少肿瘤免疫抑制细胞的数量,进而提高患者的存活率[47,48]。另一种策略是抑制由CAF表达的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在荷瘤小鼠体内,通过使用FAP酶抑制剂Talabostat,上调诱发抗肿瘤免疫反应的特异性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可以达到抗肿瘤的目的[49]。人类FAP抗体sibrotuzumab在小鼠模型中能表现出特异性和活性,在肿瘤的早期阶段可以很好地抑制肿瘤的生长[50,51]。第三种策略是以FGFR亚型为靶标对肿瘤进行治疗。在实体肿瘤的治疗中FGFR亚型已作为重要的靶标。Lucitanib是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作用于FGFR异构体1到3、VEGFR 异构体1到3、PDGF α和β,目前在FGF扩增转移性乳腺癌中正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非特异性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多维替尼,对FGFR3有抑制作用,目前对实体肿瘤(NCT014 97392)的治疗已进入Ⅰ期临床试验阶段,而对尿道癌(NCT01732107)和前列腺癌的治疗研究则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52]。
5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在肿瘤微环境中,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TIL)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肿瘤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包含各种各样的CD3+CD4+和CD3+CD8+T细胞、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以及髓系抑制性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s),是 TME的重要组成部分[53]。由于T细胞浸润使肿瘤表达的趋化因子可以介导CD8+效应T细胞的招募,CD8+效应T细胞通过穿孔素和颗粒酶B的分泌诱导靶标细胞的凋亡。然而,CD4+Th2细胞和CD4+调节性T细胞是可以有效地抑制CD8+T细胞抗肿瘤反应的[54]。MDSCs通过多种机制抑制活化淋巴细胞的功能,诱导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s,CTL)耗竭。例如,在卵巢癌小鼠模型中,MDSCs高表达PD-L1和CD80,显著抑制了对肿瘤抗原的免疫反应。TIL高表达的TIGIT与肿瘤细胞表面的CD155结合后可以显著抑制NK细胞和CD8+T细胞的功能。TIGIT-Fc在体外也能抑制CD8+T细胞的激活,这种抑制作用取决于骨髓来源的树突细胞(BMDCs)上CD155的存在以及IL-10的产生[55,56]。 由于TME的多因素复杂情况,以及肿瘤细胞表面大量的PD-L1,使肿瘤免疫微环境处于抑制状态。
在以TIL为靶标的治疗中发现姜黄素不仅可以激活记忆T细胞和效应T细胞,还可以防止调节性T细胞的形成,从而增强T细胞对肿瘤的杀伤作用。同时,姜黄素还可以改变肿瘤微环境,增强CD8+T细胞的活性,进而更好地抑制肿瘤的生长。此外,姜黄素和免疫疗法相结合,可以抑制TGF-β、吲哚胺2,3和二氧合酶(IDO)等多种免疫抑制因子,增加T细胞的募集,进而达到更好的抗肿瘤目的[53,57]。单独使用TIGIT单抗或与其他免疫疗法联合使用可对荷瘤小鼠进行免疫治疗,增强NK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应答,有效地抑制肿瘤的生长,延长荷瘤小鼠的存活时间[58]。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阻断NKG2A受体可促进小鼠和人体中的自然杀伤细胞(NK)和CD8+T细胞的效应,从而增强抗肿瘤免疫。使用人源化抗NKG2A抗体蒙利珠单抗(Monalizumab),可增强NK细胞和CD8+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达到抗肿瘤的目的。该免疫疗法打开了癌症治疗新的突破点,对开发新一代免疫疗法有重要意义[59,60]。此外,大量研究表明,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ympho-cyte activation gene-3,LAG-3)不但抑制具有抗肿瘤活性的CD8+T细胞、CD4+T细胞、NK细胞的增殖,而且直接影响其免疫功能。使用LAG-3抑制剂抑制LAG-3能够让T细胞及NK细胞重新获得细胞毒性,同时,还能够降低调节性T细胞抑制免疫反应的功能。针对该靶点的抗体药物将来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抗肿瘤药物[61,62]。最近与PD-1抗体联合治疗的策略是人们研究的热点,如抗CTLA-4、免疫监测点抑制剂BMS-986016、抗GITR BMS-986156、BMS-986205、抗IDO抑制剂等与PD-1抑制剂联合治疗,已在临床阶段取得良好的进展[63,64]。
6 结论与展望
肿瘤发生、发展、转移及复发等多种过程离不开特定的肿瘤微环境,微环境方面的研究使人们对于肿瘤发生发展机理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启发人们探索肿瘤临床治疗的新途径。然而,目前基于肿瘤微环境的恶性肿瘤治疗方法还不够完善。
尽管以TME为目标并在临床前研究阶段取得了成功,但就目前而言,将这些策略转化为临床实践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肿瘤微环境中的成纤维细胞与巨噬细胞调控可能引起微环境其他因素随之改变,导致对肿瘤的影响难以精确估测。另外,微环境疗法如何与常规免疫疗法更好地结合,从而提高肿瘤治疗效果,重新塑造而不是消除TME将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治疗策略,值得进一步探索。总之,肿瘤微环境相关疗法,仍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大量的临床验证,从而在肿瘤治疗过程中有效杀死癌细胞、延迟或预防肿瘤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