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河》里有中国的图腾
2019-01-08林秀
林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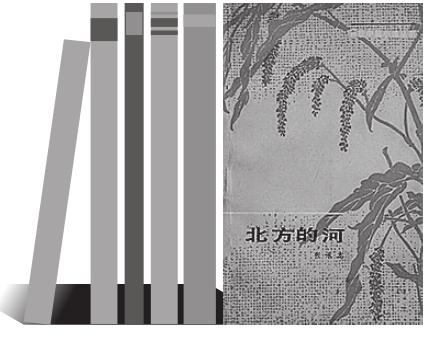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是一个以叙述知青岁月见长,同时兼具学者气质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往往杂糅了小说、散文、论文、报告文学等诸多文体的特征。发表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北方的河》是一个关于追忆与寻找的故事。一个结束知青生活回到北京的男青年不愿意接受被安排的“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工作,一心想要报考自己喜欢的“人文地理科学”的研究生。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他亲身实践,去到北方的几条大河进行实地考察,考察路上遇到了一个因公出差的女摄影师。小说围绕着二人结伴而行的溯河之旅,以及主人公回京之后的生活困扰和爱情纠葛展开。可以说,《北方的河》既是一个有关“知青”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寻根”的故事。因考试而开始的大河之旅既是对个体理想的追寻,也是对理想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并且是以“80年代”的知识与文化范式推进的。
在整个80年代,关于“中国”的故事几乎都是由知识分子来讲述的。因而80年代的文学史中,想象“中国”的主体无疑是知识分子群体。这意味着重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先要重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文学史把《北方的河》划入“知青文学”的序列,不仅因为作者张承志曾经的知青身份,更重要的是小说写出了知青们共同命运的合流和分化,内含着知青群体内部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复杂性。
作为知青文学,这部小说首先与七八十年之交返城后的知识青年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有关。随着“文革”的结束,一代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身份、生活、价值都需要重新定位。《北方的河》发表不久后,一些批评家就指出张承志的才华只擅长写大江大河寫乡野场景,刻画城市生活的能力不够。今天看来,这与其说是作者的文学才能有失,不如说是知青们对城市生活的焦虑使得小说的后半部分显得相对贫乏与黯淡。因此如何重建理想中的共同体,如何重新确认一代知识分子在共同体的历史与未来中的位置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小说开头第一句话正是在这个语境中诞生: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
如何克服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呢?《北方的河》给出了两种路径:一种是小说主人公以空间置换时间,通过重新肯定历史现场而走向未来的方式;一种是主人公曾经的知青朋友徐华北在厌恶和否定中摆脱历史奔向新生活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并不等于时髦的文化怀旧。小说中没有具体姓名的主人公考察自己青春记忆中的河流,是在他经历过历史洗礼与精神漫游后的重游。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此时的主人公已经是经过反思与重建的主体。再次游历北方的河某种程度上是他对自我重建的确认。小说在叙事方法上不断变换叙事视角,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他”)和第二人称的叙述视角(“你”)不断交错。这种自我分裂式的内心独白的产生,是现代文学中现代主体诞生的一个重要表症。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的主人公已经是一个迈入“新时期”的现代主体。而这个新的主体观看山河却不是为了凭吊历史。历史在他身上并未死去,不仅因为他曾经生活和熟识的山川、河流、台地、草原等将是他以后考试必须具备的知识,主人公在阳光下充满豪情壮志赤身站在奔流的黄河边上便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的形象,是历史的崇高客体。他在召唤青春时期那个勇敢无畏、积极健康、漫游远行的自己。通过再次寻找那个被特殊历史时期所锻造的自己来寻找未来前进的方向。在这里,历史被纳入了未来,并成为未来的指示。历史、现在与未来由此同时获得意义。张承志试图通过主人公的大河之行实现两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对接。因此,主人公所代表的这一类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是毛泽东时代与“新时期”耦合而成的。
“远行”作为80年代文学的主题之一,在张承志笔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一点如果对照80年代中后期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便可读出差别。差别不在于小说形式,不在于所谓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别,而是“远行”对于青年人自我主体性塑造的成功与失败。“远行”对于《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主人公而言,只是生活一次又一次荒诞的打击。它不仅没有帮助主人公确立自我,反而使“我”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无意义的个体。而在《北方的河》中“远行”亦是“回归”,是有动力的,有方向的,有目的的,是寻找自我和寻找意义的有效方法。这种有效性恰恰是被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所否定的那段历史给予的。

很明显,“北方的河”在小说中是作为“中国”的典型意象和图腾符号出现。如何观看和讲述“北方的河”意味着如何想象“中国”,如何重建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小说的主人公想象“中国”的核心方法是:人文地理学。他把“人文地理学”认定为“科学”,“北方的河”正是在“科学”话语中被赋予新的观看视角与价值。在主人公的知识结构中,“人文地理学”由语言学、考古学和地理学汇聚而成。每一门知识对于这个小说重新想象“中国”都有它的作用。它们分别代表想象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统一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和明确的领土。《北方的河》主要赞颂了五条北方的河流:额尔齐斯河、黄河、湟水、永定河、黑龙江。小说用这五条大河在空间上延展文明的视野,在时间上勾连出连续流淌的历史长河。它们共同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民族性格与文化气质。其中,将额尔齐斯河也作为民族国家的地理象征并不常见。这是一条流淌在少数民族地域上的河流。将边境河流与中原河流统一起来,一同纳入民族国家的表述,不仅是对来自西方的现代单一民族国家想象的突破,也提供了现代文明由海洋向内陆转移的视点,以及文明的边缘与中心变化的可能性。
由于考古学的加入,“北方的河”不只是“中国”地理空间上的坐标,它还是建构民族国家历史统一性的媒介。以黄河为主的晋陕河谷因着主人公在毛泽东时代的知青经历成为两个时代历史的连接点。而当作者试图把这两个连接起来的时代往更久远的历史源头追溯时,“破碎的陶罐”作为重要的意象就在小说中出现了。主人公和女摄影师在湟水河滩上发现了一个美而破碎的陶罐。有的研究者将这一意象视为美学观上“残缺的美”的象征。“陶罐”作为考古对象,在小说中与其说是审美的对象,不如说是历史的对象。
与主人公重走青春之路相对应的是他的朋友徐华北。同样是返城知青,徐华北丝毫不想回顾自己的知青生活,他抛下曾经的恋人,抛下一起插队的朋友,义无反顾地回城,同时将自己指认为历史的受害者。他也不满意自己在城里的工作,却通过转型为文学青年而实现自我救赎。有意思的是,“文学”在小说中对知青群体主体性重建的作用。主人公和徐华北都是热爱文学的青年。徐华北凭借“文学”找到恋爱对象,以及离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文学”是徐华北所代表的另一类知识分子可以顺利进入“新时期”的秘密武器。不难想象,徐华北很快将汇流到80年代占据主流位置的右派作家群。而我们的主人公热爱文学,却不得其门而入,他心心念念要把自己对北方河流的爱写成诗,却始终没有写完。在“文学”这个面向上,他没能得到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主人公完成自我重塑,凭借的是另一套话语:“科学”话语。
事实上,“科学”与“文学”这两种看上去相对立的话语在80年代的意识形态中与其说是南辕北辙,不如说是相辅相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实也是不同的文化修辞的产物。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80年代的两大主潮。“科学”与“文学”在“现代性”知识与观念的层面上成为8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两种不同范式。“北方的河”在小说中被“文学话语”和“科学话语”双重叙述。主人公与徐华北看似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但在80年代他们命运的相似性仍然远大于差异性,因为他们共同承担了历史的负重,共同面临着现实的壁垒(小说中强大而压抑的“体制”)。同理,《北方的河》可以视为80年代初文学界弥合两个时代的裂缝,抚慰历史转型的阵痛而作的一种尝试,文学、科学与政治在民族国家想象上完成了一次合谋。这样的尝试之所以是可能的,因为80年代有着时代的共识,有着共同的他者。而那些微小的缝隙将留给90年代,并成为90年代知识界的分歧与分化的伏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