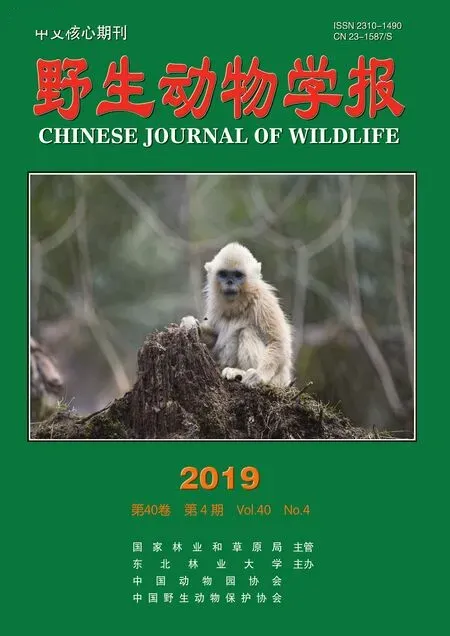国际法视野下的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研究
2019-01-08王玫黎武俊松
王玫黎 武俊松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401120)
受全球气温变暖的影响,北极地区成为近几十年气候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区域之一,进而导致常年冰封的海域不断被融化。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北极海冰预计于2080年全部融解。北极海冰、冰盖的逐渐消融不仅会影响世界整体气候环境受损,更会造成北极原有野生动物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北极地区与南极地区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南极是大陆且四周环海,北极则由中心“冰封区域”和周围零散的岛屿组成,因此大部分的北极动物要依附于积厚的冰盖才能生存。北极地区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例如北极狐(Vulpeslagopus)、麝牛(Ovibosmoschatus)、环斑海豹(Phocahispida)、海象(Odobenusrosmarus)、白鲸(Delphinapterusleucas)、北极熊(Ursusmaritimus)等。北半球全部鸟类的1/6在北极繁育后代,而且至少有12种鸟类在北极越冬[1]。北极沿岸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者国际组织以章程倡议的形式对捕猎北极野生动物的行为加以约束,但考虑到上述国际法律文件并不均具有强制约束力且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因而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保护。
野生动物是指非人工驯养、在自然状态下生长的各种动物,包括哺乳、爬行、两栖、鸟类、鱼类及其他动物。全世界的野生动物分为四种类型即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有害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物是指由于自然环境本身发生改变或者受到人类行为活动影响又或者动物自身原因而出现灭绝可能性的物种如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藏羚羊(Pantholopshodgsonii)等[2]。本文主要论述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从法律的层面来讲并不仅仅局限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名录中标注的物种,因为并非所有濒危野生动物都被该公约所收录,还存在大量的濒危野生动物物种被其他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同时濒危野生动物与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所以笔者的研究对象具有广泛性、整体性、概括性的特征。
1 北极濒危野生动物国际法律保护的现状
当前涉及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国际法律文件比较繁多,既包括国际性和区域性的条约和协议,还包含双边国家间的协定和北极沿岸国家内的立法文件,笔者仅就部分典型的国际性和区域性法律文件进行简要的论述。
1.1 《生物多样性公约》
1992年6月5日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该公约的通过并生效表明世界各国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世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具有不可估量的内在价值。《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四条规定成员国家对生物多样性的管辖范围并非仅限定于该国管辖范围的地区内,若在该国管辖或控制下开展的过程和活动,无论其影响发生在何处,此种过程和活动可位于该国管辖内也可在国家管辖区外,从而扩充了相关成员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辖权范围,对于具有迁徙习性或易于在不同国家管辖范围内频繁活动以及其他国家主权管辖无法延及地区的生物而言将会形成庞大的保护圈。该公约第五条针对生物多样性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保护开展合作事项也进行了规定。北极有大量的稀有野生动物,一部分分散于北极沿岸国家,一部分集中于无主权国家管辖的北极点附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款北极沿岸国家或公约缔约国都有义务对北极濒危动物的保护开展合作,因而该公约对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具有深远的价值意义。
1.2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又称为《华盛顿公约》,该公约于1973年3月3日签订于华盛顿,1979年6月22日修订于波恩。该公约设定的目的即为了保护某些野生动植物种不致由于国际贸易而遭到过度开发利用,所以进行国际合作是必要的。该公约将物种按照国际贸易对其灭绝危险程度的影响划分为附录Ⅰ、附录Ⅱ和附录Ⅲ,公约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缔约国均不应就附录Ⅰ、附录Ⅱ和附录Ⅲ所列物种标本进行贸易。受北极极端寒冷气候的影响,北极大部分动物均是依靠自身厚重的皮毛得以生存,正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北极野生动物如北极熊、北极狐、麝类动物等物种遭到大量的捕杀。《华盛顿公约》的生效使得北极野生动物避免因国际贸易而被滥杀,但公约的最大不足在于若该交易发生于某国家管辖范围内并不受该公约规定的束缚,因为公约仅是为防止因国际贸易而捕杀稀有动物,但并不禁止非商业贸易的物种出口,只是针对附录Ⅰ、附录Ⅱ和附录Ⅲ中所列的物种出口加以严格的限制和审查。该公约虽不完善,但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仍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1.3 《北极熊保护协议》
《北极熊保护协议》由丹麦、加拿大、挪威、苏联和美国于1973年签署,旨在承认北极地区国家在北极地区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保护方面的特殊责任和特殊利益,承认北极熊是北极地区需要特别保护的重要资源[3]。该协议的生效使得北极熊获得法律上的保护和合理化的使用,但笔者认为《北极熊保护协议》仍存在许多不足,例如该协议第一条规定了禁止捕猎北极熊的例外情形,这有可能为滥杀北极熊的行为提供“合法化”的依据。该协议第三条规定了5种例外的情形,其中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是例外规定中例外情形即可以通过狩猎获取的毛皮和其他珍贵物品能用于商业目的。尽管《北极熊保护协议》基于尊重原住民传统权利的目的做出了“例外中的例外情形”,缓和了土著居民与环保人士之间的矛盾,但这并非是长久之计。北极熊本身基数就比较低,加之北极环境的日益恶化,间接地导致北极熊的繁殖能力不断下降,一味地妥协终究会影响北极熊的可持续性发展。针对北极熊法律保护的未来走向将会是改变原住民捕猎的传统权利或者将严格限制该权利的行使。
2 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困境
2.1 国际法和治理机制的碎片化
北极地区拥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是维护世界生物多样性中的重要一环。基于北极环境的极度恶化,许多的野生动物均出现生存危机的问题,因而为加强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北极沿岸国家,亦或是民间团体组织纷纷出台相应的措施拯救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截至目前,涉及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法律文件达十余件,以此衍生出来的北极治理机制便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繁多的国际法律文件并非由同一组织机构做出,不同的国际条约由不同的成员签署,不同的治理机构也有不同的国家或组织参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法律文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治理机制之间的相互重叠或空缺,无法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产生良好的法律保障机制。上述现象有学者称之为“国际法碎片化”或“治理机制碎片化”[4],国际关系领域的机制“碎片化”是指国际政治特定领域协调公私规范、条约和组织时不断出现的多样性与挑战[5]。而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则将体系内部的各种规范和制度之间未形成一种结构上的有机联系,导致彼此之间冲突、矛盾,就像堆积在一起的“玻璃碎片”的现象称为“国际法的碎片化”[6]。
《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序言中多次重申并强调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以及对进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性,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为《华盛顿公约》)的相关规定就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所要求的宗旨和目标产生矛盾和冲突。就北极熊而言,《华盛顿公约》将其列为附录II的保护序列中,即当前不属于濒危物种,只需进行适当的贸易管制防止北极熊进入附录I的保护序列中。为了促进对北极熊的法律保护,美国在2013年向缔约方大会提出全面禁止全球北极熊制品贸易的提案,但加拿大认为美国的提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北极熊处于濒危的状态,加之大会考虑到北极土著因纽特人的生计问题因而对提案做出否决[7]。由于国际法不成体系和政出多门的分散性,《华盛顿公约》在针对北极熊法律保护上所直接关注的是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而非导致濒危野生动物面临灭绝的原因[8]。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治理机制碎片化的主要表现在治理机构虽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但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例如在俄罗斯西北部地区,许多涉及环境监测、技术转让以及增进核安全所需要的资金和资源并非来自北极理事会和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而是来自欧盟、美国的基金组织或双边合作[9]。
2.2 北极原住民法律权利本位的偏离
北极原住民法律权利本位的偏离是目前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困境之一。何为法律权利本位?有学者认为“权利本位则意味着尽可能多的权利确认和尽可能少的义务约束,除非必要,否则绝不使普通人的义务约束有所增加”,并认为权利本位应当包括权利平等、对多元利益的确认、对世俗幸福的肯定等内容[10]。北极原住民法律权利本位的偏离仍是制度设计层面存在问题,虽然北极原住居民在获取国际社会援助、谋求法律权利的道路非常漫长、坎坷,但毕竟取得较大的成果。据有关数据表明北极地区的人口约为1 342万,在环北极八国中,俄罗斯占总人口的74%,约993万人,美国占总人口的5.5%,约74万人[11],其中以因纽特人为代表北极原住居民大约有13万[12],萨米人8万—9.5万[13],如此庞大数量的北极原住民为了参与到北极事务的治理当中一直积极地向北极理事会建言献策,但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仍无法真正地融入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进程中。
代表北极原住居民法律权利的北极原住民组织基于内外部因素使得法律权利本位一开始就没有在正轨上运行,笔者认为导致这种境况发生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北极理事会中的6个原住民组织中只有因纽特人环北极理事会更好地参与北极事务的治理工作,原因在于该理事会代表的国家都是大国、强国的因纽特人的利益,通过将北极环境问题与原住民人权的相衔接、跨界污染与气候变化等议案的分析、探讨使其在北极理事会站稳了脚跟,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发言权,但其他原住民组织由于缺乏专业人士或忙于调整内部目标和结构无法有效地参与到北极事务的治理当中,无法全心全意的代表北极其他原住民的法律权利[9]。除此之外,维持北极原住民组织参与北极事务治理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14],而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治理必然会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因此北极原住民组织资金链的断裂势必影响其参与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连续性和积极性。其次,北极理事会对北极原住民组织的资格和定位就限制其应当发挥的作用,不享有表决权的北极原住民组织同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友好,应当属于“微妙”的状态,所以北极原住民组织很容易沦为北极理事会的“摆设”,最终北极理事会还是处于北极八国的掌控之中,这对于将北极视为自己生存家园的北极原住民而言,他们的法律权利很少能够在正轨上运行,毕竟限制因素太多导致他们只能依形势而行事。
2.3 北极理事会“造法”职能的局限性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北极理事会并不属于国际法上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国际机构,只能是一个商讨北极事务治理的政府间高级别论坛,这一点在《渥太华宣言》中也有相应的表述。这种现象就在制度层面限制了北极理事会的“造法”职能,所以不难发现,在北极地区有着较多的全球性框架公约以及针对特定问题或有限区域制定的双边条约,唯独缺乏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北极区域性框架公约。一方面,全球性框架公约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另一方面,双边条约缺乏全局性和协调性[15],而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作为北极生态环境的一部分,需要构建一个整体性的环境治理机制,所以北极理事会作为当前北极事务治理最为完善的区域性机构应当担负起制定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的职责。
笔者认为北极理事会“造法”职能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北极理事会的机制构建和法律地位等问题存在争议。美国之所以反对将北极理事会限定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是因为美国并不想因此受到北极理事会机制的约束而妨碍到美国对北极所进行的军事活动、资源开发、航道运输等并回避一切有关经费的承诺[16],就此北极理事会到目前仍是一个协商、沟通的平台,加之《关于成立北极理事会的声明》也并未授予北极理事会立法权,这是导致北极理事会“造法”职能缺失的根本原因。其次,北极理事会的资金来源于成员国的捐赠[17],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在就北极理事会成立之初就回避了有关资金承诺的问题,因而,北极理事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而北极理事会“造法”职能的发挥需要大量的国际法律专家、北极科学家、成员国代表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商定,这对“造法”资金提出了更为高标准的要求。当然,资金不足不仅影响“造法”职能发挥作用,对执行机构以及执行力而言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以北极理事会下设的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CAFF)为例,CAFF主要汇集整理和分享北极生物信息并提供动态评估,这种动态基线数据不仅对技术和设备有着严格的标准,对资金的需要也是非常庞大的[18]。
3 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路径选择
3.1 构建有序化的国际法体系和治理机制
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需要从制度层面搭建起一套完善、整体、统一的法律体系和治理机制,由于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仅属于北极治理事务的某一分支,所以倘若北极无法从顶层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模式,则部分领域的治理也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际法的碎片化是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6]。当认识到北极地区法律体系碎片化是国际大环境形成的结果,我们更多的不是呼吁建立超国家主权的联盟以期达到北极法律体系统一的效果,而是如何成功地协调北极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关于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碎片化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可以采用《维也纳条约法》中“体系一致原则”的相关规定[19],但《维也纳条约法》真的能够解决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碎片化的问题吗?笔者认为体系一致原则看似能够缓解法律碎片化带来的问题,但无法最终解决这一矛盾,浩如烟海的国际法规则和原则都是主权国家意志的妥协,能否为协调北极散乱的法律文件仍有待考究。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虽然被视为解释条约的原则之一,但能否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文件进行一般法和特别法的精确区分仍是比较棘手的问题[8]。
笔者认为解决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碎片化的最优措施即在北极理事会的基础上下设北极法律事务中心,北极法律事务中心分设三个附属机构即北极法律协调部、北极法律审核部、北极法律咨询部。北极法律协调部的主要职责是对当前涉及北极事务的所有国际法律文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一方面对存在冲突和矛盾的条约规范进行标注并将条约缔约国邀请制北极理事会经行磋商、会谈,会同北极法律咨询部对相关条约规范做出适合北极发展的全新解释;另一方面通过梳理还能发现北极事务是否还存在法律空白点,若存在法律空白点则将相关内容报告北极法律咨询部,由法律咨询部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并上报至北极理事会是否就此采取立法安排。北极法律审核部即对相关国际组织或双边国家就北极事务达成的法律文件进行登记备案并进行专项审核,排查是否与其他北极事务法律文件存在矛盾和冲突,若存在不协调之处,则向缔约国提出建议,若不在就登记备案作为日后解决争端的法律依据。北极法律咨询部主要由北极事务专家和国际法学者组成,旨在为北极法律提供咨询建议倡议北极理事会对北极某领域进行专项立法或对已登记备案的北极法律进行相关性的解释等。关于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治理机制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建议涉及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国际组织或下属分支机构派遣一定数量的代表人员入驻北极理事会,组成一个全新的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专项组,这样的平台有助于各组织的相互交流和互动,避免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重复投入,将资金和技术合理分配,推动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进程。
3.2 匡正北极原住民的法律权利本位
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保护需要在制度上给予北极原住民和原住民组织切实的“法律权利”,这种“法律权利”不是束之高阁的权利,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权利,应当是真正可以被北极原住居民和原住居民组织运用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极大地提高他们参与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根据北极原住民秘书处相关数据统计,6个原住民组织毫无例外的优先选择参加可持续发展工作组,其次是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对于其他工作组,只是战略性地参与[14]。北极理事会下设的6个工作组之间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关联,由于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所以若仅参与可持续发展工作组和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的活动而忽略对其他工作组的参与,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并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这种选择性、战略性参与无非还是北极原住民法律权利本位偏移造成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匡正北极原住居民的法律权利本位。
首先,权利平等是权利本位的首要原则即在解决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事务,各方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笔者认为北极濒危野生动物属于低敏感领域内的事务并不会产生北极原住民组织权利肆意扩张、摇摆北极理事会决策指向的现象,同时北极原住民长期生活在北极,对北极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种类、养护等有着独特的了解,结合专业北极科学家、动物学家将会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有必要适当放开北极原住民组织在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表决权的限制,让北极原住民组织享有对涉及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表决权,提高参与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积极性。其次,对多元利益的确认是权利本位的要义之一。北极原住民和原住民组织是北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北极的生存者、参与者、发展者,享有对北极事务治理的发言权、参与权、表决权。这些原住民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维护北极原住民权益,保护北极家园[20]。笔者认为北极原住民组织应当将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提到日程上来,并作为未来长期发展的目标之一,加快调整组织内部结构的速度,同时加快对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专业人士的培训工作。除此之外,北极原住民组织应当寻求国际组织的援助,扩充在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方面的资金来源途径,化解北极原住民组织的财务危机。最后,北极原住民传统的经济来源就是依靠捕猎活动,之所以北极原住民组织和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异常微妙,重要的原因在于北极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有所偏差,至今有些条约、协议为了尊重北极原住民的风俗习惯仍为其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无法保证这样的规定是否有益于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所以,笔者认为北极原住民应适当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旅游业、航运业、新能源开发等,减少对北极野生动物的捕猎活动。
3.3 北极理事会“造法”职能的完善
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地区最完善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是协调北极事务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虽然《关于成立北极理事会声明》明确规定了北极理事会不是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国际机构,因而就不具有立法权,只能出台一些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宣言和协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2011年到2017年间,北极理事会先后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即《北极海空搜救协议》《北极海洋油污预防与反应合作协定》《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协议》。通过上述3个法律文件,不难发现它们都属于低敏感领域的事务,同时需要共同合作方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与上述北极事务都存在着同样的特征,北极理事会应当就此制定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件。
笔者认为北极理事会“造法”功能的真正发挥要从3个方面加以讨论:首先,就是资金的问题。北极理事会应当针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形成专项资金库,将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作为独立的一项事务,允许域外国家、国际组织或成员国进行捐赠,捐赠的资金数额与享有的权利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让真正关心、热爱北极野生动物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来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这将会极大地调动各国的参与积极性,充实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专项资金库,为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立法活动通过资金支持。其次,就是立法者的问题。笔者认为北极理事会应当赋予北极原住民组织和对专项资金库进行捐赠的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相应的表决权,原因在于北极原住民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有着独特的见解,在立法过程中,针对部分条款的技术性规定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同时北极原住民传统经济依靠的就是北极野生动物,该立法活动影响着北极原住民的利益。对于捐赠专项资金库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享有表决权不再予以重复论述。最后,就是程序的问题。正所谓“程序正义才会带来实体正义”,北极理事会应当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定与实施“硬法”的程序规则,为“硬法”的制定与实施提供良好的指引。根据《渥太华宣言》以及北极理事会议事规则,理事会任何决议均须得到北极八国一致同意[17],但考虑到制定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法律涉及主体较多,牵涉的利益甚广,采用“八国一致”原则显然不合理,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民主集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更为适宜。除此之外,程序规则还要遵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这是因为“程序正义来源于程序透明”。
4 结语
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北极航道日益成为一种可能,北极八国更加看重北极背后的军事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呼吁加强对北极生态环境的保护,并签署了一系列的宣言和协议,但收效甚微并不理想。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地区政府间高级别论坛,扮演着北极事务治理的指挥者、协调者、执行者的角色,但北极理事会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改、改什么”是北极理事会乃至国际社会需要慎重思虑的问题。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作为北极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关乎北极整条生物链和生物多样性的存亡,但对北极濒危野生动物有着密切联系的北极原住民组织却被剥夺了相关治理活动的表决权,严重影响了北极原住民组织参与保护活动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北极地区尚不存在针对保护北极濒危野生动物而制定的法律文件,而是零散地分布在其他北极生态环境保护的宣言或协议中,因而,北极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亟须一部完善的区域性国际法律文件来指引、保障。北极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需要国际社会公众、相关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