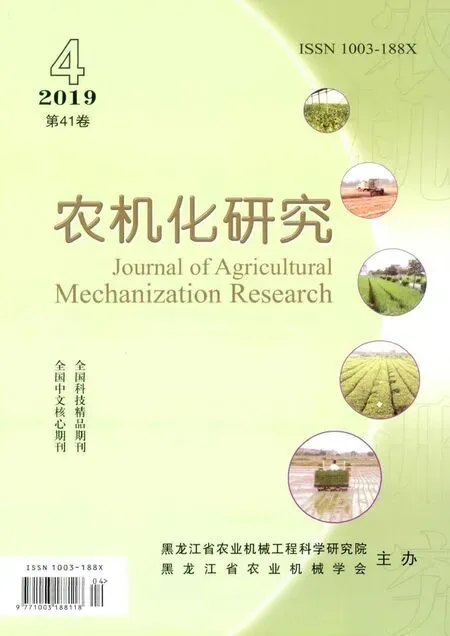我国丘陵山区应对农机化两大困境的新对策—基于宜机化土地整治
2019-01-08陈建
陈 建
(西南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重庆 400716)
0 引言
目前,我国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面临两大困境:一是整体说来,在已实现机械化的环节,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强度大及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非常突出;二是在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地方和作业环节,机械化推进艰难缓慢。多年的农机化实践表明:土地条件是制约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发展的第一因素。
但另一方面,近年来这一地区的一些土地整治项目及研究工作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环境及景观等方面,并没有很好地回应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提升农业机械化效果的现实需求。面对困境,2015年以来,山地、丘陵分别占幅员面积76%和22%的重庆实施了一项新的对策:开展宜机化土地整治行动,跳出农机抓农机,通过整治土地,为大中型农业机械顺利进入田间高效作业及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实现了用大中型农业机械取代微小型机械及人工进行全程作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及资源利用率。
1 我国丘陵山区农机化面临的两大困境
1.1 机械化效果不显著
农业机械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劳动强度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及资源利用率,从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但在目前我国丘陵山区大多数已实现机械化的环节,这些作用并不充分,仅仅实现了“机械化1.0”(即实现了机械化零的突破),由机械代替了人畜作业,但存在着劳动强度大及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例如,在丘陵山区,机耕率较高,但主要是依靠微耕机来实现的,然而“微耕机解放了牛,累死了人”却是操作者的普遍反映[1]。这是因为微耕机功率小、幅宽窄、速度低、劳动强度大、效率很低。另外,机器田间转移时间长且非常困难,常常需要搭跳板,挖临时通道,人拉、抬、推,不仅劳神费力,还不时伴随着人、机伤害的危险。由于农机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其对土地产出率提高的贡献也极为有限;同时,微小型机械日趋饱和,利用率低。
1.2 机械化推进艰难缓慢
为了推进丘陵山区的农业机械化,相关各方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收效不大。以重庆为例,2007年农业部批准在重庆市建设全国农业机械化综合示范基地[2],要求重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丘陵山区的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2011年,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精神,重庆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国最大的小型农机装备制造基地[3]。2011年,重庆市科委启动了包括“重庆市农业装备产业技术路线图”在内的“重庆市农业产业技术路线图”的研究工作[4]。与此同时,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持续增大,农机作业补贴快速跟进,小型农业机械不断涌现。所有这些对促进农业机械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重庆市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2007年的13.23%提高到2012年的33.05%及2016年的45%;但是,农业机械化推进缓慢,困难重重。以机播为例,时至2012年,重庆的水稻、油菜及马铃薯的机播水平分别为17.10%、0.39% 及 0.03%,而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及棉花的播种几乎全由人工完成。所使用的水稻插秧机主要有两行步行式、四行步行式及六行乘坐式插秧机3种机型。两行机适宜于小田块,但效率低、价格高,且由于独轮结构不便操作;四行机效率较高,容易操控,但由于较重难于转移;六行机操作更方便,效率更高,但同时要求田块较大且具备合适的道路条件,然而满足要求的地方极为有限。为了推进机插,重庆市提高插秧机补贴力度,最高时国家、市、县(区)三级补贴高达机器售价的85%以上,随后又推行450元/hm2的机插作业补贴,但效果仍不显著。
2 制约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第一因素
制约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因素涉及农机作业条件(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经济基础、机械装备、种植制度、人员素质、科技能力、社会服务及政府支持等[1,5-10]。这些因素中,哪一个因素最重要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随时空条件变化而变化的问题。就目前情况来分析,第一因素是农机作业条件。按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高到低排序,将全国31个省(市、区)及新疆兵团分成3个方阵。根据《2012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第三方阵包括的11个省(市、区)依次是湖北(45.81%)、云南(41.38%)、四川(40.96%)、广东(40.09%)、甘肃(40.02%)、湖南(37.81%)、广西(37.23%)、海南(33.66%)、福建(33.46%)、重庆(33.05%)及贵州(16.74%)。另一方面,全国有11个省(市、区)的丘陵和山地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大于60%,依次是贵州(95.6%)、云南(92.3%)、四川(91.4%)、重庆(85.3%)、福建(78.9%)、广西(73.3%)、江西(70.3%)、浙江(70.0%)、广东(63.8%)、湖北(62.5%)及湖南(62.4%)[5]。对照上述两个排位,可以看出:综合机械化率排在第三方阵的11省(市、区)中,贵州、云南、四川、重庆、福建、广西、广东、湖北、湖南等9省(市、区)均是丘陵山区占比较大的,仅有海南及甘肃例外;而在丘陵和山地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大于60%的11个省(市、区)中,只有浙江和江西两省综合机械化率进入了第二方阵,丘陵山区高占比与综合机械化率低排位的重合度高达82%。这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极强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丘陵山区地块狭小零碎分散且有高差,道路条件极差,因而只能依靠微小型农业机械;但这类机械田间作业效率低,道路至田间及田块之间的转移、运输困难,不改变这种农机作业条件,就无法运用大中型农业机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难以实现。
纵观世界丘陵山区占比很大并已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及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经过科学合理的田地整治。尽管按照著名农业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及弗农.拉坦的资源禀赋诱导技术变革理论,一国农业增长选择怎样的技术进步道路,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的国家,选择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是最有效率的,如美国;相反,土地资源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选择生物化学进步的道路是最优的,如日本[11]。然而,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的日本从1965年开始便组织实施了长达40年的4期土地改良计划,以兴建水田排灌设施、加强农田道路建设、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田块标准化为目标,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有相似地形地貌的韩国及我国台湾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5,12]。山地丘陵占国土面积76.9%的意大利在从水稻出口国一度成为进口国后,也对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平整改造,从而大大提高了机械化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又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水稻出口国之一[13]。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学者都呼吁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发展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进行土地整治及道路修建,为农业机械顺利高效作业创造条件[1,5,7-10,12,14-16],但主要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建议在实际工作中至今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丘陵山区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无法回避、刻不容缓的工作了,且我国已有经济能力来处理这一问题了。
3 我国丘陵山区土地整治与农业机械化的关系
我国丘陵山区土地整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其目标是增加有效耕地面积,以弥补建设用地。随着土地整治工作的展开,研究工作也积极跟进。应该说,由国土、农综、水利等部门主导的整治工作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对于确保我国耕地的质量及数量、解决“三农”问题及优化农村生态与景观从不同侧面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然而,不得不说,一些工程及研究并没有将土地整治与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提升农业机械化效果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可以归纳分析如下[17-20]:
1) 在评价土地整治效果时,仅将农业机械化作为社会效益予以考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业机械化带来的经济效益。
2) 在考虑农业机械化时,采用的指标是可机械化作业面积比率,没有考虑机型的大小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3) 修建道路时,没有考虑机器通过的可能性。从重庆市土地整理项目工程规格来看,0.6m规格的生产路比重远高于0.8m规格的比重,如果不是十分特殊和迫切的要求,1.0m的生产路几乎不做考虑;3.0、3.5m规格的田间路比重一般显著高于4.0m规格的田间路比重,有些项目甚至不涉及新建田间路[21]。因此,土地整治后道路系统仅方便了人的出行,三轮车、小型拖拉机都难以通过,更不用说大中型拖拉机了。
4) 用田块形状指数(圆度指数)和分形维数(方度指数)比较土地整治前后的情况,它们分别表示田块形状接近圆形、正方形的程度;但对于机械化作业田块来说,这并不是好的评价指标。为了提高作业效率,显然正方形好于圆形,而长方形好于正方形。D.R.亨特指出,“长地块可明显提高行走法的时间效率……一个荒谬的极端情况是,最有效的地块形状是地块宽度只有农机具宽度那样大,这样就没有回转的时间损失了[22]”。日本政府推荐规格化水田,即长l00m、宽30m、水平度小于2.5cm[5]。我国农业部标准要求“田块形状选择依次为长方形、正方形、梯形或其它形状,长宽比一般应控制在4:1~20:1[23]”。
5)只有机耕干道而没有机耕支道,机器无法下田,只有在干道上望“田”兴叹。
6)为了排水,在田间修建水泥渠道,导致机器田间转移困难。
4 针对困境的新对策-宜机化土地整治及其效果
4.1 宜机化土地整治的主要内容
重庆市开展的宜机化土地整治旨在通过整治丘陵山区的土地,使其适宜于大中型农业机械高效作业,其主要内容为:在土地承包人自愿的前提下,根据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的要求,政府按每667hm2补贴1 000、1 500、2 000元的标准进行资助,并充分利用以前各类土地建设的成果,通过消坎、填沟、建梯等工程措施,将一定区域内的“巴掌田” “鸡窝地”且有高差的地块进行合并,因地按需地整治成水平条田、坡式梯田、缓坡地块及梯台地块等4类地块,按照能大则大、能长则长、尽量提高机械作业效率的原则,对每一类地块的长、宽、面积及纵、横向坡度等指标都提出了明确的技术要求;联通外部路网,调顺耕作道、生产便道及沟渠,实现道路、地块互联互通;协调防洪防渍及抗旱灌溉;同时,通过秸秆还田、绿肥种植、粪肥施用、深松及旋耕等措施,快速熟化生土,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肥土壤。
4.2 宜机化土地整治对农业机械化的效果
1)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重庆永川陶义农机股份合作社,土地整治前耕地采用4.4kW的微耕机,2人轮流操作,每人每天作业0.167hm2;人工移栽油菜时,每人每天完成0.046hm2;油菜收获采用久保田688联合收割机,由于田间转移每台车需配3人,每天工作8h,但实际收割时间只有4h,每人每天作业0.18hm2。土地整治后,耕地采用55.2kW的拖拉机带动耕幅为2.3m的旋耕机,每人每天作业2hm2;采用电动撒播机直播油菜时,每人每天作业2.8hm2;采用久保田688联合收割机,1人即可完成作业,每人每天作业2.5hm2。耕种收劳动生产率分别是整治前的12、60.1及13.9倍。
2)提高了土地产出率。首先,土地整治消除了田埂、厢沟及耕作死角,耕地面积普遍增加3%~5%,有的甚至达到10%;其次,通过整治,大片撂荒地得到了利用,仅在潼南区,近两年来就有超过1 333hm2的荒废多年的田地重新种植作物;再次,整治后的土地平坦,土层增厚,加上培肥措施,为高产稳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作业效率的提高缩短了收获和播种时间,从而使得提高复种指数成为可能。例如,在永川圆桂农机股份合作社,土地整治前只种一季水稻,整治后改为稻油轮作;在永川陶义农机股份合作社,高粱-再生高粱-油菜一年三熟取代了高粱-油菜两熟模式。
3)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不进行土地整治,丘陵山区的农业生产只能依靠微小型农业机械,这类机械资源利用率很低。例如,据初步统计,在重庆,绝大多数微耕机1年工作时间至多100h,使用寿命不超过3年;而大中型拖拉机一年平均工作1 500h,使用寿命6年。因此,在整个寿命期大中型拖拉机的工作时间是微耕机的30倍。此外,微小型机械大多功能单一,如微耕机除旋耕作业外,很难挂接其它机具进行诸如犁、耙、深松、播种、运输等作业,这就使得我国丘陵山区农用动力机械与作业机械的比值低至1:1.16,与1:1.6的全国平均值相比有很大差距,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6的水平。这意味着动力机械大部分时间闲置无用,造成资源的浪费。随着我国农业全程全面机械化的推进,势必需要更多的作业机械及与之配套的动力机械,从而使得这一状况不但不可能好转,而且由于作业环节的增加及规模化程度较低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宜机化土地整治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除极少数自走式农业机械外,大中型拖拉机配带不同机械进行多种农业作业,动力机械的需求量大为减少。以潼南区章宏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例,上述比值现已达到1:4.1。另外,由于整治后地块变大,并且相互连通,从而节省了原本机械在田间频繁转移及掉头时消耗的能源。
5 发展建议
1) 科学合理地进行土地整治,为大中型农业机械高效作业创造条件,是推进我国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刻不容缓,必须高度重视。近两年来,重庆的宜机化土地整治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丘陵山区农机化的案例,值得大力研究和广泛借鉴。
2) 在相关研究中,应从全局最优出发,多学科融合,系统探讨农业机械化、农业水土工程、包括能源、材料在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为追求农业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提供理论支撑。
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破目前仍然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统一标准,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全面考虑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