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道”与“正道”
2019-01-06李奎原
李奎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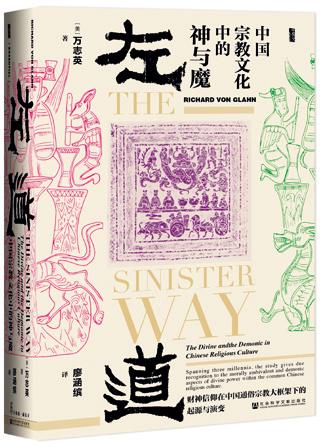
《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
(美)万志英著
廖涵缤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9月
“左道”与中国数千年来受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正道”崇拜相对立,流连于中国人的宗教视界与世俗生活内外。《左道》一书的作者呕心描绘的以五通神为代表的“左道”神魔,在中华大地的土壤中扎根生长且长期存在,正是一则经典例证。作者借此阐释了中国宗教文化中的左道神魔的产生与发展,并借陈述其走向民间大众的大体过程,试图揭示普通中国人“为控制自身命运而做出的尝试”。
笔者以为,五通神形象的生成与消亡,不仅是这种左道神魔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体现,也包含着皇权政治的控制与规范,更包含着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寄托与尝试,它的兴废源于多种元素相互作用。正如杨庆堃所说,中国社会不像在许多其他文化传统中(如欧洲或是阿拉伯文化),宗教是作为一种独立因素存在,而是围绕着世俗制度进行活动。在此过程中,一些左右左道文化的重要因素及其发挥效能的机制与路径未能引起作者足够重视。
左道的缘起与发展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本书情境中,我们应当理解为“宗教是统治阶级迷幻人民的鸦片”。不少宗教创始之初,往往富于哲理和虔诚敬畏。最终,被统治阶级发现其妙用后,成为手中便捷而锐利的工具。这是当今世界几大宗教发展史上的一段“左道化”历程。这种发展路径同样也适用于“左道”。与官方宗教和制度性宗教不同,左道形象的出现,往往带有偏见或政治目的。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别无二致,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魔起源于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后来经过世俗社会数千年演绎,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与生命力的宗教与神魔文化。作者将中华文明中的宗教与神魔崇拜做了脉络梳理,对其发展演变的各个时期的背景环境和内在逻辑做出生动介绍。
本书上溯殷商缥缈难测的祖先崇拜,中承汉代气象森严的亡者崇拜,下启宋代民心所向的神魔崇拜。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宗教的整体发展史进行透视。在这篇构思宏大绵长的神魔图景中,还蕴藏不少心思细腻的见解。例如作者对山魈的描述与解读。显然,它是中古时期生活在气候温暖适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对南方密集的山林水泽等湿热多瘴地区的未知恐惧,以及当时长期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士大夫阶层对南方瘦黑矮小的化外土人的文化歧视混合演繹而来。
当然,也夹杂了一些宗教迷信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来说,山魈形象的生成,是宗教想象建立在政治偏见、文化歧视与基层社会的想象演绎基础之上,是这种内核投射出的诡魅阴影,宗教因子在当中扮演了兴波助澜的角色。此时,这种左道的雏形在当时的等级秩序之下显得格格不入,也为名教子弟和无神论者所不容。追究根源,作者认为是中原人南迁过程中与山野蛮人的文明冲突。在当时的环境里,只能沦为志怪小说的上佳素材。经过了后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山魈才逐渐演变成为后世敬奉的五通财神。
通读全书可知,以五通神为代表的“左道”形象的生成并不是一脉相承的。根据作者的描述,山魈形象的出世发生在汉人南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疫鬼与瘟神的形象要更早产生。但它最终生成为五通神,显然是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演绎和不同地域的不同解读,彼此之间还应具备一定的独立性,生成在同一平面时就有了丰富的多元表象。更具代表性的还有作者论述的33种观音形象。
皇权政治与左道
秦代以降的中国皇帝追求长生之道,这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趋焉,一部分试图借机满足皇权私欲从中谋利的左道术士,便蠢蠢欲动。相应地,这些左道之士背后的“左道之术”时时走进统治者的活动视界。不仅旁门左道如此,所谓的名门正道亦如此,只因背后所带来的利益过于海量。例如作者列举的秦汉时期方士与唐宋时期的天台宗。受到皇权青睐的无论“正道”还是“左道”都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某一派别若因此勃兴,就会在宗教世界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诱惑,即便是心态超然不为外物所动的上人黄冠也只怕难以免俗。
统治者除了选择对其有利的既有神灵之外,也可以据己所需,人为创造和抬高相应神祗,例如玉帝崇拜与关帝崇拜。俯瞰数千年的宗教图谱,神与魔在精神世界中居于人上,接受世人顶礼膜拜,实则依旧处于统治者掌控的大体界限之内。曾经显赫一时的五通神也最终被“既有秩序进行进一步确认”的五路财神所取代,不能不说政治在这种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变化的作用力,一方面来自官方的规范与控制,另一方面也来自民间的尝试与努力。
与此同时,作为正道的对立面,左道的出现,在不少朝代以祸乱政治的异端邪说为表象,实则是反对者利用缥缈莫测的宗教神学对不容亵渎的皇权政治发起的隐秘攻击,企图阴谋作乱,因而受到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反感与排斥。结果不言而喻,任凭左道如何阴谋动作,皇权总是可以用锐利的刀斧将其戡平。
但是当整个统治者上层都信奉左道时,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例如中国历史上的谶纬之学与玄学。对此作者已有提及。这时左道的滋生,正是来自于当时“正道”的异化,即初始时期封建文人为迎合上意,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将皇权神化。
出乎统治集团意料之外的是诸侯等地方势力同样也可以利用左道限制皇权乃至颠覆皇权。这两种表象在两汉时期最为风行,甚至一度绵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政治框架内左道向外溢出的一面。
基层社会与左道
当社会秩序失调崩坏时,底层的普罗大众同样也可以利用左道反对封建统治。例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陈胜吴广起义。
篝火狐鸣和鱼腹丹书的出现,使得陈胜作为当时起义的领导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不容置疑的宗教神化色彩。以今时今日的眼光再看,显然是人为的蛊惑之言和粉饰之举,是底层人民自命的“受命于天”。它流布于局部地区,既未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也未经过饱学之士的文学演绎。准确来说是不得志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担当了这份工作。
纵观历朝历代的最终结局来看,凡是以宗教为旗帜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将原来普罗大众心目中常态的宗教“左道化”。 这种“左道化”的选择姑且算是一种捷径,毕竟拿来了既有的宗教内核与形式加以歪曲加工和利用。农民起义所托的神明,观音菩萨也罢,弥勒佛也罢,事实上皆与原来的宗教形象大相径庭,是起事者企图利用神明的感召力聚拢人心,将自身形象神化或者是将起义的理念宗教化、神圣化。
政治浑浊诚然是旁门左道兴起的一个重要因源,但大多数左道在与政治的博弈中也走向了异化的一面。一小撮别有动机的底层人民创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神魔,到头来祸乱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贻害千年。例如作者提到的白莲教。与此同时,我们抛开底层人民利用宗教与政治博弈相杀的一面来看,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生老病死、吉凶祸福,均与宗教及其体系中的神与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占据社会主体的大多数民众并不打算运用宗教这一武器与统治上层进行较量,除非多数民众衣食无着被逼无奈。他们完全出自世俗生活避祸趋福的需要,尤其是封建时代自然经济看天吃饭的不确定性,给底层大多数民众希望寄托宗教达成夙愿以绝佳良机。在统治者允许范围内,只要不是与当时根本的意识形态相左,信什么神他们并不在意。
反而,“僧道之众和官府都试图利用、收服这些地方神祗,从而确立自己在神界和人界的权威。教派领袖和朝廷命官都希望为自己的神灵体系引入合适的新成员,以在他们各自信奉的正统学说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以五通神为代表的邪异且实用的神明崇拜因此大兴就不奇怪了。
總体看来,皇权政治与基层社会关于左道信仰关系融洽的一面被作者描述的十分贴切,但二者关系失调乃至对立一面的描写则不尽如人意。
社会经济与左道
在作者的阐述中,未能充分从社会经济视角对左道形象的生成与消亡进行挖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作者认为“宋朝的竞争性货币经济中的成功或失败将导致个人运势的突变。因此,中国人在解释个人财富方面的迅速变化时会提到五通神就不足为奇了”。
这显然不够充分。一方面,宗教要想在普罗大众心中占据稳固的地位,必须具备相应的功能性,去获取信众的青睐,例如驱邪、超度、救难等等。在这种意志的驱使下,以观音为代表的神祗女性化正是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底层民众普遍存在较为稳定的宗教崇拜,用以作为精神寄托,但更需要柴米油盐。如果二者可以合二为一,那就更好不过。
拮据的自然经济使得底层民众趋于精打细算,在实用性理念的驱使下,就诞生了这样的左道神祗。遗憾的是,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对五通神产生、发展与消亡的作用力,并未展开论述,只是用民俗习惯和个案资料代替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