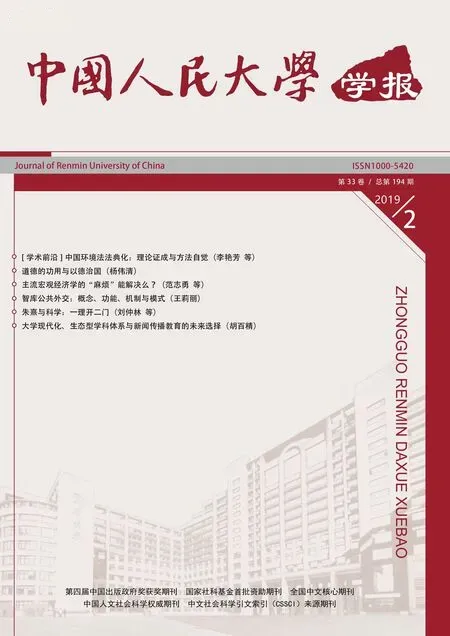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性质辨析
2019-01-06郑小静
常 凯 郑小静
互联网经济是指基于互联网在信息传递和信息更迭方面的技术能力和优势,通过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而产生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活动的总和。简而言之,互联网经济即以互联网为工具、媒介或平台的经济活动。当前,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已覆盖社会经济多个行业领域,并且正在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工作和雇佣关系领域,伴随互联网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企业用工关系呈现出区别于传统雇佣关系的某些新现象和新变化,如互联网企业不对劳动者实施直接的管理控制,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决定权,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显得更加松散等。这类新的用工形态,属于何种性质?学界对此的认识和判断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此类新的用工形式并没有改变其雇佣关系的性质[注]① Rogers, B.“Employment Righ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Getting Back to Basics”.Harvard Law & Policy Review, 2016(10):479-520; 常凯:《雇佣还是合作,共享经济依赖何种用工关系》,载《人力资源》,2016 (11); 吴清军、杨伟国:《共享经济与平台人力资本管理体系——对劳动力资源与平台工作的再认识》,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6)。;但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形式,已经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合作关系。[注]高超民:《分享经济模式下半契约型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基于6家企业的多案例研究》,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 (23);叶剑波:《分享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 (23);于晓东等:《共享经济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探索:以滴滴出行为例》,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 (6)。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到底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这一问题至今仍在争论。由于这一分歧直接涉及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性质,直接影响在互联网经济中就业的劳动者的权利保障,关系互联网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和企业的持续发展,因而有必要予以讨论和辨析。
一、雇佣关系与合作关系:定义与中外判例
雇佣关系,广义是指以就业为基础所形成的与雇佣劳动相关的社会经济关系。[注]常凯:《中国特色劳动关系的阶段、特点和趋势——基于国际比较劳动关系研究的视野》,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5)。狭义是指劳动者受雇于企业或个人,通过给付劳动形成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本文使用的是狭义的雇佣关系的概念。在雇佣关系中,雇主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劳动者接受雇主的指挥、指示或指令,在雇主控制的劳动过程中完成相应的生产或经营活动。在雇佣劳动的过程中,劳资双方的身份是独立的,但力量和权利是不对等的,雇主处于主导和决定的地位。劳动从属性是雇佣劳动的本质特征。市场化下的劳动关系是以雇佣劳动为基本特征的雇佣关系。但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概念并非完全一致,家庭保姆、个人雇佣、非体制内雇佣等用工关系,在非劳动法律领域也被称为雇佣关系,但只有被劳动法律所调整的雇佣关系才被称为劳动关系,在中国,调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法律是《劳动合同法》。
合作关系,通常指个体或组织作为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其他企业之间建立的以双方合意为基本原则的平等的经济关系,如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互联网经济中网络购物平台公司与网店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承包关系、承揽关系等。与雇佣关系(劳动关系)相比较,合作关系双方是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地位平等,具有对等的决策权利和谈判权利,共同承担合作关系带来的风险和利益。合作关系的法律规制适用于民商法,其法律形式为商业合同。
在经济合作关系中,除了企业,作为个体的自然人亦可与企业开展业务合作,从而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如传统意义上的“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即那些拥有特殊技能,并可凭此在公开市场上要求更高价格的企业家型个体。[注]Cunningham-Parmeter, K.“From Amazon to Uber: Defining Employment in the Modern Economy”.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6(96):1673-1728.由于这类个体区别于那些潜在的权利更易受到侵害、无技能或少技能的劳动者,其通常不被纳入雇佣法律保护之列。互联网经济中比较典型的如互联网设计师、技术总监、资深网络媒体人(大V)、自由撰稿人、音乐创作者等大都可归属此类。这些独立就业劳动者不受雇于特定雇主,且因其自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知识、技术、资源和能力而拥有一定的与雇主谈判的优势,决定了这部分劳动者不仅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工作强度,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创意获取有竞争力的收入,而且还可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或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企业管理决策。这部分劳动者属于技术精英或高级管理者,在与企业的合作中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注]Webster, J.“Microworkers of the Gig Economy: Separate and Precarious”.New Labor Forum, 2016(25):56-64.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市场稀缺性,这类劳动者在互联网经济中所占比例非常小,不构成影响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性质的主要方面。
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性质问题,主要关注对象为互联网经济中数量众多的普通劳动者,如在互联网出行平台上工作的网约车司机、网络订餐服务中的送餐员、快递业务中的快递员等。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指用工关系中的劳动者,是以此工作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业劳动者,而不包括那些在原有的相对固定职业之外的兼职人员。新华网的一篇关于网约车司机职业状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全职司机占比79%,占据主流,这表明网约车司机正走向职业化。”[注]新华网财经部:《一张图看懂网约车司机生存现状》,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6-10/18/ c_129326966.htmhttp://auto.163.com/16/1019/07/C3NNGFLD000884M5.html。关于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性质问题,主要讨论将平台工作作为全职工作的职业劳动者的用工关系问题。
如何认定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性质,中外判例中具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就这些判例做些分析。
2015年,美国Uber车主获准以集体诉讼形式起诉这家本土打车软件企业,以确定他们究竟是Uber的雇员还是独立承包人。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N.D.Cal.)作出Uber与司机之间构成劳动关系的判决。[注]国际在线:《美加州劳动委员会裁定优步司机属雇员而非独立合约人》,2015-06-18,http://gb.cri.cn/42071/ 2015/06/18/6991s5001774.htm。法庭给出的理由是:“Uber司机到底属于Uber公司的雇员还是独立承包人,判断标准需要考虑众多因素,但并非每个因素都具备相同的权重。其核心原则,在于雇佣方是否有权控制工作的各项细节”[注]S.G.Borello, and Sons.“Inc.v.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In:Rogers, B.“Employment Righ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Getting Back to Basics”.Harvard Law & Policy Review,2016(10):479-520.。美国西雅图、旧金山市也通过法案,允许Uber等企业司机成立工会并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以集体诉讼的形式起诉Uber。这是肯定了运营司机适用《美国劳动关系法》的事实。
2016年10月28日,英国劳动法庭就Uber司机与Uber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做出裁决,判决司机是Uber公司雇佣的员工,有权享受全国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等员工待遇。法庭认为,当一名司机在Uber授权工作的地域范围内打开Uber软件,并且有接受驾驶任务的能力与意愿,该司机就在一份包括“雇佣”合同和其他条款的合同下为Uber公司工作。主要理由如下:Uber公司经营运输业务,通过司机的专业劳动提供服务并获得利润;并且,司机与Uber公司之间的合同是非独立的工作关系,不是两个独立的企业之间的合同,法庭必须考虑Uber与司机之间不平等的谈判地位。[注]人民法院报:《英国判决:优步司机为优步公司员工》,2016-11-25,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 /2016/11/id/2356676.shtml。
上述判例是美国和英国两个最有影响的典型判例。考虑到英美法系中的判例法地位,该判决结果在英美具有普遍的意义。但中国关于此类争议的劳动诉讼,其判决结果则与美国和英国的判决迥然不同。
如北京出现的快车司机或专车司机提起的劳动争议仲裁,司机要求确认和网络软件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仲裁委经过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在管理上是一种很松散的关系,快车或专车司机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决定自己的工作日程,甚至专车司机都不知道公司具体地址与管理人员,公司也不对其进行相应考核,因而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注]苏庆华:《纠结的关系——互联网+背景下的出租行业用工关系问题探析》,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 (22)。另一类案件的判决结果也是如此:e代驾的司机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司机与互联网平台公司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三起同类诉讼的判决结果,均否认司机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庄燕生与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上诉案》,(2014)一中民终字第6355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孙有良与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上诉案》,(2015)一中民终字第176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王哲拴与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上诉案》,(2015)一中民终字第01359号。2015 年至2018年第一季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的 105 件劳动关系存在争议的案件中,确认平台与从业者建立劳动关系的仅为 39 件,占比37%。[注]好奇心日报:《纽约要求Uber给予司机正式员工的对待,类似争议国内也有过》,2018-07-25,http://www.qdaily.com/articles/55560.html。
比较一下中外案例判决,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国外Uber与司机的诉讼,还是国内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的争议,劳资双方诉求的性质和争议焦点是共同的:工会和司机希望确认其雇员的身份,以获得劳动法的保护,进而享有劳动者应有的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以及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而雇主则希望否认劳动者的雇员身份,强调其为“独立承包人”,以减轻雇主责任和义务,降低劳动成本,获得有市场竞争力的运营效率。这是在新的互联网经济用工形式下劳资利益之争的法律反映。
尽管此类案例诉讼理由和诉求性质相同,但中外法庭判决理念和判决依据却有区别。美英两个案例的法律依据都非常明确,之所以认定互联网公司与司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是由于他们之间具备雇佣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即雇主控制着劳动过程、劳动者处于从属的地位、劳资双方身份地位不平等。具体理由在判决中有着极为详尽的分析。而我国法院的判决则认为双方之间在“管理上是一种很松散的关系”,“司机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决定自己的工作日程”,“公司也不对其进行相应考核”,因而不认可司机与互联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对于雇佣关系的法律标准和特征,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具体涉及和列举,只是大而化之地简单定性。
这种判决结果,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制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特征,即英美等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法律制度已经相对比较完备,这些国家不仅在劳动法律规定方面有比较清晰的法律条文,而且在裁判理念上也具有比较一致的社会认同。但在我国,劳动法律刚刚具备一个框架,尚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法律条文也比较原则粗糙,并且在劳动争议的裁判理念上,法庭还必须要考虑到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工保护的关系。在社会认同方面,企业和经济发展比起劳工保护而言,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判例也反映出如何判断互联网经济用工关系的性质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性问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判决依据和结果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本质。不可否认,各国同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表现形式,但其究竟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对于这一问题,仅仅囿于传统的理论和现有的法律解释已经不够。对此,需要结合现实与理论,既要分析其新的表现形式,又要透过形式观察其实质,在此基础上确定其性质特点。
二、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现实与理论辨析
从上文判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不同国家的法院对于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其形态为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所做出的判断不同,但其基本标准还是一致的,即这一用工关系的劳动过程是否为“从属劳动”,这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即:雇主是否控制着整个劳动过程,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是否处于从属地位,雇主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对比关系是否平等。中外法院判决的主要差别在于对劳动过程具体特点的认定不同。基于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相比传统用工关系,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呈现出哪些特点。
(一)表面的松散管理与内在的严格控制
在传统雇佣关系中,雇员被要求服从雇主的行政管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成为劳动法中判定是否确认劳动关系的重要标准。在互联网经济中,区别于传统企业的用工管理方式,互联网企业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日程等规定比较宽松,劳动者具有一定的工作自主安排的权利。在“合作关系”的支持者看来,企业对劳动者的这种“松散”的日常管理,不符合雇佣关系的成立要件,劳动者也因此不能认定为企业的雇员。
互联网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看似不同以往,但雇主在实现预期结果的方式和方法方面的控制力却并未放松,而且凭借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得以加强。企业以此为抓手不但可以精简其对工作细节的冗繁管理,而且实现了用高科技控制劳动过程并深刻影响绩效产出的目的。尽管亚马逊(Amazon)将其配送中心的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但其仍能通过控制第三方承包人来显著影响工人的收入和工作条件;联邦快递(FedEx)虽然不对司机进行日常监督管理,但其却通过司机行为准则对司机的言行举止以及互联网设备进行严格的要求和控制;Uber司机虽被企业定性为“独立承包人”,但Uber却掌握着是否对司机派单、如何对司机进行考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雇司机的绝对权利。因此,如果忽视企业对劳动者实质性的严格控制而只突出其未对劳动者实施日常直接管理的表象,则不但会掩盖变化的工作世界的雇佣特点,而且会忽略和限制雇佣关系的内涵。
“合作关系”的支持者认为,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者亦对工作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像独立承包人那样选择并决定自己的工作日程,与互联网平台公司共同分享对工作过程的控制,互联网平台公司将此称为“双向控制”,并由此认为其不是对司机实施单向控制的雇主。但是,这种双向控制徒有虚名,劳动者对关乎其工作的重要决策难以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影响力。以Uber为例,一旦司机登录APP,Uber会期待司机接受由平台推送的每一单任务安排,否则将会对拒绝者实施账户失活的惩罚;面对来自企业的强大压力,司机对自我行程的控制显得苍白无力。并且,美国O’Connor 法院在判定时认为,虽然司机可以控制其工作行程,但是Uber却是其工资收入的唯一掌控者,Uber独立设定资费标准并固定抽取每单20%的费用,司机则对此类关乎工资收入的条款没有谈判和发言权。[注]Cunningham-Parmeter, K.“From Amazon to Uber: Defining Employment in the Modern Economy”.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6(96):1673-1728.这其实就是单向控制。可见,即使在互联网平台企业所谓对工作过程实现双向控制的背后,仍旧是企业在对影响劳动者工作持续性和收入情形、关系绩效产出的关键要素发挥操控作用,工人并没有改变其从属性的身份和地位。
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改变了对劳动者进行传统的日常管理的理由,不足以支持其否认与网约车司机、快递员、送餐员等普通劳动者的雇佣关系。无论是聘用独立承包人的P2P(peer-to-peer)平台,还是更加传统的通过第三方使用工人的企业,如果将判定雇佣关系标准从直接的日常监督管理转换为关注企业是否实质上控制劳动过程,从而具有全面塑造绩效相关期望的能力,那么大量的潜在雇主将浮出水面。
(二)形式上的独立自主与实质的劳动从属
劳动从属性是雇佣劳动的最本质特征。对于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性质,“合作关系”的支持者认为,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者是独立的业务承包人,其不依附于企业,能够根据自身喜好和自我判断,决定何时何地工作以及如何开展工作。有学者以此指出由于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者地位得到了提高,“从属性”标准已经不足以界定和诠释这种新型用工关系呈现的新特点。[注]魏益华、谭建萍:《互联网经济中新型劳动关系的风险防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8(2)。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是否已经突破了劳动从属性这一雇佣关系的本质特征?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结合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现实进行分析,认为其劳动从属性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从属性增强。互联网经济虽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机会,但这些工作多为低技能、低门槛、低收入的工作。一项研究发现,在北京的快递员和送餐员中,81.47%的快递员和77.00%的外卖送餐员来自农村;48.60%的快递员和47.63%的外卖送餐员因“容易找到工作”而选择从业;学历结构中初中及以下的占39.75%,高中占51.2%,大专以上占9.05%。[注]林原:《快递员、外卖送餐员过度劳动问题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2019新年论坛会议文件。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大量同质劳动力的情况下,任一劳动者都很容易被替代。面对生存生活压力和同质竞争,平台劳动者通常只能在当前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加依赖于当前企业以获得工作和工资,并将平台收入作为第一收入来源。[注]Choudary, S.P.“The Architectur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Platform Design for Worker Well-being”.ILO Future of Work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18, pp.1-55.同时,相比企业的正式雇员,所谓的工作灵活性带给这部分劳动者更多的是增加的工作不稳定性和削弱的劳动权益保障,劳动者抵御来自市场和工作的风险的能力在不断退化。为了维持工作,平台劳动者通常在工作条件、劳动时间、工资决定等方面受到企业更多的控制,又因缺乏劳动法律保护而无从向雇主争取自身权益。现实中,在随时面临失业、收入中断的压力下,即使同一工作岗位,灵活雇佣劳动者也表现出比正式雇员更多的对雇主的经济依赖。对此,一位研究者指出:“共享经济本质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劳动密集型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通过低人工成本的方式获取经济规模扩张,而这一点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注]闻效仪:《共享经济本质是劳动密集型经济》,澎湃新闻网,http://www.sohu.com/a/280985021_498982,2018-12-11。
二是人格从属性增强。人格从属性是指劳动者因需服从雇主指挥驱使而受到人格约束。由互联网企业开发设计的计算机应用平台是互联网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中最基础的操作机制和最重要的资源。企业通过界面呈现的方式引导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按步骤推进行程、完成任务、结束交易。对于平台劳动者来说,其劳动过程基本上是由应用系统规划的,劳动者在平台上的任何操作都在互联网企业已设定的程序范围之内,可以说,互联网企业无时无刻不在对平台劳动者下达工作指令、进行工作指挥。对照劳动从属性的概念,虽然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劳动者的这一指挥形式不同于传统雇佣关系中管理者直接下达指挥命令的方式,但从互联网平台的用工关系实质来看,作为人格权最重要内容的人身自由权,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者受到相比传统企业中的直接监控更加严格的人格约束。劳动者的人格从属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三是组织从属性增强。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可以不固定地为某一互联网企业提供服务,这为劳动者的企业合作伙伴角色提供了支持。观察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商业运营模式,可以发现互联网平台企业确实不限制劳动者转换工作,但是劳动者是否转换工作却必须考虑企业信誉评级系统对自身工作机会和收入的影响。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信誉评级系统内置于企业的应用平台,通常显示每一个提供服务的劳动者的信誉评分值,高评分值的劳动者会由系统分配优先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并由此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但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信誉评分值无法在平台之间转移。因此,即使劳动者起初同时受雇于若干个企业,但由于信誉评级系统的影响,其最终会选择某一个已积累信誉评分值比较高的平台继续工作,并持续在此平台提供服务以不断提高其评分值,这一情形对全职劳动者体现得更加明显;同时,已在一个平台投入并构筑信誉体系的劳动者会谨慎选择转移到另外一个平台。可以看出,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者在企业信誉评级系统的作用下,并不具有实质的、有效的雇主选择自由,互联网平台企业由此制造了劳动者对平台企业强有效的依附关系。
(三)名义上的平等权利与真实的失衡关系
合作关系中双方共同利益的实现需要双方具有相对平等的谈判权利,否则合作关系难以形成且无法持续。观察互联网经济中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并非具有平等的权利关系,且在互联网企业的运营模式下,劳资权利关系不断向企业倾斜,劳动者的权利弱势地位愈加突显。
一是互联网企业具有权利优势。首先,在信息获取方面,互联网企业主导企业运营,其掌握所能获取的有关企业运营的所有信息。相比平台劳动者可见的零碎的步骤性信息以及简单的二元选择操作,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实时获取广泛的市场需求信息、劳动者分布数据、市场竞争者情况等。[注]Shapiro,A.“Between Autonomy and Control: Strategies of Arbitrage in the ‘On-demand’ Economy”.New Media & Society, 2018(20):2954-2971.同时,平台企业以其意愿向劳动者分配信息,主导劳动者可获取的信息内容、信息的呈现方式和步骤,并可随时对劳动者界面进行调整,根据情况隐藏或呈现某些信息。这显著削弱了劳动者对工作的有效判断和自主决策权,但互联网平台企业则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权利优势。[注]Rosenblat,A.,and L.Stark.“Algorithmic Labor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 Case Study of Uber’s Driv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10): 3758-3784.其次,在规则制订方面,互联网企业能够单方主导规则的制订和调整,而劳动者则难以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互联网企业设计开发拟运营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以计算机算法的形式将其预定的雇主规则、商业规则、运行规则等写入计算机程序,以其自身意志开发完成计算机应用系统,同时将各种规则网络嵌入其中。平台劳动者一旦接入系统,便在平台公司的操作索引下完成学习规则和接受、服从规则的过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规则体系,计算机运行程序这种虚拟的规则网络不形诸文字,不晓谕周知,不经谈判协商,也无须民主表决,其完全由互联网公司单方决定,而劳动者实际上只是其规则体系的被动接受者。Uber就宣称,其保留“在任何时间全权收回、禁止、停用、限制以及以其他形式约束司机使用其APP的权利”。[注]Cunningham-Parmeter, K.“From Amazon to Uber: Defining Employment in the Modern Economy”.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6(96):1673-1728.
二是平台劳动者处于权利弱势地位。首先,从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来讲,受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自由化、自动化、数字化因素的影响[注]ILO: “DW4SD Resource Platform: Future of Work”,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dw4sd/themes/fow/ lang-en/index.htm,2018.,社会产生并存在大量的、持续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这部分劳动者通常低学历、低技能,就业竞争能力差,难以被正规经济部门所吸纳。伴随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大量的社会剩余劳动力涌入这一领域,为了获取更高收入开展激烈的同质竞争。加之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放松管制政策,平台劳动者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状态从根本上削弱了其与雇主的谈判权利。其次,从平台劳动者的工作性质来看,互联网平台工作的进入门槛低,仅需劳动者具有基本技术能力。劳动者通过登录平台,按照互联网企业系统平台的服务标准和步骤要求执行相关操作,即可完成推送任务。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同质竞争的情形下,低技能、高标准化、高替代性的互联网平台工作性质难以为平台劳动者带来有效的谈判权利。[注]⑦ Choudary,S.P.“The Architectur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Platform Design for Worker Well-being”.ILO Future of Work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18, pp.1-55.再次,从平台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利来看,分散化、个体化的互联网平台劳动者,除了工作地点不一致,其甚至都无法确定为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企业工作的劳动者,这使得个体劳动者对集体的认同度不高,难以形成平台劳动者集体;即使形成集体组织,组织者也无法确认谁会真正参与[注]Milland,K.“Slave to the Keyboard: the Broken Promises of the Gig Economy”.Transfer, 2017(23): 229-231.,基于此,平台劳动者在形成集体形式的谈判权利方面面临巨大挑战。⑦
综上所述,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尽管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与传统的雇佣关系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但其作为雇佣关系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其性质仍然是一种从属性的雇佣劳动。因此,认为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是对传统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的颠覆式变革,雇佣关系已经转变为合作关系的认识是缺乏依据的。从现实角度分析,互联网经济的形成,构建了一种新的灵活化的用工关系,在这种新的用工关系中,资本借助互联网技术更加强势地控制了劳动过程,造成了更加显著的劳资力量不平衡。凭借在这种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中取得的低劳动成本优势,资本在这一经济活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额利润,而压低劳动成本的一个重要的直接途径就是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以合理合法地逃避雇主义务。由此看来,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究竟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的争论,是现实中劳资利益博弈的理论反映。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雇主们之所以不承认劳动关系,是因为由此带来的劳动保障成本是他们不愿承受的,这会大大影响他们的企业收益,虽然他们正源源不断地从平台就业者的劳动收入中高额获利。”[注]闻效仪:《共享经济本质是劳动密集型经济》,澎湃新闻网,http://www.sohu.com/a/280985021_498982,2018-12-11。
三、雇佣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比较与政策选择
通过理论阐述、案例分析和现实辨析,本文认为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仍然是雇佣关系。进而得出的结论就是,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仍然是劳动法律的调整对象。确认这一用工关系的基本性质和法律适用,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促进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互联网企业的劳资两利、劳资和谐,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在具体形态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因而对于此类关系的调整,不能直接适用传统劳动关系的劳动法律规制,当前的劳动法律规制亟须调整和完善。
(一)确认雇佣关系要求保障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
互联网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虽然目前只是整体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其未来在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占比却将会越来越高。[注]Rogers, B.“Employment Right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Getting Back to Basics”.Harvard Law & Policy Review, 2016(10):479-520.统计数据显示,到2020年,美国40%的工人将会变成临时性的“伪雇员(pseudo-employees)”[注]Cunningham-Parmeter, K.“From Amazon to Uber: Defining Employment in the Modern Economy”.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6(96):1673-1728.,这意味着,在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稳定雇佣状态的劳动者将越来越多,由于资本的技术优势和资本对规则制定的主导地位,劳工权益保障问题将更加突出。
确认雇佣关系仍然是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意义在于明晰互联网经济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实质内涵。而雇佣劳动和雇佣关系调整的核心内容即是劳工权益保障。[注]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68-151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具体来讲,保障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既包括劳动者的个别劳权,即工资、工时、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权利,也应该包括劳动者的集体劳权,即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协商谈判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和民主参与的权利。在这些权利诉求方面,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者,主要还只是争取个别劳权,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则已经在争取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外劳工运动和劳动法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基本诉求是一致的,即争取基本劳动权益。在劳权保障的实现过程中,企业需承担其相应的雇主义务。所谓“合作关系”在劳权保护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将企业的义务诸如工资保障、职业安全、社会保障等,推卸给劳动者个人或者社会和政府来承担,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当然,新的用工形式需要调整传统的劳权保障的具体形式,比如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实施方式等。作为劳权实现的主要义务主体雇主方,以合作关系替代雇佣关系来规避自己的义务,如上文所述,既缺乏法理上的依据,也与现实用工关系的实际状况不符。
确认雇佣关系为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即明确了这一用工关系中劳动者和雇主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赋予劳动者争取劳权保障行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低收入的灵活雇佣劳动者的工作风险也可以得到有效降低。这不仅体现了劳动法保护弱势劳动者、矫正劳资关系强弱差异的根本立法宗旨,而且符合现代社会对公平正义理念的道德追求,而且,也是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要求。
(二)雇佣关系的确认是互联网企业和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的前提
如果将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界定为合作关系,这一用工关系性质界定看似对平台企业有利,但近年来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实践并未支持这一观点。目前来看,现实中互联网经济中企业方“去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化”的舆论宣传和实际推进,理论和司法领域对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性质“淡化劳动关系”的模糊处理,不仅持续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而且也并未使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法律制度规制的“灰色地带”获得发展进步。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企业不断降温,国内曾火爆一时的诸多互联网平台企业目前已销声匿迹;由于劳动者的地位和待遇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提高,平台劳动者收入不断下降、“过劳”现象严重存在,致使员工流失现象突出,劳动争议和集体行动不断出现。[注]林原:《快递员、外卖送餐员过度劳动问题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2019新年论坛会议文件。这些问题直接制约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突显了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用工管理进行有效规制的紧迫性。
应该认识到,确认雇佣关系是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基本性质,并不意味着会通过加诸雇主责任的方式破坏互联网经济中企业的商业模式,借雇佣保护之名阻碍科技创新和行业发展。[注]Kessler,S.“The Gig Economy Won’t Last Because It Is Being Sued to Death”, FAST COMPANY(Feb.17,2015), http://www.fastcompany.com/3042248/the-gig-economy-wont-last-because-its-beingsued-to-death;Reynolds,G.H.“Regulators Wreck Innovation: Column, U.S.A”.TODAY (June 10, 2014),http://www.usatoday.com/story/opinion/ 2014/06/09/uber-lyft-taxi-transportation-regulators-column/10198131/.劳动关系(雇佣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与资本力量的相对均衡是维护劳动关系协调稳定,促进企业、行业和社会规范有序发展的基础。[注]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68-151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将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定性为“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变相地肯定了当前企业保留实质性的控制权利却单方面将雇佣风险转嫁给劳动者的情形。这无疑是在实现资本和劳动权利和力量相对平衡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互联网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企业的权利主导地位愈加显著、劳动者的谈判权利愈加薄弱,从劳动关系理论视角来看,这一失衡的力量关系对比,将直接影响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企业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雇佣关系这一用工关系的基本性质的确认,要求改变互联网经济中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严重失衡状态,赋予劳动者对涉及自身权益事项的参与权和发言权,改变由平台企业完全主导的局面,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权力关系格局。如果企业不尊重劳动关系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不重视达成资本和劳动者力量的基本平衡,那么,无论经营战略如何,其发展都将被掣肘。
(三)雇佣关系的确认要求加强和完善对互联网经济的劳动法律规制
如果将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定性为合作关系,互联网企业可以进而置身于劳动法治之外,在缺乏劳动法律规制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将变得愈加激烈,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满足其对用工灵活性的追求,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成为“去劳动关系(雇佣关系)”的受害者,就业风险增加、劳动收入降低。同时,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的情形将更加严重,整个社会的安全性将受到威胁。
互联网经济并未根本改变和颠覆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和性质,雇佣关系仍然是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劳动规制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方法,历来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效率的有效路径。当前,资本和雇主在追求更高利润的本能驱动下,支持新兴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其“去劳动关系化”、放松劳动法律规制(deregulation)的一个有效借口。然而这种主张和诉求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牺牲劳动力利益,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就中国现状而言,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用工方式,更应加强劳动法律规制。[注]闻效仪:《共享经济本质是劳动密集型经济》,澎湃新闻网,http://www.sohu.com/a/280985021_498982,2018-12-11。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劳动法律规定,包括劳动者权利的规定和劳动关系的调整方式等,从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上来看,是适用于互联网经济中的劳动用工关系的。但由于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新的表现形式,直接套用现有的法律规定会面临适应性问题,如劳动关系的认定、劳动权利的保障方式、雇主责任的确定和履行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根据现实情况予以细化、调整和完善。
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法律规制,需要在平衡“双向运动”的两个维度即安全性和灵活性的过程中,寻求能够有效降低雇主的经营风险和雇员的工作不安全性的制度安排,这是对劳动规制的主要要求。[注]Kalleberg, A.L.“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74):1-22.为应对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面临的新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诸多方案,如考虑在现有法制体系内以具体案例为基础进行个别分析[注]Crank, A.L.“O’Connor v.Uber Technologies, Inc.: The Dispute Lingers——Are Workers in the On-Demand Economy Employees or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American Journal of Trial Advocacy, 2016(39):609-634.,或划分一个介于“雇员”和“独立承包人”之间的新的类别,如“独立的工人(independent worker)”“非独立承包人(dependent contractor)”[注]Harris, S.D., and A.Krueger.“A Proposal for Modernizing Labor Laws for Twenty-First-Century Work: The Independent Worker”.Working Paper, 2015, http://www.hamiltonproject.org/papers/modernizing_labor_laws_for_ twenty_first_century_work_independent_worker.,或构建一个新的统一框架来平衡创新和公共利益[注]Elliott, R.E.“Sharing App or Regulation Hack(ney)?: Defining Uber Technologies, Inc.”.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2016(41):727-753.,或改革当前与全日制雇佣相联系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等[注]DePillis, L.“This Is What the Social Safety Net Could Look Like for On-Demand Workers”, WASH.POST (Dec.7, 201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5/12/07/this-is-what-the-social-safety-net-could-look-like-for-on-demand-workers/.。尽管学界关于如何完善规制的具体方案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现有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雇佣性质是完善劳动规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各种不同意见和方案,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讨论和完善。
对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进行有效规制,涉及对现有劳动法律制度和体系的突破[注]Dyal-Chand, R.“Regulating Sharing: The Sharing Economy as an Alternative Capitalist System”.Tulane Law Review, 2015(90):241-309.,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劳动规制法律制度,还有诸多问题需要研究。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平衡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和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之间的关系,确认互联网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并明确政府的监管责任,以使劳动者和互联网企业得到共同发展。至此,问题刚刚提出,如何应对和解决,还需要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
四、结论
确定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性质,即这一关系是合作关系还是雇佣关系,是研究互联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与劳动者权利保护如何统一的前提,也是基本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意义。在目前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也不同。学界和实务界一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互联网经济颠覆了企业用工的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开始转变为合作关系,企业用工应该“去劳动关系化”,应该放松企业的劳动法律规制。但我们认为:互联网经济中多样化的灵活用工形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合作关系,雇佣关系仍然是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基本形态,或者说,互联网经济中的基本用工性质仍然是劳动关系。
我们的依据是,判定用工关系的性质标准,主要是看这一关系是否具有从属性,即是由一方控制劳动过程还是由双方共同控制劳动过程。尽管新的用工关系在形式上和表面上具有灵活化、多样化和自主化的特点,但实际情况是表面的松散管理掩饰着内在的严格控制,形式上的独立自主实质上则是劳动从属,名义上是权利平等,现实中则是失衡关系。用工双方并非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而仍然是劳动和资本两个不同的生产要素。由此看来,那种认为互联网经济中用工颠覆了传统劳动关系的观点,仅仅是注意了形式的变化而忽略了实质的存在。这种观点更多地成为雇主推脱自己所负雇主义务的一种托词。
确认互联网经济中用工关系的雇佣关系(劳动关系)性质,不仅对于劳动者权利保障具有直接的意义,即赋予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以正当性和合理性,同时对于互联网企业、行业来说也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种意义主要表现为:对雇佣关系这一用工关系基本形态的确认,构成了其规范有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在雇佣关系框架下,方可明确互联网经济中雇主和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并进而实现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和促进互联网经济有序发展的内在统一。这也正是对互联网经济中的用工关系进行劳动法律规制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