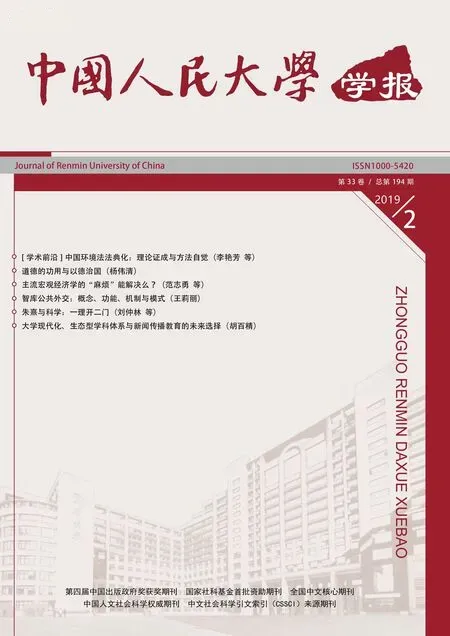比较法视野中的我国环境法法典化
2019-01-06李艳芳田时雨
李艳芳 田时雨
一、法典化浪潮下我国环境法法典化
“法典是每个时期法律制度文明的缩影和主要表征”[注]周旺生:《法典在制度文明中的位置》,载《法学论坛》,2002(4)。,不仅大陆法国家将法典法作为法律发展的理想样态,判例法国家也逐步出现了立法整合等法典化迹象。“法典化”(Codification)这一概念在近百年间都处于变化之中,历史上的法典也并未在法典与非法典之间划出一道严格界限。[注]Weiss,G.A.“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Law World”.Yale J.Int’l L., 2000, 25 (2): 435-532.古代法典通常是对整个法律系统进行全面的成文法整理工作,晚近时期的法典编纂多出现于私法领域,正如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法法典化,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化则被认为是可以发生在每一个法律领域的。[注]Van Reenen,T.P.“Reflections on the Codification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Law (1): General Considerations”.Stellenbosch L.Rev., 1994, 5 (2): 214-231.法典化由此得以在环境法领域内逐渐兴起。
鉴于环境立法的分散与冲突,欧洲国家自20世纪末开启了环境法法典化的浪潮。1988年所颁布的《瑞典环境法典》,在整合了现有15部立法的基础上予以适当创新,成为世界上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法典,又因其框架松散而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实用性。[注]竺效、田时雨:《瑞典环境法典化的特点及启示》,载《中国人大》,2017(15)。德国分别于1988年与2006年进行了两次环境法法典化的尝试[注]德国环境法典至今尚未正式出台,但先后有过四版草案:由1990年总则与1994年分则所组成的教授草案、1997年的专家委员会草案、1999年的政府立法草案以及第二次法典化尝试中的2008年草案。参见沈百鑫:《两次受挫中前进的德国环境法典编纂》,载《中国人大》,2018(5)。,虽都以失败告终,但其法典体例至今仍被称道,其经验教训也值得反思。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以法令形式于2000年与2007年分别通过了环境法典的法律与法规部分[注]莫菲:《法国环境法典化的历程及启示》,载《中国人大》,2018(3)。,其内容覆盖广泛、编排形式明了,便于公众找法与行政执法。《意大利环境法典》颁布于2006年,虽然介于法律汇编与法典编纂之间的内容与形式使之备受诟病,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立法的统一。[注]李钧:《一步之遥:意大利环境“法规”与“法典”的距离》,载《中国人大》,2018(1)。
当前,我国环境法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环境法的法典化问题,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典编纂条件,编纂法典也是“可能为世界提供先例的一个领域”[注]吕忠梅:《将环境法典编撰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载《前进论坛》,2017(4)。。对比我国民法典编纂的跌宕历程,法典化对于年轻的环境法而言似乎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欧陆国家的法典化历程也显示出环境法法典化尚未形成成熟的路径与模式,社会背景、立法发展、环境状况以及政治意愿等因素对环境法典的样态都有影响。然而,综观法典编纂史,但凡部门法的发展变革都难以脱离对既有法典的借鉴[注]刘兆兴:《比较法视野下的法典编纂与解法典化》,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1)。,考察路径不一的欧陆环境法典可以为我国环境法法典化提供有益参考。
与此同时,由于比照多国环境法典容易造成经验混杂而难以适用,为获得理论上的连贯性与中国本土的适应性,环境法典的比较研究应当基于一条基本的问题脉络。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法典?这一疑问指向了法典化的目标定位,具体则体现为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内在构造与外部衔接,分别对应确定性、稳定性与开放性的法典品格。
传统语境下的法典被视为绝对理性所构筑的圣物,其严密体系旨在回应几乎所有社会问题,而今看来,此理想却恐有乌托邦之嫌。如何对法典化的程度进行合理定位,可谓是法典编纂的逻辑起点。环境法外延的不清导致法典边界的模糊,因而需要判断哪些立法应当纳入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范围界定又产生了法典内外两部分的规范体系:环境法典内部的体例构造涉及总分结构的合理性、总则规范的抽象性程度以及分则的编排逻辑;而环境法典外部的衔接问题则主要包括法典与环境单行法的关系、法典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二、环境法法典化的目标定位
法典化的合理定位是环境法典编纂的前提性问题。传统理性主义的相对化促成了晚近法典理念的转向,由此各国在环境法法典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的分野。在法典功能主义的视角下,中国环境法典应当在形式与实质之间选择适度的法典化,并以法典体系效益为纲予以具体展开。
(一)形式编纂抑或实质编纂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逐渐成为制度构建的哲学基础,唯理主义者甚至认为可以依理性构建几乎所有社会制度。始于18世纪的欧陆民法典将严密结构及完备体系作为终极追求,而后其他部门法的法典编纂也皆遵循理性主义的指引,可以说“法典化运动的大部分原动力,无疑来自理性主义精神”[注]艾德华·麦克威利:《法典法与普通法的比较》,载《环球法律评论》, 1989(5)。。然而,晚近时期,面对愈加复杂的社会现实,传统法典难以通过纯粹的概念与逻辑推演涵摄其所调整的所有社会关系,民法典的编纂实践也呈现出理性主义的相对化。[注]冯乐坤:《从绝对理性到相对理性——民法法典化的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6)。绝对理性主义的祛魅促进了法典编纂理念的更新,不再一味苛求完美且不朽的理想体系,而代以实用且灵活的目标导向。[注]Van Reenen,T.P.“Reflections on the Codification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Law (1): General Considerations”.Stellenbosch L.Rev., 1994, 5 (2): 214-231.这一法典理念的转向与新兴法律部门的发展呈现出互动前行的态势:一方面,新兴法域自身的分散特性对传统法典编纂的理想预设产生了冲击,使之不复原先古板面貌[注]张梓太:《论法典化与环境法的发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3)。;另一方面,法典编纂条件的松懈也使诸如环境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有机会融入法典化浪潮。
法典编纂模式自此分化为实质编纂(Substantive Codification)与形式编纂(Formal Codification):前者旨在通过创制一套互相耦合的规则来系统化地革新法律秩序,而后者则仅是针对现行法进行类型化的重述与汇集。[注]Bergel, J.L.“Principal Features and Methods of Codification”.La.L.Rev., 1987, 48 (5): 1073-1097.现今主要的环境法典可依此进行学理划分:《德国环境法典(草案)》和《瑞典环境法典》当属实质编纂,而《法国环境法典》与《意大利环境法典》则是形式编纂。[注]采此形式与实质二分模式的重点在于讨论环境法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编纂的类型化理论还包括汇集型、巩固型、革新型与汇编型的法典编纂方法。参见彭峰:《法国环境法法典化研究》,载《环境保护》,2008(4)。自我创新、继承前人、移植外国以及修补现有法律等法典编纂的技术模式。参见封丽霞:《法典编纂论——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97-302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综观这些法典及其草案文本可以发现,不仅在前述法典理念上有所不同,编纂模式的区别主要还体现在对法典体系化的期望以及对现行立法的态度这两方面。
其一,采形式化编纂思路的国家对环境法典的体系化编排仅具有一定程度的条理要求,而实质化的环境法典在编纂之初就追求逻辑严密的框架结构。《意大利环境法典》的立法者仅希望加强或巩固现有立法,在欧盟指令的转化之外缺乏创新法律制度的愿望,法典编纂过程也缺乏持续性,在具体规范制定之后,一般性原则才出现在了2008年的修订中。[注]Fracchia,F.“‘Codifi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 2009(1): 1-22.松散的法典结构表明其编纂思路是将部分环境立法与欧盟指令直接汇入各编进行形式上的统一,甚至于首编定位不明,难以满足概括、指导分编等总则性功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德国环境法典(草案)》沿袭了其法典化传统中学说汇纂的特色,尤其是最初的教授草案,肩负着通过法律的系统化与协调化来实现环境法进步的任务[注]夏凌:《德国环境法的法典化项目及其新发展》,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2)。,整体上总分结构明显,总则部分高度抽象化,分则之间的编排也是有据可循。
其二,形式性的法典编纂满足于对现行法的梳理与统一,而实质性的法典编纂在此基础上还存有对环境法秩序进行革新的宏愿。在行政性法典化的背景下,《法国环境法典》的内容本就难有实质创新。[注]夏凌:《法国环境法的法典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4)。同时,《法国环境法典》的编纂缘由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强法律的可读性,即通过法典化统一现有立法而使公众易于理解,这也体现了法国法典化“总是希望将文本的革新与自身法典编纂的经验相分离”[注]彭峰:《法国环境法法典化的成因及对我国的启示》,载《法治论丛》,2010(1)。的特点。与之相反,《瑞典环境法典》虽然在规范建构上未曾追求传统法典的完美逻辑,但其整体上也属于实质编纂。从编纂动因来看,瑞典法典在协调环境立法之外,还有更新价值理念、增加监管领域以及变革法律制度的需求[注]The Environmental Code, a summary of the Government Bill, 1997/98:45. https://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1998/01/the-environmental-code-a-summary/.,遂法典在环境法庭制度、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处罚费等方面都有所革新。最终,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下,法典编纂促进了瑞典环境保护的现代化。[注]李挚萍:《可持续发展原则基石上的环境法法典化——瑞典〈环境法典〉评析》,载《学术研究》,2006(12)。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编纂模式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具体到某一法典文本,其法典化的程度通常而言是在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之间的。正如同属实质法典化的瑞典与德国,《瑞典环境法典》虽在制度革新方面具有重大突破,但在整体的体系结构上并不如《德国环境法典(草案)》严密;而作为形式编纂的法国与意大利,尽管都旨在对现行法加以统一与完善,但《法国环境法典》与《意大利环境法典》相比,在范围覆盖面与结构严密度上都更胜一筹。
一国环境法典在形式与实质之间如何进行取舍?倘若以传统眼光观之,实质编纂通常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典化,而形式编纂则易被贴上法律汇编的标签。但实际上,实质编纂的环境法典因其精密的逻辑结构在稳定性上略胜一筹,而形式编纂的环境法典基于松散的框架在容纳法律变化方面具有较高开放性,需结合具体情境选择恰当的模式。
(二)基于体系效益的适度法典化
顾名思义,法典编纂中的“编”是对现有法律制度进行系统化整合,而“纂”则是结合实践中的新问题创建新制度。[注]王利明:《我国民法典分编编纂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人大》,2018(17)。也因此,有关我国环境法典的目标定位,学界基本上形成了在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之间的共识。在宏观判断方面,降低传统理想型的目标定位,以灵活性、适应性以及渐进性为特征的适度法典化备受关注。[注]相关论述可以参见张梓太:《中国环境立法应适度法典化》,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1);吕忠梅、窦海阳:《民法典“绿色化”与环境法典的调适》,载《中外法学》,2018(4)。初期的适当妥协会随着我国环境法的逐渐成熟进行不断调整,以追求更高层次的法典化,法典定位也进一步修正为“动态的适度法典化”[注]张梓太、陶蕾、李传轩:《我国环境法典框架设计构想》,载《东方法学》,2008(2)。。在编纂方案方面,适度法典化需要明确基本概念、价值理念、规范体系等要素,这些内容可由法学家初步提出进而经法典正式确认。[注]吕忠梅:《新时代环境法学研究思考》,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8(4)。在具体路径方面,有学者提出通过多元法律形式、松散的框架结构以及阶段性编纂进程来构建开放式的环境法典。[注]李传轩:《中国环境立法发展的路径省思》,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2)。
笔者赞同适度法典化主张。在新时代环境法典的编纂过程中,绝对的理性主义追求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应当结合我国实践需求,从功能主义视角开展适度的环境法法典化。法典功能主义的核心在于“功能优先于形式”[注]张小军:《民法典解构及当代中国民事立法的理性选择:适度法典化——以比较法为视角》,载《理论月刊》,2011(5)。,甚至可以说“功能决定法典化的概念”[注]谢哲胜:《论民法法典化模式的选择》,载《法商研究》,2006(3)。。诚然,法典是法律的形式体现,但法典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以优于现行法制格局的立法模式服务于环境法治,绝非纯粹为了法典形式而法典化。欧陆国家结合现实需要及其立法传统对编纂模式进行选择,也正阐释了功能主义对法典编纂思路的渗透。
如何落实“适度”的法典化?由于法典统一国家法律、汇集文本信息等历史功能有所衰退,而今仍然留存甚至更为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体系化[注]苏永钦:《寻找新民法》,8、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因而适度法典化的具体展开,应当以法典的体系效益为纲。
近来民法典编纂中的相关讨论为理解法典体系效益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学者苏永钦将其概括为储法、找法、用法、立法与专业教育。[注]苏永钦:《体系为纲,总分相宜——从民法典理论看大陆新制定的〈民法总则〉》,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3)。比较法上的环境法典在编纂动因以及目标定位上或多或少都涉及体系效益的这几个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体系效益与法典化程度并非单纯成正比的关系。典型教训当属《德国环境法典(草案)》的搁浅,体系化的信仰之于其环境法法典化而言,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需进一步考察体系效益的决定因素。苏永钦提出可以实现体系效益最大化的十二项规则,分为形式与实体两方面。形式规则可以概括理解为关于核心概念的普通化、整体结构的均衡化以及规范编排的有序化等方面;实质规则涉及通过去政策化实现稳定性、交易中的人与文化等因素,以及如何通过立法技术与法官裁量来保持开放性。[注]笔者在此进行了高度概括,具体论述参见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为中国大陆的民法典工程进一言》,载《交大法学》,2010(1)。也有学者指出,调整范围的大小、结构层次的数量以及规范脉络关联的紧密程度是决定体系效益的因素。[注]谢鸿飞:《民法典的外部体系效益及其扩张》,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2)。
基于此,笔者从比较环境法的视角提出环境法典之体系效益的观点,即通过对法典的范围划界、内在体例与外部衔接的探讨,来实现确定性、稳定性与开放性三个维度上的适度法典化。其一,调整范围关乎法典的确定性。法的确定性通常被理解为具体法律概念的清晰准确,但考虑到环境法律繁多且公私兼具,因而法典语境下的确定性更指向法典调整范围的明确与统一。为避免大杂烩式的法律汇编,环境法典需依据一定标准确定适度的法典范围。其二,体例构造影响法典的稳定性。对于迅速发展的环境法而言,频繁修订似乎在所难免,但“法典求稳,改革求变”[注]王利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编纂》,载《中国法学》,2015(4)。,进入立法模式革新阶段的环境法必须追求适度的稳定性。环境法典是否得以经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决于其体例构造能否经受住社会变迁的挑战。其三,法典衔接反映法典的开放性。[注]法典的开放性可以从规范层面与价值层面理解,在此重点关注前者,即基于环境法渊源体系来审视环境法典的开放性。参见于飞:《民法典的开放性及其妥当实现》,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4)。所谓开放性,意味着环境法典并非绝对的封闭自洽,而是在与法典外部规范的交互影响中不断更新与进化。鉴于环境问题综合且多变的特性,环境法典如何与其他环境法渊源进行有机衔接,对法典保持开放性至关重要。
三、环境法典调整范围的划定
在适度法典化这一定位的指引下,体系效益在法典确定性的维度上要求对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予以明确。通过比较归纳环境法典的划界依据,可以为思考当前立法中哪些内容应当纳入环境法典提供有益参考,同时在法典语境下重识一些特殊规范的环境法域归属。
(一)环境法典范围的划界依据
环境法典是有关环境法规范的合集,但在识别环境法规范时却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认为所有法都是环境法、要么忽视任何形式的环境法。[注]Van Reenen,T.P.“Reflections on the Codification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Law (2): A Suggested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a Codification”.Stellenbosch L.Rev., 1994, 5 (3): 331-363.此类现象揭示了环境法范围的难以确定,这是由于环境法不仅在规范目的上存在重叠,还常常需要将其他规范作为适用基础。[注]汪劲:《环境法学的中国现象:由来与前程——源自环境法和法学学科发展史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18(5)。但法典编纂不能也不需要在每个领域达到彻底的全覆盖。[注]Weiss,G.A.“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Law World”.Yale J.Int’l L., 2000, 25 (2): 435-532.正如民法典内容范围的确定标准主要以公法与私法为限[注]张保红:《刻舟求剑抑或时移法移?——论私法一统背景下的法典内容与体系构建》,载《兰州学刊》,2017(3)。,环境法典也需要些许依据进行合理的划界。
确定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是立法者围绕环境法的核心范畴进行外延划界的过程。比较法上的经验显示,环境法调整范围主要的划界依据包括环境问题应对规范、环境立法与执法的部门权限,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人类行为以及环境利益等方面。
从环境法的发生学角度看,环境法产生与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应对环境问题的专门化法律部门的需求,因而有关污染防治与资源保护等规范作为环境问题应对法当然应进入法典调整范围。依据环境问题应对规范这一标准确实可以实现环境法典大部分内容的确定,但这一标准可能会因其问题导向的特性而导致法典内容的碎片化。如此,也就可以解释《意大利环境法典》的性质何以备受质疑。对法典范围欠缺全局考量,而仅将主要领域的环境法进行集中并在随后加入原则性规定作为总则的编纂思路,无异于将单行立法的问题直接带入法典。因而,尽管有学者指出“大环境”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典适用范围[注]李钧:《一步之遥:意大利环境“法规”与“法典”的距离》,载《中国人大》,2018(1)。,但其对噪声污染、电磁污染以及光污染等重要领域的排除又表明法典在重要内容上的缺失。[注]Fracchia,F.“‘Codifi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 2009, 1: 1-22.
环境法文本最初通常是由一国环境主管部门来组织起草,而后的法律实施也是以该部门为行政主导,可见,依环境立法与执法的部门权限来确定环境法典的范围是比较直观的。基于行政性法典化的背景,《法国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带有明显的部门化色彩,即依据环境领域主管机关的行政权限来确定法典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一些本应属于环境法的法律被规定在其他法典之中,例如机场噪声的规范被分散在城市规划法典与民用航空器法典中。[注]莫菲:《法国环境法典化的历程及启示》,载《中国人大》,2018(3)。此种依主管机构权限来确定法典范围的方式不仅在立法上难以周延,在实践中更会遭遇部门协调的难题,甚至会导致“环境超级部”[注]Van Reenen,T.P.“Reflections on the Codification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Law (2): A Suggested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a Codification”.Stellenbosch L.Rev., 1994, 5 (3): 331-363.(Super-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的倾向。
环境法调整人与人之间因环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而环境法律关系正是由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人类行为构成的。理论上,此种划分可谓是最复杂却也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划分。一方面,它可以涵盖现有的环境规划、资源利用等行为,甚至为容纳新型的环境行为而预留空间;另一方面,环境行为有可能作为环境法域内的核心概念而成为逻辑推演与体系建构的基石。然而,环境行为的界定难以满足内涵独立且外延周延的要求。《瑞典环境法典》也并未直接抽象出这一概念,而是具体规定了对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几项特别活动,同时将可能影响环境的人类活动作为核心来扩展法典调整范围,因此原则上《瑞典环境法典》可以适用于一切对环境有影响的人类活动。[注]Rubenson,S.“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Eur.Envtl.L.Rev., 1999, 8 (12): 328-332.
法律是对利益的调整,将反映环境利益作为法典规范的选择依据可以实现较高程度的环境保护。德国环境法典的教授草案主要基于学理考虑,将诸如自然保护法、水法、控制排放法以及放射性防治法等带来直接环境利益的法律纳入法典,而专家委员会草案则更具野心,认为法典应在协调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尽可能考虑到环境问题的根源并通过立法赋予环境保护更多力量,因而主张将基因工程、森林、土地利用、交通建设以及能源等方面的立法均纳入环境法典。[注]夏凌:《德国环境法的法典化项目及其新发展》,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2)。可见,德国环境法典主要是以环境利益作为法典范围的选择依据,而草案范围的变化则显示出环境利益的扩张,即在直接环境利益的基础上加入健康风险、生态保护、交通能源等相关利益而成为泛化环境利益。尽管此次法典化尝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联邦与州的立法权限问题,但环境利益理想化的扩张也侵犯了政府部门与州的相关利益,从而成为其拒绝草案的借口。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法典编纂对上述划界依据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在避免重大遗漏的同时警惕环境法帝国主义。[注]Veinla,H.“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Major Challenges and Options”.Juridica Int’ l., 2000, 5: 58-67.环境问题作为环境法产生的客观因素,法典应在现行法的基础上继续对此有所回应,但应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对环境规范进行选择。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与环境法的制定与实施联系紧密,加之我国刚刚完成生态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等相关部门的权责调整,环境法典需要适应新的机构职能,明确各部门内的环境保护职责并完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总是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而产生,尽管由于环境行为的概念界定过于抽象使其当前难以作为法典规范构建的核心范畴,但可以考虑将其融入原则条款对法典范围在抽象层面予以适当拓展,从而为未来情形预留解释空间。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牵涉甚广的背景下,法典编纂过程可谓是环境利益的文本化,尤其是当环境权陷于理论纠葛而难以法定化之时,环境利益不失为一个规范串联的线索,但为避免利益泛化而导致法典过于求全,环境利益需要结合环境法渊源而进化为环境法益。
(二)特殊环境规范的法域归属
类型化的划界依据为我国环境法典范围的确定提供了宏观的理论参考,但在选择环境立法时,还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在法典的横向比较中,诸如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等传统环境法的普遍规定无须在此赘述,疑难之处在于环境法典是否应当包含能源、气候变化、生物技术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法律。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能源与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在环境法典中大多是交织存在的。《法国环境法典》在第二卷第二编中的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效应部分规定了能源利用条款[注]例如,Article L224-1规定能源的合理使用必须有助于遵守空气质量标准;Article L229-25与L229-26提出一个气候能源计划,包括鼓励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措施。参见《法国环境法典》(Code de l’environnement)。;《意大利环境法典》在第五卷大气保护与减排中包含了燃料的相关规定[注]例如,在Art.291的适用范围中指明该编用以规制燃料的特性及其利用条件。参见《意大利环境法典》(Codice dell’ambiente)。;《德国环境法典(草案)》(2008版)第五卷排放交易的主要内容来自其能源法,甚至环境部在2007年的初稿中还包含随后所删除的第六卷可再生能源。[注]True,C.“Germany—the Drafting of an Environmental Law Code (UGB)”.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009, 18 (2): 80-90.能源法在《瑞典环境法典》中显现出更高的融合度,促进能源再利用的规定直接进入法典目的条款,节约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优先使用也出现在一般原则中,相关内容在土地与水域管理中也有提及。[注]目的条款中规定环境法典的适用应当确保材料、原材料和能源的再利用、循环利用;一般原则中规定行为人应当节约并循环利用原材料和能源,同时可再生能源应当得到优先使用; 土地与水域管理部分要求能源生产与运输的设施选址需尽量避免对该地与水域的破坏。参见《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1, Section 1; Chapter 2, Section 5; Chapter 3, Section 8。
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影响,得到了各国环境法典的普遍重视。《瑞典环境法典》在第三编特定活动中以第13章专章规定了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有机体;《法国环境法典》第五卷有关污染、风险与损害的预防中规定了转基因生物的使用与监管[注]莫菲:《法国环境法典化的历程及启示》,载《中国人大》,2018(3)。;德国委员会草案在其特别法部分规定了基因科技和其他生物技术。[注]沈百鑫:《两次受挫中前进的德国环境法典编纂》,载《中国人大》,2018(5)。至于自然灾害的相关内容,仅有《法国环境法典》在第五卷污染、风险与公害预防中的第六编专门规定了有关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可见,这些立法虽非传统环境法,却又因与环境风险或环境问题密切相关而在不同程度上被欧陆环境法典所吸纳。
中国环境法典应如何对待前述立法规范?结合比较法经验与我国现行法状况,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予以区别对待。
其一,应对环境风险的相关立法规范应当纳入环境法典。气候变化与生物技术领域均具有科学不确定性,较之传统环境问题所带来的确定性损害,其所隐含的环境风险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具体而言,能源法需借以污染防治或气候变化规范而进入环境法典[注]能源法的体系归属存在争议。有学者主张节能减排与能源立法属于环境法体系。参见黄锡生、史玉成:《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架构与完善》,载《当代法学》,2014(1)。也有学者认为能源法与环境法有联系也有不同,但可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参见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14(3)。,正如欧陆环境法典中的能源立法也并未以独立编章的形式出现,通常融入大气污染或气候变化的相关内容一样。气候变化立法涉及面更广,当前我国也缺乏专门的气候立法,法典编纂之时,可以考虑继续分散规定在相关法规范中,也可以如《法国环境法典》般单独成章节。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立法具有较高专业性,应当在环境法典中单独予以规定。
其二,原生环境问题的法律应对超出环境法典的适度化范围。自然灾害法主要针对诸如洪水、地震等原生环境问题的预防与救济。由于灾害的产生受到人类开发利用环境行为的影响,灾害也会造成环境的进一步破坏,有学者主张将其纳入环境资源法体系。[注]马骧聪:《论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及健全环境资源立法》,载《现代法学》,2002(3)。然而,自然灾害主要在其产生环节与环境问题有所联系,而原生环境问题又须得与次生环境问题相区别,至于减灾救灾、灾后重建等环节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已超出环境法范畴。[注]方印:《灾害法学基本问题思考》,载《法治研究》,2014(1)。因此,从适度法典化的角度考虑,自然灾害法与环境法的关系应该是相对独立的[注]陈海嵩:《自然灾害防治中的环境法律问题》,载《时代法学》,2008(4)。,环境法典仅需思考如何与之衔接,而非将其全盘吸纳。
四、环境法典的内在体例构造
法典边界划分之后,其内部规范在体例构造上的严密程度影响着法典体系效益在稳定性上的发挥。鉴于论理体[注]法典编纂体例可以分为沿革体、编年体、韵府体与论理体。参见穗积陈重:《法典论》,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成为欧陆国家环境法典体例的普遍选择,我国在向法典法的立法模式转化中,也需要思考总分结构的合理性、总则编的抽象性建构以及分则各编间的编排逻辑。
(一)总分之下的法典总则建构
自我国民法典对《德国民法典》总分结构的继受以来,是否采取总分结构这一前提性问题在我国法典体例的讨论中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但对于环境法而言,答案实际上取决于法典化的程度,具体在此体现为规范关联方式,即环境法规范是在垂直抑或水平维度上被切割的。[注]在此借鉴学者苏永钦的民法规范切割理论。原本苏氏以此描述民法典与部门民法的区别,但从规范构成的微观层面看,这一原理亦可用于解释环境法典体例。参见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为中国大陆的民法典工程进一言》,载《交大法学》,2010(1)。若依据规范所针对的环境问题进行垂直切割,则法典内每个部分将会自成体系而不需要总则;若依据规范之间普通与特别的关系进行水平切割,则普通性规范自然会形成总则。
诚然,环境法规范因其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特征而容易被垂直切割。在环境法的子领域中,一类环境规范的创制旨在解决某一环境问题。例如,为解决水污染问题而将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条款,甚至纠纷解决程序等所有相关规范都规定在一部法律里,重点突出且有针对性地防治水污染。在法典编纂中若依此进行分割,各编内部则自成一体,法规范也难以跨越各编界限进行横向关联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总则。例如,《意大利环境法典》在第一编中仅规定了适用范围、立法目的以及基本原则,未见管理体制等组织性规范与环境影响评价等一般性制度,如此更像是法典序言,对其后分则编的价值宣誓意义大于实践指导意义。这一规范切割的思路便于单行法时代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也因此可以满足基于现行法统一而成的形式法典的需求。
然而,随着环境问题的增多与复杂,此种切割方式会引发法典各分编之间的重复与混乱。例如,环境要素的一体两面使水资源利用与水污染防治难以彻底分离,同时各环境要素间的交互影响又使水污染防治与土壤污染防治产生联系。因此,基于我国适度法典化的立场以及生态整体主义的考量,应当主要以规范的水平分割为法典化方向,也因此宜采总分结构。
总分结构的关键在于区分抽象与具体、普通与特别的关系,即将可以适用于环境法各领域的规范抽象化后放入总则编,而将特殊规范放入具体的分则编。欧陆国家在法典体例上基本都遵循了论理体,整体呈总分之势而具体结构不一。从环境法典总则的主要内容看,比较法上的共性在于对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以及原则条款都有明确规定,大多数国家在基本制度上也着墨较多。各具特色的是,《法国环境法典》在总则中对信息与公众参与、组织机构、环境损害预防与修复以及管控与处罚措施进行了详细规定,瑞典基于自身环境特点将土地和水域管理的规定纳入法典总则,《德国环境法典(草案)》(2008版)总则包括了环境损害预防与修复、司法救济等内容。[注]刘如慧:《德国环境法典2009草案初探:以整合的开发行为许可制度为中心》,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2010(76)。从法典总则的功能建构看,各国主要通过抽象原则与综合制度这两方面来实现总则对分则的抽象统摄、分则对总则的具体延伸。
首先,专注原则条款的规定。《德国环境法典(草案)》(2008版)高度概括了三项原则[注]避免危害人类和环境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与合作原则。 True,C.“Germany—the Drafting of an Environmental Law Code (UGB)”.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2009, 18 (2): 80-90.,《法国环境法典》归纳出九项原则[注]风险防范原则、预防行动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信息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生态整体性原则、可持续利用原则、生态互补性原则与禁止后退原则。参见《法国环境法典》(Code de l’environnement)Article L110-1。,《瑞典环境法典》详细列明了十项原则[注]证明责任原则、必备知识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最佳适用技术原则、合理选址原则、产品选择原则、资源管理和生态循环原则、成本合理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与危险活动停止原则。参见《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Part One, Chapter 2。,甚至最为形式化的《意大利环境法典》也规定了四项原则。[注]环境行动原则(融合了预防原则与污染者负担原则等)、可持续发展原则、辅助和公平合作原则、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原则。参见《意大利环境法典》(Codice dell’ambiente)Art.3。其中,较为普遍规定的有风险防范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公众参与原则、预防原则以及合作原则。
以此比照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的原则条款,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风险防范原则在欧洲的兴盛与我国的冷遇。《法国环境法典》分别规定了风险防范与预防原则,《瑞典环境法典》与《德国环境法典(草案)》(2008版)直接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瑞典甚至将其作为环境法典所有规范的基石。[注]Rubenson,S.“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Eur.Envtl.L.Rev., 1999, 8 (12): 328-332.而我国环境基本法在此规定模糊,尽管也有学者认为依体系解释可以从《环境保护法》第5条解释出风险防范原则。[注]竺效:《论中国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立法发展与再发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3)。在法解释层面的讨论之外,风险防范原则是否应当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也有争议。二是合作原则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上的差别地位。合作原则作为国际环境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得到了广泛认可,意大利与德国在其环境法典及草案中也予以明确规定。我国在国内环境法的实施中虽然已经出现了诸如联防联控等合作实践,但合作原则当前还未上升到基本原则的高度。基于上述对比,我国环境法典在总则编纂时需进一步考虑风险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地位。一贯强调的预防性思维在法典总则中是否可以扩张至环境风险领域值得探讨,但毋庸置疑的是,未来国际与国内环境法治的落实将会需要更多合作。
其次,注重综合性制度的创建。《瑞典环境法典》在总则部分创制了环境质量标准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法国环境法典》在公共参与部分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而《德国环境法典(草案)》(2008版)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综合性项目许可制度,甚至《意大利环境法典》也在分则部分首先规定了战略环境评价和综合环境许可制度。可见,环境法典总则在综合性制度层面的重点在于环境影响评价与综合环境许可制度。进一步分析可看出二者之间存在融合趋势。《瑞典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环境影响报告应当与环境危害活动、水务作业、采石业、农业等活动所需的许可申请一同提交。[注]参见《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Part One, Chapter 6, Section 1。德国综合项目许可制度要求考虑开发行为所可能引起的所有环境影响,即在实体要素上融合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而程序上是将之前双轨并行的污染防治法与水法上的许可合并为一。[注]刘如慧:《德国环境法典2009草案初探:以整合的开发行为许可制度为中心》,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2010(76)。
在我国环境法基本制度体系中,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老三项”制度已有历史积淀,《环境保护法》第14条甚至透露出向政策层面的战略环评迈进的意图,而排污许可制度也已然成为环境法的基本制度。鉴于日益烦琐的审批暴露出制度冲突等问题,近来排污许可制度正经历综合化、一体化的改革,同时也存在关于环评制度被取代的担忧。我国环境法典在总则制度构建层面也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实际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关系可视为“事前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督”[注]孙佑海:《排污许可制度:立法回顾、问题分析与方案建议》,载《环境影响评价》,2016(2)。,比较环境法典上的综合环境许可制度正是二者融合的产物。
(二)环境法典的分则编排
环境法典分则编的体系编排须遵循一定的逻辑,在比较法上体现为内容整合与形式构造两方面。
首先,环境法典的分则编整体上是从资源、污染与生态的类型化视角进行内容整合。《瑞典环境法典》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沿岸保护区等生态保护内容与动植物物种保护统一放入名为自然保护的第二编,而在其后一编中针对环境危害活动、环境污染区治理、水务作业、采石业、农业、基因工程以及废弃物生产等相关活动进行污染防控。可谓是资源并入生态成为自然保护而与污染防控相分立。《法国环境法典》的分则部分首先在第二卷规定了水、海洋、大气等传统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随后的两卷分别针对沿海区、公园、保护区与风景区等自然空间,以及动植物、渔业资源等自然遗产,第五卷则涉及化学物质风险、转基因生物、放射性物质与核设施等环境风险。如此,在防治对象上区分了环境损害与风险妨害,在保护对象上区分了自然资源与生态区域。《意大利环境法典》缺乏针对生态区域保护的专门编章,但在第三卷中规定了土壤保护和抗沙漠化的内容,同时试图针对同一环境要素有关资源保护与污染防控两方面的内容进行整合,例如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管理被并入同一卷。
其次,环境法典分则各编在形式构造上可见对法典整体有序的追求,也存在分则编内自成一体的样态。这一区分的主要依据是各分编内部是否存在一般性规定或者责任条款。《瑞典环境法典》的分则各编基本都是直入主题,即开篇不再做一般规定,而法律责任也在法典最后统一予以规定。从自然保护与特定活动到环境司法与监管,再到处罚与赔偿的编排,旨在追求法典整体上“从预防到管制再到救济”[注]夏凌、金晶:《瑞典环境法的法典化》,载《环境保护》,2009(2)。的动态逻辑。与之相反,《意大利环境法典》在第三卷内的土壤保护、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管理部分各自有一般规定,如此似乎使此分卷自成一体,但其损害赔偿、行政与刑事处罚的相关内容又规定在法典最后。《法国环境法典》原先的处罚条款是分散在各个部分中,之后将其共同性规定整合进了总则。
环境法典分则部分的这两类编排形式各有特点。《瑞典环境法典》分则在整体逻辑上更为清晰,但由于缺乏针对环境法亚部门的一般性规定,因而对总则的概括程度要求较高;而《意大利环境法典》在分则中保留一般规定也是因其总则较为薄弱,此种编排无需对现行立法伤筋动骨,但也容易造成环境法典内部的分裂。
我国环境法典的分则编排亦可从内容整合与形式构造入手。有关内容上的梳理与整合可以结合环境法体系理论进行思考。从污染防治法与自然资源法的融合与分立[注]邓海峰:《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关系新探》,载《清华法学》,2018(5)。,到晚近兴盛的生态保护法,当前我国在环境实体法部分基本形成三分的通说。[注]杜群:《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创新——环境法概念的复元和范畴的重界》,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污染防治与资源保护的独立成编有其历史因素,生态保护法依其整体性思维而难以融入其他部分。当然,这三部分之间的分野与衔接还需要结合我国现实在法典分则的编纂中进一步思考。至于法典分则在形式上的编排,比较法上看似矛盾的整体与局部体系,实际上可以在双重体系中得到协调,即一方面注重法典整体逻辑将法律责任统一规定,同时根据分编的具体情况选择性设立该编的一般性规定,其中关键在于将一些难以上升为法典总则规范而又对特定分则编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内容进行适当抽象。
五、环境法典与外部规范的衔接
环境法典调整范围的确定,有助于法典的体例建构,但也会对法典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限制[注]Veinla,H.“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Major Challenges and Options”.Juridica Int’l., 2000, 5: 58-67.,进而降低其体系效益。法典因此需要与其外部的环境法规范进行有机衔接,以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既需处理好法典与环境单行法的关系以回应解法典化的质疑,又要有机联系法典与其他相关部门法以形成法律合力。
(一)解法典化与环境单行法
如前所述,在法典理念转向的背景下,法典不被期待涵盖所有相关规范,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也促进了法典之外特别法的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解法典化”(Decodification)的质疑。这一现象由意大利民法学者那达林若·伊尔第(Natalino Irti)提出,他认为民法典在民事特别法的冲击之下已经丧失了在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民法典正在被分解。[注]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载《法学杂志》,2006(5)。尽管我国环境法领域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法典现象,但环境单行法对环境基本法的重复与瓦解早已出现,应当以前瞻性的眼光审视未来可能出现的解法典化。
从比较法上看,应对解法典化的核心在于如何处理环境法典与单行环境法的关系。法典之外的单行立法可以分为两类:若要构成解法典意义上的“特别法”,需是在调整范围上与法典有所重合且价值理念异于法典的特别法[注]瞿灵敏:《从解法典化到再法典化:范式转换及其中国启示》,载《社会科学动态》,2017(12)。;而那些具有内容排他性而理念一致性的特别立法,实际上是对法典的补充而非解构,可以与法典一同作为环境法的渊源。正如我国当下的环境法典编纂,适度化的法典定位并不排斥环境单行法,单行法的存在与完善也为法典功能的发挥起到补充作用。[注]吕忠梅、窦海阳:《民法典“绿色化”与环境法典的调适》,载《中外法学》,2018(4)。
在法典编纂中,实际上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导致解法典的环境单行法。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在编纂之时即将其整合进环境法典,然而,若将前述范围有重合而价值不一致的特别立法贸然纳入法典,又可能会造成法典价值体系的不协调。对此,可以仅针对相关规范进行拆解合并,通过环境单行法的修订实现调整范围的协调。例如,《瑞典环境法典》是与公路法、铁路建设法、矿业法以及森林保护法等环境单行法并行适用的[注]Rubenson, S.“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Eur.Envtl.L.Rev., 1999, 8 (12): 328-332.,从事相关活动的主体需要同时遵守环境法典与相应法律,但这些单行法的继续适用并未构成解法典化现象,因为与法典冲突的部分需依法典进行修改。[注]夏凌、金晶:《瑞典环境法的法典化》,载《环境保护》,2009(2)。
(二)环境法典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
环境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公私兼具,甚至由于其调整手段综合而被形容为“诸法合体”[注]吕忠梅:《环境法回归路在何方?——关于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关系的再思考》,载《清华法学 》,2018(5)。。如何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以及诉讼法等其他部门法[注]环境法典与宪法、国际法的关系也值得思考,但基于比较对象所限,在此仅做比较法上的粗浅讨论。宪法对环境法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立法权限上,德国在2006年改革后,联邦政府获得更大的环境立法权,也因此在随后的2008版草案中加强了对水和自然保护事项的规定,但由于州政府同时享有在某些事项上得以偏离联邦规定的立法权,因而德国环境法典未来难测。U.Muller, B. Klein.“The New Legislative Competence of Divergent State Legislation and the Enactment of a Federal Environmental Code in Germany”.J.Eur.Envtl.& Plan.L., 2007, 4 (3): 181-194。国际法对环境法典的影响在于其适用方式,基于欧盟立法一体化的考量,欧陆环境法典普遍对欧盟环境法有所回应,例如,《意大利环境法典》至少对八个欧盟指令予以转化。 Mastrodonato,G.“The Implementation of EC Directives in Italy: The Environmental Code and the Transversal Tools”.Eur.Energy & Envtl.L.Rev., 2010, 19 (2): 82-86。进行有机衔接是环境法法典化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不仅是法典保持开放性的内在需求,也是经由跨部门协同形成环境保护法律合力的关键。[注]有学者提出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不仅包括部门法的绿化与环境法部门化,还应当关注跨部门协同。参见柯坚:《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从部门性反应、部门化应对到跨部门协同的演进》,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环境法典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在法规范上主要体现在制度措施与救济方式两方面。
其一,环境法典在制度措施方面有赖于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现有框架。环境规制理论将环境保护措施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前者依托行政行为来实现,后者涉及税收、价格、财政以及金融等经济法上的宏观调控制度。[注]李艳芳:《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载《清华法学》,2018(5)。前述欧陆几国的环境法属于公法范畴,其实施基本上都是在行政法的框架下,环境法典也几乎通篇可见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又在此基础上尝试诸如综合性许可等制度创新。税收等经济措施在环境法典中也有提及,例如,《法国环境法典》在总则卷第五编财政条款中用转致条款规定了污染税根据海关法典进行收取[注]参见《法国环境法典》(Code de l’environnement)L151-1。,德国委员会草案第6章详细规定了环境税费与环境补贴的收取与使用,《意大利环境法典》却忽略市场工具对主体行为的引导,因而对激励措施缺乏关注。[注]Fracchia,F.“‘Codifi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 2009(1): 1-22.
其二,环境法典在救济方式上需对接诉讼法、民法、行政法与刑法有关诉讼程序与法律责任的规定。在程序规范上,《瑞典环境法典》将司法救济与行政救济合并在第四编案件与事项的审查中,详细规定了程序规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立了完善的环境法庭制度,从法庭组成、管辖范围到诉讼程序都有详细规定,并与《司法程序法典》相衔接。[注]例如,规定不得损害当事人根据《司法程序法典》享有的上诉权。参见《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16, Section 12。德国环境法典草案的总则编也涉及诉讼程序规定,委员会草案规定了团体诉讼、行政法院,而后的2008版草案也规定了简易诉讼程序等内容。
在责任条款上,欧陆环境法典普遍规定了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瑞典环境法典》在第七编赔偿中规定了针对因水域、空气、土地以及噪声污染等所造成的人身损害、物质损失和金钱损失的赔偿责任。[注]参见《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32, section 1, Section 3。在传统的人身与财产损害之外,环境损害成为环境法典重点关注的救济对象。《意大利环境法典》第六卷的生态损害赔偿被认为是该法典最具创新的部分,界定了生态损害的概念与范围,环境损害的预防与修复以及赔偿。[注]Mastrodonato,G.“The Implementation of EC Directives in Italy: The Environmental Code and the Transversal Tools”.Eur.Energy & Envtl.L.Rev., 2010, 19 (2): 82-86.德国独立委员会草案也创新性地引入了针对纯粹生态损害的修复责任。[注]Rehbinder,E.“A German Source of Inspiration? Locus Standi and Remediation Duties under the Soil Protection Act, the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ct and the Draft Environmental Code”.Envtl.L.Rev., 2004, 6 (1): 4-20.《瑞典环境法典》在处罚规定上与刑法存在密切联系,不仅有转致条款[注]例如,规定从事行为违反第1款第(24)项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刑法典》第二十三章的规定进行处罚。参见《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29, Section 8。,而且还直接规定了环境侵害罪、处理化学品危害环境罪、非法从事未授权环境活动罪、妨碍环境控制罪以及不完全环境信息罪等具体罪名与相应罚则[注]参见《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29, Section 2, 3, 4, 5, 6。;而在行政责任上,新增了环境处罚费用以处罚经营者违反法典有关行政许可等规定的违法情形。[注]参见《瑞典环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30, Section 1。《法国环境法典》最初的处罚规定分散在分则各编之中,例如,水环境、动植物保护在各自部分有相应的责任条款,之后对这些处罚内容予以整合,在第一卷中新增第七编来统一规定行政措施与处罚、犯罪侦查与刑事制裁,呈现出环境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一体化趋势。[注]参见《法国环境法典》(Code de l’environnement)Article L170-174。
如上所述,在制度措施层面,欧陆环境法典基本上是基于现有行政法框架而适当有所创新,对税收等经济手段也有所关注,而在立法技术上或详细规定或外接既有立法。我国也有相关立法创制了河长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新型环境管理方式,环境保护税、碳排放交易等经济激励制度也在不断探索完善中。环境法典可以秉承这一思路,但同时需注意尊重行政执法的基本原理、谨慎经济制度的即时多变。此外,我国民法在通则时代几乎仅在环境侵权上与环境法有所联系,而今民法典为回应时代需求在总则引入绿色原则,可以预见未来物权、合同等分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新增环境保护的私法制度[注]参见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载《中国法学》,2018(1)。,环境法典因此也应关注与私法制度的衔接。
在法律救济层面,欧陆环境法典多注重与程序法的联系,尤其是瑞典环境法庭的建立使环境司法在诉讼程序上有所变化。我国也正在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法典编纂中需要注意与诉讼法的既有规定相衔接。欧陆环境法典中的行政责任一般直接在法典中予以具体化,刑事责任的创制则有限,仍需要转致到刑法典,而民事责任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也创新了环境修复责任。在我国当前的环境法律责任体系中,环境侵权责任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构成环境犯罪的亦直接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注]参见《环境保护法》第64条、第69条。,而行政责任则是在行政法的框架下进行适当创新。[注]例如,按日连续处罚,参见《环境保护法》第59条。至于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与赔偿责任,其性质虽尚未达成明确共识,但在立法上可考虑将其作为环境特别民事责任。[注]李挚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法律性质辨析》,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此外,法典保持开放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外接条款,但这不仅仅是立法技术问题,也涉及价值判断。[注]郭志京:《中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总则编体系建构》,载《法学论坛》,2018(1)。例如,环境刑事责任在环境法典中是详细规定还是仅转致到刑法典,实际上反映出环境法益在刑法典中是否得以作为独立法益而存在。环境违法从单纯的行政法规制到行政犯与刑事犯并行的格局,再到近年来环境犯罪立法由附属刑法开始向核心刑法发展,这一过程反映出环境法益的日渐独立。[注]钱小平:《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载《政治与法律》,2014(3)。随着刑法典对环境犯罪的日益重视,环境法典也因此无须多增烦扰,而仅需通过外接规范即可实现法典的开放性追求与整体法秩序的协调。
总而言之,环境法已然在经历着一场立法模式的变革,中国环境立法经近四十年的发展与积累,法典化可谓正当其时。身处法典前夜,更需要从比较法视野看环境法法典化在我国从何展开。欧陆国家的环境法典因其国情各异而在法典目标上存在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的区别,最终在调整范围、体例构造与规范衔接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法典样态。环境法法典化虽尚在探索之中,然基于比较法上的观察,仍可归纳出一般规律:在法典目标基于功能主义予以定位之后,法典范围的确定需围绕划界依据综合考量,法典内在的体例构造取决于总则抽象性建构与分则编排逻辑,法典外部的规范衔接体现为环境法典与环境单行法以及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对此,我国应当基于法典体系效益而在环境法典的目标定位上选择适度法典化,并通过对法典的范围划界、内在体例与外部衔接的思考,编纂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环境法典。此外,多元化的比较视野为我国环境法法典化提供了丰富资源,但如何调适域外经验间的适用冲突,使之共生于我国本土等问题还需要在环境法典编纂的具体进程中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