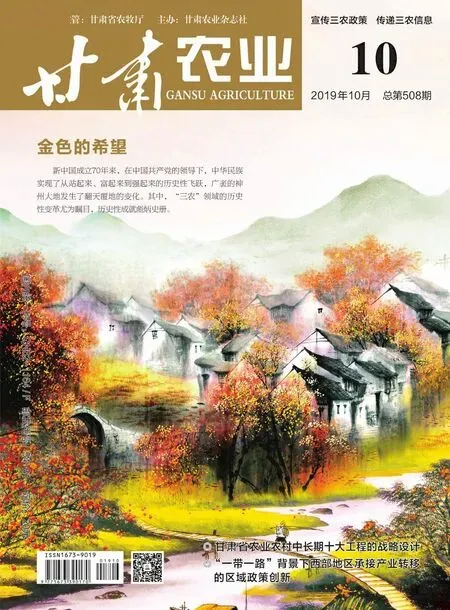20世纪30年代产销合作视域下的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发展
2019-01-06韩丽娟
韩丽娟,李 忠
1.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2.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浙江是合作事业起步较早的地区,1928年浙江萧山即成立有衙前信用合作社和衙前信用合作社。20世纪30年代,面对衰败的农村经济,“用合作方法来救济农村经济”成为浙江从官方到民间的主流观点。在浙江省建设厅及各级县政府、浙江地方银行与国立浙江大学等机构的推动下,浙江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合作运动。这场农村合作运动自上而下推行,由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起步,逐步推广至农业生产与运销领域,是近代以来振兴农业与农村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发起的困难与信用合作社的兴起
近代认为,“培养农民智识为发展合作事业的基础”[1],然而“农民知识幼稚,不知道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对于组建合作组织,农民既无意愿又无能力,“农民不识字,无知识,对于详细章程及繁重之手续,辄闻而生畏,宁愿饿死。”[2]银行在“乡间宣传组织合作社,遇不识字之农民,欲其组织合作社,因不能记账,无力雇佣记账员”。[3]
那时,农民不可能自动自发的组建农村合作组织,培育农村合作组织以救济农村经济,只能依靠农村外部的力量推动。为了尽快促进农民合作,社会各界从组建信用合作社入手,培养农民建立农村合作组织。时人记述了崇德县办理农村合作社的经过,“本县合作事业,始于民国十八年八月,当时建设厅委派促进员来县指导,惟人地生疏,农民智识浅薄,往往不明合作意义,故办理上煞费心机。”“自该员来县后,即着手于宣传工作,因本地无印刷店,致各种印刷品,无从印就。后由该员亲自赴省向建设厅领到大批宣传品,分与各村识字者;并由该员分别赴乡实地宣传。十八年九月,始成立第四区下马村有限责任信用合作社,至十二月合作社之成立已有十三处;然后合作事业,全以农民银行为后盾,本县有鉴于此,即设法于是年十二月,将带征之农民银行基金,划出一万元,先行试行放款;订具各种放款规则,于十九年一月底试行放款八千余元,经此次放款后,农民始知组织合作社,得向试行放款处借款,此种思想,虽非合作社之真真意义,然‘合作’二字,已深入一般农民之脑筋矣。”[4]从中可见农村合作组织发起的困难及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培养农民合作精神方面的有效性。
通过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农民发放借款,对于资金匮乏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可以快速引导农民组建合作社,并逐步明了合作的意义。此外,因“受高利贷之压迫与借贷之困难”、“经营信用合作较为简便”、“缺乏商业知识与经验”与“无流通资金”等原因[5],信用合作社在各类合作社中进展最快。根据时人统计:“1928-1933年,浙江共有合作社728处,其中供给合作社2处,生产合作社22处,运销合作社11处,利用合作社1处,储藏合作社4处,保险合作社1处,消费合作社14处,计共55处,而信用合作社,计有673处之多,占全省合作社总数90%以上。”[6]为什么信用合作社进展如此之快,生产、运销、储藏等合作组织虽力事宣传与提倡一时仍难见诸推行。
二、浙江单营信用合作社引导农民合作的弊端及其整顿
浙江的农村合作组织由单营的信用合作社起步,这些信用合作社大多不兼营其他业务,进展迅速。然而,从1929年信用合作社初始创办到1932年前后,短短几年,信用合作社就暴露出不少问题。
首先,单营信用合作社社务狭小。信用合作社“全都限于借款方面,储金一未举办。”“致社员对于合作社之观念,极为薄弱”,不利于培养农民的互助合作精神。[7]其次,一部分信用合作社成了一种“合借社”,“当时的农民对于合作,除感到新奇并知道可以借钱以外,不知有他”[8],“他们无非为向农行借款而组织,迨款借到,一哄而散。这种弊病,流行于江浙两省。”[9]结果是“合作社的数量虽多,但质地极坏,农工银行的放款大部分也就变成了烂账。”[10]“合作社”变成了“合借社”,这些不仅与通过信用合作社引导农民合作进而救济农村经济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进一步增加了农村经济的纷扰和混乱。再次,有些信用合作社还存在“钱庄化”的问题,“以低利借进,重利借给农民,和钱庄一样的存着谋利的目的,去剥削农民,这种合作社,可说是‘钱庄化’了。还有信用合作社兼营储蓄业务,对于社员存款,利息很低,这亦是钱庄化了。”[11]以信用合作之名行钱庄之实,以高利贷剥削农民,结果使农民进一步误解合作,看不到信用社合作社的优越性,不利于合作的有效推广。
农村信用社质地败坏,完全背离了合作的精神,结果是一方面“以土劣士绅为主要份子的信用合作社到处林立”,另一方面,“多数的贫农依然没有入社的机会”,广大的贫农不能经由合作而自救,农村经济也无法恢复并得到发展,浙江农民合作组织亟需纠正。
农村信用社发展不善,合作指导和合作放款难辞其咎:“合作指导人员,因事属草创,经验缺乏,且以求效太速”,当时的金融机关如中国农工银行“对合作社放款,事前既不知予以缜密之审查,事后又不常予以指导监督”。[12]1932年之后当局着手对“颇有组织未尽合法或办理未善者,甚至仅具合作之名毫无实际者”切实整顿取缔。[13]各县的合作指导员随时对于合作社去督促和指导,使合作社的内容日趋充实,而不专求数量之急增。经过这样的整顿之后,“民国廿二年以前的合作社,大部分均已遭解散淘汰,能够保有五六年历史的合作社,在各县,实为凤毛麟角,不可多见。有的县份,从前曾有百数以上的合作社,现在只剩二三十个了”。[14]
三、浙江农民产销合作的兴起
1932年之后,浙江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逐渐转变,一面严厉整顿以信用合作社为主的不良合作社,另一面提倡合作社兼营,扩大合作事业的范围。时人主张:“应效法累发毕式农村信用合作社,兼营原料购买合作,而业务简单易行,使能增进社员对合作社之信仰,其余各种合作社,亦采择兼营,以节靡费。”[15]人们逐渐认识到只要当合作与整个农业生产和运销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救济农村、振兴农业。
在农业生产不振、农村破败、国家危机日深之时,提倡生产合作事业,尤其具有有重大意义:一宜增加对外输出,二宜注重自给自足,三宜注重经济统制,四宜促成农村副业工业化。关于生产合作社,人们认为共同耕种是最基本的生产合作业务,它是救济农村、使“农民归农”和“使农民有田可耕”的根本办法,[17]然而人们所期待的共同耕种却未能付诸实践,“有耕种合作社、垦殖合作社之模范章程之订立,唯成立社数尚不多。”[16]浙江的生产合作主要集中于幼蚕培育、桐油生产、合作制糖等方面。蚕丝业是浙江最重要特产,在浙江以养蚕为“正业”的在30县以上,由于茧价惨落,人民收入锐减,“农村经济之枯竭,农民生计之艰困,蚕丝业之衰落实其最大原因”。根据农民生产规模小、养蚕技术不高的现状,组织蚕业生产合作社不失为一种使农民了解科学的养蚕方法、改进蚕业生产的办法。浙江最著名的蚕丝合作社出现在萧山,1928年该社成立后,即着手改良蚕种,用改良种换取农民手中的土种,并派技术人员进行辅导,成绩令人鼓舞。桐油是中国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但采用土法生产桐油损失太大。在浙江省建设厅的推动下,浙江试图通过合作的方式改进全省桐油的生产。兰溪桐油生产合作社即为其中的代表,无奈因榨油工具落后而未能提升桐油生产效率。红糖是义乌特产,但各地农民制糖的方法极其拙劣,以义乌为中心区域成立合作制糖厂一所,“据精密估计,每担甘蔗及糖粳进厂后,较以前土法生产时可增加三元至五元,即自九元增至十三四元不等。单在义乌一县机制白糖而论则该县农家每年可增收二十万元左右。”
运销合作社可抬高农产品售价,防止农民被渔利,增加农民收入。鄞县樟村的堇江贝母运销合作社即颇有成绩。该社经营贝母产销业务,出产的贝母分元宝贝、珠贝两种,元宝贝年产二千担,珠贝年产七千担,该社自成立后,元宝贝每担售洋由六十元增至一百三十余元,珠贝每担售价由五十元增至七十余元,该社全体社员每年所增进的利益,共计在三十万元以上,这巨量收入的增加,极有助于经济极度衰落的农村。[15]
总之,在农村经济衰败之时,通过合作生产与运销的方式、给予农民技术上资金上运销上的协助,改良了浙江各种特产生产与运销,有力地挽救了衰败的农村经济。
四、促进浙江农民产销合作的政策保障
浙江农村合作事业成效显著,和政府机构、金融机关以及学术团体的提倡推导密不可分。从浙江建设厅下设合作事业室到浙江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到浙江全省合作事业促进会等民间团体,再到国立浙江大学农村社会系等学术团体,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合作事业推进体系,各方通力合作,为浙江农村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首先,采取自上而下的合作指导制度。面对既贫且愚的农民,惟有政府出面指导,给予农民合作知识与技能的引导,才能推动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浙江建设厅于农业管理处下设合作事业室,其下设合作事业及合作金融两股,后者管理各县地方农民银行,使合作指导与金融得有联络。在县市方面于建设科中设合作事业指导员一人或二人,“是项指导员大都系浙江省第一、二两期合作指导人员养成所毕业学员,他们好像是一种教导农民谋生的下乡教师,向农民做户别施教,他们的任务首在教授得法,即在启发农民,引起农民对于合作发生兴趣以后,便进而帮助他们组织合作社并负责指导社务种种工作。”合作指导员关系到农民合作社的兴衰成败,“惟年来此项毕业学员既迭有更调,而因故去职者亦属不少,以此现仍留职服务者,已寥寥无几,而各县来文请求分派促进员者,则纷至沓来。”合作指导人员有“不敷分派之感”,是当时的主要问题。
其次,推进浙江特产的生产与运销合作。在共同耕种还不能付诸实践之时,浙江省建设厅着力提倡浙江特产的生产和运销,具体的举措是举办各种模范合作社,“使其生产改进,并免行家之中饱。”“俟各地各种特产合作社成立后,即行倡办各种特产合作社联合会,使其贯通联络,而收互助之效。”[16]对于各种特产的生产,由县市政府出面会同学术团体及金融机构进行技术改良与资金融通,指导农民设立农民合作社,用整个社会力量来改良浙江特产的生产,同时注意国际贸易上的调查考察及推广工作,从特产生产及运销的方面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
再次,实施示范工作。示范工作,便是择定农村的中心区域,设立农村合作事业实验区,“由建设厅派驻专员,并与当地公正之人士联络共同筹办各种合作组织。关于区内有关于合作之调查、计划、指导等工作,均由厅派专员首先领导进行。区内各合作事业经费如有不足,亦由建设厅特别筹划借用,如慈母之保赤子,一步一步使其脱离政府帮助,达到独立经营之目的。结果使区内各种事业完全合作化,将来并供各合作学员之集中实习及各地合作社职员观摩之用。”实施示范工作可补足指导制度之不及。浙江第一试验区自1933年3月成立,指导当地农民成立养蚕、烘茧、运销、及信用兼营等合作社,合作养蚕及共同烘茧,尤著成效。第二试验区于1935年8月成立,已指导该区农民成立柑类及草席运销合作社暨人力车信用兼营合作社等,办理亦多成效。
最后,调剂农村金融。20世纪30年代,因农产物价跌落,而生产成本及日用品价格渐渐高昂,致使农村对都市入超,现金源源流入都市,农村农村金融涸竭。农民缺乏生产资金,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受到抑制,流通农村金融成为当时的急务。诸如典当等旧式金融机构日渐衰败,流通农村金融只有依靠农民银行或农民借贷所等新式农村金融机构。至1932年,浙省各县现有农民银行已成立者计有衢县、海宁、嘉兴三县;先行设立农民借贷所者计有崇德等八县;筹备就绪行将成立者有平阳等四县;指定的款切实筹备者有平湖、桐乡等二十五县。资本最多者有95913元,最少者仅3495元。浙江省建设厅指出,救济农村经济,需要积极促成各县农民银行及借贷所。[16]至1935年,浙江省已成立县农民银行或农民借贷所者有衢县、海宁、余姚、嘉兴、崇德、绍兴、亲善、金华、平阳、义乌、平湖、永嘉12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