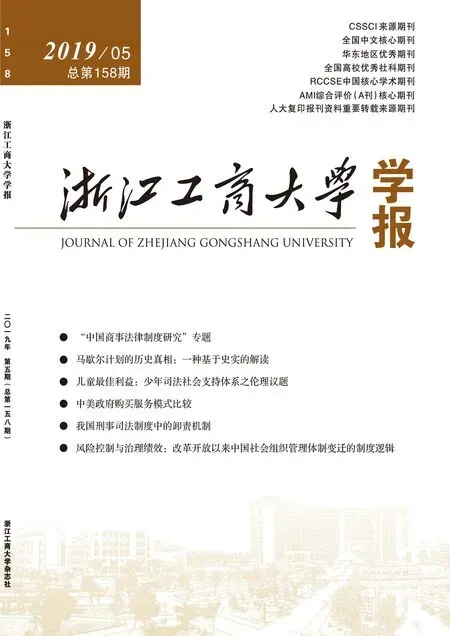日常生活史的神话认知与表达
——以《山本》为例
2019-01-06张栋
张 栋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 引 言
神话与历史,前后相继地构成了中国叙事传统的两种主要倾向,前者以虚构笔法投射出原始人类的自然与社会想象,后者则以纪实为要义,试图还原人类生存的真相。在中国叙事话语的演变中,历史书写因其强烈的指导与改造现实的目的性,成为压倒神话讲述的主要叙事形式,人们总是试图在史实中找寻事物存在的依据,以及现实社会实践的具体方法。即使如此,历史书写也从未真正远离神话,尽管神话早已失去其存在的现实土壤,但它却以一种思维的形式进入到、甚至指导着历史的讲述。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中,这种神话与历史的纠缠状态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呈现。不管是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书写,还是新时期以来以新历史主义创作等为代表的充满叛逆激情的历史重述,当代作家都为既往的历史涂抹上了一层主观化改造的色调。这种主观化改造或者创造了现代革命的政治神话,或者创造了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体性神话,这些所谓“神话”其实都是意识形态内涵浓厚的主观表达,与罗兰·巴特所言的“今日之神话”并无区别。当代作家贾平凹则采取了与上述创作不同的思路,即在一种历史的生活化还原中,凸显神话在其中的特殊位置,这不仅在最大程度上复原了神话的当下存在状态,而且丰富了神话与历史之间相关联的叙述方式。按照贾平凹自己的讲述,他对于历史叙述的兴趣始于《老生》,但其历史叙事的特点与风格早在其现实题材创作中即已开始酝酿,从《商州》《浮躁》,到《废都》《秦腔》,乃至《古炉》《极花》,贾平凹在现实书写中开创了一种将日常生活的写实与神秘表现相糅合的叙事风格,这一风格在《老生》中得以延续。贾平凹在《山本》中不仅还原了神话思维方式的多元存在,而且也以批判性视角展现了意识形态话语统摄的神话对民间神话的压制过程。
在《山本》中,贾平凹的历史叙事虽呈现为日常生活流动的表象,但又并非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是经过了审美化改造,它在“法自然”的同时又兼具了一种神秘特质,是生活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融合。从根本上来说,日常生活的神秘属性其实是神话进入历史乃至现实生活的结果。贾平凹笔下的“神话”,是观照历史的一种“方法”或“形式”,是德国哲学家谢林所说的“对于人类意识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它对意识的影响力”[1]。也就是说,“神话”变成了一种话语方式,变成了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方法。它既是对传统神话言语核心内质的提炼,同时也更多地糅合了人类生存的现实成分。神话的这一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达。在小说中,神话叙事脱离了对神话故事内容的讨论限度,而成为作家的文化与历史记忆的容器,同时成为人类原始心理与经验当代性表达的一种形式。《山本》中的神话,不仅构成贾平凹日常生活史叙述的背景,而且同时进入到涡镇人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串联起人们的思维观念与行为选择,并以具体物象呈现的方式构成了人们的民间信仰。贾平凹不仅探讨了神话在前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神话式时空重塑,而且探索了传统神话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命运。对历史的日常生活式表现,使人感受到历史似乎从未离自己如此之近,它以另一种形式还原了历史,而神话视角的切入,则使人深入到历史实践主体更为内在的心灵与精神世界,从而使读者在心理层面更深刻地理解了历史。
二、 作为日常生活知识与思想背景的神话
贾平凹为神话表现选择了一个极其恰当的场域,即日常生活。需要指明的是,这里的“日常生活”区别于人类在科学理性认知与高强度社会规约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社会生活,因为这种具有强烈规则性的日常生活往往具有琐细、芜杂等特质,它往往使生活主体陷入一种固定的秩序之中,“能够而且的确常常导致人的行为和思维中的某种僵硬”[2],神话在这种生活节奏中必然会失去滋养的土壤。因此《山本》中日常生活的发生背景,是秦岭深处那些仍未被所谓“现代性”侵染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具有明显节奏感的日常生活态势不同,秦岭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仍遵循着自然节律,自然的规则并不是强加于人类的,而是允许人类在总体规则遵守的前提下,存在多元的选择。这种选择逐渐演化为被称作“民间智慧”的事物,也就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3]。这一智慧系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解释,同时形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感性规约。神话,正是在这种解释与理解系统中生发出来的。从人的理解与生活实践规约层面,神话思维方式进入到涡镇人的日常生活与意识之流中。神话不仅构成了涡镇人日常经验与知识的主体,构成他们的日常生活知识与思想背景,而且也融入涡镇的物质生活、岁时节令、巫术仪式、组织架构之中,与涡镇的生命周期同轨运转。在某种程度上,《山本》中的神话叙事具有了仪式化叙事的特征,即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描写”“表现出文本叙事中极具象征性和表演性的仪式内涵与仪式意义”[4]。贾平凹即是在上述观念背景中,以日常生活为经,以神话为纬,塑造了涡镇日常生活史的网状结构。
《山本》中涡镇的自然地理布局与具有自然特质的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了涡镇人生活的自然节律特质,这也解释了神话作为涡镇日常生活知识与思想背景之来源的原因。据有关学者考证,陕南地区“深处秦巴山地,鬼神崇拜浓厚”[5],而据贾平凹自述,“有山有水有树林有兽的地方,易于产生幻想,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6]。可见,被自然山林环绕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人们的原始想象,这种想象被附加于自然物象乃至人身上,并往往呈现出神秘特点。另外,从贾平凹对涡镇的客观描绘中,可以推断出涡镇人具有相对自足的生产方式,涡镇独特的建筑构成(三面环水、北面靠山)使其与外界存在有限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也很难改变涡镇人既有的思维结构。因此,整体上来说,涡镇的地理区位与生产、生活方式,使涡镇人形成了相对稳定与保守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重想象、尚神秘、多联想,这正是一种神话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以这种思维方式为前提,涡镇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似乎都处于一种互动的联系之中,任何事物的意义也需要通过他者呈现出来,因此不同事物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互渗”关联。这种联系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而且在小说叙事层面,它也推动了叙事情节的演进。
“互渗”体现了涡镇人特有的神话思维方式,或者说原逻辑的思维方法。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把“互渗律”解释为“为‘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的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7]78-79,这里的“表象”,是承载人类原始集体记忆的、同时具有现实意义的象征物。具体到《山本》中,“表象”不仅指涡镇里那些被人视为集体信仰的对象(如坐落于镇中央的老皂角树),也指代具有个体性的、对人物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象(如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正是基于对“互渗”的理解,以及“表象”存在之于人类日常生活重要意义的现实,贾平凹选择将上述观念进行事实化呈现,同时注重人物视角在上述呈现过程中的重要转接意义。这便是作家自己所说的“以实写虚”的写作方式,在表面上看是实写一种神话情境,但在根本上却是表达一种思维方式的运行模式。贾平凹的这种创作特点自《太白山记》起便初露端倪,到《山本》中已蔚为大观,其目的是“以最真实朴素的句子去建造作品浑然多义而完整的意境”[8]。实与虚,犹如房屋坚实的地基与虚无空间的关系,而“互渗”在本质上也是感受主体与客体之间虚无但紧实的关联,它代表了一种在理性层面不合逻辑但其本身又自成逻辑的思维方式。
《山本》中的“互渗”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文本中作为细节存在的“互渗”书写,它证明了神话思维方式在涡镇中的普遍性,以及神话参与构建涡镇日常生活背景的重要作用;二,构成文本叙事情节推进器的“互渗”,这是细节存在的“互渗”在小说叙事层面的自然推衍,它促使神话逻辑在文本中的展开,继而影响到小说的情节建构与意义阐释。
作为文本细节存在的互渗,在《山本》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人与物、人与鬼神、梦境与现实的互渗。人与物的互渗,在《山本》中表现最为普遍,且具有叙事线索的意义。小说开头,陆菊人在九天玄女庙中解救了一只蟾,后来她持家有方、经管茶店得力、做生意利润丰厚,从而成为他人眼中金蟾的化身,这正成为陆菊人-金蟾互渗的证明。陆菊人嫁到涡镇时带的一只黑猫,不仅陪伴着她的儿子剩剩,而且能够在剩剩发生危险之前发出预警,二者之间的命运联系跨越文本始终。此外,杨钟与人面蜘蛛、陈先生与婆罗树、涡镇人与老皂角树,甚至人与影子之间感觉上的联结等等,都体现出互渗关系对涡镇日常生活的缠绕,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系统得以构成。人与鬼神之间的互渗,在小说中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氛围。人与神之间的互渗,主要体现在涡镇人与130庙(地藏菩萨庙)的宽展师父、安仁堂的陈先生之间的联系上,他们以神奇的预言及救死扶伤的能力,成为涡镇人的精神依托,而且唤起了他们类似于神灵信仰般的崇高情感。与此相对应的是鬼在涡镇引起的恐怖氛围。出于一种恐惧心理,涡镇人极力阻止人与鬼之间互渗的发生,看守涡镇北大门的老魏头用钟馗画像阻止鬼的入侵,陆菊人教花生用吐唾沫的方式抵挡鬼的干扰,井宗秀甚至把三猫被剥下来的人皮做成人皮鼓以惩戒不安分的鬼魂,但钟馗画像的丢失,以及老魏头见到涡镇中越来越多的鬼,说明人鬼之间互渗关系得越发频密与强烈,涡镇的覆灭结局即是在这种恐怖氛围中发生的。另外,梦境与现实之间也能够实现互渗。梦虽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潜意识的具象形式,但在《山本》中却变成一种“实在的知觉”,它不仅预示了人的未来命运,而且成为人“与精灵、灵魂、神的交往”的形式。[7]54《山本》中,井宗秀和陆菊人做了相似的梦,他们在梦中看到了涡镇以前的和现在的、已经死去的和仍在活着的人,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到涡潭之中,似乎在进行一场神秘的仪式。这一梦境不仅对应着涡镇的历史,而且预示了涡镇现实发展的未来走向。过去、现在与未来,就这样在梦境中得到了循环呈现,这又何尝不是对现实的真实演绎呢?人与物、人与鬼神、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互渗关系,使涡镇被包围在一种浓厚的神话氛围中,同时也使涡镇人的生命感觉与现实感受得以突出。
推进小说情节发展与演进的“互渗”,被赋予了结构性意义,就如《山本》开头的第一句话——“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9]1。这句话即点明了陆菊人与那三分胭脂地之间的互渗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了整部小说。陆菊人在听到赶龙脉的人断定那三分萝卜地能保佑出官人之后,便把它作为自己的陪嫁,建立起自己的“官人”理想与胭脂地之间的互渗关系。但当她发现丈夫杨钟难成大器,而公公又阴差阳错地将胭脂地送给井宗秀,这种冥冥之中的安排又使得陆菊人改变思路,转而将井宗秀视为“官人”的替代。这种念想鼓动着陆菊人努力建立起胭脂地与井宗秀之间的互渗关系,这也是陆菊人与井宗秀之间的关系虽若即若离,却仍能够贯穿小说始终的原因。即使陆菊人经历了丈夫杨钟与公公杨掌柜的先后离世,还要忍受涡镇人的风言风语,但她仍然选择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对井宗秀表示支持,这与其说是陆菊人与井宗秀之间隐约的男女之情的推动,不如说是胭脂地神话造成的强大互渗对陆菊人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约束的决定性影响。尽管如此,井宗秀与胭脂地之间的互渗却并未满足陆菊人的期待。井宗秀在现代革命的暴力促动下越发暴戾,对陆菊人的劝阻充耳不闻,对陆菊人介绍的花生弃如敝屣,这一切都脱离了陆菊人预想的轨道,也使局势越发难以把控。无奈的陆菊人只能把井宗秀叫到胭脂地前,在她信仰的神话面前结束了对井宗秀的期待,之后她又把井宗秀从胭脂地中挖出的铜镜归还,从而人为地割断了井宗秀与胭脂地的互渗关系。互渗关系的确立与崩塌,成为《山本》神话叙事的主要结构,所有的人事都被裹挟入这一结构中,在日常生活的展演中缓慢运行,在时间的模糊与漫漶中悄然发生。
在前现代的、以自然节律展开的时间历程中,神话不仅以“互渗”的形式展现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而且触及到了涡镇人与世间万物之间的深度关联。作为日常生活知识与思想背景的神话,构成了人们认知世界的中介,使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流动中能够时刻产生一种超验的精神感受,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向人们心灵的敞开。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普通的个体其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宏大的神话世界,它是个人精神独立性的证明,也是其生活智慧的重要来源。个人所理解的神话的外在呈现,不仅是日常生活自然流动中的细节显露,它也进入到涡镇神话空间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在整体层面进一步发掘出涡镇作为神话地域的现代特质。
三、 涡镇日常生活的神话空间建构
日常生活的神话空间建构,与神话的“互渗”式融入有所区别,如果说后者更多涉及了个体从主观层面对于神话的理解,并具体表现于生活细节的展演之中,那么神话空间建构则是一个整体性问题。日常生活的视角,使作家规避了传统历史叙事中对重大矛盾、重要现象的表现,以及对历史事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的突出,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流动展示中,着重表现人物以群像方式参与历史的建构,这自然影响到了叙事空间层面的表现,即“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象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示出鲜活的历史情境”[10]。战争等社会运动虽然介入了贾平凹的历史叙事,但作家显然更着意于一木一石对于涡镇日常生活的塑造,它使历史重归具体,而非抽象的理念显现。在《山本》中,贾平凹着重塑造了由僧、道、玄女、城隍组成的神话图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涡镇的社会形态与信仰构成,上述神话人物在文本中的具象呈现是“将社会现象和社会力量人格化形成的神”,是与“自然神”相对应的“社会神”[11]。僧、道、玄女、城隍在文本中的立体呈现,是宗教与民间信仰色彩汇融的具体表现,是涡镇日常生活展开的神话基础,同时也参与了涡镇日常生活的神话空间建构。《山本》中,僧、道,与玄女、城隍,构成相对应的两组关系,二者之间构成一种平衡,并在文本中呈现出“对位互照、双向流动”的叙事效果。
中国传统文学中“一僧一道”的叙事传统,是《山本》僧道叙事的重要来源。据一些学者的考证,一僧一道的叙事设置,在早期多是作者创作观念的一种象征化表现,明代屠隆的《昙花记》,与《夷坚丙志》卷三的《杨抽马》,则加重了僧道人物形象的巫术色彩,到明代的《于少保萃忠传》,一僧一道叙事模式逐渐成熟,一直到《金瓶梅》与《红楼梦》,僧道叙事则直接进入到小说结构层面,对人物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12]。《山本》中,“僧”是指宽展师父,“道”是指陈先生,虽然同样是一僧一道的叙事设置,但在文学表现的现代性、神话表现的集中性层面,其与传统文学中的僧道模式有了比较大的区别。一僧一道的结构设置,在小说的文学地理区位、叙事情节推进与主体意蕴的开掘等多个层面,介入了涡镇日常生活史的建构。
《山本》中,宽展师父身居的130庙(地藏菩萨庙)地处涡镇西北,陈先生处身的安仁堂地处涡镇西南,涡镇被夹在其中。这种地理空间的设置颇类似于《金瓶梅》,小说中,玉皇庙与永福寺将西门庆的府邸夹在中间,记录下了西门庆家族中的生与死。张道深评道:“玉皇寺、永福庙,须记清白,是一部起始也,明明说出全以二处作终始的柱子”[13]。杨义认为,“这道庙佛寺之设,把西门庆家族置于生与死、冷与热的带有宗教意味的潜在结构之中,呼应带有空幻色彩的天人之道”[14]。《山本》中的130庙与安仁堂,以独特的地理区位,贯穿小说的始终,同样见证着涡镇的生与灭,是涡镇人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场所。在情节推进层面,《山本》又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红楼梦》的叙事传统。《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把顽石携入尘世之中,让它在温柔富贵乡中走了一遭之后,重带回青埂峰下。在这一循环中,一僧一道屡次在叙事的关键节点现身,以点化迷途中人,这自然地推进了叙事的演进。《山本》中,宽展师父与陈先生之于主人公乃至涡镇人的意义,正如《红楼梦》中僧道之于顽石的意义。他们同时现身陆菊人的婚礼,似是接引她进入到涡镇之中,而每当陆菊人产生对于世事的困惑,他们又适时做出点化与引导。不仅是陆菊人,涡镇人每当有难以评断的是非,便要到宽展师父面前发誓,以证清白,而安仁堂的陈先生不仅疗治涡镇人的疾病,也为他们述说人生之理。一僧一道的点化,影响了涡镇人的心理与行为选择,继而使小说整体的叙事进度发生变化。在小说主体意蕴的开掘层面,一僧一道叙事设置的最终指向,其实是对人间生死之道的探讨。130庙与宽展师父,总是与小说中的死亡发生联系,起到了度脱逝者的作用。井宗秀的父亲暂时找不到墓地,可以浮丘在130庙里;涡镇中每有逝者,宽展师父就要为亡魂吹响尺八;130庙里不仅为涡镇人,也为五雷等土匪安放牌位,皆说明宽展师父面对死者的宽容态度。安仁堂与陈先生,则起到了救扶生者的作用。陈先生本为道士,之后成为治病的先生,他不仅有高超的医术,而且有扶危救困的古道热肠,当因战乱导致的大量难民涌入涡镇,陈先生更是以一己之力挽救涡镇脱离瘟疫的厄运,这说明了陈先生对于生者的悲悯心态。他对人生的独特见解,也帮助涡镇人确立了对于生命的正确态度。因此,僧与道,死与生,冷与热,在小说中辩证地存在着,贾平凹借此突出了一种神话结构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存在,它是从现实的土地上生发的,但却指向了人类最为关注的生死问题。130庙与安仁堂,成为涡镇日常生活漫流中人们心向往之的神圣场所,它是从日常生活的肌理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与外在生活现实存在天然的契合关系,因此不像一般的宗教场所那样对周围的空间产生管制与约束。宽展师父与陈先生,虽皆是出世之人,但又心怀入世之心,以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接应、点化、引导着涡镇人走向一种人生的通达之境,因此他们的形象又超越了一般的僧、道形象设置,从而具有了更为浓厚的世俗意义。
中国神话系统中的九天玄女与城隍,虽然与僧道一样同属于“社会神”的范畴,但却具有了更强烈的民间特质。原始神话、宗教仪式、民间信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诸神并存”的独特现象。虽地位有异,但在涡镇这样一个前现代社会中,诸多神灵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且共同构成了涡镇的文化结构,进而促成《山本》神话空间的建构。涡镇中不仅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自然神祇,而且在秦岭的山林中,寺院、道观、土地庙、山神庙、城隍庙、九天玄女庙等共同存在,社会性神祇亦以多元面目呈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除了上文所说的僧与道,便是玄女与城隍,主人公陆菊人与井宗秀作为这些神祇的现实映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形成与僧道模式的同构关系。然而,随着井宗秀个人心性的趋恶,两对关系之间平衡的对位互照关系被打破,也使笼罩在涡镇之上的天地神人结构迅速崩塌。
陆菊人的“玄女”身份,在文本中可得到证明。首先,九天玄女庙见证了陆菊人对自己人生的发愿以及这种愿望的实现,二者之间存在“互渗”关系。另外,九天玄女作为中国神话中的术数之神与正义之神,屡屡扶危济弱,成为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原型。比如在《三遂平妖传》中,玄女助越伐吴,在《薛仁贵征东》中赐薛仁贵以宝物,在《水浒传》中授予宋江以兵法等等,皆是玄女以神力介入现实的叙事表现。《山本》中的陆菊人,被赋予了玄女的气质与神性。她体态雍容、为人正气、沉稳老练,更重要的是,她屡次在井宗秀遇到困难之时挺身而出,为其化解危难,而且劝导手握兵权的井宗秀爱惜生灵,救护生命。基于以上各种条件,把陆菊人当作“玄女”的现实化身当无异议。井宗秀“城隍”的称呼则是涡镇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当井宗秀把预备团驻地放在以前的城隍庙,涡镇人便自觉地将二者联系起来。“城隍是守护镇子的神,城隍庙里有石像的时候,石像是不敢不恭的,涡镇也就五谷丰登,生意兴隆。而现在没石像了,却驻进去了预备团,预备团原本可以驻别的地方,偏就驻进了城隍院,这都是天意,也活该井宗秀就是城隍转世”[9]148。涡镇人将生活的偶然性无限夸大成必然性的思维特点,客观上促成了另外一种神话结构的生成,即玄女与城隍对应的神话图式。这一神话图式要求神灵的对应者具有超出凡人的能力与品性,只有这样神话结构才能保持稳定,涡镇也才会处于持久的和平之中。但井宗秀从一开始就不明白“城隍”之于涡镇的意义,而是将城隍当作权力的符号,预备团存在的意义也不再是保境安民,而是攫取更大权力的工具。因此,神话结构的失衡与神话空间的崩塌是必然的结果。驻扎在涡镇的预备团引来了更多的战争,涡镇的日常生活越发混乱无序,井宗秀与陆菊人亦呈现出反方向的人物发展态势。这种不和谐的情状直接导致了僧、道、玄女、城隍组成的神话结构的分崩离析,宽展师父杳无踪迹,井宗秀则直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涡镇的日常生活也在这种不和谐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僧、道、玄女、城隍组成的神话结构,经历了由诞生到覆灭的过程,这其中虽然存在因主体性格变异而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但从根本上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尽管在秦岭的褶皱里,仍存在千千万万个像涡镇一样的神话地域,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之中,这些地域皆经历了同样的命运。神话空间的存在,曾经庇护着涡镇人维持生命的原初形态,使他们在一种稳定的神话结构中生发敬畏之心,感受自然生命的韵律。但外来异质力量的侵入,以及这种力量对神话结构的改造,使传统神话从内部发生了变异,这也导致了日常生活史难以避免的断裂结局。
四、 两种“神话”的相遇:日常生活史的断裂
贾平凹借助神话对日常生活史的观照,其目的是“要创建一个可以作为过去记忆的技艺框架”,并“以此框架为基础来面对现在的真实”[15]。当下社会现实中日常生活呈现的僵硬特质,各个层面涌现出的诸多问题,以及信仰缺失的普遍、神话讲述的绝迹,均会使人追问这种现象发生的缘由。在这一前提下,历史的叙事者就会不由追问前现代社会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山本》即是对这一历史进行追问的文学式表达。在作家看来,历史形态的改易并非是因为重大事件的发生,那只会引起历史表面样貌的改变,最实质的变化往往发生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这是历史演进与变动的最根本源头。因此,贾平凹用贴近日常生活的叙事方式重返历史现场,并在日常生活的流动之中模拟了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神话与现代社会滋生的现代神话的相遇,并从中提炼出日常生活史断裂的逻辑。可以这样认为,与其说贾平凹写了一部关于神话的小说,不如说他以神话叙事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历史实验,他发现了传统神话在现代神话势力面前的困顿与危机,这导致传统神话开始走出日常生活史的舞台,重新回归到云遮雾障的历史深处。
现代神话与传统神话不同,它不再提供人想象自然的方式,而是表达人类现代意识与社会想象的中介,是人类历史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现代神话的发起者不再自觉地认同传统神话,而是在普遍认同传统神话内容虚幻性的同时,将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输入传统神话的形式之中,以服务于他们阐发观念并被大众认同的目的。现代神话的产生,立足于人类的现代社会情境,在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意义指向。在战乱频发的中国近现代历史阶段,现代神话与革命、权力相缠绕,在这一过程中,“‘革命’以对‘权力’的重新支配为前提,革命的目标从总体上就是发动革命的阶层攫取国家权力和集体权力,具体目标就是革命的领导者在权力的重新分配中获得个人权力”[16]。《山本》中,以“革命”为名实则攫取“权力”的诸多武装势力,勾画出笼罩在涡镇人头上的现代神话的恐怖面影。现代神话对传统神话的侵蚀与肢解,主要以压制、挤占乃至重构涡镇传统神话时空的方式而实现,这改变了涡镇日常生活的主体内容与表现方式,也使得传统神话被彻底驱离出日常生活史。
自然时间,即在四时循环、季节变换、昼夜交替、草木荣枯、时令节气的推移中自然生发的时间形式,它构成涡镇这一前现代社会中时间运行的主要方式,日常生活也正是在这一时间形式中得以和谐流动。自然时间的制约,导致了涡镇人与世间万物之间“互渗”的缓慢发生,这进而影响了涡镇人认识、理解自然世界与现实人生的角度。然而,现代革命对涡镇日常生活的侵入,却使共时性的自然时间在短时间内转变为历时性的历史时间,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以致完全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17]。历史时间的侵入,伴随着现代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的输入,使涡镇迅速被裹挟入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之中,迅捷、变动、秩序,开始成为涡镇日常生活的主要特征。
在短短十三年中,小小的涡镇被多方革命势力“光顾”,包括土匪五雷、国民党69旅的预备团、秦岭游击队、保安队、红十五军团等等。他们凭借历史时间的强大力量,轻易改变了涡镇的社会结构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程,同时也改变了涡镇人的生命形态。在传统神话笼罩中的涡镇,人们遵循的是生老病死的自然生命历程,但在现代神话到来之后,涡镇人的生命过程开始变得紊乱,死亡不仅变得频繁,而且难以避免。井掌柜、吴掌柜、岳掌柜、杨钟、杨掌柜……所有的涡镇人都脱离了自然时间的制约,以非正常死亡印证着历史时间的威力。现代革命明显加速了社会流动的进程,使得涡镇在丧失自有生命的同时,也迎来了更多的外部生命,土匪、士兵、难民不断涌进涡镇,但这并未平衡涡镇的生命,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战乱、兵变甚至瘟疫。随着现代革命的迅速展开,现代神话得到了广泛传播,但这却导致了涡镇越发严重的“异化”情境。传统神话视阈中的涡镇日常生活,遵循自然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演进形态的模仿。而在现代革命神话的催逼之下,涡镇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常常被战争的节奏打断。《山本》中四次重要的战事——消灭土匪五雷、攻打县保安队、银花河战役、红十五军团攻打涡镇,一次次地改变着涡镇的自然运行模式。如果说五雷被消灭之后宽展师父吹奏尺八发出的“惊悚的音响”是社会异化的预演,那么涡镇覆灭之前的社会情状,则是异化的直接呈现。小说借由陆菊人的视角看到了涡镇的芜杂与肮脏,“陆菊人从来没有感觉过街巷里竟这么多的破烂和垃圾。是没有打仗了,镇子里还没有打过仗,人们都在一起生活着,是邻居,是同族,是亲戚朋友,可谁又顾及了谁呢”[9]520。虽然人们依然挣扎着生存,但涡镇却再也不是之前那个涡镇了,它变成了“各种残骸瓦砾的不断聚集”,变成了“现代性生产的废弃物”[18]。短短的十三年,涡镇便面目全非了,在传统神话的庇护中,它可能曾经存在了上百年,上千年,但在现代神话面前,涡镇从一个曾经熙熙攘攘的桃源世界,变成了秦岭的一堆尘土。
在传统神话视阈下,涡镇的神话空间不仅包括由僧、道、玄女、城隍等社会性神祇组成的神话图式,而且包括带有神性意味的自然物象在涡镇中的布局,如坐落于涡镇正中央的老皂角树、涡镇城南的涡潭等等,它们不仅实存于涡镇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而且具有浓重的象征意义。由此,天、地、神、人组成的神话空间,成为涡镇现实生活空间的高级层次,也成为涡镇人日常生活的心理依托。当现代神话以革命的形式进入涡镇,其权力话语对既有的神话空间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前者深深嵌入到后者的空间系统之中,使其神圣意义被逐渐消解。正如陈晓明所说,“贾平凹的历史叙事还原了那些历史最初时刻的碰撞和嵌入建立起来的关系,到来的历史事件几乎强行把乡土中的人们卷入其中,它为中国激进现代性的曲折和艰巨埋下了漫长的伏笔”[19]。涡镇由生而灭的过程,成为现代性介入中国传统神话之重组与改造的历史寓言。
在现代革命势力进入涡镇之后,既有的传统神话空间呈现出被挤占与压制的态势,它们难以维持既有的神圣意义,而是被世俗化改造,成为承载现代性欲望与灾难的场所。宽展师父的居所130庙,被土匪五雷占据,他们在庙中分赃、杀戮,而井宗秀消灭五雷也正是在130庙中,曾经的佛家清净之地变得血迹斑斑;对于涡镇具有守护意义的城隍庙,在成为井宗秀预备团的驻扎地后,反而见证了地方势力不断壮大的过程,预备团非但不能保护涡镇,其发动的每次战争反而使更多的涡镇人失去生命,在涡镇人眼中具有神圣意味的城隍庙成为杀伐与死亡的象征,也成为井宗秀个人欲望不断扩张的象征;在涡镇人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老皂角树,通过掉皂荚的方式发挥其道德评判的作用,但正是这样一棵“神树”,却被挂上了一只人皮鼓,“老皂角树上从此不见任何鸟落过,没有了蝴蝶,也没有了蝙蝠,偶尔还在掉皂角荚,掉下来就掉下来,人用脚踢到一边去”[9]419,涡镇人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神性物象的敬畏之心,老皂角树最终选择自焚而死;涡潭本是以阴阳互转的形式象征着自然运行结构的稳定,代表着人类生命运转的自然结局,但现代神话却打破了这一自然秩序,涡潭被重塑为井宗秀等人毁尸灭迹的场所,等等。神话空间的存在,本是为了缓解涡镇人的心理焦虑与对不祥之物(如鬼)的恐惧心理,但在现代革命的权力话语对神话空间进行全面压制之后,涡镇中的“鬼”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怪事与异象开始在涡镇出现,老魏头讲的鬼故事也越来越多,涡镇从一个平和自然的小镇,演变为一个阴气森森的鬼蜮。在现代神话的干预下,涡镇的传统生活时空发生了质的变化,这象征着传统神话被驱离出涡镇日常生活史的结局。普通涡镇人的生活与信仰,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并在涡镇被毁灭的那一天消磨殆尽。
五、 结 语
在《山本》的后记中,贾平凹回忆他在完成小说之后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9]545。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细节,它可能是实指,也可能是作家创作理念的虚构化表现。当别的作家都沉浸于宏大历史的叙述中而难以自拔,贾平凹却躲在秦岭角落的一个小小涡镇中,用文字追忆神话由萌生到覆灭的过程。
神话视角的介入,使贾平凹既获得了一种历史观照的整体视野,也能使他进入到日常生活史的细节之中,神话的依托使日常生活变成了具有神秘特质与内在道德规定性的审美对象。然而,就像石狮会被风化一样,神话也会经历被侵蚀的危机,当涡镇的日常生活被卷入到现代神话的大潮之中,传统神话选择了退隐与潜伏。历史与神话的进退与纠缠,就这样在无数的涡镇里不断上演。关于这一主题的文学表现,在《山本》中获得了更为新鲜的表达。宏大的历史主题从来也不是历史的本真面目,历史也不会永远以激进的样貌呈现,只有在自然时间中缓缓流动的日常生活,才是每一个人正在经历的、也最真实的历史。在日常生活的漫流中发现神话,凭借神话的视角凝视历史,即是《山本》的深层次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