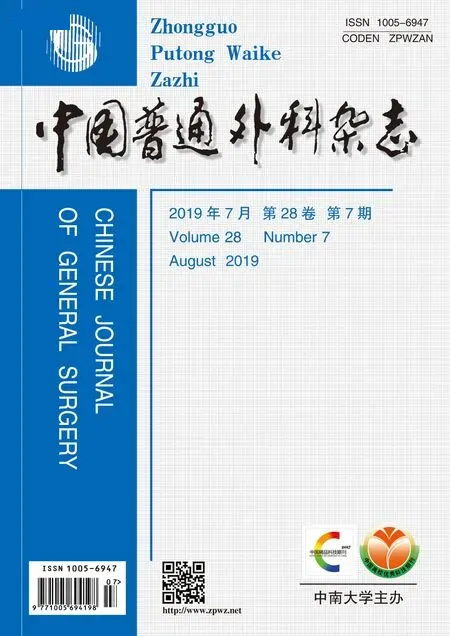《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解读
2019-01-06李民熊俊
李民,熊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肝胆外科,湖北 武汉 430022)
原发性肝癌是肝脏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018年11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最新数据表明在我国癌谱构成中,肝癌发病死亡趋势略有下降,但其发病率仍高居恶性肿瘤的第四位,肿瘤相关死亡位居第2位[1]。其中肝细胞癌占绝大部分,2011年卫生部发布了诊疗规范[2],在此基础上,卫计委医政管理局结合最新的循证学依据和我国的肝癌患者的特殊性,经过专家组的反复讨论和修订,于2017年7月发布了《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3]。最新数据表明肝细胞癌占原发性肝癌的85%~90%以上,故本文将围绕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的诊疗为中心,重点解读该规范的诊疗要点和更新。
1 筛查和诊断
1.1 高危人群的监测筛查
肝癌疗效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故本规范仍然推荐肝癌高危人群早期筛查,譬如乙型肝炎病毒和(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长期酗酒、非酒精脂肪性肝炎、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食物、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和有肝癌家族史等人群。尤其是年龄大于40岁的男性高危人群。主要手段仍是血清甲胎蛋白(AFP)联合肝脏超声检查,推荐高危人群每隔6个月进行至少1次检查。基于欧美国家肝癌多以丙型肝炎、酒精和代谢性因素为致病因素,在其人群中AFP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不高,故欧洲肝脏病学会更新指南仍仅推荐每6个月进行1次腹部超声检查[4]。但具有类似高危因素的日本,则推荐伴有肝硬化的乙型肝炎病毒和(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高危人群,每隔3~4个月需进行超声检查联合AFP、甲胎蛋白异质体(AFP L-3)和异常凝血酶原(desgamncarboxyprothrombin,DCP,又称PIVKA-II)3项血清分子标记物筛查,每隔6~12个月行CT或MRI检查[5]。因此,高危人群的监测筛查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合我国国情的方案。
1.2 影像学检查
各种影像学检查各有优劣,推荐综合应用、优势互补、全面评估。超声检查是临床最常用的肝脏影像学检查方法,尤其是在早期筛查具有无创、简便等优势。X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检查常应用于肝癌的临床诊断和分期,还可用于肝癌局部治疗的疗效评价,尤其对经肝动脉化疗栓塞后碘油沉积效果评价具有优势。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在检出和诊断小肝癌方面总体略优于CT检查,尤其是肝细胞特异性对比剂(Gd-EOBDTPA)普美显对直径≤1.0 cm肝癌的检出率和对肝癌诊断和鉴别诊断有显著优势。近年来,随着三维可视化技术的发展,借助CT和(或)MRI图像数据,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进行分析和重建等手段,实现了二维诊治模式向三维可视化图像或三维可视化物理模型的转变[6-7]。该技术弥补了传统二维图像的依靠外科医师个人经验的抽象重构缺点,可更直观、更精准、更快捷地呈现出三维立体构象。其优势在于:⑴ 肝脏、肿瘤病灶、血管、胆管等重要解剖的立体重现,明确肝脏分段、瘤灶特征、血管走行与变异等,以达到精细个体化评估之目的;⑵ 明确肿瘤灶与重要脉管关系,术前规划手术入路和模拟切除,譬如评估切除肝段范围、手术断面脉管模拟预处理,以达到精准肝切除之目标;⑶ 个体化肝体积计算,可准确评估肿瘤体积、标准肝体积和剩余肝体积,尤其是大范围肝切除、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等复杂手术的残肝体积评估,以达到精确手术风险评估之目的。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是一种侵入式创伤性检查,多用于肝癌局部治疗或急性肝癌破裂出血治疗。核医学影像学检查在肝癌的诊断中非常规使用,在通过1次检查而全面评价淋巴结及远处器官转移的方面有一定临床价值。
鉴于肝穿刺活检有着出血和针道种植的风险,已明确建议具有典型肝癌影像学特征的患者,不需要以诊断目的的穿刺活检。而缺乏典型影像学特征的患者,可采用穿刺活检获得病理学依据,但注意出血倾向、重要脏器严重疾患和全身衰竭的患者,应慎用该手段。并明确指出,穿刺路径应经过正常肝组织,避免以上风险,同时推荐在肿瘤和肿瘤旁肝组织分别穿刺1条组织,提高诊断准确性。
1.3 血清学分子标记物
肝癌当前最常用且重要的分子标记物仍然是血清AFP,其他标记物的参考价值有限。在2011版基础上,该规范已摒除了AFP升高水平的持续时间。但是,AFP需要结合有无高危因素、影像学检查,不可依靠该单一指标得出诊断。在排除慢性或活动性肝炎、肝硬化、睾丸或卵巢胚胎源性肿瘤及妊娠者,AFP≥400 µg/L时则高度提示肝癌。由于30%肝癌患者AFP水平正常,故AFP阴性时亦不能排除肝癌,需检测AFP L-3,其对肝癌的特异度高于AFP,有助于提高诊断率。当AFP低度升高患者,应动态监测并结合肝功能变化,以排除上述引起AFP升高的病因和影像学不可见的早期肝癌。此外,由于肝癌细胞不能正常合成凝血酶原前体,该前体羧化不足,故肝癌患者大量生成的DCP亦有助于肝癌诊断[8]。
1.4 临床诊断和病理学诊断
肝癌的临床诊断需依据有无高危因素,譬如乙型或丙型肝炎以及肝硬化、AFP水平,尤其是影像学检查至关重要。若具有典型的影像学检查,结合其他指标即可明确诊断,反之不具有典型影像学特征者,则需结合多种影像学检查手段或者借助肝穿刺活检,抑或密切随访AFP水平和影像学检查(具体诊断标准和路线图详见规范附录4)[3]。
肝癌的最终诊断需依据病理学检查结果,组织来源可是肝脏占位病灶、肝外转移灶活检或手术切除组织标本,经病理组织学和(或)细胞学检查明确病灶性质和肿瘤来源。2017版在病理学诊断方面制定了全面、规范的标准,尤为重要的是根据肿瘤生物学行为特点,制定了“7点”基线取材法,病理结果除了旧版规范中关注内容外,还增加了评估肝癌复发风险和选择治疗方案的参考指标。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是指在显微镜下于内皮细胞衬覆的脉管内见到癌细胞巢团,以含有膜内血管的门静脉分支为主。该指标对肝癌的规范化诊疗至关重要,推荐作为常规病理检查指标。根据结果分为3级:M0:未发现MVI;M1:≤5个MVI,且发生于近癌旁肝组织(距肿瘤边缘≤1 cm),为低危;M2:近癌旁肝组织>5个MVI,或MVI发生于远癌旁肝组织(距肿瘤边缘≥1 cm),为高危。
2 分 期
肝癌的分期是预后评估的重要手段,也是选择合理治疗方案的基础。结合近年来国内外肝癌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在2011版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定了更适合我国国情的临床分期。该分期主要纳入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提出的功能状态评分(ECOG PS)、肝功能评估、有无肝外转移、有无血管侵犯、肿瘤数目和大小,可分为Ia期、Ib期、IIa期、IIb期、IIIa期、IIIb期和IV期(详见规范附录5)[3]。其中,当肝癌患者ECOG评分3~4分,或者0~2分但肝功能Child-Pugh C级时,无论肿瘤单发还是多发,瘤灶直径有多大,则均为IV期,无法耐受积极抗肿瘤治疗。
3 治 疗
3.1 肝切除术
肝切除术是肝癌治疗的重要手段,该规范将Ia期、Ib期、IIa期和部分IIb期、IIIa期患者纳入手术适应证,但手术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安全性和彻底性。手术安全性包含患者全身情况评价和术前肝功能储备评估,前者采用ECOG PS评估患者一般情况,后者主要依据患者肝功能储备评价和残余肝体积计算,即需满足以下两个必要条件:⑴ Child-Pugh A级和ICG R15<20%~30%;⑵ 剩余肝脏体积需占标准肝体积的40%以上(伴有肝硬化)或30%以上(不伴有肝硬化)。手术彻底性即根治切除,在本规范中摒弃了2011版中的姑息性切除手术,并明确了根治性切除标准:⑴ 术中判断标准:肝静脉、门静脉、胆管及下腔静脉未见肉眼癌栓;无邻近脏器侵犯,无肝门淋巴结或远处转移;肝脏切缘距肿瘤边界>1 cm,若切缘<1 cm,但切除肝断面组织学检查无肿瘤细胞残留,即切缘阴性。⑵ 术后判断标准:术后2个月行超声、CT、MRI其中两项检查,未发现肿瘤病灶;术前AFP升高者,术后2个月AFP定量测定,其水平应降至正常范围(极少数超过2个月)。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和推广,腹腔镜手术适应证较前扩大,尤其是已熟练掌握出入肝血流控制技术、肝离断技术和止血技术的单位,推荐开展Couinaud II、III、IVb、V、VI段且瘤灶不超过10 cm,但病灶不累及第一、第二肝门结构;已有丰富腹腔镜经验的单位可开展复杂的半肝切除、肝三叶切除和Couinaud I、VII、VIII段肝切除。此外,有条件的单位可开展机器人辅助微创肝切除术。当剩余肝体积不足时可发生术后肝功能衰竭或者小肝综合征,风险极大。本规范推荐可采用术前TACE缩小瘤灶后再切除,或者经门静脉栓塞或门静脉结扎以代偿性增加残余肝体积,提高可切除性。除上述方案以外,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是Schnitzbauer等[9]于2012年提出的分期切除肝肿瘤的手术方案,为大范围肝切除而残肝不足(残余肝体积占标准肝体积<30%~40%)的高风险患者提供新的治疗策略。随着国内外多家单位的探索和临床实践[10],证实了ALPPS在大范围肝切除治疗肝癌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即通过I期肝脏分隔或离断和患侧门静脉分支结扎后,待健侧剩余肝体积代偿增生后再II期切除患侧肝脏。本规范也首次推荐可作为大范围根治性肝切除的选择方案之一,但需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尤其需考虑肝硬化程度对健侧肝脏增生影响、患者身体能否耐受两次手术创伤、肿瘤进展可能性等。
3.2 肝移植
肝移植也是肝癌根治性治疗手段之一,尤其是伴有失代偿肝硬化背景、不适合切除的小肝癌患者。目前国内多家单位也制定了手术标准,但规范仍推荐采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即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6.5 cm;多发肿瘤数目≤3个、最大直径≤4.5 cm、总的肿瘤直径≤8 cm;不伴有血管及淋巴结的侵犯。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是预后不良的主要因素,与移植前肿瘤进展程度、有无血管侵犯和AFP水平等密切相关,但术后降低早期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的用量和采用mTOR抑制剂的免疫抑制方案可能降低肿瘤复发,提高生存率。
3.3 局部消融治疗
局部消融治疗是无法耐受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获得根治处理的重要手段,其借助超声、CT或MRI引导下对肿瘤靶向定位,采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对肿瘤杀灭。根治性局部消融的适应证:单个肿瘤直径≤5 cm;或肿瘤结节不超过3个,最大肿瘤直径≤3 cm;无血管、胆管和邻近器官侵犯及远处转移,肝功能Child A级或B级。而不能手术切除的直径为3~7 cm的单发或多发肿瘤,可采用局部消融联合TACE。对于直径≤3 cm瘤灶,热消融可达到根治目标,但有证据表明无瘤生存率稍逊于手术切除。随着多项临床前瞻性对照和系统回顾性研究证实,本规范明确推荐直径≤5 cm的肝癌若患者能耐受肝切除术,以及位置表浅或者位于肝脏边缘,应首选手术切除,局部消融可作为手术切除之外的另一种治疗方案。
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和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MWA)均可以灭活肿瘤病灶并尽量减少正常肝组织损伤,且疗效、并发症和远期生存无显著差异,但后者“热沉效应”更小,消融效率更高。无水乙醇注射治疗(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PEI)相较于前两种方案,更适合于癌灶贴近肝门、胆囊及胃肠道组织,但瘤灶≤3 cm的患者术后复发率高于热消融,而直径≤2 cm的瘤灶经PEI处理消融效果确切。
有别于手术切除术后2个月复查影像学检查,局部消融治疗术后疗效评价推荐消融后1个月,复查肝脏动态增强CT或MRI,或超声造影:动脉期无强化为完全消融,而肿瘤灶内有强化则提示肿瘤残留,即不完全消融。肿瘤残留患者建议可再次消融治疗,若两次消融后仍有肿瘤残留则需寻求其他治疗手段。
3.4 TACE治疗
TACE是目前最常用的肝癌非手术治疗方法之一,适用于IIb期、IIIa期和IIIb期的部分患者,且肝功能Child A级或B级,ECOG评分0~2分,抑或其他原因,如可手术切除但拒绝手术方案;多发结节性肝癌;肝癌破裂出血;手术切除术后复发等。本规范中新增肾功能禁忌证:肌酐>2 mg/dL或者肌酐清除率<30 mL/min。规范推荐综合TACE治疗,即TACE联合其他治疗方法,其目的在于控制肿瘤、提高患者生活治疗和延长带瘤生存时间。
3.5 放射治疗
外放射治疗对于伴有门静脉/下腔静脉癌栓或肝外转移的IIIa期、IIIb期患者行姑息处理,部分患者可出现肿瘤缩小或降期,可获得手术切除机会;肝外转移患者经外放射治疗,延缓肿瘤进展;对于中央型肝癌手术切缘≤1 cm可辅以放疗降低复发。此外,放射性粒子可经组织间、门静脉、下腔静脉和胆道内植入,持续低剂量辐射,治疗肝内病灶、门静脉癌栓、下腔静脉癌栓和胆管内癌或癌栓,即内放射治疗,也是局部治疗肝癌的有效方法。
3.6 全身治疗
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晚期肝癌患者,若无禁忌证建议全身治疗减轻肿瘤负荷,延长生存时间。推荐一线治疗方案为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和系统化疗含奥沙利铂的FOLFOX4方案。其他如三氧化二砷、免疫治疗、中医药等也有一定抗肿瘤作用,还有待深入大规模临床研究。此外,抗病毒治疗尤其重要,可降低术后肿瘤复发率,故抗病毒治疗应贯穿肝癌治疗全程。而规范未明确推荐行根治性肝癌切除术后患者需行分子靶向治疗或系统化疗,但是术后需要接受密切随访,一旦出现肿瘤复发,则根据复发特性选择治疗方案,如再次手术切除、局部消融、TACE、放疗或系统化疗。晚期肝癌患者还应加强对症支持治疗和心理干预,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