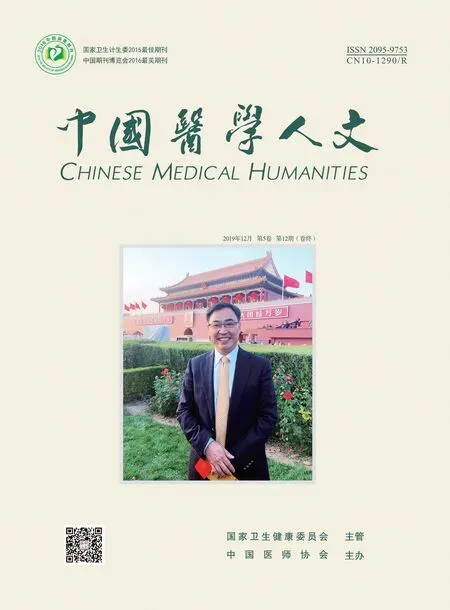论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对敦煌中医药文献的影响
2019-01-04梁永林赵志伟田永衍2
文/王 凝 梁永林 赵志伟 田永衍2,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精华,敦煌中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部分,在敦煌中医药学理论发展和临床实践中处处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观在敦煌中医药诊法文献中主要体现在关于平人脉息关系与四时平脉的论述方面;在敦煌中医药本草医方文献中主要体现在天地之象与人之生理病理之象的类比、四时加减用药法等方面;在敦煌中医药明堂经脉文献中主要体现在关于人神禁忌的论述方面的论述上。
关键字 天人合一 敦煌 中医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主要命题之一,从先秦两汉以来对我国的哲学体系甚至各个领域和学科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具体内涵从春秋战国到两宋以来发生了数次变革和发展,历来亦有所争议,但其基本内涵则为大家所公认,即:天地自然是大宇宙,人则是一个小宇宙,人与天地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一切人事均应顺乎天地自然规律,达到人与天地自然相和谐。这点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系统建构和学术发展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如中医经典《素问·咳论》所谓:“人与天地相参”、《灵枢·邪客》之“人与天地相应”以及《灵枢·岁露论》之“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敦煌中医药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分支,是唐五代时期传统医学在敦煌地区的独特呈现。与传统医学一样,敦煌中医药学也深受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其理论与实践中亦处处可见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子。兹就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在敦煌中医药学中的体现略做探讨。
“天人合一”观在敦煌中医药诊法文献中的体现
敦煌文献P.2115《平脉略例》云:“平人一日一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脉并有行五十周于身。”P.3477《玄感脉经》亦云:“人一日一夜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于身。”意为健康的人一昼夜的呼吸次数为一万三千五百次,脉气在人身运行五十周。据《敦煌医粹》1言:“古人计算脉搏至数与今人相同,即一呼脉动两次,一吸脉动两次,呼吸定息,脉动四至五次。以今人平均脉搏每分钟72次计算,则每分钟呼吸次数为18次左右,一昼夜呼吸总次数为18×60×24=25920(息)。它几乎是一万三千五百息的两倍,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尚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确,从现代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正常成人平静状态下呼吸频率约为每分钟16~20次,平均18次左右,一昼夜呼吸总次数为25920 左右,P.2115与P.3477“平人一日一夜一万三千五百息”之说似乎颇为荒谬。
但如果我们还原《平脉略例》与《玄感脉经》此论的思维与逻辑,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如前所述,“天人合一”观既是先秦以来中国传统的思维观念,也是中医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正如《素问·离合真邪论篇》所说:“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圣人所作之度数上应天之星宿数、地之经水、人之十二经脉,可见,星宿数、经脉数之度量和对应与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而这一哲学思维在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中则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的医学思维模式。
《内经》认为,天有二十八宿,人之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亦有二十八条(十二正经左右各一,计24条。跷脉左右各一,任、督脉各一,共计28条),以应二十八宿。《灵枢·五十营》即言:“天周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以应二十八宿。”人之二十八脉总长度为十六丈二尺,《灵枢·脉度》:“手之六阳,从手至头,长五尺,五六三丈……跷脉从足至目……合一丈五尺。督脉、任脉……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气之大经隧也。”而“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一吸,脉亦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灵枢·五十营》),环行二十八脉一周共需270息(16丈2尺÷6寸=270息),一昼夜气在人体行50周,故平人一日一夜13500息(270×50=13500)。故《灵枢·五十营》曰:“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营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尽脉终矣。”故《平脉略例》与《玄感脉经》“平人一日一夜一万三千五百息”之论非源自实测,而是基于“天人相应”哲学思维基础上的数术推论。这种以气论为基础、数术为模型、类比为基本方式代替精细实测的推衍方式或许在今人看来不可想象,但是脉学产生的背景恰恰发生在数术天学空前发达的时代2,数术天学亦恰为脉学从经验论向体系化、系统化过度的关键凭借,而数术天学的核心要求即为天、地、人的相参、对应与和合。因此,上述这种脉学之算法恰恰为“天人合一”思想在敦煌医学理论体系上的深刻显现。
此外,P.3287《三部九候论》曰:“上部天,两额动脉;上部地,两颊动脉;上部人,耳前动脉……三部者,天地人也。九候者,部各有上、中、下,故名九也。”以天地人类比人体上中下三部动脉。P.3287《不知名氏辨脉法二》曰:“正月、二月、三月,春木王,肝气当位,其脉弦细如长,名曰平脉。微弦长者,胆之平脉。反此者,是病脉也。四月、五月、六月,夏火王,心气当位,其脉洪大如散,名曰平脉。微洪散者,小肠之平脉。反此者,是病脉。土无正位,寄王四季(三月得十八日,六月十八日,九月十八日,十二月十八日),脾气当位,其脉大阿阿然如缓者,名曰平脉。微阿阿然缓者,胃之平脉。反此,是病脉也。七月、八月、九月,秋金王,肺气当位,其脉浮涩如短,名曰平脉。微浮短者,大肠之平脉。反此者,是病脉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冬水王,肾气当位,其脉沉软如滑,名曰平脉。微沉滑者,膀胱之平脉。反此者,是病脉也。”此段以人之脉象应阴阳、四时、五脏、五行,指出人之正常脉象会随四时气候变化发生相应变化,并以脏腑表里配属论述了这种四时平脉脉象。这一庞杂而系统的配属理论体系之建构实受中国古代早期的天道数术深刻影响,同东汉郑玄所著纬书《易纬通卦验》:“十二月、十二日、政八风、二十四气其相应之验犹影响之应人动作言语也”3将十二脉变动与八风、二十四节气紧密结合在一起论述以及隋人杨上善《太素·经脉正别》“人之合于天道”之论一样4,敦煌卷子《三部九候论》《不知名氏辨脉法二》上述所论正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医药诊法学的体现。
“天人合一”观在敦煌中医药本草医方文献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观在敦煌本草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在对药物分类的阐述上。最早的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对药物的分类是采用上、中、下三品与天、人、地相应的分类法:“上药一百廿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一百廿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一百廿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药应天、人、地,攻补有别、功效有自。敦煌文献“龙·530”《本草经集注·序录》中陶弘景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用和厚,不为仓卒之效,然而岁月将服,必获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应天”“中品药性,治病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于服之者,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人怀性情,故云应人”“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恒服,疾愈则止,地体收煞,故云应地。”清代医家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有言:“百物与人殊体,而人借以养生却病者,何也?盖天地亦物耳,唯其形体至大,则不能无生。其生人也得其纯,其生动物也得其杂,其生植物也得其偏。……圣人知其然也,思救人必先知物。”5圣人知物之原、用其性而救民疾,这均基于上古先民对天、地、人、万物的深刻认识与观察,以天、地、人的和合与相应为前提。
在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方面,P.2115《张仲景五脏论》曰:“天有五星,地有五岳,运有五行,人有五脏。”“天地之内,人最为贵,头圆法天,足方法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七星,人有七孔;天有八风,人有八节;天有十二时,人有十二经脉;天有二十四气,人有二十四俞;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骨节”这段详细的罗列出了天和人在数值上的对应与配属,正所谓“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稷之男女”,以天度人、以人象天,着重强调天人之间的相应与和合。又云:“天有昼夜,人有睡眠;天有雷电,人有嗔怒;天有日月,人有眼目;地有泉水,人有血脉;地有九洲,人有九窍;地有山石,人有骨齿;地有草木,人有毛发;四大五荫,假合成身,一大不调,百病俱起。”通过天地之象与人之常象的比对,说明人体之生理现象应于天地,反复证明人与天之间的相象与和合,认为人体脏腑组织器官、人体生理活动都与天地间事物和现象相互通应。
在医方治疗方面,敦煌医药文献P.3378中的三黄丸,特别强调随时令的不同而调整方中药物的剂量比例,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三黄丸方。疗男子五劳七伤,消渴脱肉,妇人带下,手足寒热。春三月,黄芩四两、大黄四两、黄连四两;秋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一两、黄连七两;冬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二两、黄连三两。凡三物,随时令捣筛,白蜜和丸”。春天为万物生发之时,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等量用此三药清中焦之火热,使人体气机得以顺畅生发,从而以适应春之生发;秋三月,天气收敛肃降,因此以黄芩六两、黄连七两以走心肺,清夏来之余火、平将降之肺火以应乎时节;冬三月,天气闭藏,阴盛阳衰,不能使阳气受扰,故以黄芩六两清肺胃蕴热、黄连二两清心火、大黄二两通降腑热以防外寒引发冬瘟之,此种密切关乎四时天气、五脏变化以随季节用药治病方法深刻体现了“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辩证思维和古代哲学观。
“天人合一”观在敦煌中医药明堂经脉文献中的体现
敦煌医药文献P.3655《明堂五脏论》说:“按《玉匮针经》所说:人之血脉,状如江河绕身,长流不注。春三月,一日一夜流转二百四十遭;夏三月,一日一夜流转一百八十遭;秋三月,一日一夜流转一百二十遭;冬三月,一日一夜流转六十遭。□□减一遭,是寒即注冷,是热即注风。”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敦煌遗书提倡适应四时阴阳以保存精气的养生之道,重视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的影响,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说:“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生则病”,从而确立了结合天时地理、形气阴阳进行诊察的方法和辨证施治的根本治疗原则。
“天人合一”观在敦煌中医药经脉针灸文献中则集中体现在人神禁忌方面,敦煌医药文献S.5737《灸经明堂》、P.2675《新集备急灸经》、P.3247《人神禁忌》中都有大量关于人神禁忌的记载。人神禁忌属于古代针灸宜忌的一种,关于“人神”,学者马继兴在《敦煌古医籍考释》把《人神禁忌》称为《人神流注》,这无疑能帮助我们更为深刻的理解“人神”,特别是“流注”二字使得人神这一针灸宜忌更有科学道理,“流”是流动,“注”是灌注,《诗经》有云:“如川之流,丰水东注”、《针灸大全》亦云:“流者往也,注者住也”,“人神流注”就是指人体气血最宝贵的物质在经脉中循行,营养全身,似水流般的流行灌注,使人体各部的功能活动得以平衡协调,一旦违背“人神流注”规律,就会造成不良后果6。这与《内经》中的“人气”理论不谋而合,《灵枢·阴阳系日月第四十一》有云:“正月二月三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阳……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左,无刺左足之阴”,明确指出禁刺人气所在部位,且在《内经》中所述人体生理、病理、诊治方面均与气血有关,《素问·调经论篇》:“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素问·调经论篇》:“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灵枢·刺节真邪篇》:“用针之类,在于调气”,这与人神禁忌关键性概念基本一致。而最早将“人神”“人气”作为禁止灸刺的原因论述的《黄帝虾蟆经》中也提到:“月生一日,虾蟆生头喙,人气在足小阴,至足心不可灸伤之,使人阴气不长,血气解禁泄利。女子绝产生门塞。同神”,言明人气与人神处于同一位置。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人神”其实就是指人体气血,人神禁忌即为在特定的时间气血在人体特定的部位消长,以使人体各部的功能活动得以协调和平衡,在治疗过程中要避免针灸这一部位,以免破坏气血的消长及人体的平衡。这种“人神流注”必然受到自然界气候变化及时间变化之影响,是“天人合一”思想在针灸中的具体体现。人神禁忌的内容包括逐年人神禁忌、逐日人神禁忌、十二支人神禁忌、十干人神禁忌、十二时人神禁忌等。例如敦煌医书P.2675《新集备急灸经》中有载:“月,一日人神在足大指,二日在外踝……三十日在关元下至足心。”7意指每月三十日中,每日都有“人神所在”,而“人神所在不宜针灸”《外台秘要》也有告诫:“右件人神所在,上件日并不宜灸”。人体从早到晚,从初一到三十,随着昼夜交替、时日的变化,经络之腧穴会出现周期性盛衰开合,开时气血旺盛,合时气血就衰,从而施之针灸以补泻宣通,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若违背了“人神禁忌”,灸刺损伤“人神”就会令人“阴阳结绝”“脉绝不通”“令人鬲”“血脉逆乱”“发热”“发痈”“伤精气”等严重危害。相反,我们如果能够掌握“人神流注”的规律和特点,并从“天人合一”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念出发,在灸刺时知晓“月晦、朔日、蚀主、黄天、人神、阴阳、经络”,牢记“凡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上下朔望,阴阳之道”,且“大雨大风,日月无光,人气大乱,阴阳乖和”之时不灸刺,就能取得佳效。这足以显见古人对“人神禁忌”的重视程度,也使我们感受到敦煌针灸遗书所倡导的良好的医德医风。
人神禁忌作为古代一种针灸宜忌,可溯及早期的医学文献,在《内经》《黄帝虾蟆经》中都有类似记载,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及《外台秘要》中更有较详的论述。敦煌中医药文献中就保留了大量关于人神禁忌的记载,前文已有论述,这些人神禁忌大都在医学体系中传承与发展,内容基本与医学典籍相似,但不乏有异处,王方晗就《新集备急灸经》中出现的人神禁忌与传统医经中的记载相比较,发现以P.2675为代表的敦煌医学文献中的人神禁忌虽存在着简化、普及性及其他独特属性,但所涉及的禁忌方式都可以追溯至早期的医学经典中,说明人神禁忌建构于中国古代医学8。除此之外,在敦煌医学文献中记载的人神禁忌还出现了与民间信仰、习俗相结合的新的特点,即人神禁忌出现了民间信仰化。
这种“民间特色”主要体现在《新集备急灸经》“五暮日”“月厌”“六厌日”等以及以 “具注历”为载体的人神禁忌中。例如《新集备急灸经》:“凡人不用五暮日,得病十死一生,难差”,有关古籍文献中并无五暮日之记载说明,《敦煌中医药全书》将其解释为“五脏忌日”,在此时段人们应该避免患病或者治疗疾病,这可能与受到民间择日术的影响有关。“厌,癸酉、癸未、癸巳、癸丑、癸亥、癸卯,此六日厌吉”,此为人神禁忌中的六厌日,“厌”通“压”,有压制、压抑之意,可引申为镇压妖邪迷信或压制黄道吉日,六厌日即为癸酉、癸未等六日“压吉”的日子,在此时间也忌患病或治病,这明显也是源于择日术等数术类内容。此外还有涉及“月厌”的人神禁忌,“正月戌,二月酉,三月申,四月未,五月午,六月巳,七月辰,八月卯,九月寅,十月丑,十一月子,十二月亥”,月厌来源于建除,“建除”同为我国古代的一种择日术,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被称为建除十二神,将十二神与十二地支相配,不同神煞值日各有其行事宜忌,可据此趋吉避凶9,这也说明人神的禁忌方式并非完全源于医学典籍,而是托生于占卜、选择术等民间传统8。除P.2675以外,还有来源于《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的P.3247《人神日忌》,其内容只保留了逐日人神,且人神停留位置与《新集备急灸经》基本一致,也就是说具注历中的人神禁忌延续了医经,但出现了简化,人神禁忌被大幅简化这一特点表明其就实际使用性而言与医学传统渐行渐远,而与其他阴阳五行的吉凶选择并置也证实人神禁忌由医学转入民间9。
小 结
“天人合一”观是我国古代传统哲学的核心观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积极推动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敦煌中医药学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一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吸收了“天人合一”观所带来的学术成果,在诊法文献中脉学之算法的思维与逻辑,人之平脉脉象依四时变化的过程,在本草医方文献中的药物分类、人体生理病理及治疗方面,在经脉针灸文献中的针灸治疗及人神禁忌等方面皆处处渗透着“天人合一”观的思想,这种哲学思考方式能使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传统医学,并能更好的发展传统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