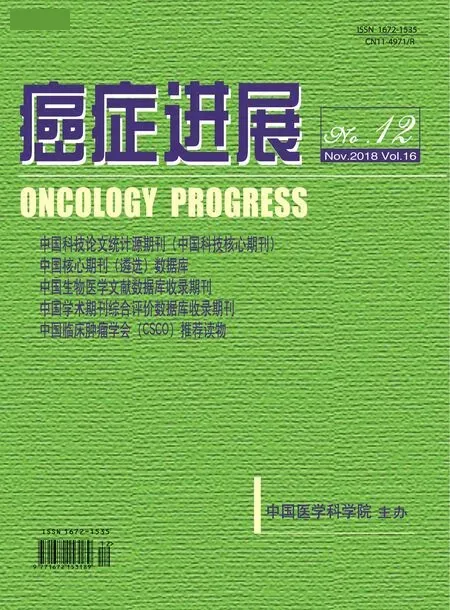氯胺酮在癌痛治疗中的潜在作用研究进展
2018-12-31王喜繁王立萍王玉吴晓红韩非
王喜繁,王立萍,王玉,吴晓红,韩非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麻醉科,哈尔滨1500810
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达429万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20%,死亡281万例"[1].相当于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平均每分钟约有7人确诊癌症.每年全世界有超过1000万人被诊断患有癌症,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500万[2].疼痛是癌症患者的常见症状,据报道,癌痛在抗癌治疗期间发生率为55%,晚期、转移性或终末期癌症患者发生率为66%,所有患者中38%~56%有中重度疼痛[3].癌痛可以是伤害感受性(躯体或内脏)、神经病理性或混合型[4].癌症相关疼痛的原因是多因素的,并且取决于癌症的类型、阶段、转移部位、并存疾病和心理因素等情况[5-6],肿瘤局部破坏和质量效应、治疗(手术、化疗或放疗)和偶发原因(如骨关节炎)均易导致癌症相关疼痛[7].抑郁症在癌症中具有双重关联性,这可能会使疼痛的管理复杂化[8].世界卫生组织起草了关于癌痛治疗的三阶梯疗法:非阿片类药物、弱阿片类药物(用于轻度至中度疼痛的止痛剂)和强阿片类药物(用于中度至重度疼痛的止痛剂),当非阿片类药物治疗失败或不充分时,可用阿片类药物来治疗癌痛[9].患有晚期癌症的患者由于非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或疗效不佳,往往需要在治疗6个月内使用阿片类药物[10].现有证据表明,95%以上服用阿片类药物的患者能耐受中度或重度疼痛[11],接受阿片类药物治疗的人群中有10%~20%的不良事件是需要治疗的.例如,服药可能会影响日常活动,日常生活的有效参与和生活质量会下降.而且,即使使用高剂量阿片类药物,在阿片类药物无反应或耐受的情况下,疼痛仍然不受控制.阿片类药物还会导致多种不良反应,如便秘、恶心、呕吐、呼吸抑制、过度镇静、尿潴留和瘙痒[12],其他不良反应包括耐受性降低、痛觉过敏、性腺功能减退、依赖甚至成瘾[13-15].氯胺酮作为临床常见镇痛药,已经广泛应用于癌痛的治疗.近些年,也有研究结果表明氯胺酮能够诱导肿瘤细胞死亡,并且提高正常细胞的生物活性[16-17].
1 氯胺酮简介
氯胺酮是一种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选择性拮抗药,通过阻断受体相关的离子通道,拮抗谷氨酸受体亚家族的NMDAR[18],作为麻醉药的药理基础是选择性地阻断皮层联络系统和丘脑-皮层系统,临床出现痛觉消失而意识可能部分存在的分离麻醉状态[19-21].其镇痛作用可单独用于成年人外科手术、诱导麻醉及癌痛的治疗[18,22].此外,临床对照试验和荟萃分析的结果表明氯胺酮具有明显的抗抑郁作用,低于麻醉剂量的氯胺酮经静脉或口服给药可以快速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心理和自杀倾向[23-24].
2 氯胺酮的药效动力学
氯胺酮的镇痛机制一方面通过对脊髓和更高级的中枢神经系统NMDAR的药理阻断而实现[25],另一方面通过与阿片受体的相互作用而实现[26].有研究显示,吗啡联合低剂量氯胺酮可以获得更优的镇痛效果[27].在抗抑郁方面,氯胺酮可以通过阻断抑制性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神经元的NMDAR,实现谷氨酸能神经元的去抑制,产生谷氨酸爆发,最终促进突触蛋白合成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释放而产生抗抑郁作用[28].值得注意的是,氯胺酮的快速抗抑郁效果并不是所有NMDAR拮抗药的共性,而是氯胺酮独有的[18].
3 氯胺酮的药代动力学
静脉给药时,单剂量氯胺酮起效快,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在30 s内发挥作用,分布半衰期为10 min,消除半衰期为2.0~3.0 h;肌内注射5~15 min血浆浓度达峰值,作用时间为0.5~2.0 h;口服30 min血浆浓度达峰值,作用时间为4.0~6.0 h[29-30].由于广泛的肝首过消除,氯胺酮的口服生物利用度相对较差.相反,有研究发现,鼻内使用氯胺酮的生物利用度为50%[31].从分布的角度看,氯胺酮具有高脂溶性和广泛分布的特点,能迅速穿过血脑屏障,而在肝脏清除率较高[32].
4 氯胺酮的临床安全性
癌痛管理很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终末期阶段.多种途径会介导癌痛,包括伤害性、神经病理性和中枢性,并且目前的药物在解决这些途径方面有限而且具有显著的不良反应.根据其作用机制和不良反应等特点,氯胺酮已经在许多不同的试验中得到评估.本文主要从氯胺酮不同的给药途径来说明其临床安全性.
4.1 静脉给药
2014年的一项病例报告指出,一例乳腺癌转移的患者开始以0.2 mg(/kg.h)(288 mg/24 h)的亚麻醉剂量输注氯胺酮,并在2天内升至0.4 mg(/kg.h)(576 mg/24 h),然后开始从静脉注射转为口服氯胺酮3天,当剂量增加到0.4 mg(/kg.h)时,患者的疼痛完全缓解,而且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由于患者的氯胺酮剂量稳定,阿片类药物的需求量减少了61.4%,这一结果表明使用基于体重的静脉连续输注给药和向口服氯胺酮的转变在控制阿片类药物难治性神经性癌痛方面是有效的[33].
4.2 鞘内给药
鞘内注射给药是通过腰部穿刺将药物直接注入蛛网膜下腔,从而使药物弥散在脑脊液中,并很快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2010年的一项病例报告指出,患者鞘内自控注射氯胺酮右旋光学异构体(S-氯胺酮)(20 mg/d)复合吗啡和布比卡因改善了顽固性癌痛的症状,并且未出现阿片类戒断反应或其他不良反应(高血压和神经功能障碍)的迹象[34].2000年,Miyamoto等[35]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氯胺酮和吗啡的椎管内共同给药增加了内脏和躯体的抗伤害作用.Fisher等[36]的研究也提倡鞘内和硬膜外氯胺酮给药用于治疗对阿片类药物升高无反应的严重难治性疼痛.
4.3 鼻内给药
近期Page和Nirabhawane[37]做了一项研究,对口腔癌患者给予氯胺酮0.5 mg/kg(稀释成50 mg/ml溶液)鼻内给药,结果表明氯胺酮组患者换药过程中偶发疼痛的评分较使用前明显降低(P<0.01).而且没有出现与成年患者服用氯胺酮相关的不良反应,包括高血压、心动过速、骨骼肌活动过度、上呼吸道分泌物增多、眼球震颤和复视[38-39].另外也有一些氯胺酮鼻内给药用于非癌痛治疗有效的证据.Shimonovich等[40]的一项S-氯胺酮鼻内给药与吗啡治疗作对比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组疼痛评分降低的幅度相似,与吗啡组相比,氯胺酮组患者的口干发生率较低.2017年Farnia等[41]将氯胺酮(1 mg/kg)鼻内给药用于肾绞痛患者,结果表明给药5 min时氯胺酮组的疼痛评分减少量与吗啡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使用S-氯胺酮鼻内给药治疗神经性疼痛的另一项研究也显示疼痛评分显著降低[42].Nejati等[43]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比较了氯胺酮联合凝胶润滑剂与单独使用凝胶润滑剂治疗鼻胃管置入引起的疼痛,联合组的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P=0.026).
4.4 其他途径
除了以上的给药途径,氯胺酮也可以口服和直肠给药,但由于广泛的肝首过消除,氯胺酮通过这些途径治疗的生物利用度很低.
5 小结与展望
美国因阿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在过去15年增长了2倍[44].虽然在中国还未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目前阿片类药物的应用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45],故需要选择用于癌痛和其他疼痛的非阿片类药物.由于缺乏重叠的不良事件,氯胺酮可能是优异的辅助用药,特别是对于癌症患者的止痛.静脉注射氯胺酮适用于住院患者,不适用于门诊患者.口服途径最常用于门诊药物治疗,但利用率局限,相对起效延迟.氯胺酮鼻内给药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止痛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可快速重复给药而且吸收迅速,允许门诊维持剂量给药,无需穿刺,也适合那些因恶心、呕吐和脱水而难以实现静脉给药的患者,而且不会显著增加晚期癌症患者的不良反应[42].此外,由于没有肝首过消除效应而具有比口服途径更大的生物利用度.再者,鼻腔表面积大,温度均匀,渗透性高且血管分布广泛,有利于全身的吸收[46],既可通过调节中枢敏化和痛觉过敏来降低全身疼痛的严重程度[47],还可以改善与癌症共存的抑郁症[48-49].
总之,氯胺酮鼻内给药是一种很值得推荐的止痛方法,对于癌症患者而言是一种更舒适化和人性化的方法,但是关于氯胺酮鼻内给药的研究还很有限,将来这方面的研究应侧重于根据目前的阿片类药物需求和其他因素来确定最佳的特异性剂量,从而不断获益.如果能够将氯胺酮鼻内给药普遍应用于临床,尤其是癌痛的治疗,则可能为临床医师控制癌痛提供一个更为简单便捷的选择,更有利于推进肿瘤科医师以及麻醉科医师共建舒适化医疗的进程,使癌症患者在多元化的医疗中获得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舒适.